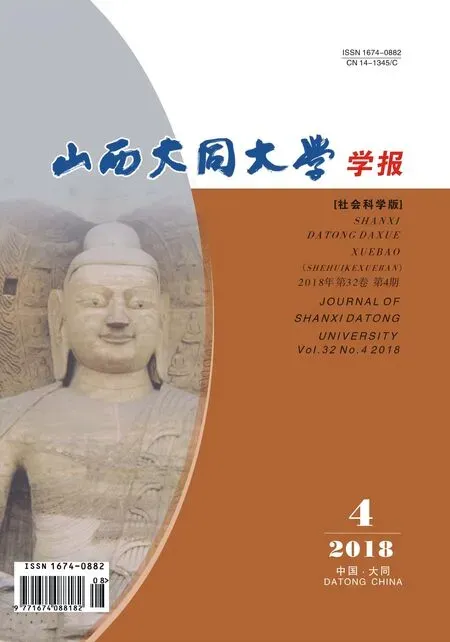王安忆小说中“空间”的意义
2018-01-29崔佳琪
崔佳琪,谢 纳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变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中,时间和空间对于人类而言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小说是人类如实或虚构书写某一固有时空故事的文本,小说在时间和空间相交叉的坐标中产生,同时也记录着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种种奇闻异事。正如让·伊芙·塔迪埃所言:“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1](P224)由此可见,只有同时考察小说中空间和时间这两个要素,才能实现对小说文本全面且透彻的了解。但是大多数小说创作者和文学批评者却更注重小说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注重以时间为主线探究小说创作动机、情节进程和人物形象,而忽略空间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空间(位置)和时间在应用时总是一道出现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空间坐标X、Y、Z和时间坐标T来确定。”[2](P251)因此,在进行文学作品鉴赏和批评时将关注的视角放在文本中存在的“空间”上,我们才能获得对相关作者和作品的全新阐释。
王安忆的小说文本中包含着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如“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弄堂(《长恨歌》)、“宁静”“文雅”“闲适”的城市蚌埠(《蚌埠》)、“是天生丽质,也是历代文人骚客的艳情装点”的杭州(《杭州》)等等。王安忆小说创作过程中不惜笔墨以琐碎细致的笔触刻画空间,显然可见她对小说中空间的重视。王安忆将自己亲身接触过的物理空间视为写作经验的源泉,这些对王安忆产生重要影响的空间不仅激发了王安忆的创作动机,而且经由王安忆精巧叙述后的空间,还具有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情节演进的重要作用。
一、“存在空间”激发创作动机
小说作者在创作时不仅需要拥有非常高超且熟练的写作技巧,同时也应该具备新奇丰富的写作素材。作者只有掌握大量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才能够将诸多情感体悟融入小说文本中,进而促使小说文本因充沛的真情实感而打动读者。作家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生活环境,无疑是作家积累和获取经验的重要场所。其实在许多作家文本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生活过的空间,如威廉·福克纳笔下的“杰弗生镇”、马塞尔·普鲁斯特笔下的“贡布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弄堂”等,这些空间都是作家内心深处的“存在空间”。诺伯格·舒尔兹在《存在·空间·建筑》一书中提出了“存在空间”的概念,他指出“存在空间”是我们非常熟悉,并注入了情感的空间。龙迪勇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故乡这一特殊空间(存在空间)的追忆和重构,是促使作家进行创作的内在动力。”[3](P30)
王安忆笔下空间众多,就连厨房、车厢、舞台、化妆间等狭小地域也可成为她作品中的景观,但若总览王安忆小说作品,则会发现她描述最多的空间还是繁荣但腐朽的上海、阴暗且燥热的弄堂以及朴实简单的乡村。王安忆对这些空间着墨颇多,无非是由于这些地方作为王安忆长期居住和生活过的场所,它们早已化作作者内心深处的“存在空间”。作者在这类空间中曾有过的喜怒哀乐等诸种情绪,不断激发起作者对此类空间及空间中所发生事件的叙述欲望。
以王安忆成长其中且多次描写的空间——上海为例,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并不像海派文人描写的上海那样充满狂欢色彩。在王安忆看来,上海的繁华不过是表面想象,只有上海的弄堂才最能体现上海的本质。因此,描写弄堂这一“存在空间”中的种种人情事态,便成为激发作家创作的动机。如《鸠雀一战》展现了弄堂中的保姆小妹阿姨为争夺自己的容身住处而做的种种努力;《角落》描写的是弄堂街角的“布店”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的变迁;《后窗》是对狭弄里“过去的日子和过去的面容”的追忆和沉思。这一类小说对于上海弄堂的全面展示,传达出作者对弄堂这一“存在空间”的情感投入,反之也正是由于作者对弄堂丰富的情感体验,才促成了这些小说的问世。了解王安忆成长历程的读者都应知道,她不仅对上海有着敏锐的感受能力,作者年轻时插队下乡的经历,使质朴自然的乡村也成为王安忆心中的“存在空间”,因此作者对乡村生活的回望和重构,便成为《稻香楼》、《招工》、《喜宴》等小说的创作动机。
王安忆对内心“存在空间”的挖掘,使她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上海弄堂里的琐碎和晦暗,激发作者探测弄堂中人们生存状态的欲望;乡村生活中的简单恬淡,引起作者对过往插队乡村的回首。这些“存在空间”不仅仅是作家建构小说的素材,同时也是促使作家进行小说建构的重要因素。
二、借空间变化推动叙事进程
任何一部优秀小说的创作都不能离开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要素,凡是有吸引力的小说文本,其情节中和叙事进程相关的起因、经过、高潮、结尾都应经过作家精心的布局。王安忆畅谈小说创作经验时提出:“作为一个小说家,故事就是他的生命线。”[4](P397)而一个故事若想扣人心弦必须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巧妙的叙事节奏做支撑。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既可以以时间为主线顺势安排故事进程,也可以通过人物性格的变化引领叙事的走向,而王安忆进行小说创作时,则是另辟蹊径的以空间变化作为推动叙事进程的重要方法。
在时间流逝过程中展示故事发展经过是许多作家会选择的创作方法,其实描写小说的叙事进程不仅仅只有时间这一个支点,“在许多小说中,尤其是现代小说中,空间元素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小说家们不仅仅把空间看做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3](P40)
王安忆的许多小说通过空间的转移推动叙事向前发展,这类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人际的摩擦、故事的缘由等都是随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如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小说开篇便引入作者对当下生活的空间体验:“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就像是个外来户”,因此探究“我们”在“上海”这一空间中孤独感、陌生感的缘由,便成为作者开始“纪实与虚构”的出发点。小说以“我”祖先从“遥远的漠北草原”到“我母亲的江南家乡”这一段空间上迁移的经历为主线贯穿全篇,作者将“我”祖先在不断征战过程中空间上的变化作为推进情节向前运作的叙事节点,她以空间转移进行小说脉络建构的写作手法创作出《纪实与虚构》这部长篇小说。
又如短篇小说《姊妹行》中的空间要素也对叙事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小说开篇,作者指出主人公“分田”和“水”出城的正确路线应该是韩集—大王集—曹城—商丘—徐州,但在接下来的叙事中,作者却借主人公“分田”和“水”从“徐州”误闯入“徐州西”引起的空间变化,推动小说情节发生转向。两位主人公阴差阳错地在“徐州西”被贩卖到不同的村庄,于是作者又依据两位主人公在空间上的隔离展开余下叙事,即“分田”从村庄逃出后,为救出伙伴“水”而再度重走二人进程的路线,历经波折终于救出“水”后,果敢坚定的二人最终如愿到达“徐州”,至此故事结束。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以人物在不同空间的转移作为叙事主线,表现出作者通过利用小说中空间变化推动叙事进程的写作意识。
客观呈现出作品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游走,详尽叙述作品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经历的悲欢离合,并以空间作为小说的主线,以空间上的变化作为故事发生转移的契机,是王安忆在小说创作时自觉选取的写作手法。王安忆对于空间要素在推动叙事进程作用上的投入性关注和创作实践,丰富了小说写作手法,也使自己的小说文本增添了一个全新的阐释角度。
三、以明暗空间对比达成叙事目的
中国古代建筑往往以屏风作为划分空间的工具,经由屏风划分后的空间往往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受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中也常常可见借助屏风的分隔性作用展示人物心理、辅助故事叙述的写作技法。如古代小说中就存在许多描写深闺中的小姐在屏风前后对心仪男子的不同表现,屏风前的世界象征的是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中,闺中小姐往往遵从礼教,表现出应有的矜持和柔婉,而屏风后的世界则是内心的私人空间,处于私人空间中的小姐更多流露出的是对“心上人”的欲望和渴求。
这种借助屏风划分空间进而辅助叙事的写作手法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比比皆是,而对于中国现代小说而言,受叙事内容影响,如若继续借助屏风作为划分空间、辅助叙事的媒介,则显得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境下,王安忆小说创作中以明暗空间的对比代替古代小说中“屏风”的作用,通过对小说中空间的色调给予详尽描写达到划分空间目的的写作手法,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王安忆的许多小说都通过将晦涩阴暗的空间和明亮艳丽的空间进行对比,从而实现将一处空间划分为两处或多处的目的。作者利用空间的色调变化进行空间划分,在渲染小说氛围、彰显作品主旨、呈现客观生存环境等方面作用巨大。如《长恨歌》“爱丽丝的告别”一章里,已和“王琦瑶”心生嫌隙的“蒋丽莉”去找“王琦瑶”时,作者写道这是一个“阴霾很重的下午,乌云压顶的”,“天就要像挤出水来的样子,阴的不能再阴。”作者对于天气的描写勾画出一个整体沉闷、晦涩、压抑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存在衬托出已被“王琦瑶”伤过心的“蒋丽莉”沉郁的心情。当“蒋丽莉”进入到“王琦瑶”家里时,她看到的是“客厅里很暗,打蜡地板反着棕黄色的光,客厅那头的房门开着,有一块光亮,光里站着王琦瑶”,“窗帘上透进些微天光,映在王琦瑶的脸上”。在这一部分叙述中作者将“王琦瑶”放在有光的空间里,从而和“蒋丽莉”所处的“阴的不能再阴”的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空间上的划分不仅借助空间的阴郁感渲染了小说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王琦瑶”的有光空间和“蒋丽莉”的暗淡空间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尽管“王琦瑶”居住在“爱丽丝公寓”这样靠男人生活的地方,但“蒋丽莉”面对“王琦瑶”的风姿绰约,仍会顿时感到黯淡无光的事实。小说中,王安忆并未刻意描写“王琦瑶”的高人一等,作者仅仅通过展示两人所处的亮与暗的不同空间,便诠释出上海女子“王琦瑶”虽命运波折却依旧是时代的弄潮儿的小说主题。
小说创作中通过刻画空间的不同色调进行空间划分的写作手法,对于作家实现叙事目的具有重要作用。王安忆作为一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作家,她在小说创作中通过运用明暗空间的对比进行叙事的创作方法,促使她的小说因色调变化而生成更多的审美意蕴。
四、通过“空间表征法”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对作品价值的呈现具有重要意义。凡是古今中外经典小说作品,其间都有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人物,如《红楼梦》中的宝玉、黛玉,《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等等。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有很多,凭借动作、语言、心理等描写展现人物是多数作者普遍使用的艺术手法,而“通过在叙事作品中书写一个特定的空间并使之成为人物性格的形象的、具体的表征,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新方法——空间表征法”。[3](P51)
“空间表征法”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用巨大,不仅可以塑造集体性格,还可以呈现个体性格;不仅可以塑造典型人物,还可以刻画多层次人物。作家创作时可以采用“空间表征法”描写人物群体生活的公共空间,如花园、街道、广场等,借由公共空间的特征衬托集体普遍的精神面貌;与此同时,作家还可在公共空间之外为主人公营造个体生活的私人空间,如私人住宅、某个只有主人公自己知道的隐秘场所所等,这种私人空间的存在更有利于展示人物回归自我时的本质特征。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黛玉的“潇湘馆”、宝玉的“怡红院”、宝钗的“蘅芜苑”等私人空间的描写,就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发挥巨大作用。此外,作家在小说创作时也可以通过描写不同空间中的异质性,暗示处于这两个不同空间中人物本质的冲突,如许多小说作者就借此表现城市人和乡下人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上的矛盾。
王安忆在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时频繁地运用“空间表征法”,不仅通过细致刻画人物生活的公共空间展示人物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而且还投入大量笔墨对人物生活的私人空间进行冗长琐碎的描写,进而展示人物内心的思想流动状态。在《乒乓房》里,作者写道“我们”居住的公共空间有着“明朗整洁的街面,殷实朴素的日常生计”,可是“在我们所住的同一条马路上,越过一道横街······明亮的街景也顿消,取而代之的是森凉的水泥气味”,这便是“微弱的散发着一些铜臭味的”乒乓房。作者着意展示乒乓房中闲逛的“社会青年”的“颓废的、没落的、腐朽的”脸色,与“幽暗而阴沉的”乒乓房彼此协调,借乒乓房中黯淡的氛围展示处在时代变迁中部分“社会青年”落寞和萎靡的心理。同时作者又通过描写乒乓房“窗户外面,那叶片枝头上跳跃着阳光的梧桐树,明亮得、明亮得就像另一个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天堂”,将乒乓房内部空间的颓废和外部“天堂”式的公共空间进行对比,表现出旧时代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社会青年”和新时代的不相容性。小说中,作者并未着意描写人物外貌,也没有对人物心理进行深入的分析,而是仅仅通过展示乒乓房内部的腐化氛围,以及这种氛围和外部空间的冲突,衬托出当代部分“社会青年”的精神面貌。
王安忆运用“空间表征法”塑造人物形象,改变了以往较为陈旧的人物描写手法,给人一种新奇感。“空间表征法”的运用不仅仅能够从侧面展示出人物内心本质特征,展示出人物之间、人物和时代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更为重要的是,王安忆将“空间”视为创作小说时可以利用的要素,发挥了“空间”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对小说创作方法的开掘和补充。关于空间的重要性,福柯指出:“今天人们焦虑不安地关注空间——这很重要,它毫无疑问地超过了对时间的关注。”[5](P21)王安忆将“空间”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并不断探索“空间”在小说中存在的重要意义,体现出她在开拓小说多种创作方法可能性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