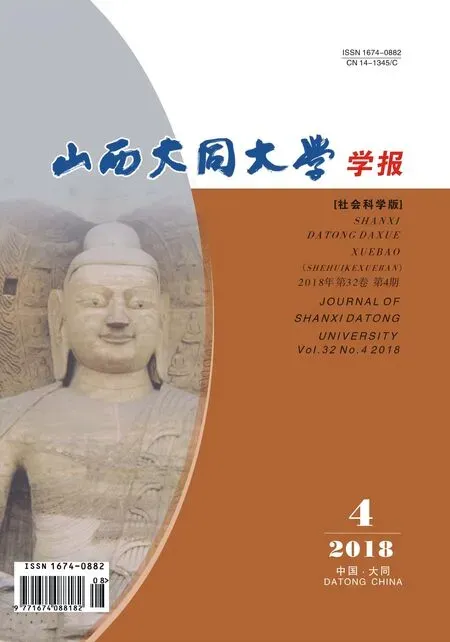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与西方哲学“时间观”的奠基
2018-01-29王博医李秋发
王博医,李秋发
(1.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上海 201602;2.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基层政治工作系,上海 200433)
“时间”虽然是先验存在于人类思维中的范畴,却时常令人感到困惑,人们将其作为日常使用的概念,但认真探究起来,却无从对它做出一个明确的界说。正如奥古斯丁一直追问“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1](P258)诚然如此,古往今来无数先哲都曾试图从逻辑和理性的角度对“时间”概念进行阐述,他们就“时间的本性是什么?”“时间是否真实存在?”等问题展开论辩,其中既有共识,又有分歧。
历史上第一位对“时间”作为日常经验的解释提出诘难的是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芝诺,他的“四大悖论”其二即是关于时间与运动的诡辩。芝诺假设有一个飞速前进的箭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运动的,但一经思考便会发现“飞矢……在每一个时刻……都占据着一个位置,因此是静止不动的”。[2](P32)具体而言,芝诺把时间分为了无数个“时刻”,因此无论我们选取任何一个时间点,飞矢都必然会位于一个与之对应的位置,那么只要把时间缩短到质点的长度,即一个“瞬间”,则它都静止在相应的位置上,表面上看起来正在运动的箭矢实际上只是在各个瞬间停留在各个位置,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运动是不存在的。
可以看出,芝诺的结论虽然在逻辑上可行,但却与经验事实严重不符,其原因就在于:“飞矢不动”悖论的前提,即时间可以被分割到一个不可再分的单位——瞬间这一认知是错误的。为反驳芝诺的错误“时间观”哲学家提出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依先后而定的运动的数目”[3](P127);奥古斯丁认为时间是“心灵自身的延伸”[1](P272);康德认为时间是“内感官的先验形式”;恩格斯认为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4](P113);柏格森认为时间是“意识的绵延”。凡此种种,众家之言既有因立场不同而产生的分歧,更有从逻辑和经验出发精密论证的普适观点。
一、连续性
除芝诺以外,几乎所有谈到“时间”的哲学家都承认时间的连续性,如亚里士多德即称“时间是关于前后的运动的数,并且是连续的……时间也因‘现在’而得以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3](P127);恩格斯称“时间的特点是一维性。这种一维性具体表现在……任何一个物体运动的持续性都可以用一个数表示出来”[4](P113);柏格森称如果“我们把已构成的数目看一下,则这番连接已经成为事实:各点都已变成线,原来的间隔已经消失,整个东西(时间)呈现了连续体的一切特征……它(时间)于是显得可以被分割到无限的程度。”[5](P61)综上所述,时间的连续性指的就是时间前后相继,且不可分割的相互渗透的流动状态。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对于时间“连续性”做出系统论述的人,他指出:“飞矢不动……是从时间是瞬间的总和这个假设中得出的。如果不承认这个假设,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3](P128)而“因为时间不是由不可分割的‘瞬间’组成”。[3](P129)质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芝诺的论证基础就在于把时间看做无数个瞬间的总和,然而“分割时间”的尝试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看来都无法达成,因为芝诺所假设的“最小”的时间质点,即“瞬间”是不存在的。时间的连续性就在于其任意前后连接的部分都相互渗透,前一段时间的终点同时也是后一段时间的起点,也就是说,时间是一个无缝连接的整体,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分割”“截取”一段时间只不过是在认知逻辑上将时间中的某一点同时作为前一段的终点和后一段的起点使用了两次,然而在客观实在中,自我同一的“时间点”是无法分割为二的。
关于时间的“连续性”,亚里士多德将其进一步解读为无限的静止的点彼此之间的“连续”关系,而非“接顺”(接触且顺接)关系。在此,他区分了“接顺”与“连续”的不同,亚里士多德指出,按照芝诺的说法,无限的静止的时间点之间是“接顺”的位置关系,如果将时间类比于无限数量的木板,则“接顺”关系指的是木板1后贴着木板2,木板2后贴着木板3……依此类推木板n则后贴着木板n+1,这种贴合关系是空间上常见的位置关系,即“每一块木板有两个外限:其一面是上一序号的终点,另一面是下一序号的起点”,[6](P492)简言之,木板n的前一面贴合着木板n+1的后一面,其后一面则贴合着木板n-1的前一面;而“连续”关系则指的是“只有一个互相包含的外限……它既是起点又是终点”,[6](P492)也就是说,木板n的前一面本身就是木板n+1的后一面,而木板n的后一面就是木板n-1的前一面。总结来说,在“接顺”关系中,起点紧密贴合着终点,但无论这种贴合多么紧密都会存在缝隙,因而是可分割的;而在“连续”关系中,终点本身就是下一个起点,若将其分割,则意味着该点必须既完整地存在于上一个时间段,又完整地存在于下一个时间段,这在思维的想象中能够实现,因此人们会误认为时间可以分割,但在客观现实中则不可能做到。
关于这一点,柏格森也用“绵延”和“渗透”的理论给予了论证,且与亚里士多德殊途同归。柏格森指出,真正的时间是“绵延”,其本质就在于连续性的相互渗透。“绵延是意识材料不可分割的连续的流动状态,在绵延状态中,分别不出前后彼此的界线,连续出现的每一个状态相互渗透,每个当下发生的状态都包含了过去,预示着未来。”[7](P49)也就是说,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类似,柏格森也强调时间的连续性并不是前后次序的堆砌,而是每一个状态与其相邻的状态的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即过去的终点是现在,而现在亦是将来的起点。如此即回到了亚里士多德最初的结论:划分时间的限不是两个,而是一个。
二、永恒与消逝
据亚里士多德所言,时间不仅是连续的,还是无限而永恒的,为此他说:“时间比一切在时间里的事物都长久。”[3](P130)奥古斯丁也对此表示赞同,他坚信时间是“流光的相续……永恒却没有过去,整个只有现在”[1](P255-256);恩格斯同样预设了时间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永恒性,他指出:“自然界和历史……中包含了时间的和空间的无限性。”[8](P119)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时间只是“有始而无终”,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时间甚至也不存在起点,但时间的无限和永恒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的“不动的推动者”奉为第一本体,并以其永恒不变的特性与“月轮下的世界”中四元素的生灭往复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对时间的流逝抱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称“时间消磨着事物……一切事物俱因时间的迁移而变老了,由于时间的消逝而被淡忘了……时间本身主要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3](P130)也就是说,在时间的无限性面前,一切现实的存在物都是转瞬即逝的,尤其对于人来说,“时间的流逝,季节的错过又给人们带来失望和恐惧。”[6](P510)在永恒之时间的对比下,人生显得愈发短促。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中只有短促和流逝,而无限性只是一种潜在的性质,在人们生活的世界上不存在无限的东西,无限和永恒只是一种超验的思辨范畴,然而现实的人却终究无法逃脱潜在的时间的消磨,因此,诚如汪子嵩先生的评价:“亚里士多德谈到时间时是很伤感的。这同他对永恒本体的称赞恰成鲜明的对照……从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直到后来的普罗提诺,他们都追求人生终极的永恒的东西。”[6](P514-515)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在中世纪哲学家的著述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如奥古斯丁就曾指出,时间是相对的永恒,而在时间制约之下的存在物都是可朽而有限的。如他所说,时间“无起无讫,无先无后,永久而同时表达一切……是真正的永恒,真正的不朽不灭”。[1](P252)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在时间的流逝面前却无能为力,无法观照和理解时间的运转,只能慨叹“时日正在过去,怎样过去的呢?我不知道。”[1](P265)但有别于亚里士多德对于时间的悲观态度的是,奥古斯丁同样认为与上帝的“常住”相比,人的时日的消逝无足轻重,因为“既然(时间)常生常在,永永无极,则无所谓逝,亦无所为继”,[1](P252-253)也就是说,奥古斯丁漠视有限的现世生活,他将全部的意义归指倚仗于形而上的永恒。
统而言之,无论亚里士多德的“伤逝”情结,还是奥古斯丁的淡然态度,其基本论调都是主张人屈从于永恒的时间,但相较而言,亚里士多德对生活的态度更加积极,他热爱时间,并为时间的流逝而感到伤怀;奥古斯丁则认为现实的“凡人”生活毫无意义,因此并不为任何变化所动。
三、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西方哲学史上始终存在着关于“时间是否真实地存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亚里士多德也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因而不复存在;将来的时间没有到来,因而尚未存在,因此真实存在的时间只有“现在”,又由于其连续性,时间也无法被分割为“最小的瞬间”,那么“现在”也必然不是一个没有长度的质点;然而,一旦“现在”有了长度,它就包含了过去和将来。由此看来,“现在”也是不存在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时间就已流逝的部分而言已不存在;就尚未到来的而言也不存在。”[3](P127-128)奥古斯丁也附议道:“过去的时间不复存在,将来的时间尚未存在,谁能度量它们呢?除非有人胆敢说,他能度量不存在的东西。”[1](P260)
诚然,过去的时间已经消失,而将来的时间还未曾到来,但人们却真切地感受到了过去和将来的时间在当下的存在?“现在”虽然不能被度量,但人们尚能感到它的存在,因此亚里士多德也称“现在”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概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是始终同一的还是前后相异的?亚里士多德对此解释道,如果时间是由不同的“现在”,即各自相异的“现在 1”“现在2”……“现在 n”所组成的,则“不可能有并存的‘现在’,后一个‘现在’出现时,前一个‘现在’就消失了”,[6](P511)但是前一个“现在”消失到了哪里?我们无从解释。因为它“不能消失在它自身内,因为当时它还正存在着;但它也不能消失在后一个‘现在’里,因为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理:‘现在’是不能彼此一个接在另一个后面的”。[3](P122)简言之,前一个“现在”不能消失在它的现在,也不能消失在它顺接的将来,更不能消失在与之不相邻的过去或将来。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又指出,“现在”必定是“多”,而非“同一”的。他说:“如果‘现在’是始终如一的,凡有限的、可分的东西可以多维延伸,但是时间是一维的,人们只能在一个维度上任取一段当作‘现在’,将在先的叫‘过去’、在后的叫‘未来’。”[6](P511)也就是说,从时间的“一维性”考量,时间中的诸多“现在”也必然是异质的。若非如此,过去的时间没有真正地过去,现在的时间是“现在”,过去的时间也是“现在”,如此,整个时间的全部也就只有“现在”了,而这于常理是行不通的。由此,亚里士多德得出了前后相悖的结论:“现在”既不是同一的,又不是不同一的。
综上,哲学家对于“时间真实地存在”这一结论是有共识的,但具体来看,却又无法对这一“真实的存在”加以把握,因为过去的时间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影像;将来尚未存在,存在的只是对将来事件的预测、期望。而“现在”作为过去与未来的临界,却又只是一个没有长度、无法测量的“质点”。
四、客观物质还是感性纯直观
从上述结论来看,时间虽然存在,但其存在方式毕竟与可感事物区分甚大:它可以被人的意识感知,但又无法测量长度。那么时间的本性究竟为何?是在客观上实际存在的物质,还是心灵中意识的虚拟产物?亚里士多德并未拘泥于其中一方,而是辩证地得出了“时间是感性对客观形式的主观反映”的结论。
他认为:“时间是运动和运动存在的尺度。”[3](P129)即言:感性事物的运动是依靠时间来计量的,而存在又是运动的前提,因此,人对于时间的意识就是事物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意识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时间,而只有作为时间存在基础的运动存在了。”[3](P136)汪子嵩先生对此评价道:“时间之于事物的运动,犹如位置之于运动的事物。质料存在于空间中,形式存在于时间中。”[6](P511)“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问题:时间的本性为何?时间同灵魂的关系值得研究。它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还是由意识认知产生的先验范畴?”(223a16)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因为所有这些地方的事物都能运动。”(223a20)紧接着他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如果没有灵魂本体,时间是否存在?”(223a22)这里的“灵魂”指理性的认知的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是:因为计数者是人,如无有心智能力的人去计数,当然就无所谓时间了。可是运动的物体总是有的,因而有“在先”和“在后”,这样,作为计数的时间实际上是存在的。(223a28-29)质言之,时间虽然不依靠意识而存在,却凭借人的意识的知觉而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对此,康德也持肯定态度,他认为时间是一种先天的、感性的直观,或称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而非“来自任何经验引来之经验的概念”。[9](P61)正如康德说“盖若非先假定时间表象先天的存于知觉根底中,则同时或继起之事即永不能进入吾人之知觉中”,[9](P61)即言时间是先天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认识范畴;“吾人能思维时间为空无现象,但关于普泛所谓现象,则不能除去此时间本身”,[9](P61)即言时间是一切感性事物和直观经验存在的根基;“时间仅有一向量……此等时间原理,绝不能自经验引来,盖因经验不能以严密之普遍性及必然之正确性者”,[9](P62)即言时间的连续性原理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程度上都超越了经验;“时间非论证的概念即所谓普泛的概念,乃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其源流不能仅起于概念”,[9](P62)即言时间不仅超越经验事物,还超越了理性所认知的概念;“时间之无限性……唯由于其根底中所具之唯一时间有所制限而后可能者耳。”[9](P62)即言时间凭借其无限性即超越了一切可能的存在。因此康德得出结论,认为“时间非自身存在之物,亦非属于事物为一客观的规定……时间仅为内感之方式……乃一切现象之先天的方式条件”。[9](P63-64)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对康德“时间观”的建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都认为时间是理性对经验事物的主观认知。当然,这只是从认识论层面得出的结论,而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时间却是无可否认的“客观物质存在”。
结论
以上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逐渐演化为西方哲学的共识。首先,时间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纯粹整体”,因此无法在静态条件下分割出最小的“瞬间”;其次,时间是永恒的、没有终点的“绵延之流”,它先于存在物产生,但不随其而消逝;再次,过去的时间已不存在,将来的时间尚未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有“现在”,所谓“过去”实质上是对于过去的记忆,“将来”是对将来的期望;最后,虽然对于时间的本性是客观的物质还是感性的纯直观,学界仍存在分歧,但这并无碍于我们对于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理解,因为他融合了两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调和了二者的矛盾,最终将“时间”归因为意识对于物质世界的反映。几千年来,后世学者在论及“时间”概念时,均未能绕开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为西方哲学对“时间”概念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范式和体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