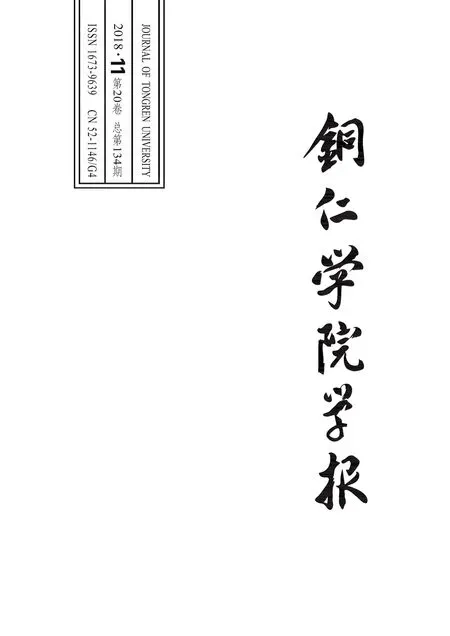政策比较视域下深圳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可行性分析
2018-01-28黄紫晗
黄紫晗
政策比较视域下深圳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可行性分析
黄紫晗
(台北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台湾 新北 237)
建市以来,深圳从社区管理逐步转向社区治理,其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变化期,即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阶段。在这两个重要阶段,深圳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资源挹注方式管理社区,缺乏自下而上的资源互动方式。台湾地区50余年的探索与改革,也经历了社区发展和社区总体营造两次政策变革,其中“社区总体营造”政策设计,为台湾推动社区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路径。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社区民众参与等五方面对两地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在比较政策理论框架下对两地政策进行诠释,提出深圳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制定建议,为深圳未来的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方向指引。
社区总体营造; 比较政策理论; 可行性
多元文化和城市向心力低既是深圳社区发展的优势,也是其缺点。故而,深圳在制定社区政策时,一直在社区福利主义和社区管理主义两种思路之间徘徊。随着福利政策的贯彻落实,社区居民不再仅仅满足于补救性的社区福利。社区政策如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是近年来政府、学者和社区实践者们苦苦思索的问题。台湾的社区政策经60年的不断修正,特别是近20余年推动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可以为深圳的社区改革提供借鉴,为深圳的社区治理提供新的可能性。
从政策比较的视阈分析深圳市和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可以较深入地为深圳市社区的发展指明未来道路。所谓比较政策研究,是指针对某一议题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比较,而发展出新的概念和理论,也可以弥补相同的社区议题在不同的背景或不同的战略选择中造成的区隔。深圳和台湾在社区治理方面,面对相同的问题:经济下滑、城市人口挤压、乡村没落、福利需求多元化、资源耗费严重,面对这些问题两地都在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本文将在深圳和台湾两地的社区治理政策的比较中寻找两者之间的区隔,指出在这些区隔中哪些会成为深圳引入台湾“社区营造”时可供借鉴的部分。
分析政策之间的相同或区隔,学者认为有两种理论途径:推论途径和归纳途径。推论途径以政策模型可以被推演结果为前提,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而归纳途径以政策不是源于特定的预设目的,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冲突,谈判和妥协的过程中形成为理论前提,政府人员、专业人员和投票者都是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Michael Cuthill认为,普通社区居民对政治是冷感的,没有兴趣参与,一般都关注于社区的小事情,而且是个人能够看到改变的一些小事情。[1]所以,在两地的政策比较中,本文将以归纳途径的方式展开,并且聚焦于非政治因素对政策的影响。
一、深圳与台湾两地社区政策比较
政策的实施由政策目标、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政策内容构成。社区政策的实施还包括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情况,所以本文增加了两地社区居民参与情况的对比。
(一) 政策目标
深圳、台湾两地在不同时期的社区政策针对不同的社区发展情况。从政策目标可知,台湾和深圳两地在不同的时期,对于社区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但是也有关联性。
台湾在社区发展阶段(1965年—1992年)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增进居民福利、建设安和融洽、团结互助的现代化社会,社区发展系社区居民基于共同需要,循自动与互助精神,配合政府行政支持、技术指导,有效运用各种资源,从事综合建设,以改进社区居民生活质量。
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阶段(1993年至今)的政策目标定位为: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和建立地方文化相关活动的过程,实现和达成社区文化、生活环境以及地区产业的整体性发展。社区总体营造的最终目标不只在营造一个社区,实际上它已在营造一个新社会,营造一个新文化,营造一个新的人。
从这两个阶段的政策来看,社区的目标从整体的社区角度,转为从社会整体和个人相结合的角度。社区政策的焦点也从社区变成人,社区发展是从技术的角度去帮助社区人提升生活质量,而社区营造的目标在于帮助营造个人,使社区的功能更加优化。社区营造认为社区的问题应该是人的问题,只有很好地营造了个人,社区的问题才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深圳在社区建设阶段(1998年—2008年),目标主要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区组织,建立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新型社区,形成功能完善、服务规范、分工科学、协作有力的工作运行机制,将社区建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现代化文明社区。
而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在2005年,社区建设的政策目标在原有的政策基础上,增加了如下内容:以人为本、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十年的社区建设任务完成以后,社区的管理得到改善,但是社区行政任务也越来越多,服务居民的主旨仍未得到重视。所以,在社区服务阶段(2008年至今)提出:将政府的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建立社会工作者服务制度,由社工引领义工,为社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性、福利性服务;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开展专业化、个性化服务;指导支持居委会组织社区居民开展自助和互助服务;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在社区发展便民、利民的商业服务。
随着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深圳逐步在社区里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的运行机制,组织以社工为骨干、多种专业人才并存的社区服务队伍,形成制度健全、监管有力的非行政化社区服务体制,构建跨部门、综合性的社区公共服务模式。
从社区政策的目标变动来看,深圳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提供切合居民的服务,特别是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性、福利性的服务,从社区管理思维转换为社区居民自助和互助服务,居民从被动地角色变为主动参与的角色。
从两地政策相比较来看,两地都注重社区环境的建设,弱势群体的福利,希望能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但是,相较于台湾,深圳未将社区的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也未将人作为社区中最重要的因素进行考虑,社区政策聚焦在社区弱势群体服务,是补救性的福利政策之一。
(二) 政策制定者
台湾负责制定社区政策的主要部门与深圳不同,社区发展主要是“内政部”(卫生与社会福利部),而社区营造的政策制定者是来自于“文化部”(文建会),这两个单位的职责不同,所以,在社区层面推动的政策方向是不一致的,“文化部”重点在于文化保护和社区文化推广,而“卫福部”在于社会福利政策执行。而深圳市的政策制定者主要是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主要聚焦于社区居民的民生,弱势群体福利改善等,所以偏向于民生和福利方向,较多聚焦于弱势群体的政策福利。
(三) 政策执行者
深圳的社区政策执行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定位,在社会建设阶段,实行党政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建立以街道、社区为主体,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方支持,居民群众广泛参与,权责利统一的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区、街(镇)要相应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的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把社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以党政人员为主,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委员、社区工作站专业人员配合参与的方式开展工作。在社区服务阶段,党政人员的角色弱化或撤离社区一线服务岗位,转变为搭建社区服务平台,缩小社区居委会,方便居民自治,以较大的社区工作站整合社区资源,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区社会组织,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服务工作队伍,鼓励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发展,培育社会工作者为社区群众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建立社工引领义工的工作机制。形成以社会工作者、民间组织和社区自治力量为主的政策执行者队伍,并在社会工作者的基础上,引入康复师、护理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参与社区服务,进一步扩大专业服务队伍。
台湾在《社区发展工作纲要》中规定“各级主管机关为协调、研究、审议、咨询及推动社区发展业务,得邀请学者、专家、有关单位及民间团体代表、社区居民组设置社区发展促进委员会,乡(镇、市、区)主管机关应辅导社区居民依法设立社区发展协会,依章程推动社区发展工作;社区发展协会章程范本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从这里可以看出社区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门的引导,社区发展协会也是在政府指导下工作。而在《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中可以看出,社区营造工作则更加注重“社区组织与社团在社区中的自动参与性,发挥居民在提案方面的事宜”,社区组织也不仅仅限于社区发展协会,认为社区的发展提案应该来自于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倡导社区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
从深圳的社区政策可以看出,政策执行者在政策中已有明确规定,特别是明确规定专业人士是特殊专业服务者(社工、心理咨询师、康复师)。而台湾在政策执行者方面未对专业人士作明确的规定,这样给了社区很大的空间去按照需求提供专业服务。两地比较而言,台湾的政策执行者比深圳更广泛,深圳更强调专业。但是两者在政府的框架下开展服务,都会受到政府经费支持的导向性限制。
(四) 政策内容
深圳在社区建设阶段,政策内容主要包括: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计生;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社区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社区服务产业化,鼓励集体、私人投资兴办社区服务业,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妇女及社会困难群体,把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失业人员安置、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低生活保障、第三产业发展等结合起来,积极通过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NPO)开展贴近社区、贴近家庭、贴近居民的各项任务。
在社区服务阶段,在原有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居民自助与互助服务,积极动员和引导各类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组织、开展自助和互助服务,特别是为社区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及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大力发展志愿者服务,培育社区义务服务意识。”
台湾在《社区发展工作纲要》中认为社区发展协会应配合政府开展如下项目:公共设施建设,生产福利建设、精神伦理建设;在《六星计划》中将社区指标性计划分为产业发展、社福医疗、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环境景观、环保生态等六个方面。
从两地的政策内容看,都集中在社福医疗、社区治安等方面。深圳在政策内容方面尚未将环保生态、人文教育、社区产业呈现出来,说明在未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深圳仍有很多的社区资源可深入开发,社区的政策可以朝着更多元化的方向进行畅想,随着“人”和“环境”这两个社区因素的不断注入,社区的永续发展将会成为两地政策制定的首要共同点。
(五) 社区居民参与
深圳市在2015年制定了《深圳市社区居民议事会工作规程》,在里面详细规定了社区民众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并且认为社区居民议事会同时履行“社区居务”(专门词汇)监督委员会的职能。社区居民议事会会议范围包括:对社区建设提出意见建议,商议解决居民关于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事务的意见建议;收集社情民意和反馈居民的需求;经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授权,商议与社区居民利益相关的事务。从这些范围来看,社区居民议事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范围很广,促进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居民可以在一定的空间内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台湾在社区政策中尚未明确规定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方式。在《社区总体营造计划》提到社区营造是培养社区自主,尽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使居民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展现自己的能力。在《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中,提出建构由下而上的组织体系,在每一个子计划中都注重培养社区居民。在《健康社区六星社区营造计划方案》中认为社区应该从社区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透过社区公约、社区建议等方式,参与政府公共政策之研究拟定或决策过程。
深圳与台湾在居民与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规定中都极力倡导社区居民关注公共事务,特别是深圳以特别政策作了详细的规定;而台湾在社区政策中极力地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各项公共事务。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深圳的社区居民是以居民代表的方式进行参与,而台湾未将居民参与的方式定义为居民全民参与,并且台湾重视社区居民的能力培养,在旅游、环保教育、社区经济等各方面的事务都希望居民参与进来,居民不仅仅是提建议,还要在具体社区事务行动中参与,而这样的概念目前尚未在深圳的社区政策中有所呈现。
二、深圳实施“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可行性
(一) 深圳“社区总体营造”定义
台湾广泛使用的“社区总体营造”一词,是由文建会于1994年提出。依据文建会的政策定义,社区总体营造是全面性、整体性的社区规划和社区经营的过程,以社区共同体及社区意识为前提,透过社区民众参与,凝聚社区共识,经由社区自主能力,使得社区生活空间美化,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也使文化产业、经济再行复苏,并让原有的地景、地貌焕然一新,进而促使社区活力的再现。这个深具包容性的政策性概念为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打造了一个宏观的愿景及多元的操作空间,但由于范畴及操作面向过于广泛,也造成不少执行及管理上的问题。
虽然已有官方的说明,但目前学界及社区总体营造参与者对社区营造的意涵,仍有一些认知上的差异。例如,陈其南特别强调社区营造在“营造人的角色”方面的意义,认为社区总体营造不只是在营造一个社区,实际上也是透过社区参与及社区教育,来塑造一个新社会中“人的角色”。日本学者宫崎清则强调社区营造多重面向的功能,他指出社区营造应从“人、文、地、产、景”等五个面向切入,进行整体性的考虑。倡议参与式设计的柏克莱大学教授Hester则强调“聆听”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社区营造工作的第一步应为“聆听社区的声音”,先了解民众的真正需求,而非仅凭专业者的价值观及主观判断,直接进行社区营造工作。[2]
通过对两岸社区现有政策的对比,依据两地之间语境不同,对深圳未来“社区总体营造”定义为: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支持下,以社区共同体及社区意识为前提,以居民议事会为平台,协同社区社会组织、专业工作者、志愿者,凝聚全体居民共同需求,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美化生活环境、发展社区文化产业、重点解决特殊群体居民的服务需求,将社区逐步打造成全体居民的舒适活动空间。
(二) 深圳“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建议性内容
(1)政策目标方面,将政府原有业务与社区服务分开。目前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的内容主要是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内容下移到社区中,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小了政府规模,但是却造成社区公共管理事务任务越来越繁杂,政府的规模虽然看起来在变小,但是管理范围并未变小,这不利于社区本身成长。
(2)在政策执行者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发挥自下而上的力量,让居民真正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做决定。
扩充专业工作者的角色,不应局限于社会工作者单一角色。从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来看,并不是很强调某一方面专业工作者的角色,反而从文化、产业、环保等方面去培养社区人员。而深圳在政策中特别强调社会工作者、康复师这些专业角色,将社区作为问题去看待,忽视非问题型的社区居民的需求。所以,要真正让普通群众对社区事务有所兴趣,而不仅仅只是关注部分弱势困难群体和专业角色的引入,不能将社区作为问题的社区来看待,而应该引入多元多层次专业工作者。
传统意义上,社区工作站作为政府在社区的服务平台,主要是协助、配合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在社区开展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政府延伸服务。政府在社区设置政府的服务平台,经证明,无法解决社区问题,并且造成民间力量与社区工作站在资源上的抢夺和日常工作的冲突。所以,如果要发挥社区的活力,首先就应该去掉政府在社区的干预,撤销社区工作站可以让社区逐渐从传统的管理定位走向服务定位、自我治理定位。
积极支持社区居民自主成立社区社会组织。汤京平等学者认为社区作为一个集体,应该发挥社区内个人或组织最大的功能,只有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方可实现最好的适配性。
(3)在政策内容方面,应充分考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增加社区生态环境教育与保护的政策内容。从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推动经验来看,生态环境是社区永续的根本,是推动社区总体营造的立足点,特别是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融合,应成为社区政策内容不可缺少的部分。
(4)在社区居民参与方面,应将居民议事会与居民委员会分开。在《深圳市居民议事会工作规程》中要求,以社区居委会为主导,但是社区居委会经过多年的发展,政府主导性强,居民议事会应充分发挥居民自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减少社区居委会在居民议事会工作中的参与度;那样才真正让居民议事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将居民议事会的管理与运作真正交给居民去执行。让居民议事会真正成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平台,慢慢地引导更多的居民关心社区公共事务。
(三) 深圳“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实施的困难
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实施近30年,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深圳引入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政策,需要去思考如何避免类似台湾目前的一些困境。社区总体营造虽然在政策定义上与社区建设、社区服务有所不同,但是在先前的政策影响下,居民已经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政府不断拨款,依赖于政府的引导下被动开展社区活动的方式;所以,在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实施后,如何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并提出计划,让居民在参与社区总体营造中真正感受到社区“主人”的角色,不受限于政府财政拨款的框架,灵活地与政府开展合作,也是“社区营造”成功推广的关键所在。
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的资源挹注,可能会改变既有的社会关系与行动者的诱因结构,导致维系社区行动的要素被破坏,社区营造的集体行动反而难以维系。[3]
如何塑造社区居民共识的公共领域,需要不断地塑造居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的责任感;而社区总体营造作为社区治理的方式之一,可以大大提高社区居民关注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作为公共领域,社区需要居民的参与才能真正发挥活力。
三、总结
对深圳、台湾两地的政策的比较,两地在政策内容、政策执行者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台湾的社区政策制定者角色不稳定,历史中出现多次变化,也是造成政策方向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深圳的政策相较之于台湾,在规定方面更为严格。深圳的社区政策目前偏向于为弱势群体服务,属于补救性政策。台湾的社区营造政策虽然经过了近30年,政府的引导性仍在发挥作用,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工明显,合作性却很难体现出来。这也是两地在探索社区政策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1] Michael Cuthill. Exploratory Research: Citizen Participation,Local Gover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2002: 85-87.
[2] 吴钢立.永续社区理念之社区营造评估体系建构之研究:以台南县市社区营造为例[J].住宅学报,2007(1).
[3] 汤京平,黄诗涵,黄坤山.灾后重建政策与诱因排挤——以九二一地震后某社区营造集体行动为例[J].政治学报,2009(48).
The Policy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Shenzhen Community's 0veral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Comparison
HUANG Zihan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Xinbei 237, Taiwan, China )
Since the founding of Shenzhen, it has experienced the shift from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to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During this period, Shenzhen has witnessed two important policy changes. One is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other is the community service. In these two important stages, Shenzhen has been using the top-down resources to manage the community, hence lacking the bottom-up resource interaction. Taiwan, Over the past 50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reform, has also undergone two policy chang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overall construction. The policy design of ‘community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vides a good practical path for promo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aiwan. This pape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mparative policy theory, will make a comparative policy study between Shenzhen and Taiwan from the five aspects: policy objectives, policy contents, policy makers, policy implementer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overal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Shenzhen with an aim to provide a new policy design direction for its future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overall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policy theory, feasibility
2018-07-05
黄紫晗(1985-),女,江西九江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社区工作,社区治理。
C916
A
1673-9639 (2018) 11-0119-05
(责任编辑 赖 全)(责任校对 张凤祥)(英文编辑 何历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