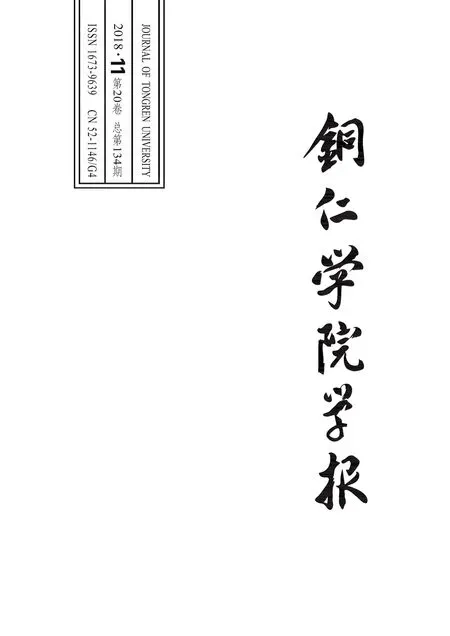论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基本原则
2018-01-28梁正海
梁正海,刘 剑
论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基本原则
梁正海,刘 剑
(铜仁学院 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铜仁 554300)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般性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基因,延续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生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既需要遵循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宏观背景提出的原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原则,又需要坚持以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特殊性为基础的最少干预和利益均衡原则。只有多种原则相互兼顾,相互促进,才可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最佳预期目标。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 传承与保护; 基本原则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般性特征。因此,我们对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基本原则的探讨,将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下展开。众所周知,从国外到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与保护正在被各国政府加以重视并积极实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文化建设热潮。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推动文化建设,我国先后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方针、保护要求、保障举措等作了具体规定。但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属性,在实践中应遵循怎样的保护原则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要遵循以人为本、原真性、完整性或整体性、可持续性等原则。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权利原则和发展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1]原真性、完整性或整体性、可持续性等原则并不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原则,它们只是保护工作在形态上的一些具体要求而已。不过,我们认为无论是原则还是要求,只要能达到更好地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与保护目的,就值得坚持。
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不是呆板地记录保存,而是在不破坏其完整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既要保存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基因,又要延续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生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原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等原则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宏观背景提出的,对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这些原则同样具有可操作性。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属性,我们认为,实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原则,又需要坚持最少干预和利益均衡原则。只有多种原则相互兼顾,才可能实现最佳的预期目标。
一、原真性保护原则
“原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中文翻译,它的英文本义是表示真的而非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原真性”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Authentic-ity”来自于希腊和拉丁语的“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即“举止带有权威的人”和“用自己的手制造的”的意思。在宗教占统治力量的中世纪,“原真性”用来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性,而有关这些宗教圣物的真实并不需要有真凭实据,而是依靠传说轶事[2]。
原真性原则也被称为本真性原则、真实性原则,这一概念由《威尼斯宪章》首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原真性开始引入遗产保护领域,并逐渐成为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原则。1994年,日本《奈良文件》将原真性在遗产保护中的表述更加透彻和清楚[3]。该文件明确指出:原真性本身不是遗产的价值,而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取决于有关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有效。由于世界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将文化遗产价值和原真性的评价,置于固定的标准之中是不可能的[4]。1995年的亚太地区会议、1996年的美洲地区会议、2000年的非洲地区会议等遗产保护国际会议,都对《奈良文件》做了进一步补充,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在国际上基本上形成共识。
世界遗产委员会明确规定:本真性是检验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原则,并要求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明确提出被登录的遗产不能是按照今人臆想过去历史情况重建恢复的东西。尽管这一规定有针对性的将原真性保护原则指向了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我们认为这一原则对于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适用。因为,遗产资源保护的首要任务和内容可以理解为基因的遗传。由于全球化、现代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原真性正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进行原真性保护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坚持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原真性,意味着我们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内容应该是原生的、原创的、最初的、第一手的、非伪造的。坚持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原真性原则,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认识,有效防止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受到外来非和谐因素的入侵和破坏。
我们认为,坚持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原真性,必须坚守两点。其一,要正视传统医药知识的复杂性。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不管是对有形的民间医书、制药工具、储药设备、药方,还是对无形的治病药理、咒语神符、民间传说等,都应该以其遗存状态为基础进行传承与保护。既不能杜撰其诊疗理念,也不能强制约束药材的采摘时间、加工储存方法,更不应该用现代科学标准来轻易否定咒语神符等元素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价值。其二,要强调并维系传承与保护主体的原真性。人作为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主体,其行为与传统医药知识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相关研究表明,后继乏人已经成为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巨大危机。在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因传承人日渐减少而失去理性,乱了阵脚,更不能盲目寻找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人。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具有时空二维性特征,即这一医学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环境中产生。原真性原则需要尊重传统医药知识产生的时空二维性特征,传承人是需要时间和环境逐渐养成的。因此,我们在坚持传统医药知识原真性保护原则的同时,还必须强调传承主体的原真性,避免“山寨”传承人,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正统血脉或基因。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主体的原真性,并非要将传统医药知识传承群体封闭起来,否定传统医药知识具有的开放性,走向文化和知识的我族中心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这种原真性的坚守,肯定传统医药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自身逻辑,实现对传统医药知识自身发展规律的遵循。
二、整体性保护原则
“整体论是近代哲学中的重要思想,它强调自然界的事物是由各部分、或各种要素组成的,但各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整体的性质大于其组成部分性质的总和,整体的规律不能归结为其组成部分的规律。”[5]不论是宏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还是作为微观层面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它们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形态存在着,拥有各自完整的文化生态空间。
显然,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是由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整体性特征决定的。这意味着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既要注重生态整体,又要注重文化整体,达到文化共生的效果。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极为丰富和宝贵,这种丰富和宝贵不仅仅体现在单一民族的传统医药体系中,更体现在整个中华传统医药知识系统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生境,正因为如此,传统医药知识在民间常常与“草草药”划等号。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这样的划分并非足够严谨,但是换一个视角看,这种划分却充分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智慧。这种民间智慧本身又凸显了传统医药知识整体性保护的重要性,因为“草草药”来自于复杂的大自然,自然界是它们存续不可或缺的载体。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由若干具体的文化事象构成的,所以,我们说传统医药知识丰富多样,内涵博大精深。但是,不管传统医药知识如何的多样而丰富,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本身仍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传统医药知识体系“不是某些‘代表作’和零散的‘文化碎片’所能涵盖的”[6]。比如,我们长期调查研究的武陵山地区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不仅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还与武陵山地区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因此,实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有效保护,必须把其依托的自然生态以及人文生态纳入保护范畴。
首先,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一个完整的基因库。作为一种医疗技术,救死扶伤是其追求的目标,当然这种目标的实现又是多种文化元素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构成要素中都包含有治疗机理、药方、药材、疗病器具、知识持有者、仪式等,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各要素共同构建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完整的知识系统。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原则出发,既要重视传承人的传承地位,又要加强对药材、药方、器具等物质要素的保护,还要正确认识仪式在治疗过程中的辅助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保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包括传承人和文化生态环境。只有主体而无客体,或只有客体而无主体都不会达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的理想目标。
其次,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及自然环境中产生并不断走向成熟的。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是以自然环境为存续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地理条件复杂,自然资源丰富,生物种类多样。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因在茫茫大山中饱受虫蚊蛇兽的侵害,在经济能力及现代医学极度有限的条件下,不得不尝试着使用大自然中的一些生物进行自救,不管有无效果,总之别无他法,只能进行盲目的尝试。日积月累,少数民族先民在与环境的博弈中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医学体系,并在今天独树一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体系中并非全部使用采自大自然的生物药材进行治疗,在有些疾病治疗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使用了“仪式操演”,比如说使用画符念咒的非药物治疗进行治病。虽然难以从现代医学视角评价这种巫术或符咒治病的科学性,但是,从医学人类学视角看,疾病治疗中的仪式操演对于增强患者信心,激发抗病潜力的作用不可低估,这种作用与心理治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对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如果武断地视仪式操演为“迷信”而加以割裂,这种实践既不理性,也不科学。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上被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或理念酝酿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这一思想随着愈演愈烈的全球环境问题逐渐演变直至发展成熟。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人类求得自下而上地发展的唯一途径。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7]此后,可持续发展被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及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等权威性的国际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世纪转换之际最重要的命题和重大国际会议所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可持续既是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对这一知识体系进行传承与保护的最终目的。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确保传承人的持续发展。传统医药知识作为传承这一行动的客体,或者说作用的对象,从理论上讲,一旦这种知识已经形成,那么,无论是否被传承或者说是否传承下去,它都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现实来看,这一理论上的推论似乎又不完全成立。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主体,或者说这种知识存在的依存载体。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传统医药知识尤其是民间秘方,其传承主要仰赖于口口相授,用心记;其存在依托的载体即是传承人本身。就单个的人而言,谁也无法逃避人生的基本规律:出生—成长—衰老—死亡。这一规律意味着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仰赖于口口相授、记在心里的传统医药知识的延续,需要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传承人,如果由无数传承人组成的知识延续链脱节,知识将随着最后一节链的消失而消失。因此,依赖心记而延续的传统医药知识与依赖纸张等记录而保存的知识相比,前者面临的生存危机更为严峻,延续其传承主体的生命显然更为迫切。毫无疑问,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一个一个接续的生命构成的生命链才是无限。延续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主体生命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让个体的生命无限延长——事实上,就现在的科学而言,是不可能的,而是动员更多的潜在传承人加入学习的行列,成为实在的传承主体。传统乡村本身的传统形成的传统医药知识传承的“保守性、血缘性、地缘性、隐喻性”[8]等特点,使得传统医药知识对传承人具有了选择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局限于一定的家庭、家族或地域,更大群体被传统规约排除了对知识的承继权。一种知识一旦被视为一种私有财产,那么,打破这种“财产”继承权就变得十分的困难,“传统的惯性作用,又使它形成一种惰力,当历史进步要求摆脱或改造某些传统时,必须作出艰巨的努力。”[9]67我们无能斩断传统,做一个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因为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是民族内聚力的源泉、维系民族生命的抗体。”[9]67但我们又不能食古不化、全盘承袭,任其发展。我们需要继承传统,同时又要不断创新。对于传统医药知识主体长期形成的自封闭传统,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引导现有的传承主体认识到传统医药知识开放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逐步引导他们走向开放,同等对待传承群体之外的群体,接纳诚心诚意学习者,扩大自己的传承群体,增强传统医药知识延续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市场经济对传统乡村形成的强大影响,一方面要给予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人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给予他们必要的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生活保障,让他们的生活过得相对体面——至少是在自己所在或周边村落,增加他们的自豪感,提高他们的自信度,增强他们的吸引力,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如果传承人主体群生活窘迫,那么,无论他们如何开放,都不会对潜在主体形成向心力。“本地没得好多人愿意来,他们宁愿出去打工。我们这个比较麻烦,跑来跑去的,病人情绪也不是很好。”民间医生陈永常的感慨值得深思。潜在传承主体为什么宁愿出去打工而不愿学习民间医药知识?难道真是嫌弃行医麻烦?显然不仅如此。事实上,离乡背景并不是传统村落的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被打破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外出打工能挣更多的钞票。面对钞票的诱惑,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惊险,都值得一试,哪怕是背水一战。传统医药知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到自然生态的制约,又受到经济基础的支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医药知识本身即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管子•牧民》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里缺乏粮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们尚且顾不上礼节、荣辱。如果民间医生吃不饱、穿不暖,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他们饿着肚子去传承医药知识呢?王夫之在《诗广传》卷五中说:“来牟(小麦)率育而大文发正焉。”这进一步表明,人类从事一切精神文化活动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物质生存条件之后方能进行。
其次,保持生态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发展对资源的索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存续的生态空间已经或正在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人们关于工业文明对人类生态家园破坏的反思,绿色发展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战略,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人类对于工业文明的理性反思和绿色发展战略的科学定位,是生态空间修复和生态逐步走向平衡的一个重要机遇和挑战。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源于自然,其生存和发展依托于特定的生态空间。可以说,是生态空间里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飞禽走兽维系着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不竭的生命源泉。传承少数民族救死扶伤的理念和医技固然重要,但是,就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依托的生命之源而言,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空间似乎更为重要。面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生态空间的完整性被不同程度打破的现实,我们需要做的当是理性节制对自然资源的无限索取。在现代化进程中,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努力通过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友好型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权力的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四、最少干预原则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形成有其自发性,它是一种代表地域内民族意愿和需求的反映,非外在力量进行的直接性引导。自发性和非引导性,是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讨论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需要考虑这种机制的存在和影响。在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最少干预”原则逐渐引起重视并成为学界研究和政府实践文化遗产资源传承与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最少干预原则也被叫做最小干预原则,目前主要运用于文物修复、古迹修缮、遗址保护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少干预原则还缺乏系统性研究。对于遗产保护工作的“最少干预原则”也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定义。关于“最少干预原则”,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俞孔坚指出:“最少干预就是越来越简洁,最后做到基本上不破坏,基本上不改造,但是又能够满足人的需要。”[10]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认为:最少干预才能真正使文物保护“祛病延年”。遗产资源保护工作遵循最少干预原则,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保护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科学等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并将其传递给后人,从而实现遗产资源的持续发展。最少干预原则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实践,对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同样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保护工作中引入“最少干预原则”,理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尽管在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力量可以越俎代庖。在地方职能部门作出任何一个决策前,都必须全面把握实施对象的属性,以此明确政府的立场和决策定位,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政策措施。就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而言,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行政资源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正视并重视行政资源配置不当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消极影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生并长期存活于特定的生态空间内,形成了一个个独特而又完整的文化系统。这些完整的文化系统需要以掌握本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当地人为主体、遵循客观规律进行传承发展,发扬光大,外界的过度干预和介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这些系统的整体性,威胁其可持续发展。
其二,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一方水土育一方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特定民族的宝贵财富,对本民族的存续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少数民族群众是本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这一文化遗产资源真正的主人,在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政府、社会组织等外在的力量扮演着辅助性或引导性角色。在我们极力推进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制度建设的工作中,政府、社会组织等外在力量应该在尊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其传承和保护给予适当的宏观指导,如通过资金的保障和政策的扶持来调动遗产传承主体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相反,如果政府、社会组织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大包大揽,用自己的思维或想法过度干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结果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不仅不能促进和加强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还会加速其破坏与消亡,变“遗产”为“遗憾”。因此,对待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外在力量最大的保护或帮助可能是“最少干预”,最大限度的保存传统医药知识的历史价值和原生性的科学价值,做到“民间事民间管”,给文化传承主体更多自主和空间,让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在原有的文化社区内进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主张最少干预原则并非否定政府对于行政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因为政府对于行政资源的主导性配置是就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外在保障而言的,而最少干预原则是针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内在发展规律而言。
五、利益均衡原则
我们尝试将“均衡”(Equilibrium)这个物理学概念引入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主要受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的启发,目的在于运用均衡原理分析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利益分配机制。“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是指经济体系中变动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平衡,以致这一体系内不存在变动要求的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是一种所有重要经济变量都保持稳定不变的状况,即经济体系内各有关变量的变动都恰好相互抵消,没有引起重要经济变量发生变动的压力和力量时的状态。”[11]使用“均衡”概念考察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旨在尝试探索一套保障遗产资源传承与保护各关系方利益的分配机制,在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中求得一个相对公平、相对均势的状态,确保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传承人的利益不受损害,或尽量减小其利益的损害,调动各方积极性,协同推进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
“利益均衡是在一定的利益格局和体系下出现的利益体系相对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利益平衡的合理性体现在它是协调冲突性利益的基础性原则。”[12]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目标能否得以实现,关键在于传承主体的主动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努力确保创造保持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如果掌握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民众放弃了其手中的知识权力,那么,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将变成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如何充分调动传承主体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最终要落实到一套健全完善的保障机制。假如文化主管部门每天只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强调传承和保护遗产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使用行政手段命令民众怎么传承,怎么保护,除了一个红头文件别无其他,民众会如何反应呢?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民众会因为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是现有传承机制没有实现利益均衡而放弃参与其中。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认为,要实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同样能够享有和我们一样的知识权力,遵循“利益均衡原则”不仅重要,而且十分必要。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是实现利益均衡的前提。一方面,少数民族民众是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主体,他们是真正拥有传统医药知识权力的群体。我们需要尊重并肯定传承人的知识权力,并努力为传承人发挥其知识权力营造和谐氛围。另一方面,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人是普通的自然人,他们同样享有衣食住行的权利。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和保护还应该尊重并尽量满足传承人的现实需求,而不应该以妨碍传承人经济发展、降低生活水平为条件。
第二,强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利益均衡的保证。从对国内外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的大量研究中我们获得的启示是:本民族的知识权利被其他民族盗用,会大大挫伤权利所有人的传承积极性和文化自信,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有前车之鉴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专题研究、论证、制定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专属的产权保护制度,用制度来保障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体系的知识权利,增强民众对本民族遗产资源的文化自豪感和传承积极性。
第三,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是实现利益均衡的途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不同于传统村落、文化遗址、民俗表演等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前者主要带来社会效益,后者直接创造经济收益。这是就保护与开发的目的而言。就其参与的主体而言,它们之间又存在共性,那就是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这意味着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机制必须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惠益分享。否则,传承与保护的预期目标将难以实现。就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主要相关利益主体而言,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与保护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必须处理好这样一些关系,即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政府与传承人的利益关系、企业与传承人的利益关系、企业与媒体的利益关系、政府与媒体的利益关系、媒体与传承人的利益关系、民间医生与患者的利益关系,现代医药与传统医药的利益关系等。只有各相关利益主体各得其所,相互配合,形成共生互补的利益共同体,协同推进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目标才可能实现。
[1] 刘永明.权利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191.
[2] 阮仪三,林林.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
[3] 何俊乔.小城镇历史街区生存之道——原真性把握[D].天津:天津大学,2009:2.
[4]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09.
[5] 胡文耕.整体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703.
[6] 李启荣.文化生态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J].美与时代(上),2015(2):26.
[7]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
[8] 梁正海,马娟.地方性医药知识传承模式及其内在机制与特点——以湘西苏竹村为个案[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6-31.
[9]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题记[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5).
[10] 孙祥伟.俞孔坚访谈:《城市环境设计》[EB/OL].
[2007-8-21]http://www.chla.com.cn/html/c138/2007-08/1434.html.
[11] 吴宇晖,等,编著.西方经济学[M].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1.
[12] 冯晓青.论利益平衡原理及其在知识产权法中的适用[J].江海学刊,2007(1):141.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Inheritance ,Transmission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in Ethnic Minorities
LIANG Zhenghai, LIU Jian
( Wuling Ethnic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Guizhou, China )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ethnic minorities has both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own trait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authenticity, integrity and sustainability based on the macroscopic backgroun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minimal intervention and balance of interests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of ethnic minorities so as to protect the genes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continue the life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active transmission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best expected goal of the inheritance, transmission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of ethnic minorities only when various principl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promote mutually.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heritance, transmission and protection, basic principles
2018-10-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山区土家族为例”(11 BMZ032)。
梁正海(1970-),男,苗族,贵州思南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贵州省重点学科“民族文化遗产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
刘 剑(1989-),男,贵州毕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民族文化。
C953
A
1673-9639 (2018) 11-0089-07
(责任编辑 黎 帅)(责任校对 李锦伟)(英文编辑 谢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