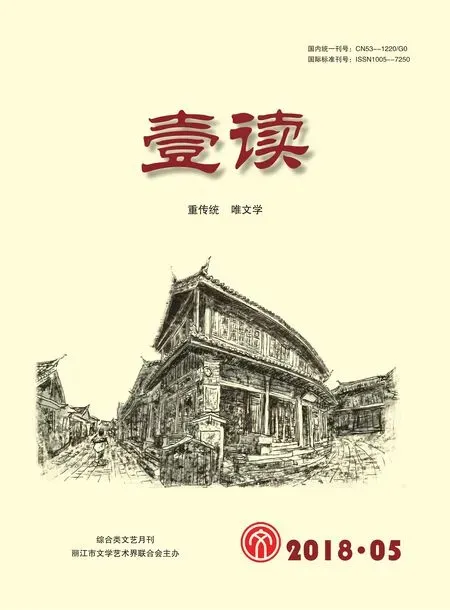龙蟠对话
2018-01-24张建梅
张建梅
也许此行,我已没法找到当年陈光老人穿越时空,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和他心爱的妻子黛(独龙语二女儿)一起,一路长途跋涉,攀越雪山垭口,沿着那条他大半生曾用双脚无数回丈量过的羊肠小道,踏上归途的艰辛步履;也许此行,我已没法追随独龙女黛,当年怀抱她五个月大的二儿子和公公身上背着的因当时独龙江缺医少药落下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不会走路的大儿子一路翻山越岭,徒步走出独龙江,去到美丽的金沙江畔劳作生息的艰辛足迹。但我能用心感受得到,那个虽不可复制,却深深烙在我心底的难以忘怀的历史场景。
此行,跨越三江、去探访独龙女黛的旅途似乎有些遥远,但每个陌生的路口,总会遇见一个个热心肠的好人,让初秋的雨拍打的车窗内,少了许些淡淡的凉意,多了几分兴奋、激情与向往。沿大丽高速一路往北,苍山的云、洱海的风、双廊的景、剑川的田园和玉龙雪山的雄姿,让旅途增添几分童话般的色彩与浪漫的情调,仿佛,和爱人一起,重拾初恋的感觉,来一回说走就走的浪漫旅行。从拉市口下了高速,汽车沿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随海拔的降低驶向美丽的金沙江畔,再沿金沙江畔的沿江公路逆流而上,没多大会儿,便到一座叫松园桥的跨江大桥桥头,过了松园桥一路往北,便是人人向往的香格里拉迪庆高原,往南便是著名的长江第一湾。而我们此行并不需要过江,只需沿金沙江逆流而上,便可以抵达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龙蟠乡政府。车刚到桥头,正想停下车来问路,便恰好遇上一辆从松园桥方向驶来,正打着左转弯灯准备往龙蟠方向的越野车,开车的是个女孩,我们下意识地放缓车速碾压着前面越野车车轮滚过的车辙,想随它一起前往龙蟠,做我们此行探访独龙女黛的“移动导航”,可走着走着,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生怕我们要去的村庄没准还不到乡政府就得岔路。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路程可就走远了,于是加速超车,好向越野车驾驶员问路。才超车没走多远,只见左前方摆放着一块标有前面施工、车辆慢行的警示牌,紧接着一位操着纳西族口音、口里叼着哨子,手举小旗子的工人师傅把我们拦了下来,说前面正在施工,要等一会儿才能放行。堵车,正好可以跳下车来问问后面的越野车驾驶员:请问两家三社怎么走?女孩面带微笑,热情地告诉我们:两家三社不用到乡政府,你们已走超过了,往回走几公里就是两家三社。幸好问路,要不那南征北战的冤枉路可免不了少走,于是调转车头,边走边问路边的村民两家三社的位置,一位正低着头忙活着手头农活路的村民告诉我们说,沿公路走到路上方有个小卖部的地方再问问,小卖部上面的村庄就是两家三社。我们按老乡说的,走到路边正好有个唯一小卖部的地方,我说唯一,毫不夸张。不是吗?今天,当你路过集镇或村庄时,到处是沿公路和集镇建盖的密密麻麻的房子,感觉去哪都和喧嚣的城市没多大区别。而此行,很难得过村庄沿公路两旁就只见一个被田园半包围着的小卖部,感觉得到两家三社人对耕地的保护意识,我们和小卖部的店主打听起陈光老人,店主人非常热情,立马拿起手机用纳西族语言和老人的家人咿咿呀呀的一阵对话交流后,紧接着告诉我们,陈光老人已让他的女婿来公路边接我们到他家。
不一会儿,我们便和黛的女婿联系上,并和他一起,沿着一条渐渐消失在玉米地和山林里的便道往上攀爬,我们一边攀爬一边用双手扒开缠得密密麻麻、刺着脸颊的荆棘杂草,汗流浃背、一鼓作气地朝着金沙江畔半山腰的两家三社方向爬去。快走近村庄,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站在田埂边喘喘气,好久没感觉爬山会让人有胸口火辣辣的刺痛感,很明显,年过半百,加之缺少锻炼,爬山的劲头已大不如从前。可此时,路似乎也懂得让远方来的客人有一丝半会儿的歇脚的理由,小路也由直上攀爬、变成顺着田埂平缓穿行,地势也在台地间渐渐缓和下来。走近村庄,只见背靠大山、面朝金沙江的两家三社村,每家每户的房屋建筑都沿山建盖在山坡上,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全都是小树林,且绝大多数人家的院墙和房子的背面都背依着大山,小院似乎都隐藏在绿树丛中,站在玉龙雪山半山腰的田埂上,朝江对岸的远方眺望,连绵起伏的云岭山脉被低垂的夜幕晕染,只见山的轮廓,不见山的颜色,站在高处看风景,只感觉,别有洞天。快到你家了吗?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问道。黛的女婿连忙答应道:快了,就在前面。那一刻,只感觉周身闷热得跟被火烤似的,可探访独龙女黛的心,却依旧不舍得放缓匆匆前往的脚步。快走到家门口,只见一位七十开外的老人正在自家院墙外的一角忙活着整理木楞房里堆放的杂物,我估计他定是我们要找的陈光老人,木楞房看上去像是用来堆放杂物和柴火的简易房,我和爱人连忙迎上前去和老人打招呼:阿叔,我们是你儿子建华的好朋友,从怒江到大理办事,顺便转到龙蟠来拜访您和阿姨,来您家坐坐。阿叔连忙放下手中正忙活着的活路,带着我们一起朝他家的院门走去。还未等我们走进院门,只见一个重度残疾的男孩,说是男孩,可年龄大概在45左右,只见他拖着重度残疾的下肢,整个人几乎是在随双脚膝盖的滑动挪动着身体和下肢,可动作却麻利得跟个小矮人似的,口里一边咿咿呀呀的说着什么,一边比划着朝我们迎过来,听得出他说话非常吃力,我们几乎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但能感受得到,对我们的到来,他很高兴,也很兴奋和热情。我和爱人俯下身去和他握手致谢,便和老人一起走进小院。
坐在条凳一般长长的屋檐坎上,阿叔和妻子黛及儿女和从独龙江嫁到龙蟠的侄女,用最热情的气场把我们团团围住,那一刻,没有一丝的陌生,只感觉特别温暖,特别亲切。才接过主人递过的热茶,天已渐黑,可漆黑的夜,并不能包裹一群似久别重逢的亲人再见一般的老怒江人的心,我们一边聊天,一边不停地向两位老人追问着独龙江的历史与昨天,总想从他们身上找到许许多多未知的答案。因为,陈光老人毕竟是六七十年代初,从丽江师范毕业后徒步走进独龙江教书的老教师,而妻子黛则是独龙江土生土长的文面女最多的龙元村人。带着好奇与疑惑我们不停地追问着:阿叔,您是哪年到独龙江任教的?您去独龙江任教时是从吉束底茨楞村方向、顺着普拉河逆流而上,再翻越雪山垭口走进独龙江的吗?当时走了几天?您在东哨房和其期露宿了吗?您攀爬过藤梯吗?当时在独龙江小学教书有专用的教材吗?开设几门课程?您当时不会说独龙话您是怎么和独龙族孩子交流的?您的在昆明大学里教书的两个独龙族博士儿子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在独龙江吗?我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快把两个老人问得喘不过气来,可我们的话题仍旧像那对世间万物百般好奇的顽童一般,不停地抛出,感觉独龙江的故事怎么问也问不够,怎么听也听不够。也许,这就是一种缘,更是两位从怒江赶来的“陌生”的晚辈对独龙江、独龙人及老怒江人的一种难以言表的情节。可面对我们的好奇与询问,阿叔一脸慈祥和蔼,一个接一个,认认真真的回答着我们的询问。特别忘不了的,是阿叔给我们讲的故事中的其中一个细节,为了便于在独龙江更好地承担好教学任务和与独龙族孩子沟通,他用汉字标注着写在纸上记录的方式学习独龙语,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已基本学会独龙族语的常用语,并和孩子们交流和开展教学,特别当时在其他教师都被抽到县乡做其它工作的情况下,他一人一校,却尽自己所能,尽量开齐开全课程,并通过自学和努力,把自己练就成能够独当一面的“全科教师”,圆满完成教学任务,既满足了独龙族孩子对学习知识的求知欲,又培养了孩子良好的兴趣爱好。
由于连续降雨,村里的电线杆被滑坡给冲毁正在抢修中,村子里停电,整个采访过程,我们都只能和老人在烛光中对话,阿孃黛更是非常热情,总是不停地用浓浓的独龙族方言,一边倾听着我们和阿叔的对话,一边风趣地插着话题,一看就感觉阿姨是个热情好客、性情开朗的独龙女人,让整个访谈多了几分轻松和歉意。暮色中,烛光点亮的农家小院不时传递着开心与欢笑,那阵阵欢笑声似点燃礼花的导火索,划破天际,满天的星星似绽放的礼花在寂静的天空中点缀着。屋檐坎上,那依着主人脚跟的小狗乖巧地趴在地上,仿佛也能听懂我们的对话。我接着问阿孃:你从独龙江畔来到金沙江畔生活,最大的不习惯是什么?阿姨用不是很地道的汉语回答道:不习惯的地方太多了,一句两句话说不完,说话不一样的不习惯,劳动工具不一样的不习惯,干活背的篮子、用的劳动工具不一样的不习惯,生活习惯不一样的不习惯,反正不习惯的地方太多太多。阿叔接过话题说:我们到这边居家生活,样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所经历的过程十分不易,一时半会儿,确实难以说清楚,你阿孃更是非常不容易,也非常辛苦。她非常好学,才来一年多就基本上能够听懂纳西话。特别文革结束后,我重返工作岗位,曾经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也就是现在在昆明大学里教书的两个儿子到贡山工作生活,直到退休我才回到龙蟠,而她却一个人带着重度残疾、不会说话的大儿子和女儿在龙蟠两家三社农村生产生活,更是十分不易,每天都起早贪黑的干活,而且她挺能吃苦,她挣的工分要比当地女人挣的多,苦要比别的女人苦得起,她这样做,都是为了想好好供几个孩子上学读书,你阿孃的勤劳贤惠,两家三社当地许多农村妇女都赶不上她,这些,左邻右舍及村民都非常认可。只听得阿叔不停地夸着阿孃,在一旁的我们,能静静感受得到独龙女黛为何要走出大山,离开家乡、死心搭地地爱着一个外族男人的理由。我接着问阿孃:来这边生活那么多年,你想过家吗?想过独龙江吗?阿孃带着一脸的纠结与无奈用方言答道:想,咋过不想?老实想过。想独龙江、想家的时候哭也哭过很多,阿叔上骂也骂过很多,现在想起这些,后悔也来不及了。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时,我们和阿叔及所有在场的人都心疼的笑了,特别阿叔心里更加明白,那是阿孃对生活,对爱、对家辛勤付出的见证。正如常言道:打是心疼骂是爱。可这种爱,这种难以言表的“后悔”,不正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先生笔下《在那遥远的地方》歌词中所描述的细细皮鞭“抽打”的千般情、万般爱?访谈中,我们能切身感受得到两位老人对来自家乡的小辈的信任与热情。特别,当听到独龙女黛面对两个来自家乡的小辈,娓娓从心底道出的许许多多的“不习惯”及纠结的“后悔”的话语时,倍感漫漫人生,让人所承受的难以言表的酸甜苦辣、背后蕴含着的那一份沉甸甸的爱,是独龙女黛走出大山的理由,更是一个慈祥的独龙母亲,为爱、为家默默付出的不易。在与我们的对话中,阿叔一次次就要夺眶而出、却又强忍着的噙满眼眶的泪水在默默告诉着我们:其实人生,它就是一出唱不完的戏,道不尽的情。也许,有时候你是编导,编导着自己,也编导着别人;也许,有时候你是角色,扮演着别人,也扮演着自己;但无论你是编导也好,角色也罢,真正能够倍伴你一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痴心爱人。
就要结束采访,我们把此行带去的礼物、由我本人参与收集整理,由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集.独龙族卷》交到老人手中,并告诉两位老人,书里有他们的两个博士儿子及外孙女的文章时,老人激动地从我手中接过书卷……我接着说:阿叔,非常敬佩您和阿孃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把孩子培养成独龙族第一个中医学博士(云南中医学院民族医药学院副院长),培养成独龙族第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培养成两个在省城大学里教书育人的老师。阿叔却回答说:是党和国家培养关心的结果。
夜幕低垂,带着对两位远在他乡的老怒江人的敬重与不舍,匆匆告别龙蟠,告别两家三社,手电筒的光在漆黑夜里,照射着崎岖的乡村羊肠小道,圆圆的光圈随着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步伐不停地晃动着,似乎在为我们寻找着回家的路,走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身边,山林、小草和树的影子及猎狗的吼叫声陪伴着我们,继续走完那段从远古走向文明的心路,眺望远方,香格里拉的灯火,似马帮遗落在云岭深谷沟壑间的暖暖的火塘,一头,连着远古;一头,连着幸福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