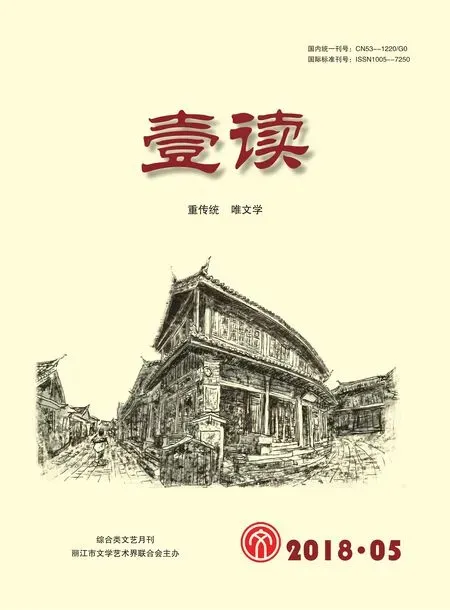地球褶皱里的生命交响
——读《三重奏》兼谈陈洪金文学创作
2018-01-24一苇
一 苇
丽江作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多文体间的自由穿梭和现代意识的多角度表达,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我的感觉如是。这应当以定居昆明的海男为代表。后来的和晓梅,还有更为年轻的东巴夫,都有这样的特点。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渗透于他们后现代主义的表达中。而陈洪金的写作却是个异数,他的写作传承有序,更多来自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其文字的畅达一如奔流不息的金沙江水。如果说日常生活是文学的肉身,那么陈洪金却在地球的褶皱里寻找肉身走失的灵魂。他不甘于行尸走肉的庸常,他要给文学的肉身赋予存在的理由,这是陈洪金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
优秀的作家是能够熟练驾驭各种文体的,其实这样的作家不胜枚举。以西方为例,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诗歌、散文并存,同样出色,而且他已经打破了文体间的界限,他晚年的名作《沙之书》是个范例。在中国,唐代的韩愈、宋代的黄庭坚,乃至清代的世界文学巨匠曹雪芹,无不诗文俱佳。现代以来,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旧体诗歌,同样闪烁着耀眼之光。贾平凹以小说扬名,而散文尤精;阿来以诗成名,而长篇小说奠定其在文坛的地位……丽江作家陈洪金的创作,在目前而言,自然无法与前辈大师比肩,但同样是在散文、诗歌、小说中游刃有余,其散文具有诗性、诗歌具有叙事特征,而小说却有着“散淡”的倾向,这就使得其创作打破文体间的界限相融互通。
这在其新作《三重奏》中可见端倪。其实《三重奏》是陈洪金的“独奏”,只不过这部作品用“散笔”“抒情”“叙述”分成了三个独立的部分,按传统的说法便是散文、诗歌、小说,而这三个部分又构成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母题。这种行走是极具地域性的,这应当是陈洪金的文学主张之一。他认为,地域性是作家对于庞大而复杂的客观世界的主观回应。个体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创作置于整个世界的所有时空之中,作家只有把自己的写作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点上,才有可能创作出充满细节与个性的作品来。否则,作家想通过某个作品表达所有的思想和观点,很明显是野心超出其所能的范围。这样的作家,往往是明智的,现实的,脚踏实地的。由此,陈洪金的《三重奏》选择了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大地作为局限,并将自身思考有效地用散笔的方式、抒情的方式、叙述的方式呈现,对母土的依恋、对自然的依赖、对村庄的亲近、对滇西大地的血脉相连,都有着细微的体察与反思。
诗性与智性的交融闪现是陈洪金散文的特征之一。陈洪金散文中,俯拾皆是闪烁着诗性与智性光芒的句子,如《镜庐笔记》:“我不敢把我沾满了俗世尘埃的手探进去,生怕那平静的水面上兴起了一丝波纹,我却无法去用一种恰当的表情去回应。”“只有世间的尘埃,才会让人受到伤害,或者伤害别人。”“当我们谈笑风生,当我们踌躇满志,当我们流落江湖,谁又能够始终保持内心的清白?”“天空是指头大的一块深蓝布,抬起头来,目光就窜到上面去了。”《一个逝者的博南古道》:“一场变故,竟然让他(杨升庵)从此远离京城,如同一片被狂风吹走的叶子,飞向了千里万里之外的疆域。”“当北京城里的廷杖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那些曾经以雅士自居的文人们,在紫禁城里被脱光了裤子,阳光照着他们比脸面更加私密的屁股,他们的灵魂就先于那些皮囊,飞升到了他们向往着的高空中,任由肉体们被敲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飞。在这一群人里,杨升庵的痛苦就在于,他的肉体始终没有让他的灵魂走远。他还必须得把灵魂与肉体重新缝合起来,从干燥寒冷的北方,向着一个梦里都没有见过的南方,一路贴近潮湿的大明王朝最南端的天涯陌路。”“命运把他当成了一支箭,拉开满弓,射向京城西南角的天边,落到地上的时候,他肯定会深深扎进云南这片土地里,并且长成一株枝繁叶茂的榕树”。《水润大理》:“红河,其实是一条开满鲜花的河流,那些花朵,便是云南土地上的一个个神秘而古老的民族。”《相逢或者别离》:“那时候,巍山古城栖息在典籍里,纸张上、词语里。它是一个弥漫着香气的古人,阳光的香气、干草的香气、布匹的香气、古歌的香气,甚至是刀剑和箭镞的香气,都隐藏在旧纸里。”“在每一个时刻里都有着一晃而过的速度,因此,我们在车窗内的行程,错过了太多的山水和花朵,错过了太多的飞鸟和游鱼。”“暮色到来的时候,拱辰楼是整个巍山古城最后进入梦乡的头颅。月亮慢慢地从树梢露出来,皎洁的月光把宁静的巍山古城照亮,石街清静,竹影婆娑。居住在古城中的人们,轻轻的鼾声响起来,竟然让人更加真切地聆听到深夜里的微风路过拱辰楼雕檐,轻微的响动从那些木质廊柱细微的缝隙里传出来,仿佛一个圣人在幽暗处不经意的叹息。” 《正如匆匆而去的时光》:“在这个夜晚,子弹途经一片肌肤,让伤口迸开。”“于是,在天亮之后,攻与守不复存在,各自带着流血的伤口和失去体温的躯体,离去。”《荒野的气节》:“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跪迎新主得富贵,有人血溅沙场把命丧,有人远走他乡不复返,有人隐居山林浇愁肠。”“它们郁积成一股戾气,在砚池里蛇一样游动。那些诗句,看似一无所求,但似乎又在诉说着什么。”《大地上的居守》:“群山意味着阻拦,江河意味着屏障。桥梁意味着离开,村庄意味着停留。”《远处的喜洲》:“喜洲远离了我的故乡,它从村庄里悄悄地脱离出来,把无数的房屋拢在怀中,把曲折的道路缠在腰间,成了一座古老的小镇。”《曲硐古镇让我成为一个幸福的幽灵》:“曲硐古镇,从此把我这样一个游走者,从它洁净的俗世,送到另一个更加繁杂的俗世。回望在那些巷道里,屋檐下的游走,我怀念那一段短暂的、作为幽灵潜入古镇的幸福时刻。”《以醉眼,洗游魂》:“只有我自己知道,此时,我是以怎样的一种身姿,如同一粒风中的尘沙,飘荡在凤羽的幽深而狭长的巷道里,用自己的灵魂去抚摸这个古老的小镇。”“正午的薄酒,就这样让一群用墨水与纸张收藏生活的人们,在眉宇与唇吻之间,顷刻之后,便醉了。”“春风托举了花瓣的旅程,花瓣标注了春风的灵动。”
在阅读陈洪金散文过程中,我随手勾划出令我眼前一亮的句段,这些浸泡着作者浓郁情感的字句,如同暗夜中跳动的烛光,瞬间便奠定了文章的基调,使整篇文字充溢着跌宕起伏的诗性光芒。而智性的思索又将文章向深度和厚度推进,使得陈洪金的散文既有灵秀之气,又有深厚根基。
陈洪金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小开口,大视野;小情怀,大背景。这在其《镜庐笔记》中显露无遗。在这篇匠心独运的美文中,没有所谓历史文化大散文的体量,也没有游记散文的简单边走边看,而是撷取了“镜庐”这个具有历史背景的大宅院的几个小景,如同山水画家的水墨小品,从院子里的水缸、天井、残墙上的窗棂这些小景入手,徐徐展开了与镜庐有关的一切,南诏大理国历史之悠远、喜洲商帮贸易全球化、镜庐建筑之精巧,全在冰山一角中若隐若现,作者在此舍弃了对镜庐建筑的正面铺陈,对喜洲商帮的深入挖掘,只是在那些残墙、天井、窗棂、水缸等细微的物事入手,表达的也是文人的小情怀,却能以小见大,独辟蹊径,实为佳构。《一个逝者的博南古道》亦是如此,无论是“明朝第一文人”杨慎,还是穿透数千年悠远险僻的博南古道,都具有无限的张力,大笔一挥,即可洋洋万言,但作者紧扣杨慎与博南古道的联系,使智性书写置入特定时空,便使这篇文章有别于相同题材的散文,作者在此不必详尽交代明朝的“大礼议”,也不必书写杨慎的前世今生,不必将博南古道纳入考据学的范畴,这就是散文之巧。《正如匆匆而去的时光》从石碑铭文入手,展开想象回顾那场地方史上中共游击武装与国民党地方部队之间的战斗,也是典型的小开口,大背景,这多少受了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记得某评论家说过,西方现代小说的特征就是往小处写,更多关注人的内心、关注日常的细节,陈洪金的散文显然受到了这种影响。
开阔、饱满、温暖、通透,构成了陈洪金诗歌的质地。云南人民出版社编审海惠说“他的诗是沉默中流淌的响亮音符,那是开阔的想象和自然的伟力浓缩的风景,让人想起艾略特的《荒原》和聂鲁达诗歌中那些大地的回响……”窃以为是中肯的。《鸡足山:与佛相关的三种心境》:“为了接受一颗心/一颗被生活和爱困扰了许久的心/用森林来沐浴凡俗的烟尘/用风声来吹拂远远近近的城市/纷乱的脚步声/我对自己说/如果要把红尘看清楚/那就站在山顶,仰望着一朵云/向着越来越近的天空/合十啊”,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此刻通透的心境,静而能生万物,便是豁然开朗。“有人说,你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鸡足山却成了世外净界/有人说,你已经侧身远去/我却在一群世俗的人群中看到你”,哪里是净界,哪里是俗世?诗人提出了问题。《漾濞简章》:“苍山兄,在杜鹃花丛中/我慢走,我徘徊/我独坐/我静卧/我心如止水,我若有所思/所有的状态/在那么多杜鹃花的陪伴下/都是顺理成章的/你让我成为一个自在的灵魂,不再奢望远方”,显得温暖而开阔,颇有“相看两不厌”的味道。“这条路太累了。清晨的时候,它不愿睁开眼睛/石头沉睡在泥土里,翅膀沉睡在巢穴里/门洞沉睡在深道里,壁画沉睡在墙壁里/古镇,沉睡在时光里/一群人的踏访,被视为多余”,诗中用铺陈的方式,不停地转换视角,将古镇的静美展露无遗。《剑川遗迹》:“让我们看见大地上的面容/敞开最纯净的内心,让耕作时的艰辛/栖息在飞鸟的翅膀上,让爱情,栖息在/蜜蜂的路途中,让祭词与香赞栖息在/一页页沉睡了许多年的经卷里/忘记了泪水与忧伤,从此/天堂与人间水乳交融”,文字富有张力,情感饱满而纯粹。“天空是云朵流浪的梦乡/每当它们疲惫,流离失所在峰峦与江滩/就会乘着夜色而来,在剑湖里濯足/让细微的浪花/把滚烫的脚掌,在远行过后/抚慰成草尖上的愉悦”,云朵的愉悦也是人类的愉悦,不管如何疲惫,如何流离失所,都会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找到生命的温暖。“沙溪是一只孤独的萤火虫/夜风吹来的时候,它在茶马古道上形单影只”,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在此具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
丰富的想象、严密的逻辑、多元的结构是陈洪金小说的长处。如果说按照现在“情节性小说和非情节性小说”,或者是“刚性小说、柔性小说”的分类,陈洪金的小说是情节性的、刚性的,有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也有现代主义的影响。小说《半朵雪花》想象力令人钦佩,从无量山走出的打工仔董时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了“故事匠”,为影视编剧搜集素材服务,后来受命“盯梢”,被人痛殴后随即失业,小说从高潮跌落。接着董时光又去饭店跑堂,从“上菜”到亮出南涧“跳菜”的绝活,中间经过了耐心的铺垫。因“跳菜”饭店食客爆满,因食客爆满饭店遭到打砸,因打砸董时光再次失业,他打工生涯第二次从高潮跌到谷底。而此时,另一家酒楼又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乌云密布的天空透出了一隙阳光。然而,董时光已经惧怕了都市,想和杨彩莲回无量山老家过春节。小说结尾是:“‘回去,没钱,怎么办?’ 杨彩莲问。董时光依然看着半朵雪花消失的街角,没有作声。”小说设置了皆大欢喜之后的突变,开放式的结尾。这篇小说看似写得漫不经心,实则经过精心的设置和安排,情节环环相扣,又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故事匠→盯梢→挨打→失业→跑堂→挨踢→跳菜→客满→砸店→再失业→成名→想家→没钱→看雪……,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其中哪个环节断了,情节的走向都会发生变化,因此,陈洪金的确是讲故事的高手。就想象力而言,仅“故事匠”的职业就充满了想象。在《最后的挽歌》中,作者精心设置的两条线索几乎骗了我,以为是可有可无的闲笔,滇西抗战老兵的讲述时时被“我”的生活打断,被女徒弟“吉吉”的生活打乱,往往是抗战老人杨进才讲到精彩处,手机即刻响起,“我”升职的事、孩子读书的事、“吉吉”恋爱的事,都挺闹心。直到最后,杨进才老人抗战的故事仍没有讲完。这篇小说的妙处就在于结构的巧妙安排,使得小说显得像杂乱无章的散文,情节似真似假,地名、事件似乎都是真的,主人公也是“陈作家”,松山抗战也实有其事,这就使得整篇小说似讲述亲身经历(或许也是真的),包括那些烦恼,都是生活中时常发生的,而某些细节又读出来虚构。如此,有经验的读者就会明白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把滇西抗战的浴血奋战与目前碎片化的生活作为两条线索交替进行,一方面是老人讲述打鬼子的慷慨激昂,血流成河,可见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另一方面又是那些升职潜规则、异地恋维系、 借钱伤友情、老师找家长等等破事。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就显得无比荒诞,作者的写作意图到此就显露无遗了。看似漫不经心其实精心的结构安排,确是独具匠心。
优雅、畅达、舒展,构成了陈洪金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偶有生僻冷硬。陈洪金的语言,是植根于《诗经》的传统,优雅、圆润、不温不火,时有象征、通感、拟人、拟物等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也有着西方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和生僻性,力图在语言表现上求新、求异,不甘沦落于庸常或熟知的表达方式。比如“子弹途经一片肤肤,让伤口迸开;在这个夜晚,血液像鲜花一样绽开,让生命伴随着血液渗进甘屯的泥土”,很明显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语言的影响,在中国的思维模式里,是不会如此轻描淡写地说人中枪,也不会将血液比做鲜花,这样的写法,就是典型的后工业化时期的冷酷。
倘若陈洪金文学作品稍有不足,窃以为有语言和行文两处微瑕。其诗歌语言稍显平铺直叙而浅显,文似看山不喜平,诗歌尤重语言,传统诗歌理论讲究凝练和含蓄。散文和小说的语言稍显冗长,结构较为松散,舒展有余,紧凑不足。当然,文无定法,个人管见,我们有理由期待陈洪金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突破,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