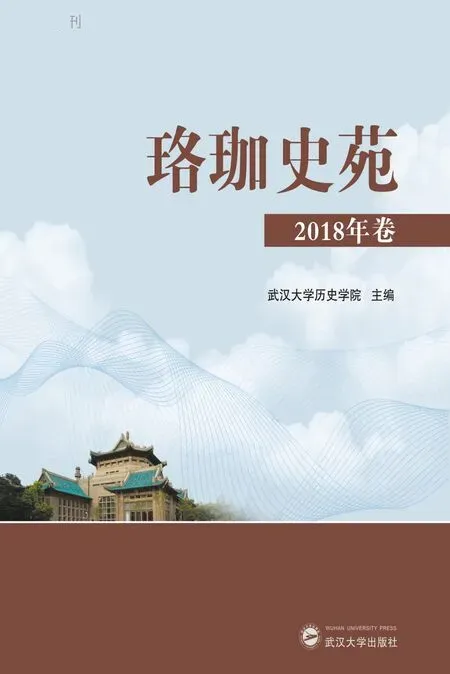古巴导弹危机研究综述
2018-01-23张亮
张 亮
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激烈对抗的一次极限。①赵艳:《近年学术界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研究述评》,《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2003年第2期,第84~86页。它不仅影响了美苏攻防态势和冷战进程,更以核危机的方式改变和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对核武器的态度。因而,古巴导弹危机自发生以来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历史、政治、军事、社会心理等领域学人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梳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学术史既是了解冷战历史的必需,也是进一步控管核武器和核冲突的需要。
国内学界对于古巴导弹危机学术史的梳理成果不多。《近年学术界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研究述评》是国内首次对古巴导弹危机学术史的专题梳理,赵艳从危机的缘起、决策、后果等角度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的国内学界研究现状,但未能介绍国外学界的研究现状,也未能提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国内研究情况。①赵艳:《近年学术界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研究述评》,《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2003年第2期,第84~86页。赵学功在《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的前沿部分细致梳理了2008年之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尤其补充了国外学界在档案材料开放、学术会议召开等方面的内容,扩展了对国外学界研究现状的认知,给予笔者诸多启发。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拟扩展学术史梳理的范围和时间跨度,以时间为主轴,从国内、国外研究两方面,简要梳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
言必有据是史学研究的关键性特征,相关档案的解密程度部分决定了国内学术界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情势。三十年解密的期限,决定了美国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档案材料在20世纪90年代初公之于众。这一时间点恰逢苏联解体和苏联档案的公布,两大当事国的文件档案为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苏联解体的时间点就成为划分研究阶段的节点。
据此,本文将国内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苏联解体之前,相关档案材料未解密,国内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较为薄弱;第二阶段:苏联解体至2002年为档案解密、解读期;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侧重于理论分析,研究的对象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一)第一阶段:苏联解体之前
由于档案材料的缺乏,本阶段主要侧重于介绍古巴导弹危机的基本史实,分析论证缺乏强有力的材料支撑,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录,而披露史料和隐恶扬善是这些回忆录的共同特点。《十三天》在日记的基础上回忆了美国决策者视角下的古巴导弹危机全过程①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人民出版1969年版。最新译本根据《十三天》的1999年英文版翻译而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1月出版,在1969年译本的基础上,新译本更新了序言,新版序言由小阿瑟·施莱辛格撰写,主要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在古巴导弹危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新译本也扩充了内容,增加了后记和相关文件。所补充的文件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最高领导人的部分声明和通信。后记部分由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和格雷厄姆·T.艾莉森撰写,肯定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提供大量详实材料的同时,也指出回忆录中存在的不足,并以此为个案,揭示出“白宫-国会”决策程序中存在的机制性问题。;《肯尼迪》则回忆了危机过程中的肯尼迪②西奥多·伦索森:《肯尼迪》,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这两部著作的作者分别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和头号亲信,其中不乏美化肯尼迪之词。赫鲁晓夫则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回忆了古巴导弹危机,在为学界提供苏方材料的同时,也刻意美化了自身的形象。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则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从联合国的角度回忆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在联合国的斗争以及联合国所展开的调停,其中亦不乏夸大联合国作用之嫌。④吴丹:《古巴导弹危机》,《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5期,第63~82、38页。
由于档案材料的局限,本阶段国内学界仅有为数不多的专题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场核赌博——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美苏之争》,文中在美苏争霸背景下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在危机背景方面,韩华认为美国的过激行为(如“猪湾行动”)推动了苏联与古巴的结盟,而在古巴部署导弹是赫鲁晓夫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在危机过程方面,韩华认为苏联最终撤出导弹,既是中苏敌对的掣肘,也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肯尼迪软硬兼施的结果;在危机的影响方面,韩华认为,赫鲁晓夫撤出导弹有助于人类和平,而整个危机也促使美苏双方更为谨慎,此成为美苏对抗缓和的转机。①韩华:《一场核赌博——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美苏之争》,《政治研究1987年第4期,第85~101页。
(二)第二阶段:苏联解体至2002年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和苏联大批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档案解密。有学者估计,美国国务院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文件资料80%已经公开,成为冷战时期资料开放程度最高的历史事件之一,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等相关部门的大量文件也相继解密。②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4页。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也在1992年参加古巴导弹危机学术研讨会时,就该事件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公布了危机期间古巴的相关秘密档案,这些材料的解密使学者可以比较清楚、全面和客观地分析古巴导弹危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原因、影响和决策分析的研究。
在分析原因方面,该时期的主流观点依然承袭上一阶段,认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主要是为了增强其在美苏争霸中的地位,而郝承敦则认为,“美国在北约盟国部署导弹是诱发古巴导弹危机的重要因素”③郝承敦:《古巴导弹危机新论——关于赫鲁晓夫决策动机及政局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0页。。
在研究决策过程方面,首推桂立的《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分析》,文中分析了美苏双方的决策过程,肯定了肯尼迪“封锁古巴”的合理性,这一点得到了学界认可。在此基础上,桂立还提出了“隔离政》,策”的概念,对美国封锁古巴展开专题研究。①桂立:《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76~82页。
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关注危机期间的情报研究。一方面肯定美国情报机关在危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又揭示美国在事件之前的情报失误。徐起认为危机期间美国的情报搜集能力对美国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②徐起:《电子情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特殊作用》,《现代舰船》1999年第3期,第38~39页。而高金虎则关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的情报缺陷,认为美国误读误判情报以及敌方的干扰导致了危机的发生。③高金虎:《从珍珠港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看情报失误的原因》,《情报杂志》1995年第3期,第71~73页。随着时间推移,国内的学者逐渐运用相关的理论来研究危机期间美国情报的得失。2017年张力运用组织理论,研究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的四份《国家情报评估》,认为当时美国情报失误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出多门、互不统属;二是情报组织为了保持情报结果的一致性而没有完全客观地分析后续情报。④张力:《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情报失误——从组织理论视角对〈国家情报评估〉的分析》,《情报杂志》2017年第8期,第1~5、22页。
在危机的影响方面,本时期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古巴危机促使美国不再武力威胁古巴,成为美苏争霸的转折点,并对世界无核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冷战结束之后,学界从冷战的角度看待古巴导弹危机,认为古巴导弹危机部分程度上加速了两大阵营内部的分化。危机之后,苏联开始寻求共处之道,为国际关系的缓和乃至冷战后大国关系提供了借鉴。
本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是张小明的《古巴导弹危机的再认识》。该文坚持本阶段主流观点,在解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古巴危机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是美苏领导人的谨慎和接触最终将古巴导弹危机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该文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完全是赫鲁晓夫左右下的一次冒险行动。①张小明:《古巴导弹危机的再认识》,《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第83~89页。而后一观点受到了蔺陆洲的质疑,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是苏联高层集体决策的结果。②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法治与社会》2011年第5期,第292~293页。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沈志华主编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第29卷专涉“古巴导弹危机”,涉及自1962年8月至1963年1月整个危机期间的149份苏方档案,这些档案涵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多个部门间的通信往来以及美苏领导人的通信,揭示了危机期间苏方观点的变化,对于了解危机期间的苏方态度具有重要价值。③沈志华等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与此同时,美国方面的档案材料也相继解密,尤其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其中专门辟出两卷收录古巴导弹危机的相关档案材料:《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古巴1961—1962年》(卷五)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果》,是研究古巴导弹危机的重要基础。
(三)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
本阶段以2003年赵学功的《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为开端,文中赵学功在继承上一阶段主流观点的基础上,充分使用解密档案等新材料,令人信服地论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背景、发展的曲折以及危机的结束和影响。同时,作者将古巴导弹危机置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和美国国内政治背景之下,论述了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对危机的影响,也论述了美国国内诸多因素对肯尼迪决策过程的制约,并认为,危机的和平解决是美苏双方领导人克制的结果。④赵学功:《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第65~72页。这篇文章论述有力,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其所提出的“危机外交”的概念,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该文发表后,国内学界围绕危机的史料性探讨告一段落。学界开始侧重对危机进行理论分析,并呈现出研究对象多元化的新特点。
2003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学者采用新角度(理论)来解释古巴导弹危机。这些成果中,既有从核控管①如高恒建:《古巴导弹危机对军控与裁军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9期,第314~315页。、国际博弈②代表性著作如,张昊:《博弈纬度下的国际管理研究——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宝宝:《浅析战争调节机制在美苏冷战中的运用——以两次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0~72页。等方面认识古巴导弹危机,也有从危机决策③代表性著作如,刘畅:《心理传导与危机决策:基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张盛发:《试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与决策——写在古巴导弹危机50周年之际》,《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6期,第57~70页;荣正通、胡礼忠:《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国际政治》2007年第1期,第1~5页。、首脑外交④代表性著作如,吴金宝:《国际危机处理中的“首脑外交”——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个案的分析》,《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9~12页;李宝宝:《首脑外交在处理国际危机中的作用——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64~68页。等角度来分析美苏双方领导人。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尝试研究“危机时期美国执委会官员”,代表作是吴文成、梁占军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官僚位置与决策》,文中通过对整理资料和统计分析,发现参与执委会的官员,其立场及其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时的信息、认识、个人经历以及总统的决策态度,从而在一定层面上推翻了“位置决定立场”这一经典解释。⑤吴文成、梁占军:《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官僚位置与决策》,《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第54~82页。同样是研究决策人物,彭洁则把目标集中在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认知上,她运用认知失调理论,从统一性、自重程度、自身恐惧和愿望三个方面,分析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认知变化。①彭洁:《认知失调对政治决策者决策的影响——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3~15页。
除了理论分析之外,本阶段的研究不再限于固定的领域,研究对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中英苏美等方面。
关于中国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主流观点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国始终从舆论上支持卡斯特罗政权,在危机的末期引起苏联的不满,再加上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中支持印度,从而导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②相关著作如,戴超武:《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0年第4期;夏明星、薛正霖:《中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分歧》,《国防时报》,2010年9月3日,第22版;冯云飞:《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与苏联对中印边界问题立场的转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普罗佐蒙什科夫:《中印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与中苏分裂——前苏联档案中的新材料》,许剑波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4期。2016年,姚雨在《浅析古巴导弹危机与中苏关系的变化》中,结合冷战背景和中苏关系,首次系统而又完整地展现了古巴导弹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③姚雨:《浅析古巴导弹危机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在英国与古巴导弹危机方面,刘勇为认为,英国通过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积极配合美国政策,修复了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外交的一次胜利。④刘勇为:《英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应与处理》,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而腾帅则强调,英国在危机中的表现是第二次柏林危机缓和的延续,不仅缓和了美苏紧张,也对英国欧洲政策的制定以及60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的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⑤腾帅:《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与古巴导弹危机》,《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20~24页。除了英国政府外,英国的罗素作为一个个体,也成为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韩锡玲在《论罗素对古巴危机的调解》中展示了罗素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所做的各种调节努力,认为罗素的奔走只是给已经萌生退意的苏联一个台阶,并非如罗素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作用重大。①韩锡玲:《论罗素对古巴危机的调解》,《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31~34页。
就苏联决策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关系而言,蔺陆洲认为古巴导弹危机前后,苏联决策机制中,赫鲁晓夫权力下降、集体领导加强,同时军队影响力上升。在古巴部署导弹是苏联高层集体决定的结果,这就否定了部署导弹是赫鲁晓夫个人冒险的说法。而苏军实力不足则是后来苏联妥协的直接原因。②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法治与社会》2011年第5期,第292~293页。
总体来说,本阶段对中、英、苏的研究相对较少,更多的是集中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在这方面,除了运用新的理论框架解释美国在危机中的行为决策之外,其新突破还在于,2012年和2013年分别出现了对美国中央情报局③韩福松:《美国中央情报局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作者将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范围拓展至古巴的独立之后,认为,中央情报局对古巴的各种颠覆行为点燃了古巴导弹危机。详细论述和主要肯定了中央情报局在危机前和危机期间的情报搜集工作。突出了时任中情局长约翰·麦科恩在解决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作者还分析了导弹危机的解决对于中情局的重要意义,认为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中情局重新获得总统的青睐。、美国新闻署④赵继珂、邓峰:《美国新闻署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探析》,《世界历史》2013年第3期,第14~24页。文中利用新解密的新闻署档案,详细展现了美国新闻署在古巴导弹危机高潮期间所发挥的对外宣传和情报搜集活动,并介绍了当时美国新闻署的实际负责人“破格”参加执委会的由来和实际所发挥的作用。美国新闻署在危机期间的出色表现,一方面推动了美国对新闻署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新闻署在美国官方中的地位。更为难得的是,作者还注意到了古巴危机所造成的美国新闻署与美国之音两大机构之间关系的恶化,不能不说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的专题研究,从情报搜集、宣传攻势等角度展现了这两个机构在危机期间的行动和作用。
本阶段,南开大学的赵学功教授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古巴导弹危机研究领域的专家。2003年赵学功发表了《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成为本阶段的开篇之作。①赵学功:《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第65~72页。随后又陆续发表了他的“军事三部曲”:2007年的《简论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隐蔽行动计划》②赵学功:《简论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隐蔽行动计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0~18页。、2011年的《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军事反应》③赵学功:《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军事反应》,《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10期,第8~15页。以及2013年《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④赵学功:《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97~115页。。他充分利用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展示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所采取的军事措施以及所拟定的紧急作战计划,并探讨了紧急作战计划没有实施的制约性因素。其对危机中美国军事行动计划的研究填补了大陆学界的空白。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赵学功发表《避免战争: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古巴导弹危机》,其中不仅涵盖了以上所说的四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还增加了苏联避免危机升级的内部讨论,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对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双方的分析和研究。⑤赵学功:《避免战争: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古巴导弹危机》,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118页。2017年,赵学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美苏秘密交易问题》中,利用最新解密材料,展现了美苏“导弹交易”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结论,即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并非是美国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而是美苏“导弹交易”的产物。⑥赵学功:《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美苏秘密交易问题》,《历史教学》(高校版)2017年第16期,第62~72页。
本阶段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赵学功的专著《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⑦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目前大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论述散见于许多著作中,专著极少。①主要专著如,李德福《千钧一发:古巴导弹危机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杨存堂《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专著侧重导弹危机始末的记述,缺乏深入解读,对档案材料的使用也不尽如人意。《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充分使用了解密档案,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是目前大陆研究古巴导弹危机的经典之作。相较于之前的研究,这本书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充分使用解密档案材料,资料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②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从美国、苏联和古巴三个国家的角度详细展示了危机的全过程,并论述了危机期间的各种意外事件,研究了苏、古在危机过程中的内部决策,加强了国内研究薄弱之处;③白秀娟:《美苏冷战博弈——柏林危机(1961—1963)与古巴导弹危机的相互影响》,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将研究的范围向后延伸,覆盖到古巴导弹危机的余波。但是,赵学功的部分观点也存在争议。
在古巴导弹危机与柏林危机的关系方面,赵学功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古巴导弹危机与柏林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②。然而,白秀娟③却强烈反对赵学功的看法。她从美苏冷战的背景出发,详细梳理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认为赫鲁晓夫因为柏林谈判失败而在古巴冒险,而美国方面也是担心苏联把柏林危机和导弹危机挂钩,所以才显得十分谨慎。邓志博同意白秀娟的看法,甚至走得更远。④邓志博:《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影响研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他将古巴导弹危机与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相联系,认为欧洲的激烈斗争促使赫鲁晓夫在古巴设置导弹,古巴导弹问题的解决,使美苏在柏林问题和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问题上偃旗息鼓,促使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相互承认。与之不同的是,张盛发既没有否定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完全赞同白秀娟的看法,他综合了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各种诱因,认为,“苏联同美国在欧洲的争夺也对赫鲁晓夫最后决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①张盛发:《试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与决策——写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50周年之际》,《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6期,第57页。。
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学界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已经突破基本档案材料的瓶颈,相关理论的运用以及分析视角的多样化极大地深化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理解。但即便如此,不论是档案运用还是理论分析方面,国内学界都与国外学界有较大的差距。以下将着重梳理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情况。
二、国外研究
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研究力量目前集中在美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学界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具有世界代表性。根据研究成果所展现出的特点,本文将国外的研究历程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传统学派、20世纪70—80年代中期修正学派、20世纪80年代后期—21世纪初期(2003)、2003年至今。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研究的起始期,第三阶段是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期,而第四阶段则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精品迭出期。
(一)第一阶段:传统时期(20世纪60年代)
传统时期因成员不少都曾是政府官员而又被称为“官方学派”,该学派在详细阐述危机时期美国决策过程的同时,积极为美国政府的行为辩护,不少人在90年代承认自己在本时期曾有意美化肯尼迪的形象。
传统学派主要对肯尼迪政府的危机处理持肯定态度,认为肯尼迪的冷静判断和果断决策使美国最终摆脱了危机,这既是肯尼迪事业的巅峰,同时也为以后的决策者树立了典范。同时,传统学派还认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肯尼迪总统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才对古巴实施隔离,而这也是美国的最佳选择。
本阶段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的《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①Graham T.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 little, Brown, 1971.。该著作也是研究古巴导弹危机的经典之作。20多年后,这本书再版,在保留原版大致框架结构的基础上,运用了更多的新材料,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了修改。②Graham T.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2d ed).New York:Longman,1999.该书已发行汉译本,格雷厄姆·艾利森等:《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光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该著作弱化美苏双方的各种价值观念对双方高层决策的影响,假设美苏两国都是普通国家,提出了“理性行为、组织结构、官僚政治”三大决策分析模式,认为缩小美苏在远程战略武器方面的差距、保卫古巴、增加在柏林问题上的筹码是苏联部署导弹的原因。虽然肯尼迪总统在危机中采取了封锁、谈判和最后通牒三合一的行动。但封锁本身并未改变赫鲁晓夫的想法,最终迫使赫鲁晓夫撤出导弹的是美国的强大威慑。因此,美国提升国家安全状态,威胁“空袭或者入侵古巴”,是十分必要的。艾利森在书中所展现的理论分析与史料相结合的框架为进一步研究古巴导弹危机提供了范式,也推动了理性决策模式的发展。
(二)第二阶段:修正时期(20世纪70—80年代中期)
随着赫鲁晓夫回忆录在西方的出版以及美国方面部分材料的公开,学界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更为深入,出现了对传统时期观点的修正,对危机爆发的原因、美国政府决策的过程等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在危机爆发的原因方面,本时期更多将危机的爆发归咎于美国。不少学者认为,肯尼迪是一个“顽固的冷战斗士”,他对古巴的敌视和颠覆政策,将古巴推向了苏联,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而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肯尼迪政府时期,大力发展核力量,并在土耳其部署木星导弹,这些行为打破了美苏之间的核平衡,才迫使赫鲁晓夫冒险在古巴部署导弹。
其次,从危机解决的过程来看,部分学者认为,肯尼迪在发现导弹后,应该秘密联系苏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冲突,而不是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使整个世界处于核灾难的边缘。沃尔顿(Walton)在《冷战与反革命》一书中认为,肯尼迪对危机的做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和冒险的”①Richard J.Walton,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John F.Kennedy.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2, pp.103-104, 141-142.转引自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3页。。同时,伯恩斯坦(Bernstein)在《那一周我们几乎走向战争》中强调了国内政治因素对肯尼迪外交决策的影响,认为肯尼迪确信古巴导弹危机是对其个人信誉的挑战,只有公开对抗、公开的胜利才能使美国民众、盟国以及苏联人看到肯尼迪的果敢和美国的信誉。②Barton Bernstein,The Week We almost Went to War.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76(32),p.17.转引自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4页。
与批评肯尼迪相反,本时期学界对赫鲁晓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赫鲁晓夫没有公开美苏之间的木星导弹交易,冒着损害自己名誉的风险撤出了导弹,拯救世界和平。因此,危机的和平解决要归功于苏联的克制和肯尼迪的运气。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21世纪初(2003)
1987年首届“古巴导弹危机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进入第三阶段。本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使用。
首先,从档案方面来看,最大的突破在美国方面,苏联、古巴则进展有限。
苏联解体前后,苏联方面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档案部分解密,但是这些解密档案不成系统,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苏联国防部、海军、情报等关键部门的档案以及总统档案都没有解密。③Radchenko, 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ssessment of New, and Old,Russian Sourc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26), pp.327-343.后来,虽然通过国际会议、口述史以及国际冷战史项目,在苏联资料方面获得了一些进展,但进展不大。
在古巴方面,虽然卡斯特罗在1992年哈瓦那“古巴导弹危机研究”讨论会上公布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些文件,并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推动了对古巴的研究。①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6页。但是,古巴方面的许多档案仍然处于封闭状态。
相比较而言,本时期美国在档案方面进展最为迅速。从美国方面来看,国务院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文件资料已经公开了80%,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等相关部门的大量文件也相继解密。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肯尼迪卷,包括大量国务院和白宫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有关会议录音带的文字记录,大量而丰富的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的重要文件。②参见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4页。1997年,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两位教授整理出版了《肯尼迪录音带》,汇集了危机期间在内阁会议室和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21次会议的会谈记录。2001年,他们又进一步整理了肯尼迪录音资料,编辑出版了3卷本的《总统记录:约翰·肯尼迪》,其中2卷涉及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会议和会谈记录。③参见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4~5页。199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举行古巴导弹危机学术研讨会,解密了一百多份有关文件。④参见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5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曾在肯尼迪图书馆工作长达二十多年的谢尔登·斯坦(Sheldon Stein)出版了其代表作《转移“最后的失败”:约翰·F.肯尼迪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秘密会议》①Sheldon M.Sten, Averting'the Final Failure': John F.Kennedy and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Meetings.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书中,作者将肯尼迪录音带与其他的口述史资料、文件材料相互映证,资料翔实,成为这本书的关键性意义所在。
在国际交流方面,1987年、1988年、1989年、1992年以及2002年先后在美国、苏联和古巴召开了五次“古巴导弹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苏联和古巴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会议,相互讨论和应证,加强了对危机期间苏联和古巴的认识。
一些学者将这些会议的发言记录整理出版,由此形成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研究的“批评性口述史”。美国学者詹姆斯·布莱特(James G.Blight)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传统的观点认为,美苏双方领导人的克制与冷静避免了核战争。但布莱特在其代表作《破碎的水晶球: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恐惧与改进》中,推翻了传统认知。他运用现象学和“批评性口述史”的方法,从当事人的指认反应中,分析出当事人残存记忆中的恐惧心理,进而认为危机期间,美苏双方的领导人因害怕事态失控所以才抓住各种机会寻求妥协,进而改变了危机原有的发展轨道。②James G.Blight, The Shattered Crystal Ball: Fear and Learning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0.作者对古巴危机期间的恐惧气氛的论述,极具创新和说服力,甚至得到了危机期间执委会成员麦克纳马拉的认可。
除了“批评性史学”之外,本阶段学界还加强了对苏联的研究。雷蒙德·凯瑟夫(Raymond L.Garthoff)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回声》中突出了对苏联动机和决策的研究,凸现了苏联在危机中的经历和获得的教训。③Raymond L.Garthoff,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与此同时,学界再次重新评价双方领导人,怀特(Mark J.White)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传统的观点做出了双重修正,认为古巴导弹危机不仅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冒险政策,也是由于肯尼迪对古巴的敌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对危机的爆发负有责任,同时也对危机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①Mark J.Whit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1996.
除了重视苏联之外,对美国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入,并将新方法和新理论引入其中。尤塔·韦尔兹(Jutta Weldes)的《构建国家利益:美国和古巴导弹危机》被誉为古巴导弹危机研究中“不可绕开的作品”。作者从建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解释了美国领导人为什么认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韦尔兹认为,“苏联侵略”“共产党暴力革命”等话语长期以来在美国被反复重复,从而逐渐变成了常识,再加上“自由世界的守护者”的自我定位,就形成了“虚构的国家安全利益”,成为美国领导人必须消除古巴导弹的动因,而这就是美国“从古巴导弹走向古巴危机的原因”②Jutta Weldes,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四)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
21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档案、材料的解密,以及各种新方法新视角的出现,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为了便于理解,谨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分为对美国以外地区或组织研究和课题方法研究两部分。
1.对美国以外地区或组织研究
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代表性研究体现在苏联、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联合国五个方面。
苏联/俄罗斯方面,2012年谢尔盖·拉德琴科(Sergey Radchenko)发表了《古巴导弹危机:对于俄国新旧材料的评估》,回顾了俄国/苏联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历程。以赫鲁晓夫部署、撤退导弹的原因以及距离核战争有多远为线索,梳理了苏联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领域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史资料。拉德琴科认为,俄国或者苏联档案解密不足,导致了学界多根据碎片化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包括目前关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的考虑等。①Radchenko, 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ssessment of New, and Old,Russian Sourc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26), pp.327-343.
在英国方面,此前的主流是关注危机期间的美英关系以及麦克米伦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作用。近年来,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罗宾·沃尔芬(Robin Woolven)的《对档案与记忆的反思: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是一部类似于回忆录之类的作品。作者是英国皇家空军战略轰炸机的领航员,记述了其在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中所经历的古巴导弹危机,展示了个体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认识和理解,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②Robin Woolven, Reflections on Memory and Archives: RAF Bomber Command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Britain and the World, 2012(5),pp.116-126.与此同时,珍·西顿(Jean Seaton)和罗萨林·休斯(Rosaleen Hughes)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危机期间官方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关系。他们详细论述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BBC的各种相关报道活动,一方面肯定了其报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报道的独立性,表明英国政府在危机初期,对美国的支持并非是全心全意的,而是更多关注美国有没有和盟友磋商以及封锁古巴的合法性。③Rosaleen Hughes and Jean Seaton,The BBC Public Service and Private Worlds: How the Corporation Informed the Public, Related to Government and Understoo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cited from: David Gioe, L.V.Scott and Christopher M Andrew e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 50-Year Retrospective.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4, pp.43-71.
作为美国的盟国,危机期间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美外交政策早已被研究。但这些传统的研究结论遭到了挑战。在加拿大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危机期间加拿大对美国的支持是半心半意的。但2011年,阿萨·麦克切尔(Asa·Mchercher)在《“半心半意的回应?”:加拿大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认为加拿大早在正式的官方声明之前,就私下展开了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此后加拿大官方和民间对美国的支持也进一步加大。①Asa Mchercher, A “ Half-hearted Response?”: Canada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11(33), pp.335-352.然而,卡洛尔·黛戈尔·豪(Carale Daigle Hau)却有不同看法。他在仔细研究了从古巴革命到导弹危机期间加拿大公众对古巴的看法后,认为加拿大民众虽然对古巴印象消极,但是却从团结(solidarity)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立场出发,最终选择在危机期间保持加古外交关系和经贸往来。②Caralee Daigle Hau,Time to Grow Up?Canadian Understandings of Revolutionary Cuba to the Missile Crisis of 1962.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2014(44),pp.82-95.
澳大利亚的传统观点认为,危机期间,澳大利亚孟席斯政府对美国是无条件的高度支持。但2013年劳拉·斯坦利(Laura Stanley)和菲利普·德里(Phillip Deery)在《孟席斯政府,美国盟友与古巴导弹危机》中质疑了这一观点,作者发现,危机期间孟席斯政府的真实反映与其支持美国的公开宣言不同,在支持美国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是勉强的而不是无条件的,是基于国家利益深思熟虑的,而不是条件反射式的支持美国。③Laura Stanley, Phillip Deery, The Menzies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Alliance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2013(59),pp.178-195.
联合国是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的调节人之一,吴丹是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2012年多恩·A.沃尔特(Dorn A.Walter)和波克·罗伯特(Pauk Robert)在《擦肩而过:联合国秘书长如何挪开世界末日》中考察了吴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认为,危机期间吴丹在美国、苏联和古巴三方之间斡旋,并在危机末端,就如何核查导弹运出古巴提出有效的建议。④Dorn A.Walter and Pauk Robert, The Closest Brush: How a UN Secretarygeneral Averted Doomsday.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2(68), pp.79-84.该文的突破在于,不仅使用了新的材料,而且更为公允地肯定了吴丹所发挥的斡旋作用,摒弃对联合国作用的夸大。
2.课题方法研究
21世纪以来,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进一步拓宽和细化,并出现各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主要体现在正统研究、军事情报、社会心理学研究三方面。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档案进一步解密。在各种档案泥沙俱下的情况下,鉴别史料和档案尤为重要。2012年,谢尔登·斯坦(Sheldon Sten)出版《美国记忆中的古巴导弹危机:神话与现实的对抗》①Sheldon M.Ster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American Memory: Myths Versus Reality.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谢尔登凭借其在肯尼迪图书馆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对相关材料的熟悉,在对比和鉴别中指出了《十三天》《肯尼迪》《肯尼迪录音带: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白宫内幕》等著作中所存在的许多错误,重塑了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执委会成员的形象。
除了史料鉴别外,本时期的研究范围也开始拓展。2012年,戴维·科尔曼(David G.Coleman)在其著作《第十四天:肯尼迪总统与古巴导弹危机余波:白宫秘密录音带》中,重点关注古巴导弹危机的余波,将研究时段扩展至1963年2月美苏关系改善之前,并详细阐释了13天危机高潮之后,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对肯尼迪的影响。②David G.Coleman, The Fourteenth day: JFK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 W.W.Norton& Co., 2012.
在科尔曼拓展时间跨度时,也有学者利用新解密的档案细化对危机期间的情报研究。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情报部门在危机期间成效显著。③代表性作品如,Dino A Brugioni and Robert F McCort,Eyeball to Eyeball,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书中作者结合新近解密的材料和自身经历,展现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紧张气氛,着重强调了美国情报组织尤其是航拍情报对于白宫决策的重要性。但这一观点现在已经被学者所批判。①参见 Len Scott, Eyeball to Eyeball: Blinking and Winking, Spyplanes and Secret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26), pp.344-366. 以 及 Len Scott,Macmillan, Kenned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olitical,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Aspects.London: Macmillan, 1999.其中的代表作是大卫·巴雷特(David Barrett)和马克思·霍兰德(Max Holland)的专著《盲照古巴:照片的间隙和导弹危机》②David M.Barrett and Max Holland, Blind over Cuba: the Photo Gap and the Missile Crisis.College Station:Texas A& M Univ Press,2012.。大卫在研究美国侦察机对古巴航拍照片的过程中发现,美国的航空侦查存在盲区。盲区产生是由于1962年9月美国为了减少U-2飞机被古巴击落的概率和外交纠纷,要求侦察机避免飞过已知的古巴导弹发射机基地,这就在事实上绕开了古巴西海岸,留下了侦查照片上的盲区,而恰恰就在此时,苏联开始在古巴部署导弹。此外,中情局和国务院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延迟了美国检测侦查漏洞、发现古巴导弹的时间。而后来,国务院以天气糟糕不适宜于飞机侦查为由,逃避了情报失误责任。在大卫等人看来,这些都是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严重情报失误。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之外,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也成为潮流。
2013年,亚历克斯·吉莱斯皮(Alex Gillespie)在《核边缘政策:一项非语言性交流研究》中,运用“为他者设置舞台”的模式,解释了美苏双方在危机期间的决策过程。③Alex Gillespie, Nuclear Brinkmanship: a Study in Non-linguistic Communication.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Behavioral Science, 2013(47), pp.492-508.而在《末日书信: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中,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与珍妮特·朗(Janet Lang)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展现了1962年危机期间,肯尼迪、赫鲁晓夫、卡斯特罗等人的内心混乱、怀疑、恐惧、愤怒以及自负。④James Blight and Janet Lang, The Armageddon Letters: Kennedy,Khrushchev, Castro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2.同样是关注决策者,大卫·吉布森(David Gibson)从对话实践的角度分析了肯尼迪决策层的动态变化以及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他在《边缘交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审议和决策》中坚持微观社会学的理念,肯定了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对于认知、选择和结果的根本性影响。从这一观念出发,大卫详细解析了肯尼迪录音带,分析了执委会决策过程中的争论和辩护,展现了他们立场的相互影响和彼此挑战。最后,大卫总结说,肯尼迪的决策就产生于决策层的交谈之中,由于事先没有任何既定方案,因此,这次决策实际上就是个人观点和利益纠合的产物。①David R.Gibson, Talk at the Brink: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2.
就在学界主流为研究决策层而各显神通的时候,爱丽丝·乔治(Alice George)关注到了危机期间的普通人,她在《等待末日:美国人怎样面对古巴导弹危机》中,考察了美国公众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应,展示了危机的结束对于肯尼迪威望的重要影响;同时,爱丽丝也注意到了危机后遗症:一方面,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小孩和年轻人,开始出现强烈的逆反心理,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代际冲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认为危机在美国创造了共产主义入侵和核技术不再能保护美国的思潮,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压倒性的无能为力意识。②Alice L George, Awaiting Armageddon: How Americans Face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这既是美国人冷漠面对核战争的原因,同时也是冷战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三、争论不休的问题
随着档案解密以及新方法的出现,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已经迈向成熟。但赫鲁晓夫为什么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土耳其木星导弹问题?危机期间世界距离核战争到底有多近?这三大问题成为学界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关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动机,学界大多采用单一解释模式,在战略核平衡、冷战态势均衡、保卫古巴等观点中争论不休。1987年,战略核平衡成为学界公认的动机。然而,苏联官员的证词很快就挑战了这种舆论一致。其后,学界逐渐远离单一解释模式,主要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有两个动机和目的,首先是为了实现全球战略平衡,其次是为了阻止可预料的美国对古巴的进攻。”①Raymond L.Garthoff, USIntelligence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James G.Blight and David A.Welch(eds.),Intelligence and Cuban Missile Crisis.London: Frank Cass, 1998, p.50.然而,有学者仔细核对了探讨该问题时所使用的材料,发现这些材料的解释力比较脆弱。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
尽管导弹危机以赫鲁晓夫的让步而告终,但肯尼迪所允诺的撤出土耳其木星导弹,这一因素究竟对赫鲁晓夫撤出导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一问题仍在争论中。肯尼迪敢冒着破坏北约盟友关系的风险(指肯尼迪愿意撤出木星导弹),这就证明了他决心避免战争。但是这种决心能够走多远呢?②L.Scott,Should We Stop Study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26), pp.255-266.对此,反事实假设的推论中包含着扑朔迷离的争论:在赫鲁晓夫没有首先后退的情况下,肯尼迪会不会愿意接受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如果肯尼迪愿意接受古巴导弹的存在,那么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风险,甚至这种行为也就不是赌博。
对于许多史学家而言,古巴导弹危机是人类接近核灭绝边缘的时刻。③参见 Don Munton and David A.Welch,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 Concise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那么,当时究竟离核战争有多近?通过运用新材料和反事实假设的方法,学者们越来越强调核灭绝的偶然性和未知风险。这些偶然性主要集中以下两个层面:①决策层的错误认知和错误估算;②核武器运行人员的擅自行动和误会。传统的观点认为,美苏双方高层的克制和谨慎,制止了核战争的爆发。但是,美苏决策层的决策心理研究始终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所出现的各种误会和底层人员的擅自行动都加大了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①相关 代 表 作 如: Michael Dobbs, 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2008.该书已发行汉译本(迈克尔·多布斯:《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陶泽慧、赵进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书中作者通过发现和深度使用美、苏、古等各方材料,对包括U2飞机误入苏联领空等一系列偶然事件进行了细致的说明,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理性地希望避免战争,而真正导致战争可能爆发的是那些意外的“非理性角色”。甚至有学者认为,1962年避免核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幸运。②James G.Blight and Janet M.Lang, The Fog of War: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S.McNamara.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61.因此,加强决策心理研究、深化对各种意外核战争风险的研究成为学界目前关注的热点之一。
古巴导弹危机的学术史,既是发掘档案、坚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历史,也是突破史学框架、多领域研究方法交叉运用的过程;既有宏观建构的奠基,也有微观细致研究的风范。学之为大,经世济怀。继续探究古巴导弹危机既是求知求实的必须,也是以史为鉴、控管核武器的人类福祉所在。学术追求与现实需求的有机结合,这或许是古巴导弹危机研究迈向长远的无穷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