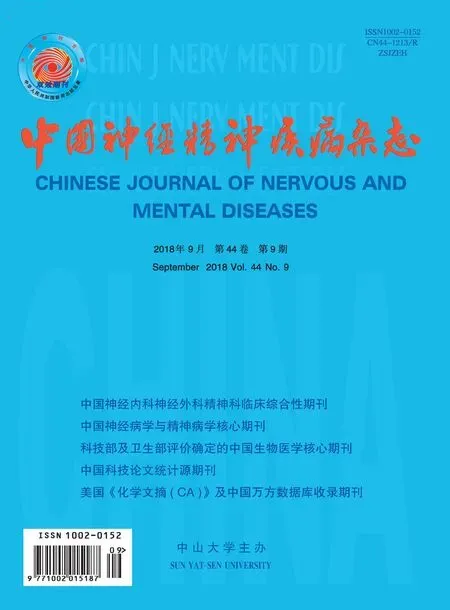老年抑郁症的磁共振成像表现
2018-01-22孔焱蒋常莲叶兰仙
孔焱蒋常莲叶兰仙
基于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WHITEFORD等[1]预测,精神疾病和物质滥用是造成全球范围人类寿命缩短的首要原因。其中,以持久、难以缓解的情绪低落等为特点的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占据着更重要的一部分[2]。抗抑郁药物治疗是目前抑郁症主要治疗手段,虽然能够及时诊断,并且患者也能够坚持配合治疗,但标准化的抗抑郁药物治疗抑郁症患者缓解率也只有30%~40%[3]。 老年抑郁症(late-life depression,LLD)包括早发型老年抑郁症(早期抑郁发作持续至年龄大于60岁或60岁以后抑郁复发)及晚发型老年抑郁症(首次抑郁发作年龄大于60岁)[4]。LLD不仅会增加自杀和痴呆的风险,更会恶化患者本身存在的其他疾病[5-6]。在LLD的诊断及治疗中,神经影像学检查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同时具有巨大的潜力。本文将从结构磁共振(structural MRI,sMRI)和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RI,fMRI)两方面来阐述LLD患者各脑区变化。
1 LLD结构磁共振成像表现
在众多神经影像学技术中,磁共振成像对观察LLD患者神经解剖学的细微改变最为适用。该项检查中大脑暴露在一定频率的磁场,大脑水分子中的质子在磁场中恢复稳定态时会释放出能量,磁共振成像的扫描序列接收这些能量,从而对大脑的解剖学结构进行高分辨的3D重建。T1加权像能够很好地增强大脑灰质和白质的对比;T2加权像则有更好的大脑白质增强;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则通过测量水组织弥散的定向性,评估髓鞘的完整性,再以部分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来量化表示[7]。
1.1 各脑区体积与LLD的关系在许多文献中已有报道,相比于健康对照,无精神症状的LLD患者部分脑区出现广泛性萎缩[8-11]。meta分析也显示相似的结果,其中眶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海马、壳核以及丘脑萎缩最为明显,尾状核的萎缩也呈增加趋势[12]。此外,额叶、边缘系统、基底节以及丘脑也是LLD中很常见的萎缩部位[8]。
在额叶区域,萎缩见于OFC和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9]。 此外, 额前皮质背侧(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及其亚区也存在脑体积萎缩[10]。DISABATO等[9]对126例抑郁症患者研究发现,不论是早发还是晚发的患者,大脑额叶部分(前极、额前回、额中回)以及边缘系统(杏仁核、海马和扣带回前部)的体积均小于对照组。CHANG等[10]和BURKE等[11]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边缘区结构中,海马萎缩最为常见[9,13],而CA1-CA3、齿状回和脑下角等海马子区的萎缩则更为明显[9,11]。
另一方面,脑区体积也和LLD的预后相关,脑区的体积越小,患者预后就越差。TAYLOR等[14]对92例抑郁症患者进行长达2年的标准化药物治疗后发现,与药物治疗后症状缓解的患者相比,无缓解的患者海马体积减小更多,并且海马的萎缩程度和抑郁严重程度呈正比。
1.2 脑区白质高信号与LLD的关系脑白质病变(white matter lesions,WMLs)是一种与年龄、高血压[15]、家族性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紊乱[16]、缺血[17]以及糖尿病[18]等有关的可以反映心血管负担的标志物。这些损伤在T2加权像上显示为脑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WMHs),并且与血管性抑郁有关。
在LLD患者中,脑白质呈现高信号的脑区更多。DALBY等[19]在一项纳入22例抑郁症患者和22名正常对照的研究中发现,与对照相比,LLD患者在左侧纵束上层部分和胼胝体在右侧额叶投影部分的脑白质密度增高,呈现出WMHs。另一项meta分析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脑室周围白质高信号(periventricular WMH,PVWMH)和深层脑白质高信号(deep WMH,DWMH)的发生率分别是正常同龄人的2.15倍和1.92倍,而这个数字在晚发型抑郁症患者中更突出,分别为2.57倍和4.51倍[20]。
按照抑郁症的血管假说,LLD治疗中的低应答性也与WMH有关。BELLA等[21]使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89例抑郁症患者12周后发现,无缓解患者表现出更明显的DWMH。SNEED等[22]使用舍曲林和去甲阿米替林对38例抑郁症患者进行治疗后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1.3 脑白质完整性与LLD的关系DTI通过FA值来量化神经束髓鞘的完整性。FA值减小意味着髓鞘完整性缺损,这些缺损很可能由炎症、免疫或是脑血管因素导致[23]。LLD患者FA值减小可见于额叶皮质和额叶—边缘系统束,包括勾状束[24-25]、丘脑前辐射、纵向束上层[26]和扣带回后部(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PCC)[27]。这些缺损与 LLD 抑郁发作时出现功能紊乱的通路相一致[28]。
ALEXOPOULOS等[29-30]在两项研究中分别纳入48例和13例老年抑郁症患者,结果发现在未经治疗时,SSRI类药物治疗12周后无缓解的患者与有缓解的患者相比,脑白质FA值减小,具有特征性的区域包括ACC喙部和背部、dLPFC、胼胝体膝部、海马旁回白质、扣带回后部皮层白质以及岛叶白质。然而,随后TAYLOR等[31]的研究得到相反结果,该研究纳入74例LLD患者,尤其是在未经治疗的状态下,无缓解的患者在中央前回上部及ACC中出现高FA值。对这一结果最可能的解释是TAYLOR等[31]在选择感兴趣区时避开了WMH的区域,而ALEXOPOULOS等[29-30]则没有避开这些区域,WMH区域与白质信号正常的区域相比,FA值更低[32]。
2 LLD功能磁共振成像表现
fMRI可以及时识别药物的反应[33],并能够在早期预测药物治疗的效果(最早可以在药物开始起效时)。fMRI进一步可以分为任务态和静息态fMRI。任务态fMRI是采用血氧水平依赖(blood-oxygen level dependent,BOLD)信 号来识别突触活动增加的区域,在预先设定好的任务中,BOLD信号增加的区域被认为与任务执行有功能上的关联。同时,任务态fMRI还可以识别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的区域,如果不同脑区在活动上显示出短暂的同步性,则这些脑区间有功能连接。而静息态fMRI则与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一样,可以评估静息态脑网络的活动和FC。
2.1 静息态fMRI与LLD的关系静息态fMRI能够强化LLD患者DMN和认知控制网络(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CCN)中的改变[34]。ALEXOPOULOS等[35]在研究中纳入 16例LLD患者和10名正常对照,LLD患者经过12周的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与正常对照相比,CNN在静息态时显示出低FC,而DMN则显示出高FC,而静息态下 CNN的低 FC则预示着对治疗抵抗。
另一项ANDREESCU等[36]的研究探讨了DMN的FC预测治疗抵抗可能方式。尤其与最终治疗有效的患者相比,治疗无效的患者在12周抗抑郁药物治疗之前,其PCC和前扣带回背侧(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dACC)以及楔状叶之间的FC增加,而PCC和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PFC)中部以及楔前叶之间的FC减少[36]。
2.2 任务态fMRI与LLD的关系任务态fMRI是对静息态fMRI的进一步完善。AIZENSTEIN等[37]在研究中使用对CNN更为详细的任务模式,发现与正常对照相比,LLD患者dLPFC的活动减少,dLPFC和dACC之间的FC则更少。任务态fMRI还可以用于探索LLD患者脑血管病理学改变和大脑功能活动的联系。例如在情感反应的背景下,WMH与边缘系统的超活化有关[38]。
AIZENSTEIN等[37]认为 PFC的任务态fMRI对于预测治疗效果具有潜在作用。在该研究中,使用SSRI类药物治疗之前,13例LLD患者在任务态fMRI下dLPFC的活动与对照组相比有减少,而经过12周的SSRI类药物治疗后,患者的症状均有所改善。BRASSEN等[39]也在相似的药物治疗研究中发现PFC的任务态fMRI在预测方面具有潜在功能。总的来说,任务态fMRI的研究表明,LLD与PFC的活动减少有关,这种PFC活动减少可以减弱边缘系统的抑制作用[39-40]。此外,使PFC的超活化变为“正常化”也与治疗应答相关。目前疗效预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情绪调节环路,较少涉及奖赏神经环路,前额叶、扣带回、杏仁核及海马在疗效预测中具有重要作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讨奖赏神经环路对抗抑郁药物疗效预测的作用,采用多模态的磁共振成像方法来检测相关抑郁症神经环路以及能够预测疗效的脑结构和功能[41]。
3 总结
LLD相关的神经影像学在临床使用方面还需要更多研究。而最具有潜力的应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制定最好的初始治疗方案——LLD由多种致病机制累积作用,这些神经影像学的应用也许能识别不同药物治疗下,在结构和功能上与药物治疗时机体应答模式可能相关的生物标记物,以帮助对患者个体化最佳治疗模式的选择;②优化抗抑郁药物初始剂量——fMRI可以在几秒内识别大脑的相应变化[33],如此,在首次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后的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就可以通过fMRI来识别达到最优治疗时的神经影像学标志物;③药物疗效的早期干预——对于sMRI和fMRI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将这些神经影像学技术转化为临床应用,从而获得LLD患者脑部发生特征性病理改变的部位,制作患者个体化的“脑部地图”,并在治疗开始后再次扫描,寻找“脑部地图”中发生变化的部位,则可以在治疗早期预测疗效。
由于磁共振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LLD患者脑部的结构与功能方面变化,LLD患者脑部的病理变化也更为直观。但研究过程影响因素众多,现有技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人脑又是机体中最为复杂和神秘的器官,不是单用机器就可以完全探究其中的规律,此外,不同的仪器、环境等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目前研究还不能作为LLD诊断和治疗的直接证据,仍然需要结合多方面资料进一步探索。但也许将来通过技术发展,可以找到诊断LLD的生物学 “金标准”。相信今后会有更加完善的研究,为LLD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