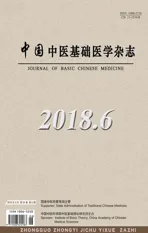中医隐喻思维规律刍议❋
2018-01-22石勇
石 勇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00)
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1],中医独特的认知方式通过西方认知隐喻理论进行诠释和解读,形成中医隐喻思维,即以体验哲学为指导,以“天人相应”为逻辑原点,以取象比类为核心方法论,对接阴阳五行思维逻辑,对人体、疾病、健康进行描述,进而寻求疾病辨证论治、指导养生之道的复杂认知活动[2]。中医隐喻思维串联中国传统哲学和医学中诸多概念,涵盖中医象思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整合中医理论中的点线交织、动静结合、理论与实践对接、知识传承与理论创新并举等问题。
1 中医隐喻思维:经验与认知
隐喻是理解人类经验的一条重要途径。Lakoff[3]认为,意义是生命经验的产物,它直接建立于“人类经验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共同的经验性基底自动发挥认知作用。中医概念的形成和拓展无法脱离共同的经验性基底,并始终与普遍的感知层次相融洽。因此,作为建构中医核心概念的隐喻能够被中医共同体理解和接受,并纳入中医知识体系恒久而弥坚。
《周髀算经》曰:“知地者智,知天者圣。”在认知水平相对局限的时代,抽象思维依赖对天地的认知,这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崇尚的“天人相应”和“取象比类”暗合。《内经》的作者们将人体比附自然,将五脏六腑与日月、星辰、山川、四季等对应,一方面体现了高超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折射出特定实践环境下的共同经验基底,即对生命现象的认知囿于对自然中“天之气”“地之形”“日月星辰”的认识,诉诸取象比类。中医学许多概念和理论通过这一共同经验基底展开并形成知识,而隐喻思维在知识与映射、猜想与临床、规约与创新间架设桥梁,促发具有通约性的主体间性,为中医学共同体成员之间、中医与其他学科之间、中医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有效途径。
2 中医隐喻思维:局限、批判、合理
2.1 中医象思维的“概念”性
概念思维是把事物的一切可感形象抽调后得到的反映事物内在本质的思维形式[4],西方医学基于概念思维,采用确切内涵和明晰外延界定人体和疾病的本质属性和规律,即许多中医批评者强调的“科学性”,并以此为参照衍生出旷日持久的中医科学与非科学论战。中医象思维有别于概念思维,这可从中医之“象”的特征推知:中医之“象”是具有不同形态的信息态存在[5],可分为客观事物表现于外的形象、人工符号对客观事物进行模拟标示的象、如同阴阳五行和道一般的抽象之象[6]。这种根据抽象度高低而构成的“象”的连续统姑且可以算作是中医思维的“概念”形式,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此“概念”非彼概念(概念思维所言的概念),此“概念”无法直接定义客观事物(特别是人体)的本质属性,而只能对客观事物(包括人体生命活动、生理病理等)外在征象进行模拟、反映和概括。任秀珍[7]生动地将其称为“带象的观念”,即在保留事物形象的状态下,反映事物的本质。如《内经》中出现许多诸如“君主之官”“相傅之官”“将军之官”等以象论脏的描述,建立了人体内部的“君主”“相傅”“将军”等形象,揭示了其对应脏腑在体内的功能。中医象思维的概念性局限只是针对概念思维而言,虽有局限即不能准确地“把握理”,但它兼具理性思维元素和非理性思维元素的特征,不仅能反映静态物状,更能在时空维度下反映人体生理活动和生命现象动态化特征,从而全面“把握物”。采用这种方式对事物本质进行描摹是概念思维无法比拟的。
2.2 取象比类的方法论局限与实质
取象比类以“象”为媒介,基于事物相似,勾连彼此,寻求类比,实现“应象”。这在探寻未知的道路上具有其他思维方式无法比拟的推动作用。但受限于事物间差异性羁绊和认知水平局限,取象比类很难从本质上把握未知事物,如果忽视这两方面的限制而展开推理,其结论必然是模糊、不严密的,其方法论缺陷也会因此被无限放大而遭受批判。如《灵枢·邪客》中:“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精彩地描述了自然与人体互参,这与逻辑学上的类比推理很相似,即基于天地与人体某些方面的相应,最大限度地类推到其他方面,但要作为认知人体结构和察病观色的准绳,未免太过随意和牵强,这既有认知水平、方法和手段的原因,又有过分凸显相似性而忽视差异性的局限,因此,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这样的互参描述被大众揶揄,显然无法取得公众对中医理论的信服。事实上,二者虽有相似但本质有别。类比推理是一种主观或然的不充分似真推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或然性。而取象比类的主要功能在于说明某一类事物的共同性质,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的抽象思维过程[8],体现为一种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并举的思维形态。其一,取象比类通过隐喻映射的方式反映事物的本质,是对既定事实的描述,并没有新质事物的产生,因此不同于类比推理。其二,取象比类的演绎推导强调由此及彼的本质性追问过程,而不是结果。相比之下,类比推理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其结论是一次性完成的,缺乏实践性检验。中医之所以传承沿用至今、长盛不衰,是因为中医取象比类的知识映射具有反复性,其中有证据匮乏的主观猜测,也不乏证据充足的理性判断,但其正确性与合理性始终面临严格的实践拷问,体现为“取象”到“比类”思维路径上不断重复、不断深化的心智加工过程。
2.3 中医隐喻思维的合理性评判
中医思维通过隐喻的方式对其理论进行解释和说明,其有效性体现在中医隐喻在把握实在对象方面的综合性考察,仅仅用“科学”的名义、理性的标准评判其合理与不合理,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中医隐喻作为一种方法论,其运用虽不能覆盖中医理论描述和阐释的方方面面,但是它的存在对讲究整体性、辨证性、实效性的中医学来说,绝对是不可规避的。任何理论和语言都不是一个始源域匹配一个目标域的封闭隐喻系统,几乎所有情况都是以一配多或者以多配一的不规则隐喻体系。如《内经》的作者们在著书立说过程中,基于不同的意象展开丰富多彩的隐喻谋划,其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始源域对目标域描述的清晰度和适切性。但无论思考维度多么天马行空,他们对中医理论的立论和论证始终围绕着天人相应展开能喻与所喻的设定,始终将阴阳五行整全式框架作为支配中医思维正常运转的基本逻辑,这是中医隐喻思维的最大特色。在天人相应和阴阳五行语境下,中医隐喻思维将概念构造置于特定的坐标体系中,促使相关的中医学概念在特定语境所营造的广阔范围和视角下被描述、被解释、被运用,并通过对隐喻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比较、验证、扬弃,进一步将合理的隐喻具体化、固着化,并不断丰满完善,这体现为中医隐喻思维与临床实践的有效衔接,以临床为前提,通过隐喻推理提出理论假设并展开临床检验。基于临床又回归临床,这是检验中医理论合理性的必由之路。衔接临床与临床之间的接口便是中医隐喻思维,以此方式形成的结论毋庸置疑具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其一是在临床实践中被淘汰,其二是在严苛的医学实践中被证实而保存,并成为下一步隐喻推理的知识储备,驱动中医理论不断完善与发展。
3 中医隐喻思维:实体与过程
中医象思维若以实体本位为主导,虽能形象生动地描述医理和命理,但在中医理论诸多方面的解释力缺失和推导性缺陷成为中医理论身陷囹圄的根源。近代以来,中医批判大多基于实体本位看中医,其眼界显然无法覆盖中医的本真面目,“窥一斑”未必能“见全豹”,但基于“一斑”而攻击中医存在的理由,否定中医发展的基础,显然是对中医不公正的对待。因此,打破实体本位思维在象思维中的垄断地位,用过程本位弥补实体本位的不足,用自然动象阐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才能更加清晰全面地解读中医理论,这也更加符合中医理论动生造化的理念[9]。过程本位思维强调对人体的宏观把握,强调脏腑功能与疾病变化、时空运转的圆机照应,如“经络”“三焦”“命门”等没有对应脏腑实体的中医学谜团便可以迎刃而解。同时,当过程本位不依赖于位素的开放性特长得到凸显,动态变化的主体和客体也因此由封闭转为开放,过程的类型便可以百花齐放、海纳百川,可以是(五行)生克关系,也可以是(五脏)濡养和抑制,可以是(事物间)促进和阻挠,也可以是(发展中)“推波助澜”和“从中作梗”等,这样一来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取象比类的推导作用,为“取”与“比”提供无限的畅想空间。如从五材到五行,将现实中的5种材质抽象为5种特性,五行学说因此摆脱了“实体之物”的束缚,再从五行到过程将5种特性之间的关系抽象化为过程性存在,从而进一步解放了5种特性,使五行从真正意义上摆脱了“物性制约”,打开了具有循环论倾向的五行封闭式谜团,迎来了动象本体思维的开放与灵活,大量的医学事实、成果、假设被纳入到过程体系中进行考量,凸显了五行思想最精华的东西。
4 中医隐喻思维:发展与创新
宇宙世界的普遍联系、经验的主客体关联、可认识性假设、意义的溢出和延展,促使人类与未知世界不断地接轨,从而创造相似并形成“可能性隐喻”。自然之象与人体之象因共同的过程特性而具备无限的转换生成可能,促使隐喻思维机制在医学认知精进的实践道路上不断“出场”,将形态、方位、关联、变化精妙地融合起来,通过不同场景交换和语境转换实现隐喻意义的超越,不断改变审视人体内外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刷新业已存在的思维积淀,为中医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无限畅想空间。中医隐喻创生的效度、深度、广度,不仅可以通过可分析性维度进行把握,还体现在创生与临床的张力之间,中医辨证论治和整体思维模式提升了这个张力的弹性空间及其空间的有效性效度。任何科学隐喻都是始于佯谬,在试验的驱动下通过规约化的过程,被某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接受认同,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科学范式。在医学现代化的感召下,中医隐喻思维的开放性特质可以防止理论范畴的僵化,隐喻思维链接不同语境的强大能力,又促进了中医知识与其他各学科之间敞开交流与互动的窗口。鉴于此,中医隐喻思维可以创生各种新的假设和理性洞察,利用中医之“象”的特性,解构宇宙物性和动性中的各种尚未挖掘的界限与鸿沟,由此架构可察对象与不可察对象之间的桥梁,从而缩小当下(权益性)认知与真理(永恒)认知之间的距离。因此,有学者[10]提出“观察-归纳思维”的回归模式,强调运用现代化医学手段的调研,为不断验证中医理论提供参考,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有效归纳。在探索生命和疾病规律诸多未知世界的过程中,中医隐喻思维无疑具有强烈的利导作用,对于确定的知识体系可以提供完备的描述方案,对探索未知提供有说服力的参考,创生性对于规约的超越正是对于已有思维空间的突破甚至是革命,在破与立之间,中医理论早已破除了经验医学的枯燥与呆板。
5 结语
中医隐喻思维在古代有限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医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从事物的功能性、整体性、动态性角度出发,宏观认识人体结构,辩证寻究生命奥秘。人类进入21世纪已近20年,提倡科学施治,在先进的科学仪器辅助下,对脏腑功能和疾病规律的认识越来越彰明昭著,中医思维方式如若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将很难掩饰其理性缺失。因此,在时代浪潮中追求嬗变才是生存之道,除了“实践”这一泛化方法论取向,更要实现逻辑思辨基底的深刻变革。中医的发展必须仰仗思维方式的更新,中医隐喻思维的相关研究成果便可以为中医思维方式的更新开启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