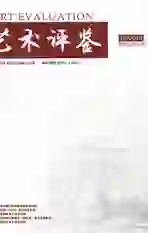汉代乐舞动态遗存研究
2018-01-19相宁
相宁
摘要:以汉代墓葬祠堂出土的画像石(砖)、陶俑、玉器、青铜器等为载体的汉代乐舞静态遗存为世人熟知,而民间舞蹈、地方戏曲、民俗祭祀等活动中的乐舞动态遗存,世人却了解甚少。本文以徐州地区的汉代乐舞动态遗存为例,从汉代乐舞的动态遗存、遗存方式论证及动态遗存的主要特征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阐述,以期推动汉代乐舞遗存资料更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关键词:徐州汉代乐舞 动态遗存 动态遗存方式 动态遗存特征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20-0079-03
汉代乐舞丰富的乐舞艺术形象,除了以世人熟知的汉代墓葬祠堂出土的画像石(砖)、陶俑、玉器、青铜器等静态形象遗存外,民间舞蹈、地方戏曲、民俗祭祀等活动中的动态乐舞形象也是其重要的遗存方式。汉代乐舞的动态与静态遗存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同样是我们了解汉代乐舞的主要途径和依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徐州是古代楚汉文化中心、汉文化的集萃地和发祥地,徐州地区汉代乐舞在传承炎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独具时代特征和鲜明本土色彩,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等众多领域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一、汉代乐舞动态遗存
事实证明,舞蹈这门古老艺术的历史遗存形式,一种是以出土文物或文献资料为依据的静态遗存方式,一种则是融于其它艺术种类之中的动态遗存方式。对于汉代乐舞而言,如果说汉代墓葬祠堂出土的画像石(砖)、陶俑、玉器、青铜器及文献资料是汉代乐舞形象静态遗存的载体,那么融于民间舞蹈、地方戏曲、民俗祭祀、武术杂技等活动形式中汉代乐舞的遗存,可以说是汉代乐舞的动态遗存形式了。
孙颖先生编创的汉代舞蹈作品《铜雀伎》中,就采用了今天流行于江苏北部邗江、江都一带的“花香鼓舞”的舞蹈动作元素,通过实践证明了汉代乐舞在民间舞蹈中的动态遗存。
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在击败英布得胜还军途中,返回自己的故乡沛县(今属江苏省徐州),与乡亲共同欢饮十数日。酒酣情至,刘邦一面击筑,一面唱着自己即兴创作的《大风歌》,“慷慨起舞,伤怀泣下”(《汉书·高帝纪》)。以汉高祖刘邦《大风歌》为精神特征的“楚汉文化”,赋予徐州地区独特的文化秉性,成为徐州地方文化的个性内核。徐州地区现已挖掘整理了包括睢宁“落子舞”“云牌舞”、邳州“跑竹马”、沛县“荷叶落子”、舞龙、舞狮等102种民间舞蹈,梆子戏、柳琴戏、徽剧、京剧、花鼓戏、丁丁腔等众多地方戏曲艺术和一些民俗、祭祀活动。这些民间舞蹈、地方戏曲及民俗祭祀活动,不仅是文字记载的几百年历史,更是千年文化的孕育,为徐州地区汉代乐舞动态遗存提供了佐证和线索。
二、动态遗存方式
(一)民间舞蹈
徐州地区民间舞蹈资源丰富,朴拙的民风、雄豪的个性形成了徐州民间舞蹈舒展雄肆的艺术风格。以睢宁“落子舞”为代表的徐州民间舞蹈延续着汉代以来中国乐舞的血脉,承载着苏北地区从古至今的历史信息,展现了徐州地区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和美好愿望,是千年大汉民族血脉之相传,生命之延续。
据文字记录,“落子舞”是明嘉靖年间流传于睢古邳一带。清康熙35年,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描绘徐州“霸王鞭”:“徐沛伎妇,以竹鞭缀金钱,击之节歌,其曲名《叠断桥》,甚动听。行每覆蓝帕,作首妆,其诗曰:‘窄样青衫称细腰,蔚蓝手帕髻云飘,霸王鞭舞金钱落,恼乱徐州叠断桥”。“霸王”是对楚国名将项羽的称谓,秦亡后项羽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世称“西楚霸王”,而诗中所说“霸王鞭”,便是今天的“落子舞”。“霸王鞭”是“落子舞”的主要道具之一,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推测,这种舞蹈道具是“西楚霸王”项羽曾用过的一种武器或是与之相似的一种器械,舞蹈从命名上就被赋与了深厚的汉文化气息。另外,传统“落子舞”的表演动作中,既有高难度的虎跳翻身、单双扫腿等;也有韵味浓厚的骜子翻身、白鹤亮翅等形象化动作,其中男演员表演的“大翻小翻”,与汉画像中的形象十分相像,是乐舞类汉画像中“飞檐倒立”动作的延续。
(二)地方戏曲
戏在民间,徐州历来被称为“曲艺之乡”,剧艺表演源远流长。受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徐州地区的剧艺表演形式繁多,地方戏曲地域特色鲜明,有着强烈的本土特征。
“梆子戏”是徐州戏曲艺术的代表剧种之一,历史悠长。传统戏曲表演具有“精”“险”“奇”等特点,在表演形式上吸收了武术、杂技和魔术等元素,如爬竿、滚棚、吊辫、风摆荷叶、高台颠米等。表演时会爬上十几米的竿子,做各种难度和技巧性很高的动作,这与汉画像石(砖)中“百戏”动作十分相似。特别是旧时徐州“梆子戏”班中,常有一种用在正戏开场及唱敬神戏、还愿戏之前,戴着假面称之为“跳加官”的哑剧节目,这种表演由演员着青相貂、红蟒、玉围带,足蹬粉靴,手端牙笏,嘴咬假面,在鼓乐声中表演各种象征性动作。这种寓意逐凶趋祥的“跳加官”表演,显然是从古代的“大傩”发展而来的,是徐州汉画像中“傩舞”在“梆子戏”中活态遗存的有力佐证。
(三)祭祀活动及地方民俗
随着王朝的更替与灭亡,汉代乐舞从宫廷流入民间,广阔民间成为汉代樂舞传承的丰富土壤,特别是各地传统的年节庆典、婚丧仪礼、祭祀仪式等民俗活动,为汉代乐舞提供了广阔的传承空间,为它的表演内容提供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据《睢宁县志》载,睢宁县“龙虎斗”源于明朝,属祈雨祭龙的祭祀性舞蹈。“龙虎斗”的起源与发生地的典型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睢宁古属下邳,当地百姓曾称刘邦为“天龙”,项羽为“地虎”,龙虎相遇自是一场恶斗。于是,每次战事之后,当地百姓便会跳起“龙虎斗”,以祈求不再发生战事,渴望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睢宁“龙虎斗”共十二人,舞龙九人,舞虎二人,镇虎一人。舞蹈形象逼真,技巧高超,与徐州地区出土的“鱼龙漫衍”“羽人戏虎”类汉画像中的形象及动作十分相似。
(四)武术、杂技
徐州尚武精神源远流长,这种尚武传统在徐州地区出土的“比武”类汉画像石(砖)中得到印证。“鸿门宴”上,谋士范增命项庄宴前舞剑借机刺殺刘邦。项庄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史记·项羽本纪》)。这里的“剑”并不单纯是搏杀的武器,而是作为舞蹈道具来使用,具有双重功能,可见徐州地区“以武作舞”的历史由来已久。
沛县素有“武术之乡”之称,“枪刀剑戟戈,斧钺钩叉棍”都是沛县武术训练时使用的武器。这些器械与徐州出土的“比武”类汉画像石(砖)中使用的器械非常相似,武术属世代传承,项庄“请以剑舞”正是汉代乐舞在武术中动态遗存的极好佐证。另外,杂技表演是徐州地区许多民间舞蹈的动作特点,特别是邳州“竹马舞”,女舞者在竹马背上倒立、抢鞭、踹燕、探海等舞蹈动作,充分体现了徐州地区民间舞蹈与炫技性武术、杂技等高难度动作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独特艺术风格。舞蹈动作惊悚悬念,虎虎生风,与“百戏”类汉画像中的“杂耍”特别相似。
三、动态遗存特征
(一)四维动态性
二维平面图像,有左右、上下四个方向,不存在前后,即只有平面,没有立体。四维图像则能够实时地观察其立体结构,可直观、立体的显示人体的三维结构及动态。汉代出土文物中的乐舞形象以静态的形式遗存于某些载体之中,可以看作是一种二维图像,在后人从静态转化为动态继承的过程中,从一个静止动作到另一个静止动作,需要我们多方面的资料去进行合理连接,使之开成流动的舞蹈语汇,否则就成了僵硬的乐舞造型摆放。而动态遗存的四维性,则可以直接选取其舞蹈动作元素,舞姿更具流动性、更立体。
(二)文化特征相对稳定性
动态遗存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在不同方面汲取了众多姊妹艺术的精华,但不论如何兼收并蓄,其主流文化内涵在传承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改变,千百年传承的主流文化特征及个性内涵不会改变,地方个性文化特征也被当地人传承和保护,这种对先人文化的传承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换和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动态遗存依附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间活动之中,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地方特征。
(三)继承的多样性
传统文化在世代相传中保留着基本特征,同时,它的内容和形式又因时而变。为了顺应时代的更替与社会的发展,舞蹈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借鉴和融合其它姊妹艺术,如睢宁的“落子舞”就是吸收了邳州落子、安徽落子的一些动作特征,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舞蹈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进行着纵向与横向的传承和融合,因此其动态遗存不会像静态遗存一般固定停留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四)环境的影响性
在娱乐形式匮乏的旧社会,人们最常见的消遣娱乐方式就是乐舞,乐舞出现在娱乐、祭祀、婚丧嫁娶、节庆民俗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社会功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及多元文化的渗透,人们在文化生活、娱乐方面有了更多形式的选择,因而与这些民间乐舞及民俗活动等相适应的原始生存环境在慢慢消失,一些民间乐舞及祭祀、民俗活动也就与我们渐行渐远,有的甚至完全消失。如徐州地区的民间舞蹈经20世纪80年代统计有102种,但今天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并传承下来的并不多;徐州地区的祭祀、民俗活动也有许多也已消失不见,如徐州地区著名的云龙山庙会,早已不复当年的热闹情景。
(五)文化继承的连续性
从秦统一六国到楚汉战争,直至汉王朝的建立,再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进入新社会,中间虽经历朝代的更替和社会的发展,甚至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文化浩劫”,但中华文化始终在民族发展中得以传承和发扬,动态传承中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也并未因时代的发展而中断。
(六)鲜明的地域性
各地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地域、人文、历史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各自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主流文化,如徐州的汉文化、北京的明清文化、西安的唐文化。在此主流文化的大背景下,又产生了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具有各地主流文化特色的艺术种类,历史的发展为地方文化烙上了不同的印记,动态传承伴随着这种深深的文化烙印世代传承,即便受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这种鲜明的地域特征也不会改变。
四、结语
动态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可以填补静态遗存的不足,是对静态遗存的补充,是汉代乐舞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遗存方式。动态遗存的乐舞动作更具知性,乐舞动作元素更具象、流动,形象也更丰满,是更为具象的活态呈现。相较于当前汉代乐舞静态遗存研究的硕果累累,汉代乐舞动态遗存研究成果则显太少,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民间传承的艺术形式和种类在逐渐减少甚至消亡,因而对民间活动中汉代乐舞动态遗存资料的挖掘、整理尤显迫切与重要。汉代乐舞的动态遗存,为我们更好、更深入地发掘和研究汉代乐舞开拓了更多的途径,提供了更大的探知空间。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苏卷(上)[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0.
[2]丁洁.浅析睢宁民间舞蹈[J].大众文艺,2011,(11).
[3]刘克.汉画图像叙事中的民俗功能和人文精神考察[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
[4]赵咏维.徐州汉画像石(砖)与中国戏曲[J].东南文化,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