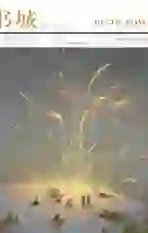《北京学林旧话》续谈
2018-01-18李村
李村
牟润孙先生在《北京学林旧话》里,提到他藏有一部石印本钱玄同墨迹,内中收录的是钱先生给魏建功的信。其中一封,是商量给顾颉刚的父亲祝寿:“天行兄:顾颉刚封翁之寿礼,我想最好的确还是以送寿屏为当,而且最好还是请仲澐(即范文澜)撰文,弟当尽写字之责。请与仲澐商之。送的人,则范、魏、马九、钱四人为已知者。此外如有欲加入者,当然更好。”收在这封信后面的,就是钱先生所写的寿屏样稿;样稿为荣宝斋制,共十二幅。在末尾署名的有钱玄同、魏建功、范文澜、马廉、马幼渔、马衡、董作宾、刘半农、钱稻孙、徐炳昶、周作人、陈垣、沈兼士、吴肇麟诸先生,共十四位。
牟先生在写这篇文章时,《顾颉刚日记》还没有出版。他根据寿序里“今年春,颉刚自粤北来”一句,断定信写于一九二九年。从而有了很深的感慨,说当年顾先生重返北平、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而这些在寿序上署名的,很多是顾先生的老师辈。他们在学界都德高望重,又不认识顾先生的父亲,愿意联名为顾先生的父亲祝寿,这种超乎常情的礼数,足以“反映出顾先生露头角之早,在学术界地位之高了”。
牟先生的说法当然不错。不过《顾颉刚日记》出版后,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面。那就是他离开北平这三年,北平学界的变化很大。许多“旧日师友”对他回北平来燕京大学执教,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原因是他以《古史辨》成名后,虽然在史学界备受瞩目,但盛名之下也树立了许多敌人。三年来饱受攻讦,不断为流言所苦。洪业曾就他当时的境况,替他做过分析和总结,说:“许多人反对你,有三故,为胡适之弟子,反胡者即反顾,一也。你自己的怨家,如鲁迅等,常为你宣传,二也。在学问上,你自己打出一条新路,给人以不快,三也。”
因此,他这次回北平,从一开始就遭到抵制。从《顾颉刚日记》中看,他“回京之计早决”,“南行两年,魂梦常系于此”。尤其是在广州与鲁迅发生冲突后,更希望早一天回北平,使生活安定下来。所以当容庚告诉他,司徒雷登在美国获得二百万捐款,拟在燕大办一所国学研究所,想请他去做研究,他立刻表示“极愿就”。以其“在北京,一也。生活安定,二也”。他还特意嘱咐容庚,“此事请兄暂守秘密,勿告京中同人,免得引起敌派之排挤与挑拨”。
想不到他还没离开广州,就陆续听到对他不利的消息。王伯祥告诉他“北平方面”知道他要去,正在为他“铸造空气”,想办法来对付他;卫聚贤更明确说,马叔平(即马衡)对他“返北平一事极不欢迎”。这都让他对今后何去何从又犹豫起来,决定先向中大请假,“到北平后看情形再定”。果然,他一回到北平,就发现有些人很不欢迎他。五月十五日,他在容庚家“吃夜饭”,容庚和郭绍虞告诉他,国文系主任马季明正在燕大破坏他,周作人也“不赞成他去”。有些人听说他这次返北平“志在燕大”,“近又钻营清华”,还相互警告说,他“是到一处闹一处的,你不要喜欢,同你闹散的日子不远呢”。
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他回北平不久,正忙着给父亲作六十大寿时,又遇上鲁迅回北平省亲。众所周知,鲁迅与顾颉刚有过节。顾自己也说,“愿此生数十年中,不再遇鲁迅先生其人也”。而结果却冤家路窄,在北平又不期而遇。這势必使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重新成为北平学界的话题。
从《顾颉刚日记》看,鲁迅离开北平后,他明显感觉到周围的变化。尤其是鲁迅在燕大演讲时,为了打击燕大的研究系势力,“从成仿吾骂到徐志摩”,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据说有些学生正蠢蠢欲动,在校内酝酿风潮,要求校方聘请鲁迅来学校执教。而这已经引起一些人的恐慌,如果真的演变成事实,岂不是一切都要重演,燕大又成了中大?这让他对今后是否留在北平,更加犹豫不决;一度考虑“半年来平,半年去粤”,不成“则回苏州矣”。以致六月十二日,郭绍虞告诉他“燕京职事已通过”后,容庚反而劝他尽早回广州,“盖懼我复南行,为此激我作一决绝之论也”。
他下决心来燕大后,对今后的生活很有期望。希望能从此脱离干扰,专心研究,将生活安定下来。从而在给胡适的信里,将事情看得非常乐观。说他到了燕大以后,可以“生活上比较安定,校中固有党派,但我毫无事权,且除上课外终日闭门不出,人家也打不到我身上”。“这种超然的生活”,是“研究学问的理想境界”。他还急着花三天时间,将离开北平时存放在大石作的书,全部搬运到成府胡同燕大宿舍,准备“闭户数年,学业必大成”。
可是事实却不尽如愿。一年前,容庚告诉他燕大考虑成立国学研究所时,他曾以“这两年的经验”,在用人问题上提了七条建议。其中的二条是,一、“不引进学阀,免致学术机关为其私人垄断”;二、“不引进复古派,免致学术不能照了轨道走”。然而燕大虽然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校长吴雷川却出身翰林,是个守旧的官僚。国学研究所成立后,他以臭味相投,拉拢来许多旧派人物。这些人对他推翻古史,在史学界掀起的革命早就十分反感,宣称“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如此妄人!”现在知道他来燕大了,更如临大敌。因此他来燕大不久,洪业就告诉他,学校在商量聘请学侣时,他提议请他做第二名学侣,结果遭到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反对—“学校里反对他的人这样多,恐不便。”他这才恍若大悟,知道“反对我的声音不但传在中国人的耳里,亦传至外国人耳里”。
而更让他苦恼的,是他接手《燕京学报》后,又和陈垣发生了不快。陈垣曾任教育部次长,辅仁大学副校长,燕大国学研究所成立后,又被聘为研究所所长。他在来燕大之前,本来与陈垣关系很好;因为张亮尘的关系,彼此还很有亲近感。可是他来燕大后,发现陈垣“近年太受人捧,日益骄傲”,其“声音颜色,直拒人千里之外”,俨然在以学阀自居。而他若不接手《燕京学报》,或可以对陈垣敬而远之,“现在编《燕京学报》,便不能不与之接触,每见辄感不快”。尤其是每期学报出版后,陈垣总要在稿费上挑剔一番,似乎“非此不足以表示其所长之地位”,这更让他难以忍受。几次痛下决心,“决定明年摆脱矣”。
当然,这些都是小事。最让他难以应付的是,他决定来燕大后,陈大齐出任北大校长,几次请他回北大任教,都被他“婉词拒之”。这让很多人产生误解,说他“卖身投靠”,看不起“国立大学”。他说有一天,潘家洵来找他,没说几句话便突然问道:“何谓包衣?”他回答说,就是“满人的奴仆”。潘家洵听了,大声说:“这是外国人的狗,怪不得要架子大。”他就是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骂自己。而傅斯年甚至写信直接问他:“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他觉得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被迫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历数自己来燕大的苦衷,以此证明“弟之到燕大,兄不能责之于我,还须自责也”。endprint
就这样一年过去后,他发现自己在这“做学问的理想境界”里,生活并不那么“超然”。他为了应付环境,同样耗去了大量时间。以致一年半的时间,他“仅为学报撰《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耳,(想来)未免惭愧”。
我想在这种背景下,以他与周围的关系,他要请人联名为父亲祝寿,难免会遭到冷遇。特别是有些人顾及与鲁迅的关系,更不愿因此被人误会。何况鲁迅在北平时,已经对许多“旧朋友”表示不满,说“此地先前和‘正人君士战斗之诸,倘不自己小心,怕就也要变成‘正人君子了”。因此我认为,有些人同意在寿序上署名,这既是对顾先生的爱重,也是顾及钱玄同的情面。与其说这反映了顾先生“在学术界地位之高”,不如将这句话赠给钱玄同。
因为从上面的信里看,送寿屏的主意是钱玄同首倡的,最初确定在寿文上署名的,只有钱玄同、魏建功、范文澜、马廉四个人。而后来加入者,或者是鲁迅的知交,而反与顾先生“相交甚浅”;或者对顾先生抱有的成见。没有钱玄同出面请托,顾先生不便主动请求对方,对方也不会主动攀附。
以沈兼士、马幼渔为论。这两人都是顾先生的老师,互相有师生之谊,但是因为胡适的关系,很早便产生了芥蒂。顾先生曾在《顾颉刚自传》中说,他在北大国学研究所时,“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有一次,“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这让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从这以后,两人关系便“逐渐疏远起来了”。尤其是在厦门大学的半年,经过鲁迅的“极力挑拨”,两人的关系急剧恶化,几乎走上决裂的边缘。
两年前,顾先生在武汉《中央日报》上,看到鲁迅给孙伏园的信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两次写信质问沈兼士,要沈“详细答覆下列数事”:“(一)我在厦时有无反对国民党之事?(二)先生对于我的行事有无不满之处?如何愤愤?(三)先生的脱离厦大,和我有无关系?”在这之后,他虽然向沈兼士解释,“前发之双挂号信,正值愤怨之际,措辞当有过当,乞谅之”,但沈兼士始终没有表示谅解,反而“在北平常为我散布流言,友朋相告,已非一次”。
至于马幼渔,更是胡适的死敌。他任北大国文系主任,经常在校评议会和教务会上,对胡适“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相反,他与鲁迅的关系却很亲密。从《两地书》中看,鲁迅这次在北平的时间很短,但到北平的第二天,就去看马幼渔。在之后十几天里,两人至少三次见面,马幼渔还两次请他来家里吃饭。据钱玄同说,鲁迅离开北平后,马幼渔几次劝告他:“你如何与顾颉刚往还,他这样的性情,同鲁迅闹翻了,同林玉堂闹翻了,同傅孟真也闹翻了!”
但是钱玄同就不同了。他虽然与“三沈二马”一样,都是“章门弟子”,但没有任何党派成见,对顾先生的学识、人品都极为欣赏。认为“颉刚之疑古的精神熾烈,而考证的眼光又极敏锐,故每有论断,无不精当之至,尚在适之、任公之上”。甚至认为顾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远在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之上。而顾先生对钱玄同也十分敬重,曾在许多文章中说过,近代以来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不是胡适而是崔适和钱玄同。他在经学上的心得,很多来自于钱玄同的启发。直到晚年写《自传》时,仍然忘不了这段师生情缘。
因此他回北平以后,两人往还更加稠密。从《顾颉刚日记》中,他回北平的第二天,便“到玄同先生处”;以当天“未遇”,过一天便是“钱玄同先生来”,带他去参观北平图书馆。他去燕大执教后,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很少进城拜客。但每一次进城,总要去大辞典编纂处(即“某海”)或孔德学校拜访钱玄同。同样,据牟润孙先生说,他在燕大国学研究所读书时,就知道“钱先生在燕大兼课,下课之后,必往海甸成府胡同顾先生住处长谈”。他便经常在顾先生座上“遇见玄同先生,听到他口若悬河,高谈疑古之论”。
基于这层关系,钱玄同对顾先生的境遇非常不满。一九三○年一月,他得知单不庵病逝,曾在日记中发过这样的感慨:“年来王静安与梁任公之死,我最痛心,因其若在,则对于学术上之贡献尚多也!因思有四人均有某一类人所恶者,年来死其半矣!(一)梁任公,(二)单不庵,(三)黎劭西,(四)顾颉刚。”似乎对顾先生还能“幸存”多久,也深感忧虑。不仅如此,他因为顾颉刚的关系,还不惜与鲁迅决裂,结束了几十年的友谊。
有关这件事,鲁迅在《两地书》中说得很简略:“我这天出门,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鲁迅逝世后,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回忆与略评》里谈到更多的细节。他说,那天鲁迅去孔德学校访马隅卿,恰好他正在那里和马隅卿谈天。他见鲁迅的名片上印着“周树人”三个字,便开玩笑说:“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意谓何以不印“鲁迅”?不料鲁迅听了,正色答道:“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讽刺他学日本作家废姓外骨,“废姓而以疑古玄同为名”,说完便扭过头去,与他“默不与谈”了。钱先生说,他“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
依照两人的说法,两人的争执未免莫名其妙,似乎只是一场误会,老朋友间口不择言而已。事实并不是这样。据黎锦熙后来透露,两人决裂的真正原因,是彼此话不投机时,突然有人叩门进来,这个人是“钱先生最要好而鲁迅先生最不喜欢的”,那就是顾先生。这使两人更加对立,“因此更愣住了” 。
其实这件事鲁迅在《两地书》中也提起过:“少顷,则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出,状极可笑也。”所以经过这起不快,鲁迅回到上海后,几次在信里斥责钱玄同,说他“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将钱玄同周围的朋友称之为“昏虫”。钱玄同也在日记里谈到对鲁迅的反感,说“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不知道“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两人关系的不断恶化,最终走上互不见面的地步。据王志之说,一九三二年,鲁迅再次回北平省亲时,他和几位同学去找钱玄同,提出想请鲁迅来北师大演讲,钱玄同听了大怒,说:“我不认识什么姓鲁的。”endprint
我想正因为这样,钱玄同在与鲁迅发生争执后,更有意借给顾老先生祝寿的机会,帮顾先生“恢复名誉”,以发泄对于鲁迅的不满。而马幼渔、马衡、沈兼士等人碍于情面,只好随从钱玄同的提议。钱玄同的这种用意,在寿序中看得很清楚。从上面提到的信里看,这篇寿文是出自范文澜的手笔。但正如牟先生所说“寿序虽然出于仲澐之手,而文中的议论必定是钱先生指示的”,甚至有些文字经过他的亲手改动。寿文的写法非常奇特,开篇不是按一般寿序的体例,从顾老先生的履历写起,而是先写顾先生在古史辨伪上的成就;由顾先生史学上的成就,推及他的性情与人格,然后才转入顾老先生的“硕德美行”:
书不可尽信,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秦氏燔书,旧典零落。两汉经师蔚起,捃摭焚余,笃守残缺,缀葺不遑。黠诈者蹈隙作伪,苟便私意,淆乱弥甚。自是以来,沿为风习。烟瘴蔽塞,不可清梳。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辨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异以鸣高,将求理以安切。故好之者,比于执锐陷阵,学林之骁将;而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凡与其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咏陶铸者甚厚。与夫器小易盈,衔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今年春,颉刚自粤北来,友好留居旧都者,闻其至,皆欣然走访无虚日。高谈今古,备及身世。得备闻其尊人子虬先生硕德美行,而后知曩之忖度果信。
因此壽文的内容传出后,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顾先生的老家苏州,更称赞他“为苏州人争了面子”。章廷谦为此两次写信给鲁迅,不理解顾先生在广州落荒而逃,何以到了北平大受欢迎。鲁迅知道后,当然心里更不是滋味。他对于顾颉刚,本来是既憎恶又鄙视,一直以为他这次重返北平,“他的前途,殊未可乐观”,现在看来却事与愿违,回信时话说得极其刻薄。谓顾先生“奔波如此,可笑可怜……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顾先生的父亲字子虬)的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藉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从此以后,他对“北平诸公”便更加反感,说“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将他们看作垃圾和废物。他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他还预告这只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有情面的一棍”,“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
以上这些故事,就是我对牟先生《北京学林旧话》的续话。现在回头看这段往事,有些内容的确称得上“学林逸话”,值得作为史料保存下来。而据我所见,这些内容在现有的鲁迅传、鲁迅年谱中都没有提到,顾潮先生在《顾颉刚年谱》里也没有谈及,故尝试着写出来以飨读者。遗憾的是,由于《钱玄同日记》缺少这段内容,有些细节无法查证。好在国内研究鲁迅的人很多,任何不当之处,都可以有待指正。
二○一七年十一月七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