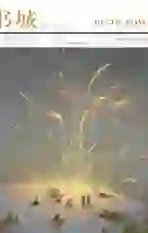谈几部印度传统“艺术”电影
2018-01-18何钧
何钧
近年来,随着像《摔跤吧!爸爸》《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些宝莱坞商业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引进并获得相当成功,引起了国内一部分观众和电影界人士的热议,探讨其艺术特征及商业成就。
以往一提到印度电影,人们的脑海中就浮现那些穿插歌舞的俗套镜头。这并不是对宝莱坞主流商业电影的扭曲印象,实际上,大多数我国观众没有看到的宝莱坞电影,艺术水准更低;而且宝莱坞之外的印度电影业,比如南部的泰米尔电影,往往更多粗制滥造的作品。即便如此,宝莱坞电影的类型风格还是很多样的,好莱坞的元素,比如警匪、灾难、侦探、政治、历史、神话、社会现实,荒诞、喜剧、先锋、魔幻等等,这里应有尽有。当然也包括所谓艺术片。同时印度电影也远远不止是宝莱坞。比如说,如果要找现实主义名作,我们便应该避开宝莱坞和泰米尔纳德,去左派色彩浓厚的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领略孟加拉语和马拉雅兰语的电影传统。
由于印度电影的复杂性以及导演风格的个人化,定义电影的基本类型也不容易。人们可以从主题故事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演员的表演、台词,导演的風格和艺术追求,以及面向的观众群,来划分不同的类别,而这种划分本身也是一种个性化的评判。一般来说,印度观众喜欢把充斥穿插歌舞的商业片笼统地称作“商业片”,而写实主义主题作品,就是所谓“平行电影”,或者也叫艺术片。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为了保持现实主义的叙事节奏和风格,严厉拒绝以轻松明艳、热烈欢快为基调的穿插歌舞。艺术电影拒绝迎合观众感官刺激和低幼退化心理定式的麻醉品风格,追求艺术和思想性的统一。
然而,所谓艺术电影的定义也是模糊不清的。在笔者看来,明显的形式特征(摈弃歌舞)与思想性(是否反映社会现实)都不是很好的界定作品的方式。事实上,所谓商业片的俗套主题,比如善恶二元对立,穷小子突破等级藩篱娶得富家女,等等,也大多涉及一些社会矛盾。只不过商业片是以程式化的,甚至不现实的方式处理这些矛盾。像《三傻大闹宝莱坞》这样歌舞场面很少的作品,表演细腻,剪裁精致有现代性,尖锐反应社会矛盾,就赢得了城市中产阶级观众的认可,也被我国的一些观众归为“艺术小清新”。但是实际上还都是比较标准的商业片。就连故事来自真人真事的《摔跤吧!爸爸》,也是典型的宝莱坞商业片的风格,甚至可以说是好莱坞风格。不过,我们在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另一类国内很少被人谈起的,也是介于典型的平行电影和商业片之间的所谓印度传统“艺术”电影。和很多商业片类似,它们的剧情不是很突出,甚至可以说是俗套,还经常抄袭,也无惧剧透。然而,如果说情节梗概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描述的话,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的意义却独特、含蓄、细腻,深刻而多面地反映社会与人性,绝不落入观众期待的俗套。电影中塑造的人物,虽然可能也有典型戏剧角色的类型,但是被艺术家赋予丰满的血肉,难以简单用言辞准确地形容,往往成为独特的新典型。不刺激感官、赚取眼泪,却回肠荡气,促使观众思考,留下隽永悠长、难以忘怀的记忆和经典的艺术形象。所以传统艺术电影与商业片的最本质的区别,是作品的目标和艺术理想。
为了表现这样独特的人物,避免疏离感,让观众觉得真实而受到感动,影片注重演绎,除了布景以及人物身份的精心设计,最依赖的是演员深厚的表演功力,有明显的舞台韵味,这与其电影产业早期的传统舞台血缘相关;如果与早期的中国电影相比,倒有明显的相似性。这种一直坚持和继承早期电影传统的倾向,又与自然主义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他现代电影视听技术有明显区别。简而言之,印度传统艺术类影片,是以最传统的形式,表现适合当代观众的丰富的社会和人性主题。
《丹尼》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平行电影的中心移到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识字率高、左派思想影响浓厚的喀拉拉邦。
T. V. 昌德拉是著名的平行电影导演,《丹尼》(Dany)是他的名作之一。整个故事线索有点像《阿甘正传》:小人物丹尼一生的每个转折,都和印度,特别是喀拉拉邦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马拉雅兰语影星马木提演的丹尼·托马斯是个被教会收养长大的孤儿,以在丧礼上吹萨克斯管谋生。在一次动乱中,新婚的妻子不辞而别,留下他一个人在混乱荒诞的社会中流浪。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印度教上层社会人家收留,被迫娶了该户人家因为失贞怀孕而嫁不出去的女儿。丹尼是个质朴真诚的人,人生在社会政治的狂潮中跌宕起伏,却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根本不能适应上流社会的伪善和空谈。他备受压抑地度过后半生,连起码的亲情都没有得到;病重的时候,妻子、儿子都觉得他丢人,把他送到医院等死,并在那里偶然遇到玛丽卡·萨拉白主演的退休女教授。女教授虽然在上流社会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但是丧女后内心郁郁寡欢,理解并欣赏他的率真。最后丹尼垂死之际,想回自己生长的地方看看,在车站碰上要来陪他一程的女教授,还有怒气冲冲前来捉奸的孩子。他就在那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女教授毅然为他在印度教的社区举行了天主教徒的仪式。
就算不知道那些动乱中的历史事件背景,观众也可以静静地欣赏电影优美明快的画面场景,舒卷自如的节奏编辑,铺陈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以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还有戏骨巨星举手投足的表演功力,对人物的动人刻画。玛丽卡·萨拉白扮演的女教授,最后才出场,戏份不多,但是举止优雅,明眸善睐,气质逼人。
《海之花》
导演巴拉塔·拉吉本来擅长的是泰米尔农村题材,为了让自己当演员的儿子成名,在电影《海之花》(Kadal Pookkal)中勾画了一幅浓郁的南印度渔村风情画。
卡鲁与彼得是同村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卡鲁来自一个印度教家庭,沉稳宽厚,特有人格分量和男子汉气质。而彼得则出生在天主教家庭,比较好面子,成天想多打点鱼,发家致富做大事业。野心勃勃的彼得如果没有卡鲁照应,早就死几回了。他一直奇怪卡鲁一身好本事,怎么就甘心一辈子当个乐呵呵的渔民,不想当城里的人上人。卡鲁的妹妹卡娅喜欢上了彼得,而彼得的妹妹玛丽亚被城里小青年勾引怀孕,成了家庭的奇耻大辱。为了遮丑,他提出让卡鲁娶自己的妹妹玛丽亚,作为自己娶卡娅的交换条件。彼得明知道卡鲁已经和村里辣椒店的乌琵丽心心相印,还是卑鄙地欺骗自己的朋友,把不贞的妹妹塞给他。而且还自作聪明,以为别人不知道。卡鲁和乌琵丽为了卡娅的幸福,还有拯救玛丽亚,只好硬着头皮分手。endprint
《海之花》的最后,城里的青年又来找玛丽亚,怀着刻骨仇恨,正愁无从报复的彼得把他骗上船后,绑上石头丢入海中,卡鲁奋力跃入波涛之中救人。姐妹们焦灼期盼。电影至此戛然而止。
印度电影的设计,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主角一般都富有宽厚坚强的男子汉魅力,而女演员只能靠自己的形象、风格出彩。卡娅有一股清纯可爱之气,活脱一个善良有礼、天真烂漫、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形象。而乌琵丽则成熟坚强,泼辣机灵而又羞涩温柔,勇敢追求爱情,又深明大义,默默接受命运的打击。说起来,扮演乌琵丽的演员普拉西莎也是命运多舛,因为家境贫寒,很小就出来演戏帮着养家。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女演员,非常艰难。好不容易熬到女孩子终身大事,婚事又遭到对方父母反对,二人双双服毒自杀,结果她死了男方被救活。后来真相被揭露,是男方先掐死了她后假自杀,可谓遇人不淑。这也表现印度电影业中相当残酷的一面。游刃有余的业者,十之八九来自于背景深厚的演艺世家。
《稀世的恋曲》
前面说到泰米尔电影的数量不少,早期的泰米尔黑白片,歌舞往往自然融入情节之中,需要坚实的舞台功力,涌现了不少影响整个国家的名作。后来的电影则艺术成就比较低,大量的英雄单枪匹马对抗恶势力的俗套。
我曾在一家卖印度电影VCD店里,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轮廓和眼睛極漂亮,皮肤还特别白。叫她给我推荐一部最好的爱情故事片。她眼睛转了一下,走到帘子后面,没多久就拿着一张光盘出来了,这就是《稀世的恋曲》(Apoorva Raagangal)。影片讲述的是一九七五年,一对歌手母女与另一对富豪父子,颠倒相爱的故事。母亲爱上了离家出走的叛逆青年,而同样离家出走的女儿则爱上了失去儿子的富商。巴拉昌德尔导演的片子,总是有离奇的情节和传唱不衰的经典插曲。
饰演中年女歌手的斯丽·薇迪雅体态丰腴、面容秀美,举止端庄优雅,眼含秋水,歌喉圆润哀婉,招人爱怜。青年鼓手的演员卡迈·哈桑后来成为集演导编于一身的印度巨星。男女主角二人都曾是童星,他们俩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坠入爱河。
二○○二年,巴拉昌德尔再次用印地语翻拍了这部经典,仍然由卡迈·哈桑担任男主角,但是斯丽·薇迪雅已经不堪病魔的折磨,不久于人世,因此由另一位印度女星中年美女赫玛·玛琳尼出演女歌手。好在目前网络上还有这部经典的视频,可惜没有字幕,但是读者仍可以从中领略斯丽·薇迪雅的绝代风华。
《火和雨》
《火和雨》(Agni Varsha)这又是一种印度文艺片类型,挖掘、演绎神话传统中本已有所深刻表现的人性。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包括戏剧)传统的国家,有不少印度电影都以历史和神话作为题材。但是除了黑白片时代的电影很见舞台表演功力之外,后来的佳作不多,往往是男主人公坚毅凝重大义,女主角歌舞婉转、明眸深情、理解知音之类的俗套。
这部《火和雨》的灵感来自史诗《摩诃婆罗多》里面一个小故事:一个优秀青年,门第优越,上进有为,抛弃世俗之念去修炼法力,大家盼望他能成功造福乡里。另一个一块长大的不成器的朋友嫉妒别人处处强过自己,也去发奋修炼法力,但是后来忍不住报复和好胜之心,勾引了别人的老婆,结果被恶魔杀掉。但是改编的剧本却天马行空,一开始就完全变换了主题:老天七年不雨,骄阳似火。一对婆罗门兄弟,哥哥是懂事早熟长子性格的优秀青年祭司,为了求雨的宗教责任丢下老婆七年不回家。婆罗门弟弟是典型的幺儿,酷爱演戏,还爱上一个部落女,准备放弃婆罗门身份和情人结婚。哥哥被老婆迷惑,误杀了自己的父亲。为了摆脱制裁,完成宗教仪式的责任,他诬赖自己弟弟杀父。弟弟被逐出婆罗门,为部落女所救。最后,哥哥作法失败,身败名裂。弟弟却通过巫舞感召来雨神因迪拉,而部落女却同时也遭遇了危险。因迪拉让他选择是解脱邪魔下雨还是救情人。他做出了痛苦抉择,爱人香消玉殒,焦渴的大地拥抱倾盆大雨,万民雀跃。
这是一部唯美主义的制作,在褐黄的乡村基调里,男女主人公健美自然的肌体,有如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居住的众神,使人血脉贲张。虽然故事的人物有典型戏剧角色模式的影子,但是作者以电影语言做了个性的处理。隐含的众多主题,包括舞蹈戏剧的宗教来源,以及男人的成长,情感和责任。拯救大地万民的,不是阅尽世事的老父,也不是被责任与盛名压碎人格的伪君子,反倒是一对至性至情、洒脱不羁的少男少女。
《我的名字是小丑》
我们再回到宝莱坞,看看她的一个文艺片的经典,拉吉·卡普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的名字是小丑》(Mera Naam Joker)。
这个拉吉·卡普就是曾在中国流行过的拉兹,上了岁数的中国人很多还能哼出“阿瓦辣武”的调子。他演的流浪汉形象,正迎合了那个时代中国青年人的叛逆思潮。卡普是印度西北靠近巴基斯坦的一个刹帝利种姓的名字,经常被用作姓。宝莱坞电影业有名的卡普家族不止一个,但数拉吉·卡普他家最显赫。拉吉·卡普自己,其实是影视权贵第二代,并没有流浪汉的体验。他的父辈倒是流浪的舞台艺人。拉吉上了岁数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声名欲望值得追求,就倾尽自己的资源,耗费巨资,拍摄了这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电影.讲述一个戏剧演员的情感故事。场面宏大华丽,演员阵容豪华。
影片的开始是一个马戏团喜剧演员死了,他老婆不希望他们的小男孩以后也当喜剧演员。可是孩子从小就有天赋,从后台的打杂小工,一路成长为知名的艺术家。只是感情经历一直不顺,先后爱恋的三位女性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到一起。在他最后的盛大告别演出上,三位他曾经倾注爱情的女神都被邀请光临。繁华之后,他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想他当喜剧演员的原因:给人欢笑后面是自己的孤独和寂寞。
这个电影在商业上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耗资巨大,里面充满了中距离、不切换镜头的直播式舞台表演。拉吉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要为印度的普通观众献上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同时呈现自己的扎实的舞台表演功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它永恒的经典价值:它表现了少年、青年和中年之爱,蓬勃丰富而又压抑怅惘的情怀。艺术家的情感经历,比他的事业更能表现艺术的本质。
印度的电影早期的政治现实功用,与中国电影有类似之处。英国殖民当局曾经禁止任何反应殖民压迫的电影制作,只允许拍摄维护其殖民统治的“反法西斯”主题电影。
而独立的新兴国家,需要寻找进步的新精神文化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这是一代电影人的文化使命感,曾得到印度政府和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与所谓的商业片抗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印度“平行电影”的黄金时代,曾经为印度电影获得崇高的国际声誉和影响,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比如首届(1946)法国戛纳电影节大奖,就被印度孟加拉语电影大师阿南德的Neecha Nagar夺走。到了九十年代,印度的平行电影传统逐渐消亡。但是后来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又带来了艺术电影的某种程度的回归和复兴。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宝莱坞影片的商业化元素非常强大和明显,但是获高票房的商业片,往往都有浓厚的文艺片的元素,包括演技风格和精致的布景。到目前为止,传统依然是印度电影的魅力所在。像《午餐盒》这样完全自然主义的实验风格,还没有深厚的根基。
尽管如此,受批评界欢迎的有着不同电影理想的传统“艺术”电影,依然面临着商业电影的冲击,包括对市场、渠道和投资的争夺,成本和明星片酬的迅速膨胀,等等。实际上,在印度,产生伟大作品背后的那些因素(激烈的社会矛盾,思想上强烈的进步诉求)依然存在,但随着商业片的投资不断增大,电影已不再像文学那样,充当影响现实的有力工具。虽然有着相同的制作形式和类似的电影语言,商业片和严肃片其实是不同产业,遵循不同的商业规律,也应该有不同的组织运作管理方式和渠道。在其他领域中,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严肃电影,恐怕不能继续指望商业影院永远是自己和商业片分享的领地。随着商业片和市场的发展,二者的交集越来越小,终会分道扬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