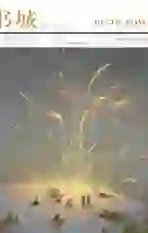艺术与恐惧的对抗
2018-01-18金衡山
金衡山
一九四一年,纳博科夫与家人从法国来到了美国。他在麻省韦尔斯利学院找了一份教授比较文学的工作,后来又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研究蝴蝶的结构。多年后,他自述道:“那是我生命中一段晴朗无云、神清气爽的时光。我的身体棒极了,每天香烟的消耗量达到四盒。”他在韦尔斯利学院和哈佛大学之间来回跑,文学课教授与蝴蝶研究两不误。同时,他也在全身心地写一部小说。一心三用,在于纳博科夫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那是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六年春的一段时间。一年后,小说《庶出的标志》出版,这是纳博科夫的第二部英语小说,也是他到美国后出版的第一本小说。
小说写的是一个警察国家里发生的故事,通常会被称为是反乌托邦小说,与奥威尔的两部著名作品《动物庄园》和《1984》有着类似的指向,但纳博科夫似乎对这种显而易见的比较不屑一顾,很不愿意把自己等同于奥威尔,就像他不愿意因为此前写的一部俄语小说《斩首之邀》表现出的荒诞情节而被认为与卡夫卡的风格类似(这部小说也曾被称为是有反乌托邦的痕迹)。这些话都出现在纳博科夫为一九六三年再版的《庶出的标志》写的前言里,在这篇一边为自己这部作品的主题做某种程度的“辩护”,一边阐明他的文体格调的文字里,纳博科夫甚至还直截了当地说:“我所处的时代对我现在这本书的影响微不足道,就像我的书,或者至少是这本书,对我所处时代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一样。”他说,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并不是要“讽刺”什么。但同时,他也申明他的生命历程中曾遭受过“愚蠢可憎的政体”带来的打击。显然,纳博科夫的话语有点自相矛盾,这可能是因为他不愿看到读者拿那种社会批评的套路来读他的这本小说,他需要的是一种可以超越现实指正的阅读理解,上升到深入人心的挣扎和苦痛的展露这个层面的意义,这自然也是纳博科夫一贯的写作风格。
但即便如此,在这部小说中,政治讽喻、现实讽刺的意味还是非常浓烈。纳博科夫所能调和的只是在虚构的成分上做一些文章,不仅仅是虚构的人物,更是虚构的国家,一个说着自己的语言,阐释着自己的思想的政体。前者是纳博科夫自己构建的语言,在小说中时时出现,显示了当地人的本地身份,后者被他冠以一种主义的指称。只是在看似浓厚的虚构氛围里,现实的影子依然会时隐时现。虚构的语言闪现俄语的尾巴,而充斥主义的思想则更是透视了二十世纪种种暴虐可能发生的轨迹。
现实的指向与讽喻的笔调在这部小说里手拉手跳起了滑稽和恐怖的双人舞蹈。恐怖政体的领袖在纳博科夫调侃加讥讽的描述里,以小丑的面貌出现,他被称为“蛤蟆”,模样奇丑,让人恶心,且似乎智力也有问题,但就是这么一个垃圾级的人物却摇身一变成为了领袖,呼风唤雨,天下为之匍匐。纳博科夫在用哈哈镜与夸张手法展露人物的特征的同时,也不着痕迹地讲述了他的发迹史。相比于小说主人公的睿智和气势,这位看似极其木讷的丑怪人却有着惊人的政治嗅觉,在中学时就开始拉帮结派,后来更是利用了思想与文化名人的遗产宣传起某种主义,并且扯起“普通人”的大旗,竟然风生水起,进而声势浩大,席卷天下。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说法,纳博科夫在小说中描述的主人公中学时代目睹的社会思潮的涌动来自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二十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的动荡是纳博科夫心中抹不去的创伤,也以一种幽灵的形式在其文字里飘荡。现实的影子即便是在讥嘲、嘲弄、揶揄、挖苦、奚落、耻笑等多重笔触的挤压下,也挡不住其在故事中生根的欲望。纳博科夫在描述领袖掌权后实施的种种政治手段时,则更让现实无限地贴近了文本。与所有专制政体一样,思想的控制总是走在行动的前列。正是这个层面上,我们的主人公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这位大学哲学系教授,身兼思想家的伟名,在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似乎可以与领袖相比拟,他们两个本是中学同班同学。几十年不见,再次相见时,天壤之别俨然不可逾越,但是这个名叫克鲁格的人物—名字读出来铿锵有力,与他的强壮的身体一样有力—却似乎并不领会,或者不屑理会这个差别的含义,依然是摆出一副思想者的模样,我行我素。尤其是在领袖向他发出邀请,请他为其代言,给予舆论的支持时,克鲁格先生断然拒绝。只是,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这样的邀请,但他不能阻止身边的朋友因为他的拒绝被便衣警察一个个地带走,且是有意当着他的面让这样的事发生,直至最后他和唯一的亲人、八岁的儿子也加入了被带走的行列。故事临近结尾,发生了一个拐弯的情节,克鲁格不能忍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他同意了领袖的要求,条件是把儿子还给他。但不幸的是,儿子进入“少年教养院”后很快被那儿天生的折磨机制折磨至死,知道真相的克鲁格于是崩溃、发疯。
从颇为风光的著名人物到受尽折磨后的疯人,纳博科夫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力的现代专制社会的图景。克鲁格的遭遇让我们战栗与心焦。纳博科夫的冲击力更在于描述出了个人的无限的渺小,纳博科夫是真正地和盘托出了在那个特殊的场景里一个人的无能为力。这是一种绝望、无望和全部的心力耗尽之后的孤独与无助。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的最后一次的反抗,一方面让克鲁格走向了成为疯子的道路,另一面似乎也是回应了反抗的无力。
但是,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纳博科夫让克鲁格经受的不仅仅是外在的残酷压力,还有内在的精神煎熬。其中失去孩子和朋友这种来自外在的打击转化而成的内在苦痛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失去爱人奥尔嘉带来的生命意义的殆尽。用纳博科夫自己的话说,小说的主题“是克鲁格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经历的折磨”。小说自始至终围绕克鲁格的爱人奥尔嘉逝去后对其产生的打击展开。克鲁格对于爱人的无尽思念,以及由此转化成对儿子大卫的充满父爱的呵护,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另一条主线。也就是说,在勾勒那个虚构的专制国家的蹂躏行为的同时,纳博科夫笔下的叙述者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了对主人公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描述之上。这种双向主线的发展构成了小说的一个张力,爱意的情感形成了对无人性的暴虐的一种对抗,纳博科夫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对抗的存在,小说情节的安排与敘述者语调以及叙述角度的变化本身透露了这种对抗的存在。换句话说,小说的文体层面向小说的内容层面发起了一种抗争。endprint
小说伊始,叙述者就以一种象征的手法表露了克鲁格即将面临的残酷事实,不是领袖领导的“革命”的成功,而是他的爱人在遭遇车祸后手术失败,生命即将走向结束。之后,思念爱人的画面时时出现在克鲁格的脑海里,这种思念是如此之重,以至让克鲁格的身体和心都无法安宁,甚至会让他一时忘却了外在世界的喧闹和残酷。但是,从情节安排上看,纳博科夫并没有让这两条线独立发展,泾渭分明,除了有一章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叙述了克鲁格与奥尔嘉相识、相近的过程以外,对克鲁格的思念之情的叙述都是以情绪流动或者是爆发的手法,混杂在专制暴虐行为发展这条主线之中。这使得小说的叙述过程常常发生貌似被打断的迹象,而这更是表现在叙述者语调和角度的变换上。小说在描述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时语调多为讥讽,现实感与荒谬感共存,而在描述克鲁格内心的思念时,语调则充满了绵绵之情。对于前者,叙述者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角度;对于后者,则常常转换成了第一人称。前者的对象是读者,后者的对象变成了人物自己。但与此同时,这种描述方式也让读者时时随着镜头的变换走进了克鲁格的内心,暂时离开了凶险的现实世界。纳博科夫似是要从这种文体的变换中延伸出一种力量,来对抗现实之险恶和凶残。
除此之外,小说也暗藏了另一种力量,一种文本实验的力量,不是来自后现代式的叙述自涉,而是来自对文学名著改编实验的行动。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让克鲁格的朋友安波—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和翻译者,讲述他对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的改写计划,用原剧中的边缘人物,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替代哈姆雷特成为剧中的主角,并为这种改写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克鲁格被安波的想法所吸引,两个人不由自主沉浸到颠覆性想象的快乐之中。克鲁格同时也与安波分享了他从一个美国人那里得知的拍摄《哈姆雷特》的想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对于哈姆雷特的恋人奥菲莉亚的各种各样的憧憬。所有这一切让两个人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到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欣快症中。纳博科夫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克鲁格和他的朋友陷入的迷幻般的情境,纳博科夫的似真似假、游戏般的刻意与豪华精致的语词表述文体也在这里获得了充分的展示,以至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发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沉浸的时刻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经由文字发挥无边无际的想象力,由此产生了一种要把文本本身—莎士比亚的文本和纳博科夫自己的文本—撕个稀巴烂的企图。前面提到纳博科夫在前言里说,书中的人物是他的“幻想与怪念的产物”,他试图用这种简单的总结来轻描淡写其文体应该发挥的力量。确实如此,我们看到的是幻想和怪念的狂欢,但显然这场狂欢不是独立发生的,尽管存在一种非常强大的愿望—无论是从读者还是从作者的角度而言,希望这是一个能够把这场狂欢进行到底的时刻,直至永恒。现实毕竟就在眼前,无论是纳博科夫还是他宠爱的克鲁格以及他的朋友,幻想的时刻在文字的怂恿下可以让人迷醉;但是在现实面前,文字的力量立刻消失且形象可怜。在这一章的结尾处,克鲁格看着秘密警察上门把安波带走,面对着这位幻想家对他的哀求,却毫无办法。很快他自己也会被抛入同样的命运,同样的无能为力会把他抛向死亡的刑场。从文体中发酵的种种能量终究不能抵挡现实中恐怖的弥漫与笼罩。这是小说的骇人之处,也是点睛之笔,点到了读者和作者的痛穴。
但,纳博科夫似乎于心不甘,他要对普遍的无能为力做出一种反应。在小说结尾时,叙述者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客观地描述了克鲁格的最后一搏—朝着前来威胁和哄劝他的昔日的同学、今日的领袖扑去,就在一颗子弹即将击中他的时候,突然间,作者—纳博科夫先生本人出现了,第三人称转换成了第一人称,“我”告诉读者说,“我”只是在写写这个故事而已:“我知道我赋予那个可怜人的不朽是一种含糊的诡辩而已,一种文字游戏。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幸福的,而且他也看到了死亡只是一种风格问题。”纳博科夫在前言里说,这位“我”是一位由他自己赋形的人格化的神,“这位神在最后一章里为了他的人物揪心痛惜,起了怜悯之心,匆忙接管了小说”。纳博科夫把克鲁格拉进了他的怀抱,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从作者干预的角度再一次抵抗了现实的包围。“‘蹦,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的夜晚。”那颗射向克魯格的子弹被纳博科夫挡住,变成了飞蛾扑向窗户的撞击。小说如是结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