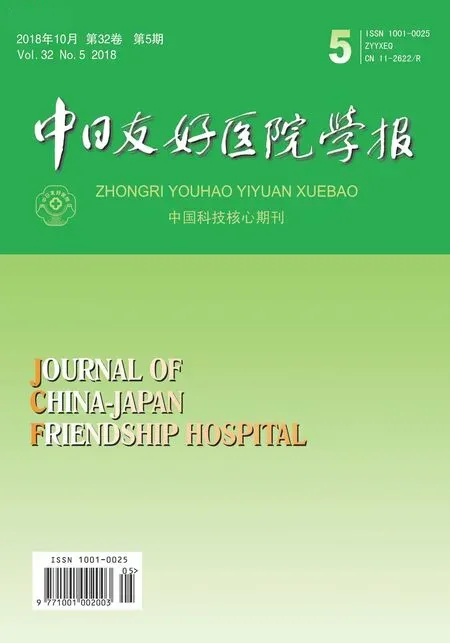成人非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的病因及诊断
2018-01-17葛亚如李友林
葛亚如 ,史 琦 ,阎 玥 ,李友林 *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 中医肺病二部,北京 100029)
支气管扩张症(bronchiectasis,BE)是一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通常可区分为遗传性囊性纤维化(hereditary cystic fibrosis,HCF)或其他原因 (非CF支气管扩张,non-cystic fibrosis bronchiectasis,NCFB)所致。由于HCF有其独特的病理生理学及治疗途径[1],本文暂不予讨论,而将综述重心集中于NCFB。BE的主要特征是支气管壁结构破坏、不可逆的气道异常扩张及粘液淤滞,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病理改变的严重程度,最常见和最典型的症状是与粘液脓性分泌物有关的慢性咳嗽咳痰,随着疾病的进展和/或肺功能恶化,亦可出现慢性鼻窦炎(70%),呼吸困难(62%)、疲劳(74%)及咯血(45%)。
1 流行病学
由于胸部高分辨CT计算机断层扫描(HRCT)技术的临床应用,BE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正在增加,但尚不清楚是真正的增加还是检测手段的完善所致的发现率增高。基于国外一项大型研究[2]的结果表明,约有34万~52.2万成年人正在治疗BE,并且以每年7万人的速度新增,2001年以来的年增长率为8%。另有研究[3]发现,BE中女性发病率从2004年的21.2/10万人年上升到2013年的26.9/10万人年;男性发病率从2004年的18.2/10万人年上升到2013年的35.2/10万人年,且年龄增加与死亡率相关。随着疾病的进展,BE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治疗负担加重[4]。
2 病因
所有导致支气管壁结构损伤的因素都有可能引起支气管扩张。无论何种原因,支气管扩张都可能导致粘液淤滞、慢性感染和炎症的“恶性循环”,称为Cole的“恶性循环”假设。其病理改变主要有粘液分泌过多或堵塞,细菌、真菌或病毒等微生物病原体的定植,黏膜纤毛清除率降低,平滑肌增生和炎性细胞浸润。
2.1 慢性感染
感染后支气管扩张是NCFB中最常见的类型。支气管扩张患者的气道,特别是成年人,易被潜在的致病微生物定植[5],继而引起慢性细菌感染,其中以流感嗜血杆菌最为常见 (34%~36%)[6],其次是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sA)、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卡他莫拉菌[1,5,7]、 非 结 核 分 枝 杆 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8],酵母和丝状真菌或霉菌则较少见。
2.1.1 细菌
除PsA外,其他细菌对支气管扩张致病机制的相关文献报道较少。研究[9]表明PsA是通过释放侵蚀每根纤毛上皮层的炎症介质直接损害黏膜纤毛清除功能,进而导致痰液排除受阻,粘液淤滞。目前有关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BE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仅有研究表明其与肺功能、恶化频率或住院情况无关,不是疾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10]。
2.1.2 真菌
支气管扩张患者最常见的真菌感染病原体是白色念珠菌和曲霉菌[8],真菌对支气管扩张发生的影响主要涉及三方面:抗原和真菌蛋白酶、遗传易感性及可能与其他微生物的相互作用。真菌蛋白酶能够诱导活化多种气道趋化因子,如人胸腺活化调节趋化因子 17及 11(CCL17、CCL11),促使T辅助2型(Th2)细胞募集到气道,Th2细胞和 Th2细胞因子,如白介素 4(IL-4)、白介素 13(IL-13),是变应原攻击气道黏膜后导致气道阻塞的关键介质;此外,真菌还可以产生蛋白水解酶,如真菌丝氨酸蛋白酶能促进IL-8释放,进一步诱导嗜中性粒细胞募集以增强肺部炎症[11]。有动物模型表明烟曲霉分泌的过敏原蛋白酶—Asp f5和Asp f13—能促使大鼠模型中炎症细胞及细胞因子(如嗜中性粒细胞、IL-6)募集,产生过度炎症反应,从而引起气道损伤[12]。过敏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llergic bronchopulmonaryaspergillosis,ABPA)通过依赖 Th2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如IL-4,IL-5和IL-13),抑制气道上皮细胞免疫调控作用,导致肺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放射性浸润、气道阻塞和近端支气管扩张。故欧洲[1]和西班牙关于支气管扩张指南[13]中建议在所有诊断为BE的患者应常规筛查ABPA,推荐的筛查项目包括血清总IgE检测、肺曲霉特异性IgE和IgG抗体[1]。
2.1.3 病毒
目前病毒与NCFB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高永华等人[14]对119例成人NCFB患者鼻咽拭子和痰中呼吸道病毒进行检测,结果发现,相比稳定期,NCFB急性加重期呼吸道病毒出现的频率更高(100例中有49例,P<0.01),急性加重期最常见的病毒是冠状病毒(65例中有19例)、鼻病毒(65例中有16例)、甲型/乙型流感病毒(65例中有16例)。且NCFB合并病毒阳性者气道炎症标志物(血清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痰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显著增加。
虽然感染后支气管扩张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主要类别,但目前对细菌、真菌、病毒三者在支气管扩张病因、病理中所产生的复杂机制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进一步深入以指导临床诊治。
式中:δH为行星架转过的角度,此时,δH=2π/nb,nb行星机构均布行星轮的组数;δR为齿圈转过的角度,此时,δR=0;δS为太阳轮转过的角度,该角度只要满足整数个齿的约束条件δS=2Nπ/ZS,其中N为整数.
2.2 免疫缺陷综合征(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IDS)
先天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通过诱发反复肺部感染导致支气管扩张。免疫缺陷相关原因包括慢性肉芽肿性疾病、低丙种球蛋白血症或普通可变免疫缺陷等。故早期诊断和治疗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有益于NCFB患者的预后[6]。John P.Hodkinson等人[15]??的研究表明IgA和IgM缺乏(除了IgG)是初级抗体缺陷(primary antibody deficiency,PAD)的共同特征,患有IgA和IgM缺陷的患者中支气管扩张的发病率高达48%。
2.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COPD是支气管扩张发生的常见原因之一。Gema Sánchez等人[4]的研究发现当NCFB是次要诊断时,最常见的主要诊断是COPD,并且NCFB作为二级诊断时支气管扩张患者的费用明显增加(P<0.01)。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数据库显示NCFB是哮喘和COPD受试者的重要亚群[3,16],但是,两者并不被认为是导致支气管扩张发生的直接原因。亦有人[17]提出,COPD-支气管扩张重叠综合征(bronchiectasis-COPD overlap syndrome,BCOS) 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临床表型,重叠与死亡率升高明显有关,然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治疗策略仍然对我们的临床实践构成重大挑战,因此,迫切需要更多地了解两者的流行病学、自然史及治疗的具体情况。
2.4 结缔组织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CTD)
CTD中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和干燥综合征(sjogren syndrome,SS)更容易与支气管扩张相关联[6]。目前关于CTD与BE之间发病机制的研究较少。一项回顾性研究[18]表明BE是RA的主要并发症,并且与RA的高发病率、死亡率密切相关。沙特胸科协会指南[11]建议若怀疑NCFB合并CTD者,可初步筛查自身抗体,包括类风湿性因子(RF)和抗核抗体(ANA)。
2.5 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PCD)
由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导致呼吸道分泌物清除障碍的疾病都有可能引起支气管扩张,PCD就是其中一例。PCD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根本病因是编码纤毛结构蛋白或纤毛功能调控蛋白的基因突变[19]。不同患者的临床表现差异较大,当它与右心耳有关时,被称为“Kartagener综合征”。Goutaki等人[20]对1970例PCD患者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最主要的表现是支气管扩张(89%)。欧洲呼吸学会指南[1]建议具有自幼持续性湿咳、器官反位、先天性心脏缺陷、慢性鼻窦炎或鼻息肉、伴或不伴听力丧失的慢性中耳疾病以及新生儿呼吸窘迫史或足月新生儿重症监护入院的患者,应考虑检测PCD。Young’s综合征是另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粘液清除异常,表现为支气管扩张、慢性鼻窦炎和梗阻性无精子症的临床三联症,其特征是异常粘稠的分泌物,发病机制可能与跨膜调节因子(CFTR)基因内的突变有关[6]。
2.6 其他疾病
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alphe antitrypsin deficiency,A1ATD):α-1AT的缺失导致丝氨酸蛋白酶活性增加,释放IL-8,或因α-1AT聚合物易于在肺间质聚集,两者都可诱导肺部嗜中性粒细胞聚集,介导过度的炎症反应,造成持续性肺损伤[6,21]。
间质性肺病、反复吸入及暴露于毒素[6]等也可引起支气管扩张,目前尚不清楚其致病机制。
3 诊断
3.1 血液测试
虽然全血细胞计数(whole blood cell count,BCC)、C 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CRP) 及血沉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无助于支气管扩张的确诊,但却是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和恶化的相关炎症标志物,故应检测。如上述病因所述,NCFB患者还应测定血清免疫球蛋白(IgE、IgA 和 IgM),类风湿性因子(RF)、抗核抗体(ANA)等。
3.2 放射学检查
3.3 肺功能检查
在BE患者中,最常见的肺功能模式是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50%),但仍有1/3患者的肺功能检查是正常的[16]。
King等[24]在61例支气管扩张患者肺扩散能力的纵向研究随访期间发现,这些患者的FEV1、FEVI/FVC、DLCO及DLCO/VA均显著降低,且DLCO下降与年龄和FEV1下降之间存在相关性。所有诊断支气管扩张的患者应在开始和随访时每年进行肺功能检查[6]。
3.4 痰炎症指标检查
3.4.1 痰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utrophil elastase,NE)
近几年有关NE与支气管扩张的研究越来越多。NE是一种29KD的丝氨酸蛋白酶,其储存在嗜苯胺蓝颗粒中,主要与促进炎症、减缓纤毛运动频率并刺激粘液分泌有关。Chalmers等人[25]的研究指出痰中NE活性与疾病恶化、肺功能下降的风险独立相关,是支气管扩张严重程度及疾病进展的生物学标志。Gramegna等人[26]的研究亦表明,痰中NE活性可用作稳定状态支气管扩张和恶化及局部或全身抗生素治疗的炎症标志物。NE水平可以反映临床状态,用于临床评估,但是,作为支气管扩张特定靶标的NE的抑制研究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仍需进一步研究。
3.4.2 常规微生物学评估
支气管扩张患者易合并细菌、真菌、病毒的感染,故应对其进行常规评估,明确诊疗方向。分离病原体的检出率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环境、患者的年龄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等,临床常规痰培养标本可通过自然咳痰法、高渗盐水诱导或胸部物理疗法等获得,所送痰标本应尽可能地反映下呼吸道的菌群群体,最好在抗生素治疗之前,特别是疾病感染的加重期[6]。流感嗜血杆菌、PsA、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等都是比较重要的病原体,然而标准微生物培养基是有选择性的,可鉴定的细菌种类有限。基于基因测序的研究方法比标准微生物培养基能提供更好的痰微生物成分鉴定和定量评估,完善患者管理策略[27]。除上述病原体外,支气管扩张通常与NTM的分离株有关[22],而实验室痰培养可用于检测非结核分枝杆菌肺部疾病(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respiratory diseases,NTM-PD)。 常规微生物评估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尽早识别感染病原体,提高诊疗效果。
3.5 支气管镜检查
在胸部CT或HRCT可用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支气管镜检查来协助诊断支气管扩张,除非CT扫描提示肺部存在阻塞性病变、异物或肿瘤引起远端支气管扩张或因咯血需进一步局部止血。
3.6 其他检查
鼻一氧化氮测试能测量鼻腔黏膜纤毛清除率,当怀疑患者是PCD时,可以用鼻腔NO来筛查。故建议若怀疑PCD并且鼻一氧化氮测试不可用时,可对PCD行基因检测。除外常规检查,还可以进行其他测试以排除先天性免疫缺陷或其他潜在病因,如琢-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鼻窦炎等。
4 总结
成人NCFB是一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目前国内尚无被普遍认可的支气管扩张指南或专家共识,大多参考欧洲呼吸学会和沙特胸科协会指南。NCFB潜在病因是管理支气管扩张患者的关键部分,诊断技术的提高可实现NCFB的早期诊断、尽早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