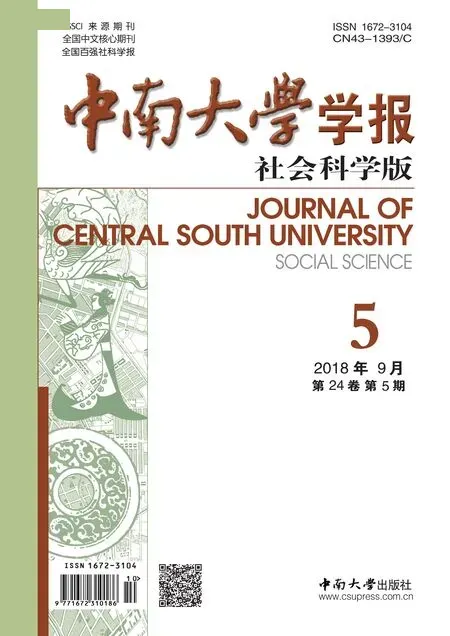从“合多为一”到“化多为一”——先秦儒家“大一统”的逻辑进程
2018-01-14路高学
路高学
从“合多为一”到“化多为一”——先秦儒家“大一统”的逻辑进程
路高学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以“一”为代表的王道秩序,经历了从“合多为一”到“化多为一”的演变。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形势,希望通过重建西周礼乐文明以匡正天下秩序,是“合多为一”。但到了战国时期,经孟子天下“定于一”和荀子“一天下”的诠释,儒家在政治秩序方面对于“一”的认知,已经由“合多为一”转变为“化多为一”。而《公羊传》的“大一统”虽然在表现形式上给人一种“合多为一”的感觉,但其实质内核却是“化多为一”,强调作为“一”的王道秩序。这是在汉初郡县制逐步取代封建制的情况下,以“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学能够走向兴盛的重要原因。
孔子;孟子;荀子;《公羊传》;大一统
“大一统”是先秦儒家的核心主张之一,为历代思想家所继承和发扬,并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作为一个范畴,“大一统”首次出现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公羊传》中。《公羊传》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其思想主旨反映了当时华夏文明由列国纷争走向统一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文字的多义性和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后世学者对于“大一统”三个字的理解各有偏重,有人着眼于“大”来理解“大一统”,也有人着眼于“统”来理解“大一统”,这也就带来了对“大一统”是强调“统一”还是“一统”的不同认识。因此,本文拟结合先秦儒家三位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思想中的“大一统”元素,对《公羊传》“大一统”产生的思想根源及其演变历程进行系统的探索。这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推崇西周宗法封建的儒家在汉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中国古代的王朝反而不再是封建制的“合多为一”(多仍旧在),而是郡县制的“化多为一”(多不复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孔子的“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的意思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1](211),出自《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2](5457)。孔子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周平王东迁之后,内有王权衰微、礼乐崩坏,外有夷狄入侵、诸夏危亡,而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匡正天下秩序。因此,孔子称赞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2](5456)众所周知,孔子尚“仁”,但在《论语》中极少见到他用“仁”来评介一个人,除对管仲的一次“如其仁”评价之外,仅见他说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2](5382)。在孔子的弟子中,颜回向来以高尚的德行著称,而如果说他的“仁”代表内在的德性修养,那么管仲的“仁”就是外在的辅佐君主“一匡天下”,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后世儒家崇尚的“内圣外王”之道。由此可以推测,像管仲一样辅佐一国君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恢复周公建立的礼乐文明秩序,是孔子在德性修养之外的另一个向往和追求。
春秋之世,本应是周天子拥有“礼乐征伐”的权力,却先后出现了“自诸侯出”和“自大夫出”,以及“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孔子推重周公建立的礼乐文化与宗法制度,希望效法管仲“相桓公”而“一匡天下”,再建西周礼乐文明秩序。西周礼乐文明的政治基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封建制度,遵循着“封建亲戚,以藩屏周”[2](3944)的原则,是一种“家天下”,其内部的治理规则是礼治和德治。而礼治和德治能够有效实现的前提则是宗法封建秩序的稳定,也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能够持守各自的名分而各安其位。所以,孔子认为,如果由他来执掌一国之政,首先就是要“正名”。
“正名”一词出自《论语·子路》篇,其中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2](5445)对于“正名”这两个字的解释,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但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将“名”理解为“字”,所谓“正名”即“正字”。如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1](186)第二,从“名实”关系上理解“正名”,认为孔子在强调“名”与“实”的关系。如孙中原认为:“孔丘所谓‘名正’(名词概念正确)主要就是要求名称与实际一致,名实相符,即语词、概念与其所指对象一致。”[2](27)第三,把“名”理解为“名义”和“名分”。如杨伯峻根据《左传·成公二年》中孔子所说的“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认为“名”与“器”相对,二者分别指“名义”“名份”和“礼器”,“《论语》这一‘名’字应该和《左传》的这一‘名’字相同”[1](186)。第四,认为“正名”只是一个“虚壳”的语言问题,与“名分”和“名实”并无天然关系,“只是在历史上孔子第一个意识到了语言对政治的重要性”,“言语之不统一会导致政治的不统一”[3]。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确存在着“言语之不统一”的问题,但是在一国之内,特别是像卫国这样的国家,语言上应该是统一的,所以从语言来理解“正名”并不准确。孔子是在回答如何在卫国为政的问题时提出的“正名”,这是理解“正名”的关键。在春秋初期,卫国就先后发生过臣弑君①、君杀长立幼②等名位混乱的现象,导致国运衰颓,从一个强盛的大国沦落为大国的附庸。因此,“正名”并不只是简单的语言上的“虚壳”,而是确有所指。所以从“正名”一词出现的语境来看,杨伯峻的观点更符合孔子的本意。
在《论语》中,孔子之所以提出“正名”的观点,源于子路的问题,即如何“为政”。而在此问之前,还有两问,分别是“子路问政”和“仲弓为季氏宰,问政”。由此可断定,孔子的“正名”,与“政”密切相关。然而,子路对孔子的回答并不满意,于是又展开了新一轮对话。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孔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2](5445)
很显然,子路认为孔子为政首先强调“正名”是迂腐的,这反映了春秋末期人们面对礼乐崩坏和名位失序的局势,对于王不像王、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子路会说“子之迂也”。但孔子却认为,正是由于“名”的“不正”,才出现了“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的情况,造成天下的混乱,而君子“名”正则自然“可言”,然后“言”自然“可行”。对此,朱熹说:“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乱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5](143)朱熹的分析是很准确的,虽然说的是卫国的情况,但也是春秋时期的社会实际。因此孔子的“正名”说所要表达的就是:人如果都能各安其位,说与其职位相符的话,干与其职位相符的事,则天下就自然安定了。所以就有孔子在齐景公问政时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5438)。而这种理论必然的走向,就是通过“正名”实现“一匡天下”。
孔子试图通过“正名”实现“一匡天下”的理想,在《春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春秋》是孔子以鲁国历史为主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记载了发生在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历史事件。钱穆先生认为:“《春秋》既不是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6](17)孔子修订的《春秋》,言简意赅而含义隽永,饱含着他的思想旨趣,暗含着他的褒贬之意,在后世被称为“春秋笔法”。而“正名”作为孔子的主张之一,在其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尊王。《春秋》开篇即言:“元年春王正月。”[2](4765)此处元年指的是鲁隐公元年,春是指春季,王正月是指周王历的第一月。第二,不记载违反礼制的事情。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了三月和五月发生的历史事件,而忽略了四月,但在《左传·隐公元年》中明确记载了“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2](3724)。第三,坚持西周的爵禄制度,用周王分封爵位称呼各诸侯。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先称王,后吴、越两国的国君也称王,但孔子在《春秋》中仍然用他们原来的爵位称呼他们。如《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 盂。”[2](3930)这三个方面都反映出孔子试图以“正名”匡正天下秩序的美好愿望。
总的来看,孔子希望通过“正名”来“一匡天下”,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自天子以至于诸侯、卿大夫、士、庶人都各安其位,言其所当言、用其所当用、行其所当行。如此,天下则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核心,层级分明、秩序稳定的“合多为一”(多仍旧在)的“大一统”社会。孔子的这种主张,奠定了后世儒学发展的基本格调。
二、孟子的天下“定于一”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远比孔子生活的年代更为动荡。此时的周王室已无任何权威可言,只剩苟延残喘之势,而各强国的国君也相继称王,不断地进行武力的兼并扩张。面对此种情况,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希望“一匡天下”的理想,提出了通过行“仁政”而实现天下“定于一”的主张。
孟子在一次拜见过梁襄王之后,对身边的人说:
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2](5807)
孟子和梁襄王的这段对话首先谈到了天下统一的问题,其次是如何统一的问题。就前者而言,表达的是孟子渴望结束列国相争,实现天下统一、社会太平的理想;而后者,反映的是孟子的政治主张,即实行“仁政”,通过“不嗜杀”而实现统一,这与孔子主张通过“正名”实现国家的治理和王权秩序的稳定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名义上还受到各诸侯国的尊重,而且尊王攘夷的大旗还没有完全倒下。但是到了战国中期,周王室在各诸侯国面前已经毫无权威可言,甚至沦为附庸,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同时,各强国已经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吞并他国而夺取天下,因此发动的战争也比春秋时期更为残酷。如孟子所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2](592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梁惠王“天下恶乎定”之问,也有了孟子通过“不嗜杀”达到天下“定于一”的主张。而孟子的观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孔子倡导的王道理想的一种适应性发展。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继承了西周“以德配天”的“德治”主张,认为王道以德胜,而霸道以力胜,并崇王而抑霸。孟子通过“不嗜杀”而实现天下“定于一”的主张,是儒家王道理想的一种表现。因此,有学者认为:“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6]而儒家王道理想的核心,也正是通过施行文的“仁政”,以德服人,进而实现社会大治、天下太平。其中,“仁”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居于统治地位的君主要有“仁”,而且治理国家必需推行“仁政”。
儒家的“仁”由孔子首倡,而“仁政”是孟子对孔子“仁”的进一步发展和推进。孟子认为,“仁者无敌”[2](5800),只有实行“仁政”的人,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2](5909),“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2](6037)。而在孟子看来,“仁政”之所以有这样的功用在于它是以德服人、爱民、爱物,能使人心悦诚服;能够施行“仁政”的统治者,人民归顺他就像“水之就下”,所以他将无敌于天下。这种主张显然与孔子所称赞的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而“一匡天下”的“如其仁”是不同的,其中预设了天下应由能行“仁政”之君重建统一的理论前提。
具体而言,孟子的“仁政”包括:“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2](5800)这句话是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如何对付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时说的。在孟子眼里,秦国和楚国皆为蛮夷,不行王道,所以终其一生也没去过这两个国家。他主要把施行“仁政”的希望寄托于魏国和齐国,所以劝说梁惠王轻徭薄赋,减轻刑罚,鼓励百姓深耕细作,同时教导他们孝悌忠信之义;而君王只要实施这样的“仁政”,那么天下的人心都将归顺于他,即使让百姓们拿着木棒也可以战胜秦楚两国的坚甲利兵,实现天下的统一。
另外,孟子崇尚“仁政”而反对“嗜杀”,并不代表他完全反对武力。孟子所谓“不嗜杀”的意思是不好杀,即不以征战杀伐为乐。而在必要的时候,孟子也是主张使用武力的,这主要表现为讨伐残暴不仁者。此时讨伐的军队,孟子称之为仁义之师,而以仁义之师讨伐不仁者,就如商汤伐夏桀、周武讨殷纣,是“顺乎天而应乎人”[2](124)的正义之举。因此,孟子所谓的“不嗜杀”,“其实是站在同情百姓的立场,反对违背正义的战争”[8]。所以,在孟子的眼里,只有实施“仁政”,能兴正义之师的君王,才具有使天下“定于一”的资格。
三、荀子的“一天下”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生活于战国中晚期。荀子和孟子虽然同为儒家,都上尊孔子,但二人的思想主张却有很多相异之处,如:孟子持性善论,荀子持性恶论;孟子强调“法先王”,荀子强调“法后王”。尽管如此,在主张天下“大一统”的方面,二人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荀子主张“一天下”和“天下为一”。
“一天下”在《荀子》中一共出现了13次,主要集中在《非十二子》《儒效》《王制》《王霸》《强国》《礼论》等篇,例如:
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9](114)。
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9](162−164)。
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于是矣[9](202−204)。
与“一天下”意思相同的还有“天下为一”,在《荀子》中有7次,分别出现在《儒效》《王霸》《君道》《致士》《致士》《正论》《成相》等篇,例如:
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9](167)。
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敌[9](279)。
古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他故焉,能凝之也[9](343)。
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9](388)
主诚听之,天下为一,海内宾[9](541)。
从以上可以看出,“天下为一”多与“诸侯为臣”相对,而且有多处是在称颂商汤与周武王。这说明,荀子“一天下”的观点,与他对商汤和周武王的认知是紧密相关的。而后世称荀子“法后王”的“后王”,所指的应该是商汤与周武王,不同于孟子所颂扬的“先王”尧和舜。
在荀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相继完成了政治经济改革,原来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解体,各国在内部开始以郡县制取代原来的封建制,在外部则积极进行领土的兼并与扩张。郡县制下的地方长官,由国君统一任命,且有一定的任职期限和考核标准,这就使国家内部的权力集于君主一身,能够调动更多的力量进行对外战争。而随着战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升级,小国被大国兼并瓜分,政治、经济、军事优势渐渐集中到几个大国手中,天下统于一的趋向也越来越明显。荀子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提出“一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9](82),并在制度上和思想上对于即将到来的天下“大一统”进行了构想。
在制度方面,荀子非常重视“礼”的准绳作用。“礼”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凡儒士没有不讲“礼”的,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却又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孟子和荀子都言“礼”,但孔、孟侧重于倡扬周代的礼乐传统及其所具有的道德教化意义,以及通过“礼”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与文化理想;荀子则偏向于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对“礼”在政府中的组织模式、运行方式以及其在政治原则中的作用非常重视。荀子曰:“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大夫。”[9](175−180)这显然是以是否有“礼”、知“礼”为基本原则和标准,定上下等级之分,而不是按照人的出身。以此作为人才选拔的标准,则是对封建制度下的世卿世禄的一种否定,反映了战国中后期郡县制开始取代封建制的历史发展趋势。
对于具体的“礼制”,荀子也有深入论述。以官僚制度为例,荀子将其区分为“士大夫”和“官人百吏”两个层次。“士大夫”的主要职能在于“志行修,临官治”,如此“上则能顺下,下则能保其职”,这是他们能够获得田邑的合理依据[9](69);“官人百吏”则主要负责“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如此则“三代虽亡,治法犹存”,这是他们可以获取俸禄的合理依据[9](69)。此外,荀子还说:“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百吏之事也。”[9](262)这些都是荀子对于“礼”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设想和构思,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对此,白奚认为:“荀子发挥、充实了‘礼’的制度方面的意义和内容,其礼治的思想中既贯注了孔孟儒家的政治理念,又充实了王政、王制的具体内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十分适合酝酿中的大一统王权政治的需要。”[10]
在思想方面,荀子认为要结束“百家异说”,实现“齐言行,壹统类”[9](112)的思想大一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和诸侯相伐的加剧,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诸侯以力相争的情况不同,诸子百家则是以言相争。诚如孟子所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2](5903)孟子所谓的“邪说”,概指儒家之外的其他学说,并将礼乐秩序的混乱与“邪说”的盛行等同起来。对于此种情况,荀子则称之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9](456)。而“随着七国争雄局面走向统一,诸子争鸣局面也应趋向思想上的一致”[9](199),于是也就有了荀子“齐言行,壹统类”的主张。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当时流行的诸子之说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9](105−107)以对慎到、田骈的批评为例,荀子认为:“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9](109−110)在荀子看来,能够“经国定分”的,只有他所崇尚的儒家“礼治”传统,但他并不是盲目地推崇周礼,而是综合众家之说,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为己所用,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援法入礼”和“以法释礼”。
荀子“援法入礼”的行为,实现了儒、法两家学说的优势互补,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帝国提供了有效的治国方案,经汉代儒士的阐扬,被统治者所奉行。但必须注意的是,荀子虽然使“礼法”结合,但是还是以“礼”为主,以“法”为辅。因为在先秦儒家的认知里,“礼”始终代表着王道,而“法”始终代表着霸道,而“崇王抑霸”则是他们的共同主张。正如韦政通所说,荀子所持有的“礼仪之统”,“是他全副精神所倾注的重心,也是他各部分思想所辐射的焦点”,而“这个重心,这个焦点,是荀子一生思想活动的结晶,也是他时刻不能忘怀的”[10](280)。所以,荀子作为儒家的代表,当然还是以坚持孔子的王道理想为本,这也是理解荀子大一统思想的关键所在。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荀子的大一统思想是“礼仪之统”,不同于孟子的“仁政”之统。
四、《公羊传》的“大一统”
《公羊传》是一部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著作,与《左传》《谷梁传》一起,合称“春秋三传”。根据杨伯峻先生的考证,“《左传》为先秦著作,最初是用西汉以前文字,如小篆或大篆写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先是口耳相传,到汉代写成定本”[13]。在文本的写作风格方面,晚清学者皮锡瑞认为:“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传》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14](19)与其他两传不同,以“兼传大义微言”为主的《公羊传》,其最为核心的思想则是从《春秋》中阐释出的“大一统”。
《公羊传》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为什么先言“元年春王正月”中,提出了“大一统”的观念。“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4765−4766)这里的文王,指周文王;“王正月”,指周代历法中春季的第一个月。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周王室颁布的王历,但是各诸侯在国内并未统一采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先秦诸侯各自为政的局势”,另一方面是由于“书写载体的不同性质导致”[15]。孔子在修订《春秋》的过程中,多次使用“元年春王正月”,一方面这是一个确定性的时间表达,另一方面也包含有尊重王统的意思,是以时间上的“一”来表示政治上的“一”。《公羊传》从中诠释出“大一统”的观念,是对先秦儒家自孔子以降强调尊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黄开国所说:“大一统有文王之正的理想性一面,也有尊王的现实性一面。”[16]但是,由于中国文字的多义性和概念界定的模糊性,有人着眼于“大”来理解“大一统”,也有人着眼于“统”来理解“大一统”,还有人纠结于“大一统”是强调“统一”还是“一统”的问题。
在古典文献中,“大”除了有“大小”之“大”的意思外,又通“太”和“泰”,有推崇或赞美的意思,还有使动的用法,即“以……为大”。如果单从“大一统”三个字来理解,很容易把其中的“大”理解为“大小”的“大”,这就可能将“大一统”与广大的疆域联系起来。杨念群就提出“‘大一统’的第一个意思是要树立一种正统的王道秩序”,而“要获得正统,王者不只要据有王位,还得拥有相当广大的疆域领域”[17]。
这一认识显然并不完全符合“大一统”提出的背景。“大一统”是《公羊传》在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时提出的,这里的王是指周文王,其中确实有正统性的含义在里面,但是与国家疆域的广大并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文王在位的时期,周还局于西部一隅,名义上是商王朝的属国。儒家推崇文王,在于文王之德,而非他在位时期国家疆域的大小问题。
在儒家眼里,正因为文王的德行,才使周享有了天命,获得了统治天下的正统地位。因此,蒋庆认为:“大一统的‘大’字不是形容词‘大小’之‘大’,而是动词‘尊大’之‘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推崇’的意思,大一统就是‘推崇一统’。”[18](352)刘家和则认为:“按《公羊传》文例,凡言“大”什么者,都是以什么为重大的意思。”[19](370)但无论是“推崇一统”,还是以“一统为大”,强调的都“一统”,二者的意思并无显著区别。而根据“大一统”在文本中的前后逻辑来看,它是在回答“何言乎王正月”的问题,因此将“大”理解为动词性的“推崇”或“以……为重大”更为合理。因为儒家自孔子起就有尊王的传统,而王又是天下的共主,天下只应有一个王,所以《公羊传》从“王正月”中诠释出“推崇一统”的意思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对于“大一统”中的“一统”是“统一”还是“一统”的分歧,可以理解为是“化多为一”还是“合多为一”。黄开国认为:“一统之义即统一,《公羊传》在一统前面加上一个‘大’字,是对统一的美好渴望与赞美。”[16]这是“化多为一”的代表。而刘家和则认为:“‘一统’不是化多(多不复存在)为一,而是合多(多仍旧在)为一。”[19](370)这是“合多为一”的代表。如果单从《公羊传》的文本内容来考虑,把“一统”理解为多仍旧存在的“合多为一”是合理的,因为“一”代指王,而“多”代指诸侯,所以“合多为一”就是以王为核心的各诸侯分列有序的“大一统”,这符合孔子重建西周封建礼乐等级秩序的理想和主张。然而,也不能简单地将“统一”的观点理解为是对“大一统”的“误解”[20]。因为任何一个概念,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如果只是把“一统”理解为“合多(多仍旧在)为一”,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西汉公羊学在“化多(多不复存在)为一”的武帝时期开始兴盛呢?而且《公羊传》本身也是成书于西汉时期。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一统”的理解,关键不在于是“化多为一”还是“合多为一”,而在于“一”。
先秦时期,“一”常常与“天下”联系在一起,表示“天下”归于“一”,这也是《公羊传》的主旨。葛荃认为:“传文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大一统’政治主旨,即要张大君权一统天下。”[21]而从“王者无外”“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和“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等表述来看,《公羊传》无不是在强调君权的“一”。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由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国社会是由“合多为一”走向了“化多为一”,也就是由分封制走向了郡县制,合起来说就是由分封的“一”变成了集权的“一”。在汉初虽然存在过“一”与“多”并在的状态,但是在公羊学思想的影响下,又“化多为一”。所以说,从《公羊传》的核心思想来看,将“一统”理解为“统一”也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从孔子的“一匡天下”,到孟子的天下“定于一”,再到荀子的“一天下”,最后至《公羊传》的“大一统”,说明先秦儒家在社会秩序方面对于“一”是非常重视的。在孔子那里,“一”主要表现为匡正天下秩序,重建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的礼乐文明,可以理解为“合多为一”。但是,经过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的发展,儒家在政治秩序方面对于“一”的认识,已经由“合多为一”向“化多为一”转变。这种转变与历史的发展同步,反映了从春秋至战国,诸侯之间的关系由尊王攘夷的争霸发展为兼并统一的历史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公羊传》通过解释《春秋》所阐发出的“大一统”,在表现形式上虽然给人一种“合多为一”的感觉,但是在内核上却是“化多为一”。或者说,为建立儒家理想的礼乐文明秩序,《公羊传》的着眼点根本不在于是“合多”还是“化多”,是“一统”还是“统一”,而在于以“一”为代表的王道秩序。为了追求理想的王道秩序,儒家之士是孜孜不倦的,任何试图挑战王道正统、危害天下秩序的人,都是他们挞伐的对象。如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汉初在以“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学开始复兴的情况下,中国历史的走向不是“合多为一”(多仍旧在)的封建大一统,而是“化多为一”(多不复存在)的郡县大一统。
注释:
① 《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② 《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急子(又称伋子)是卫宣公的长子。卫宣公听信宣姜与公子朔的构陷之词,派人在急子出使齐国的路上,将其杀死。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 孙中原. 中国逻辑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4] 曹峰. 孔子“正名”新考[J]. 文史哲, 2009(2): 61−69.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6]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7] 赵志浩.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J]. 理论与现代化, 2017(2): 55−59.
[8] 徐鸿, 解光宇. 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论[J]. 学术界, 2015(5): 162−169.
[9]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0] 白奚.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3(5): 20−27.
[11] 白寿彝. 上古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
[12] 韦政通. 荀子与古代哲学[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
[13] 杨伯峻. 《公羊传》和《穀梁传》[J]. 文史知识, 1982(8): 58−64.
[14] 皮锡瑞. 经学通论: 卷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5] 薛梦潇. 早期中国的纪时法与时间大一统[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2): 91−105.
[16] 黄开国. 《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J]. 齐鲁学刊, 2011(3): 5−9.
[17] 杨念群. “大一统”: 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J]. 南方文物, 2016(1): 12−15.
[18] 蒋庆. 公羊学引论[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19] 刘家和. 史学、经学与思想: 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0] 马卫东. 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J]. 文史哲, 2013(4): 118−129.
[21] 葛荃. 论《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政治思想[J]. 政治学研究, 1987(3): 67−70.
From “combining many into One” to “merging many into One”:Logic progression of pre-Qin Confucian Great Unification
LU Gaoxue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The core of pre-Qin Confucian Great Unification is kingship order, represented by “Yi” (One),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combining many into One” to “merging many into One.” Faced with the decline of imperial power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between numerous stat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onfucius hoped to correct the order of the world by rebuilding the etiquette and music civilization in West Zhou Dynasty, which indicates “combining many into One”. But by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in terms of political order, the Confucian cognition of “Yi” had changed from “combining many into One” to “merging many into One” after Mencius’ “setting the world in One” and Xuncius’ “Oneness under the sky”. But, the Great Unification inessentially indicates “merging many into One” which emphasizes the kingship order as “Yi”, although revealing a feeling of “combining many into One” in the form of express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study of Gong Yang, which is a representative of Confucianism, could flourish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the feudal system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Confucius; Mencius; Xuncius;; Great Unification
2018−03−06;
2018−06−1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视域下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研究”(14ZDA010);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06090154);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秦始皇政治合法性建构路径研究”(KYZZ16_0098)
路高学(1986—),男,河南新郑人,东南大学与日本东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联系邮箱:lugaosue@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5.005
B222
A
1672-3104(2018)05−0033−07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