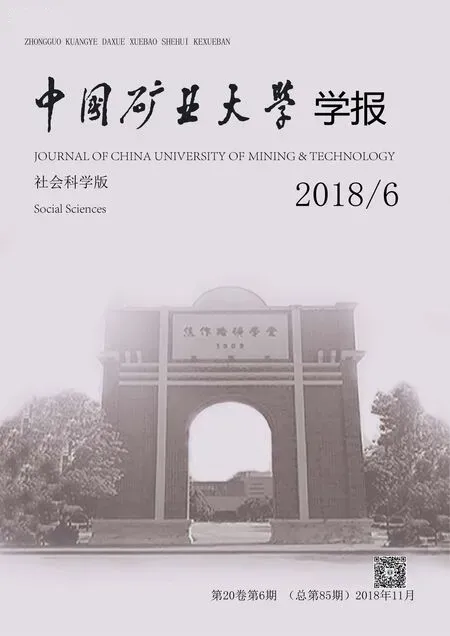改革开放四十年词学研究片论
2018-01-14薛玉坤
薛玉坤
近四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而逐渐复苏并繁荣起来的。四十年的研究历程,留下了太多值得回顾与反思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学术史的梳理,这样的回顾与反思,本身即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今后研究的起点和可能达到的高度。也正因为如此,相关工作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即以宏观的词学研究史著述而言,过去令笔者印象深刻并深受教益和启发的就有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刘扬忠《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王兆鹏《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进展和瞻望》,张宏生《清词研究的空间与视野》,朱惠国《民国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文。此外,更有如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曹辛华、张幼良《中国词学研究》等专著对20世纪词学研究进行全方位的总结。鉴于上述成果的丰富,本文无意、也无力对近四十年来词学研究的成败得失作全面的评述,仅就阅读与研究过程中个人的观察和思考,略呈管见,就教于方家。
一、 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学科队伍的壮大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向上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系列以“词学”为名的研究专著的问世。这些著作在理论上将词的研究与词的作法作了区隔,初步确立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基本范围。1933年4月,龙榆生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对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该刊常设栏目有论述、专著、遗著、辑佚、杂俎、近人词录、词林、文苑、通讯、杂缀、附录等,作者则囊括当时词学界一流人物,如夏敬观、夏承焘、梁启超、叶恭绰、唐圭璋、赵尊岳、王易、吴梅、陈匪石等,包括来自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重庆大学、之江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学者。而龙榆生本人在1934年《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刊载的《词学研究之商榷》一文,则显现出其明确的创立现代词学学科的意识。此文将词学研究分为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谱之学、声调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词史之学、批评之学八个方面,非常概要地揭示了词学研究的任务和范围,无疑对后世的词学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978年以来,词学研究者对词学研究的对象有了更为系统和明确的思考。1981年,唐圭璋与金启华两位先生合撰《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一文,从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与词学评论十个方面,梳理历代词学研究的得失,实际隐含了其对词学研究范围的厘定。1985年,吴熊和先生出版的《唐宋词通论》一书是至今仍对词学研究入门具有指导意义的一本专著。其最后一章《词学》对“今后词学研究”应努力的方向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建议:1. 评论唐宋各家词的论文集;2. 词人年谱、传记丛书;3. 汇集与研究唐宋音谱及词乐资料;4. 在清人《词律》《词谱》的基础上,重新编撰包括敦煌曲在内的《唐宋词调宗谱》;5. 汇辑唐宋词论、词话,成《唐宋词论词评汇编》;6. 总结历代词学成果,作《词学史》;7. 历代词籍目录版本,作《唐宋词籍总目提要》;8. 保举上述词家、词调、词籍条目,编纂《唐宋词词典》。在此基础上再完成完备的词史。1989年,刘扬忠先生出版的《宋词研究之路》,应该说是八十年代“方法论”思潮的产物,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视角,试图重新建构现代词学研究的体系。此书将词学研究分为基础工程与理论研究两个部分,基础工程又分为宋词音律文字格式研究、宋词基本资料的整理研究、宋词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理论研究部分则分为鉴赏和批评、宋词规律研究、宋词研究之研究。而每一部分又分成若干门类,如宋词规律研究分成外部规律研究和内部规律研究,内部规律又分为宋词的来源、宋词与音乐的关系、宋词的声情、宋词的艺术个性、宋词的风格流派、宋词的发展演变规律等等。可谓体大思精,在当时实具总结既往词学研究经验教训、完善现代词学学科的意义。2004年,王兆鹏《词学史料学》则从简明起见,将词学研究的范围确定为词体、词人、词集、词论、词史和词学史六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所论词史研究部分,除了传统的词的创作史研究之外,还增加进了词作传播史和接受史的研究[注]王兆鹏.词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词学史料学》一书是今天许多高校词学研究方向研究生培养的教材或重要参考资料,对当下以及今后词学研究的格局影响更为深广。
以上所述,加上引言提及胡明、严迪昌、刘扬忠、王兆鹏、张宏生、朱惠国等人所作的词学研究史的梳理,可以看成是几代学者对词学研究内涵的阶段性的思考和总结。对词学研究内涵的揭示自然是现代词学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专业研究队伍的成长则是学术研究正常开展、学术传统有效继承的有力保障,也是现代词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根本基础。
王兆鹏、刘学《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一文曾统计对比了1900-1978及1979-2000年词学研究的情况,统计结果表明:20世纪前78年的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仅为5294项,后22年则暴增为17615项;研究队伍方面,前78年有2967人,后22年则高达8563人,而从个体产出量来看,发表过10项以上成果的活跃作者,前78 年只有71 人,后22 年多达252 人,后者是前者的3倍[注]王兆鹏、刘学.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J].学术研究,2010(5):134.。如果加上21世纪以来的统计,则这一数字会更为惊人。
必须看到,近四十年来词学研究的繁荣、词学研究专业队伍的壮大,是几代词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当中首先是1978年以后“复出”的老一辈学者,如在民国时期即已从事词学研究并有丰富成果的唐圭璋、夏承焘等先生,尽管年事已高,这一时期仍然努力从事学术研究,并奉献出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和论文,同时,他们又认真培养词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为词学研究传续灯火,也为新时期词学学科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教育以后,由老一辈学者所培养的学生成为这四十年词学研究的真正中坚。四十年中,最早完成答辩的词学硕士论文在1981年,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世昌先生指导、刘扬忠撰写的《论周邦彦及清真词》,江西师范学院胡守仁先生指导、祝宗武撰写的《辛词艺术初探》,辽宁大学孟庆文先生指导、张高宽撰写的《论稼轩词的用典》,哈尔滨大学张志岳先生指导、胡新中撰写的《论梅溪词》,南京师范学院唐圭璋先生指导、杨海明撰写的《张炎论札》,华东师范大学马兴荣和万云骏先生指导、方智范撰写的《从张惠言到周济——试论常州词派词论及其发展》等;最早完成答辩的词学博士论文则在1985年,分别是扬州师范学院任中敏先生指导、王小盾撰写的《隋唐五代燕乐雅言歌辞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世昌先生指导、施议对撰写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等[注]王伟勇.中外词学硕博士论文索引[M].台北:里仁书局,2016.。第一批词学硕、博士中,尤以杨海明教授词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先后出版《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唐宋词史》《张炎词研究》《唐宋词纵横谈》《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等专著,后汇集为8册12卷近400万字的《杨海明词学文集》。此外,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人中,如夏承焘先生的弟子吴熊和先生,万云骏、马兴荣先生的弟子邓乔彬先生,吴世昌先生的弟子刘扬忠、施议对、陶文鹏,以及唐圭璋先生的弟子钟振振、王兆鹏等,后来都成为词学研究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左右着四十年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薪火相传,正是这种传承有序的词学教育,保证了词学研究的基本队伍。王伟勇《中外词学硕博士论文索引》(1935-2011)一书曾收集整理此间中外硕、博词学论文2560笔,其中1978年以来大陆地区即有1678笔。此书统计虽有疏漏,但正如王兆鹏、刘学《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一文所称:“我国大陆自1978年以来,高等学校大量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大批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人才。日益壮大的词学研究队伍, 其成员绝大部分来源于高等学校毕业的和在读的研究生。”[注]王兆鹏,刘学.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J].学术研究,2010(5):135.这表明,从学历层次上来讲,拥有学位、特别是博士学位的研究者正越来越成为词学研究队伍的主体。
需要思考的是,词学研究教育的系统化固然会让研究更加专业和规范,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专业化的另一面是否会带来知识结构的“窄化”?规范化的另一面是否会带来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固化”?因为和老一辈学者相比,今天的研究者深受学科分野日趋细化的影响,研究词的,往往不会专门去研究诗和曲,研究唐宋词的,也不太会去关注明词、清词和近现代词。这样的研究或许会在“专精”方面有所收获,但很难做到“融会贯通”,从而最终影响到词学研究的整体推进。须知词体本身并非是历史的独行侠,其发展变迁向来受到其他文体如诗和曲,其他艺术样式如音乐,以及经济、民俗、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除了高学历的研究者日趋成为主体外,词学研究队伍的“女性化”似乎也正逐渐成为一个趋势,并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增强之中。考虑到词体本身的“女性化”特质,或使其更易受到女性的青睐,以及词学研究人才培养体系中女性生源正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则研究队伍的“女性化”应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但男女在思维、兴趣等方面的差异,会对词学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样是词学学科建设不应被轻忽的问题。
近四十年词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各级词学学术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对开展学术活动、交流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也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除了各地相继成立的词人专门研究会,如欧阳修研究会、苏轼研究会、秦少游学术研究会、李清照辛弃疾学会、陆游研究会等等,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词学讨论会上,就已经倡议并选举产生了中国词学会筹委会[注]邓乔彬.首届词学讨论会召开[J].文学遗产,1984(1):153.。词学前辈夏承焘先生、唐圭璋先生、任半塘先生都曾担任过词学会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词学学会正式成立,活动渐趋正常化、规范化,两年一次的年会,至2018年已举办了八届。规范、持久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增强了中国词学学会的凝聚力、感召力,另一方面,也为词学研究的长久繁荣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 思想、观念与方法的创新
新的研究思想、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往往能带来学术研究的裂变,现代词学学科之所以能摆脱传统词学的束缚而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正是得益于此。正如刘扬忠先生在《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中所提出的那样: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熏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注]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J].文学遗产,1999(3):2.。
1978年以前的二三十年内,词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决定论、庸俗社会学与阶级分析模式的左右,研究思想僵化、研究方法单一。改革开放以后,在新的学术环境中,研究者开始在新的研究思想指导下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带动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又一次转型。如杨海明教授的《唐宋词风格论》是新时期词学界有关词体风格流派的第一部著作,刘扬忠先生1995年撰写的《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一文认为:“这本简论性著作还带有初创和尝试的性质,而且至今仍是唯一,我们希望看到较多的继轨之作问世,以使词的风格流派学形成一定的规模。”[注]刘扬忠.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J].文学评论,1995(4):146.又如杨海明教授的《唐宋词史》被称为当代词学研究“断代词史中问世时间最早,学术转型意义最显著”的著作,“凭借开放的思维方式、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创新色彩较浓的体系,建构出词史研究和表述的新框架,打破了仅以时间为序平面排列词人词作的旧词史框架”[注]刘扬忠.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纂[J].文学遗产,2000(6):127.;而对其《唐宋词论稿》,王兆鹏认为:“近年来,文学研究提倡多元的方法、多维的视角、主体的观照,《论稿》为此提供了一种范式。它不仅对唐宋词学研究,就是对处于‘危机’‘低谷’中的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也同样具有启示性和参考价值。……(《论稿》)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对唐宋词进行了新的立体观照,标志着唐宋词研究‘未来时’的开端。”[注]王兆鹏.对唐宋词的立体观照——评《唐宋词论稿》[J].苏州大学学报,1990(3):135.
当然,新思想、新方法带来的词学研究转型,并非仅有杨海明教授这一个案。审视四十年来词学研究的脉络,那些具有突破和指引词学研究方向性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自觉的产物。笔者个人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词学研究空间维度的重视。文学研究的空间视角和方法在我国本有非常悠久的传统,但在现代词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我们仍习惯从时间的维度上去描述词人、词作以及各种词学现象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不同时代词体的继承和差异。直到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和观念的解放,将词学置于空间的维度下进行研究开始重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词学研究的现象。
早期的如唐圭璋先生对两宋词人的占籍研究[注]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M]∥宋词四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16.、文化地理学家陈振祥对北宋词人地理分布的研究[注]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3.,都曾经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1984年,杨海明教授更是大胆提出,唐宋词(就其主流的婉约型作品而言)从主体来讲属于“南方文学”的范畴[注]杨海明.试论宋词所带有的“南方文学”特色[J].学术月刊,1984(1):57.,其后又曾对这个观点加以补充性的阐发,认为水之“钟秀”于词,功莫大焉,“烟水迷离”帮助造就了词境的柔美性,“斜桥红袖”帮助造就了词情的香艳性,“江南小气”帮助造就了词风的软弱性[注]杨海明.试论唐宋词中的“南国情味”[J].文学遗产,1987(1):59.。此后,金诤又“从历史上南北经济文化变迁及地域文化特点等方面阐述词的体制风格特征和源流发展演变过程,强调运河——江南经济发展居于全国主导地位与词体之兴的密切关系,指出词是一种典型的南方文化风情的文学体裁,词的兴起标志着自晚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黄河流域南移长江流域的总体历史状况。”[注]金诤.宋词综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1:1.而笔者和陈未鹏也受此启发,先后撰写完成博士论文《区域文化视野中的宋词研究——以江南区域为中心》(2003)、《宋词与地域文化》(2008)。
严迪昌先生1991年出版的《清词史》是一部以新思想、新方法观照清词流变的力作,其中即有大量篇幅是从文化文学地理的角度去论述广陵词人群、阳羡词人群、梁溪词人群、杭嘉湖词人群、吴中词人群、宛陵词人群的构成和历史地位,实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我们看到,近年从空间角度切入清词研究的著述大多受其泽溉,如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谢永芳《广东近世词坛研究》、陈雪军《梅里词派研究》、李康化《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究》、袁志成《晚清民国福建词坛研究》等,而以空间角度切入词学研究的硕、博论文选题更是不一而足。
而随着相关研究的日渐丰富,从学理上总结文学地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心。这一方面的研究,以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地理学概论》及杨义、邹建军等人的探讨为代表。这些研究,虽然并不主要针对词学而言,但毫无疑问对词学研究具有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作用。我们只要看到从空间维度切入词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每每引用上述诸人的论述,即可明白这一点。
第二,史学观的变迁与词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曾经非常流行宏大叙事式的书写方式,文学史家往往醉心于文学史宏观演变规律的揭示,多钟情于文学史中的所谓“一流”作家,相信只有揭示规律,书写“一流”作家,才能建构起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其作为史家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与洞悉历史的眼光。这种研究追求的是对作家和文学史变迁作定性的判断,而那些所谓的二流、三流作家和所谓“宏观规律”之外的日常、底层的文学事件,通常只能作为一个附庸者,甚至被直接抹去身影。
1989年,王兆鹏教授《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一文,借用西方社会学的“范式”理论,将唐宋词的演变史浓缩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与“清真范式”三大范式的相互更迭,认为:“‘花间范式’自晚唐五代花间词人,经宋初晏殊、欧阳修诸人的发展,到晏几道而臻极善。柳永崛起词坛,打破了‘花间范式’的一统天下,但他没有建立起一种为词坛所普遍接受的完善的范式。他的成就一方面被苏轼接过去创立了‘东坡范式’,另一方面则被周邦彦发展为‘清真范式’。自柳永之后,宋词的发展可说是二水分流,即‘东坡范式’与‘清真范式’的分流发展。两条曲线此起彼伏,时或靠近,时或交叉,时或分离。‘东坡范式’经南渡初张元干、叶梦得、朱敦儒、向子諲等人的发展,到辛弃疾而达高峰,此后日益式微。而北方的金元词坛,效法‘东坡范式’则历久不衰,至元好问为一总的集结。‘清真范式’在南渡初相对沉寂,到姜夔日趋完善,此后吴文英又作变化,自此成为词坛主流。”[注]王兆鹏.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J].文学遗产,1989(5):20.这一论述策略在其后来出版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唐宋词史论》等著作中得到继续贯彻,并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一史观作了系统提升。以我个人的理解,王兆鹏教授词学研究“范式”理论的提出,大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的二次东进,而上述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宏大史观,恐是更为直接的诱因。“范式”理论提出后,在当时大有“新天下耳目”的效应。直至今日,这一理论仍然影响着人们对唐宋词史变迁的认知,以及词史研究的表述模式,显示出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词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更加多元。其中,历史研究向日常生活史研究或微观史学的转向也开始影响到词学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学原本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又称为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不同的是,微观史学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哪怕是庸常生活琐事都自具其意义。它不像宏观史学那样总是在长时段、大跨度的宏观视野中试图去揭示历史演变的规律,并努力藉此规律去理解和解释未来。相较而言,它更倾向对历史的“细节”和“过程”作某种“碎片化”的描述。因此,举凡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生与死、爱与憎、健康与疾病等等,都可以成为微观史学的研究内容。这样的史观应用到词学研究领域,就使得过去在宏观史学视野中消失的中小词人、无足轻重的词学事件,得到了同等的关注。黄杰《宋词与民俗》、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程继红《带湖与瓢泉——辛弃疾在信州日常生活研究》、韩梅《唐宋词与唐宋文人日常生活》(浙江大学博士论文)、杜运威《抗战词坛研究——以晚清词史相关现象为背景》(吉林大学博士论文)等都是非常可贵的尝试。
第三,独领风骚的词学定量分析以及词学传播和接受研究。应该来说,王兆鹏教授是近四十年来词学研究领域创新意识最强的研究者,除前述“范式”理论的提出,主要由其参与开创的词学定量分析及词学传播和接受研究,引领着词学研究的方向,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气象。这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词学研究,不妨可以称之为“王兆鹏现象”。
1995年,由王兆鹏、刘尊明联合撰写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注]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J].文学遗产,1995(4):47.一文,开创了国内利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词学的先河,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该文以六个方面的数据资料作为统计基础,从宋代词人三百家、词人地位与词作数量的关系、十大词人的历史定位、词评家与词选家的异同、古今变异与本世纪词学研究的走向五个方面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并总结出三点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沿此研究路径,此后王兆鹏、刘尊明还撰写了《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等文。进入新世纪,王兆鹏和他的学术团队的词学定量研究又有了不小的推进,相关手段的运用更加成熟,计算模型也更加合理,并在2012年出版了词学定量分析的集大成之作《宋词排行榜》与《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二书。虽然词学定量分析的方法自问世便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定量分析既可为传统的感性判断提供验证式的证明,更能在统计中发现差异,凸显问题,拓展新的学术研究空间。二十余年来,受其引领,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词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成为词学研究领域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
成为词学研究潮流的还有词的传播和接受研究。从1993年起,王兆鹏教授陆续发表了《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等文,既有对文学传播和接受研究的学理探讨,亦有具体传播和接受问题研究的操作示范,很快带来了词学研究的另一大热点,各类著作、硕博论文、期刊论文层出不穷,或整体,或个案,或通代,或断代,乱花渐欲迷人眼。如钱锡生《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一书考察了唐宋词的歌唱、吟诵、手写、题壁、石刻、印刷等传播方式,并在宏观上将唐宋词的传播方式和唐宋词的历史演进作了融合;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在考察宋词各种传播方式之外,还专门探讨了售卖、传抄、驿递三种传播途径,以及传播过程中误传和失传两种现象;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则兼顾“传播”和“接受”两个层面,将唐宋词置于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特殊时期进行考察;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刘双琴《六一词接受史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陈景周《苏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专题研究论稿》、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娄美华《梦窗词接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等则是对词人接受和传播的个案研究。
事实上,定量分析与传播和接受研究是相互牵扯的两种研究方式。审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定量分析指向的常常是传播和接受问题,传播和接受研究过程中也常常用到定量分析的方法。笔者以为,两者背后共同的理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中国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接受者(读者)在作品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主张文学研究应该关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这显然与定量分析及传播和接受研究的关注点有相通之处。
四十年来,研究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每一次创新,每每都能带来词学研究的一次飞跃。而下一次的飞跃,或许将会出现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应用之后,这应该是值得期待的词学研究新格局。
三、 余论
以上所论,只是笔者个人观察和感受最深的两点。事实上,相较于传统而言,近四十年来词学研究所呈现出的新气象、新格局,确有许多令人称道的地方。其他诸如词学基本文献的整理,清词研究的全面深化,明词研究的拓荒,民国词研究的异军突起,域外词学受到关注等等,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特别是《全清词》的陆续出版,堪称这四十年最具标志性的词学研究成果。
当然,四十年的词学研究也并非没有留下遗憾,特别是作为音乐文体的词体,龙榆生当年提出的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谱之学、声调之学,总体上进展缓慢。除了施议对先生《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刘崇德先生《姜夔与宋代词乐》《燕乐新说:唐宋宫廷燕乐与词曲音乐研究》之外,中青年学者中似乎只有田玉琪教授在踽踽独行,近年奉献了《词调史研究》[注]田玉琪.词调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编纂》[注]田玉琪.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编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北宋词谱》[注]田玉琪.北宋词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8.等佳作。此外,朱惠国教授正在承担“《明清词谱研究》与《词律》《钦定词谱》修定”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相信有关成果的涌现指日可待。
以词的声调之学研究来说,在词乐失传之后,讨论词的音乐和情感关系,事实上已失去了根基。正如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所云:
词为声学,而大晟遗谱,早已荡为云烟。即《白石道人歌曲》旁缀音谱,经近代学者之钩稽考索,亦不能规复宋人歌词之旧,重被管弦。则吾人今日研究唐、宋歌词,仍不得不以诸大家之制作为标准。词虽脱离音乐,而要不能不承认其为最富于音乐性之文学。即其句度之参差长短,与语调之疾徐轻重,叶韵之疏密清浊,比类而推求之,其曲中所表之声情,必犹可睹[注]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C].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96.。
换言之,讨论词的原始音乐和情感的关系虽不可能,但仍然可以依靠“句度之参差长短,与语调之疾徐轻重,叶韵之疏密清浊”等文本因素,去体会词的声情特点。此后,其《词学十讲》又从选调和选韵、句度长短、韵位安排、对偶、结构、四声阴阳等方面对如何研究词的声情关系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应该来说,龙榆生已经建立起了比较严密的声调之学的理论体系,可惜在过去这四十年的词学研究中,这一宝贵遗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遑论发扬光大。今后如何深入文本内部,讨论包括声情关系在内的诸多文体特征,对词作真正的本体研究,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大的精力。
总之,近四十年的词学研究,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学术史经验,这理应成为未来词学研究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