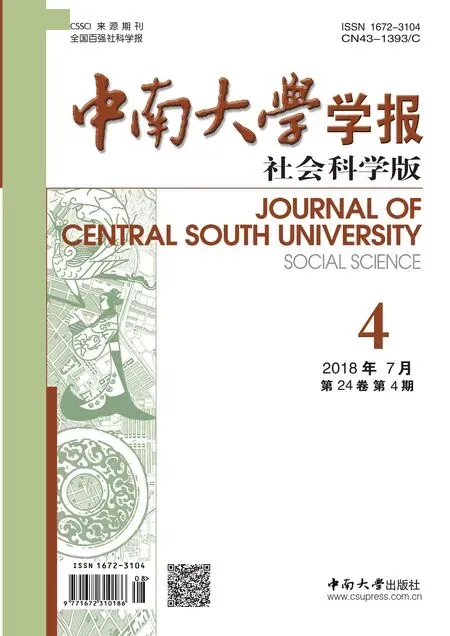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以译代作”现象(1966—1976)
2018-01-14杨东伟
杨东伟
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以译代作”现象(1966—1976)
杨东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在1966—1976年间,一批创作受到限制的诗人以诗歌翻译的方式代替诗歌创作(简称“以译代作”)。这些作品呈现出迥异的文化特质,一部分译作在主流文化视野的掩饰之下,通过译文内容隐晦地表现译者的情思;另一部分译作则完全摆脱了当时的美学束缚。诗人们通过这种“以译代作”的方式迂回地展示出他们在当时的语境中无法表达的各种现实愿望和艺术诉求。同时,也展示了当代诗人在“公共空间”之外的“潜在形象”,承续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并提供了另外一种更加曲折的“言说范式”。从译介学的角度观照和评价“以译代作”现象,能够进一步彰显它应有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史价值。
“文革”语境;以译代作;翻译诗歌;艺术坚守;知识分子精神
现代汉语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诗歌构成了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新诗传统的确立与历史建构都伴随着也依赖于“翻译”这种跨语际的艺术实践。总体来看,20世纪的新诗创作与诗歌翻译在相互映照、相互激发和相互支撑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寻求着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学生态。然而,时间进入当代之后,尤其是在1966—1976 年间,政治的收缩既划定了作家们的命运,又在无形之中改变了诗歌创作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文学创作和翻译都受到了意识形态的严格管控,与此同时,大多数的诗歌翻译也必须遵守既定的政治标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许多严谨而正统的诗歌翻译实质上缺乏活力与生机,也较少能为当时的诗歌创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但任何时代逆境都不能摧折追寻自由的灵魂。在这异常艰难的十年间(1966—1976)就出现了一种“以译代作”的文学现象。这是一批创作遭到官方严格限制或完全失去写作和发表权利的诗人们,如郭沫若、穆旦、何其芳、冯至、施蛰存。当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的一切表达渠道都被封堵,任何常规的文学形式都无法真实地表现自己之时,便选择以诗歌翻译的方式代替诗歌创作来吐露他们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无法表达的现实愿望和艺术诉求。诗人们通过这种“以译代作”的写作方式隐晦地突破了当时主流话语对文学的限制,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中艰难地发出知识分子真实的声音。也正是这种“以译代作”现象,记录了诗人们在特殊年代幽微的精神状态,展示了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
一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艺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1](3),文学的政治话语空前浓厚。进入“文革”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不断加强以及阶级斗争的不断强化,许多诗人或创作遭遇限制,或完全失去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而且生存受到巨大的威胁。在这种境遇下,一些诗人转而选择用诗歌翻译的形式代替诗歌创作。冯至在1973年“怀着激愤的心情翻译了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2](146);郭沫若在痛失两位爱子的情况下,翻译《英诗译稿》时“并没有想到过这本译稿的出 版”[3](146);穆旦翻译《英国现代诗选》也“纯粹是一种真正的爱好”“并不知道还有发表的可能”[4](332);何其芳强忍着身体的病痛和精神的折磨自学德语,并翻译海涅、维尔特等人的诗作,只是为了“不辜负我所经历的生活和我们承受的中外文学遗产”[5](32);施蛰存则怀着炙热的心,“想编译外国诗选”[6](2),却不料译稿也被红卫兵“抄走”了。这些作品大都是诗人们在严酷的环境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私译”的。然而,有些译作还没来得及等到公开出版,译者却溘然长逝。
这样的“以译代作”既是一种绝境求生的翻译行为,又是拯救自我的写作行动。因为“写作的不可能”而走向“翻译的可能”,这些诗人们都将诗歌翻译当作最后的归宿和安身立命之所。无论他们这一生多么坎坷,最终还是回到了诗歌,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即使是以翻译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从纵深的视野来看,他们创作命运的终结和翻译命运的“发生”正好形成了一种文学上的对接。在被时代终结了文学表达的命运之后,他们通过“以译代作”这种更迂回的“创作方式”承续文学抒写真情实感和表达现实关怀的重要功能。他们力图恢复文学应有的尊严,同时保持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集中展现出特殊年代的诗人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的困境中所做出的“反抗绝望式”的精神突围。他们试图突破自己在生命与写作中所遭遇的重重禁锢,也尝试超越时代的局限,去追寻文学自我救赎的可能。由于这些翻译文本都产生于一种较为密闭的空间,大多数译本的存在并不为当时的文坛所知,因而,它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主流话语的疏离,还显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和气质。
首先,部分译作在主流文化视野的过滤和掩饰之下,通过译文内容隐晦地表现译者情思。“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无论是建构还是批判都必须被规范到主流文化视野范围之内才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在这种前提下,上述诗人们也选择了主流诗学所推崇和称赞的作家或诗人的作品来翻译。实质上,这种选择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了迎合主流标准和价值取向,也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外国文学资源缺乏,而是这些译者们将主流的文学规范作为一种过滤网和保护伞。在这种“文化幕布”的保护之下,试图在译本内部开掘更有效的言说空间。在当时的语境中,这是一种相当隐晦且有可能只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翻译意图和路径。它的复杂性在于,既要在主流政治承认和允许的范围之内选择外国诗歌,又要在翻译的内容上和过程中苦心经营以使得译本能够代替译者表现“被压抑的情思”,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与主流话语的对话关系,进而表现出对它的审视与反思。
何其芳和冯至的诗歌翻译倾向于这种类型。何其芳有较坚实的英语基础,而且能够读懂法文作品,但在“文革”期间却历经千辛万苦自学德语去翻译海涅和维尔特的作品。何其芳之所以选择这两位诗人,当然是因为他们都是德国民主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诗人,前者曾受到恩格斯的赞扬,后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除此之外,何其芳还“放出风声,说学德语是为了要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7](333),因为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何其芳的诗歌翻译才是合法且安全的,才不会授人以柄。而在接下来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何其芳借着这种隐性的庇护,独自用“翻译代替诗人创作,从而达到抒发译者自我情感的目的”[8]。诗人冯至翻译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同样出于这样的考量。在后来的出版序言中,冯至用大量的篇幅申述了海涅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冯至认为,“马克思给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很高的评价”,而且“马克思离开了巴黎后还很关心《童 话》”[9](252),等等。这些有关二者关系的论述确实是事实的客观呈现,但我们未尝不能将其看作是诗人冯至对当初翻译这本诗集的合法性的某种追述和自我辩护。换言之,诗人当初在翻译之初就更倾向于他所熟悉的而且符合主流文学标准的海涅,这至少能使冯至的翻译看起来显得合情合理且合法,这也可确保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那么惶恐不安。通过这样的文化掩饰,诗人获得一种文学上的“豁免权”,也借此更好地隐藏起他翻译这部诗集的真实意图。
其次,部分诗人的译作则完全摆脱了当时的美学原则和政治标准对文学翻译的限制,呈现出与时代语境极不相符的诗歌翻译“奇观”。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以象征派、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文学思潮采取抵制的态度,对它们的译介基本完全停止。而施蛰存却陆续翻译起了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等人的诗作,并“打算译满一百首,编成一个集子”[6](2),穆旦更是偷偷译起了T.S.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的现代主义诗作。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诗歌翻译是对整个时代氛围和美学规范的全面超越,也是译者另一种“写作意识”的觉醒,一种无法向现实敞开却只能真诚地逼视自我、面对良知,因而也更深刻更内在的诗歌写作。
事实上,这些翻译诗歌彰显出诗人们清醒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的诗学意识。这种清醒和自觉体现在对当时文坛和文风的深刻认知上。在穆旦看来,“文革”时期,“假诗”和“伪诗”充斥着诗坛,这时期的诗歌“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10](150)。然而,“形式化、公式化代替不了个人的细微感觉”“标语口号、政论等等,永远也代替不了诗歌及文学”[10](160)。出于对“假大空”的厌恶与警惕以及对真诗歌的呼唤与憧憬,穆旦深知完全有必要引入诗歌翻译来涤荡这种“不正之风”。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读者会看到:原来诗可以如此写,这可以给他打开眼界,慢慢提高欣赏水平,只有广大水平提高了,诗创作水平才可以提高。”[10](150)所以穆旦才会着手翻译后来被命名为《英国现代诗选》的外国诗歌作品。在他心中,奥登、艾略特、叶芝才是真正能给时代的美学风貌和诗歌创作方式带来改变的人。这些诗人创作的现代主义的作品“来自对生活的深刻体会,不总用风花雪月的形象来表现”[10](182),它们像普希金那些伟大的诗作一样,“不只在形式,尤在内容,即诗思的深度上起作用”[10](148),给中国当代诗歌注入新的血液。诗人施蛰存的翻译行为和翻译内容无疑也表明了跟穆旦相似或相近的观念。正如诗人王家新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诗人译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翻译与他们所关注的创作和诗学问题深刻相关,和他们自身的需要及其对时代的深切关注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11]。
因此,无论是将主流文化作为掩饰翻译目的的保护伞,还是完全抛弃审美固有的条条框框重新为文学确立尺度,都是诗人译者们“对自己身处的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不满,利用其他系统的元素来实现自己的目的”[12](238),即用翻译的方式来达到创作的目的。他们利用译者自我的隐性主体意识“突破制约”(moving beyond the constraints),从而达到对中心文化的免疫和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并获得个人话语的表达自由。这既是对现存翻译系统的颠覆,又是对现存写作系统的某种突围。从文学自赎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诗人们“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们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们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11]而做的卓绝的努力。他们希望通过“以译代作”的方式与时代对话,向历史发声,也希望获得时代甚至后人的倾听与理解。
二
卞之琳先生曾在谈论何其芳的译诗活动时说:“我了解译诗的苦处,但是其中也自有一种‘替代性’的乐趣。”[13](238)这种“替代”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然就不止于文学层面的愉悦和“乐趣”,而是那个时代诗人们用翻译代替诗歌写作的独特形式,是一种写作策略与诗学隐喻。诗人们将多种写作诉求或隐或显地蕴藏在翻译的内容与形式之中,以获得文学上的“换气”。因而,揭示这些翻译文本究竟代替译者表达了哪些在当时无法坦露的心声,就成为研究“以译代作”现象的主要关注点。这既是我们深入理解翻译文本的有效途径,又是我们进入历史漩涡进而获取历史真相的最佳方式。本文将从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来探析作家们隐匿在翻译之中的“秘密”。
首先,部分译诗代替诗歌创作真实地再现了作家们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众所周知,由于政治规训的范围几乎覆盖了“文革”生活的每个角落,作家们的私人空间遭到极大的挤压。许多知识分子都无法在公开的写作中随意表露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私人情绪,尤其是一些负面情绪。在这种境遇中,作家们经常是有苦难言,也不敢言。这时翻译就可作为“替代性的补偿”成为作家们隐秘的抒情通道,部分诗人就通过翻译外国诗歌来表现自我的艰难处境。
一些诗人通过“以译代作”展现自己在时代语境中的命运处境。郭沫若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的《给人生》一诗,开头写道:“人生带着个凄凉的面孔/我不想看到你的尊容/你的肮脏外套, 跛脚行动/你那过于做作的轻松。”这“凄凉的面孔”正是郭沫若在“文革”中的真实写照:他连失二子但无人可以倾诉,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自身难保,外套肮脏、行动跛脚的描绘则是一种形象化的展示。虽然如此艰难,但他还必须做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郭沫若遭遇的人生酸楚尽在这首翻译作品中。诗歌的最后一节尤为重要:“我将和你合演哑剧/从早到晚都不声张/对这假扮的幕间剧/我也装得来相信一样。”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历史真相:时代文化迫使个体配合演出着“哑剧”,诗人自己也只能“从早到晚都不声张”,但他的内心始终澄明而清醒,一个“装”字透露出他的不信任。诗人也曾意味深长地对他人说:“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大家都恢复赤子之心吧!”[14]这种追求真诚的愿望与当时“假大空”的现状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多数时候诗人不得不将自己的爱与恨以及内心深处的悲哀、愤懑和激情默默藏在心底。何其芳的译诗《现在到哪儿去?》则表现了知识分子被弃绝后无路可走的“精神迷失”,他们如同一群孤魂野鬼“迷失在人世间的扰攘和忙碌”中,找不到灵魂的归宿与安宁,这也正是特殊历史时期作家命运的真实写照。
部分诗人通过译作表现了他们内心孤独和悲伤的心绪。例如郭沫若的译诗《割麦女》抒写了割麦女独自刈麦的情景,她唱着“凄凉的调子”,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他唱的是什么”。这种感情正好与译者郭沫若这一时期内心的寂寞与苦楚相契合,诗人心中的哀伤无人了解,也无法排遣,只能在诗歌翻译中暗自歌唱。何其芳的多首译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思,如《一棵松树孤独地》运用拟人的手法将知识分子比作松树,他们“在那遥远的东方/在火热的悬崖上孤独地/而又默默地悲伤”。这样的译作饱含了诗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刻体验。种种关于生存困境和内心孤独无依的个人化的表达,是根本无法被纳入当时的“一体化”叙述规范中的,作家也只有借翻译之口才能一吐心中块垒。
其次,译者通过翻译诗歌表达了自己在逆境中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很多诗人在政治语境中虽处境艰难,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拥有非比寻常的生存信念。有些诗人通过翻译诗歌来昭示不屈服和不妥协的个人勇气,比如郭沫若翻译的英国诗人罗素·葛林的《默想》一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我不能让我尊严的人性低头”“我不能在无量树的星星面前低头/那无声的装矜并不能使我投降”。而在译诗的附白中,郭沫若说“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15](115)。这充分展现了诗人们在“文革”期间虽遭遇磨难却不屈服的精神,突显出他们不屈的尊严与人格。另外,在《树》《林》《山岳是沉默的好汉》《像大麦那样》等译诗中,郭沫若借翻译赞颂“山”“树”和“麦”的峭拔与挺立,实则是以物自况,表达心中的坚强和笃定。由此可知,文化重压只能使部分作家表面屈服,他们内心始终闪耀着不妥协的文学之光,并在私下自觉地选择了“以译代作”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信念与操守。
再次,诗人们通过翻译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介入和承担。“以译代作”通过翻译两类诗歌呈现作家对现实的观照。第一类译诗表达了作家对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反思。冯至翻译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歌的题名作为一个隐喻,它暗示着德国黑暗的现实就如同一个不会长久的“童话”,终有一天会化为泡影。对于诗人冯至而言,其身处的现实也是“死亡、黑夜和沉默/管领这巨大的空间”。冯至的翻译动机十分明显,他欲借译诗来揭露“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伤害。他创作的七言绝句《题<海涅诗集>》的最末两句“重展旧编新耳目,齐鸣万箭射毒鹰”[16](208),也印证了这种翻译意图。在长诗的第四章中,冯至借译作批判现实,认为“四人帮”统治集团“把教堂的内部/当做一个马圈使用”“用忘恩负义的黑心/把他的百姓当做愚氓”。这样的现实境况让诗人感到担忧和悲哀。在其他章节,诗人海涅对德国顽愚的封建思想进行了讽刺,这都是冯至借海涅的诗表达内心的所思所想。这表现出诗人们虽身处逆境,但仍心忧现实的担当精神。另外,还有部分译诗从微观角度出发,着重表现下层人民的艰难生活,何其芳翻译的海涅和维尔特的诗就涵盖了这一内容。他们的翻译通过对底层生活的生动刻画既揭示了各种悲惨的生存状态,又间接地隐喻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对社会的批判达到了那个时代难得的高度,而这在“文革”期间公开的文学创作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冯至、何其芳等人借助诗歌翻译的形式曲折地达成了这种 目的。
最后,诗人通过翻译作品表达了内心深处对真诚的人际情感的赞颂与呼唤。“文革文学”在激进的政策引导下高扬革命友谊和阶级情感,反而不重视私人感情的表达。爱情这样敏感的题材自然也成了文学创作的禁区,但我们却可以透过翻译作品看到诗人们还在竭力维护这些人性的根基。在何其芳的译诗《让你的脸挨着我的脸》中,诗人毫不掩饰地要“让我的心紧压着你的心/然后火焰一样跳跃”。不仅“明目张胆”地向情人示爱,诗人还要紧紧地抱住她,并为了获得爱情而不惜牺牲生命,这种爱的忠贞深深地震撼着那个“铁面无私”的时代。译诗《你像一朵花一样》赞扬爱人美丽、纯洁、温柔,并祈求上帝能让她始终保持这些美丽的品质。诗人们敢于在译作中颂扬纯洁而可贵的爱情,这与许多公开发表的反爱情的诗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样的诗歌翻译从根本上颠覆了“文革”期间大众与读者的“情感结构”,诗人们也以个人化的翻译瓦解了文学大一统的神话。
除此之外,在互不信任的人际环境中,对亲情和友情的刻画也是译者内心最真切的呼唤。例如郭沫若的译诗《冥冥》描写了和睦的家庭关系,“灯火家中归/亲人共笑谈”的温馨场面虽然短暂,却也是诗人内心深处的温暖;何其芳的译作《悲谷》描绘了两个可怜之人将死之时也要相拥取暖,最后拥吻而逝,他们虽死却显示出对同类的尊重和友爱。在作家无法正面表达人情诉求的时代,这些翻译诗歌所展现的刻骨铭心的情感真实地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对真诚的渴望。这些译作代替诗歌创作继续以“潜在”的方式抒写着人性和人道主义,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的这些诗歌翻译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与其说是原作者的主观感受和生活体验的抒写,毋宁说是译者真情实感的抒发。翻译就像创作一样表达了作家在现实语境中意欲书写的情思。诗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适合表达自我真实情感的作品内容,在翻译外国诗歌的同时,也迂回地“翻译”出了自我的情感和诉求,并翻译出自我与时代的“精神史语境”。
三
郭沫若、冯至、何其芳、穆旦、施蛰存等人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且都已取得了不凡的文学成就,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形成了稳定而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按照文学阶级性类型学尺度,被分为不同的等级”[1](15),作家们也或多或少地转变了自己原有的文学态度,放弃了自己在现代文学时期所坚持的文学手法和艺术立场。“文革”期间,这种与旧时代的文学划清界限的做法在公开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更为彻底。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们真的毅然绝然地背离了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自我。事实上,诗人们除了用翻译代替创作表达现实诉求之外,还用翻译作品的表现形式来满足他们在“文革”语境中无法实现的艺术追求。
首先,翻译代替创作彰显出诗人们对现代文学时期他们所钟爱的文学风格的回归。穆旦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代表诗人,其诗歌常呈现出强烈的反叛性和异质性[17](58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得不“以对过去那个诗人‘送葬’的方式”转变成一个职业翻译家[11],但他内心深处却从未放弃文学创作上的现代性追求。“文革”后期他悄悄译下了《英国现代诗选》,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这本译诗集是对当时国内“标语口号、分行社论”诗歌的极力反驳。更重要的是,这本译诗集凸显出诗人借助翻译的形式表达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现代主义风格的回归。
这种回归体现在诗人直接翻译具有现代主义美学风格的诗人作品上,这从穆旦所选择的翻译对象便可一目了然。奥登、艾略特、叶芝等人都是深深影响过青年穆旦诗歌创作的西方现代主义大诗人,穆旦从他们的诗作中不仅学到了诗歌技法,而且领略了诗歌的现代精神。而在“文革”动乱之中,诗人选择重新翻译这些“资产阶级的堕落诗人”,且在译介过程中再也不像20世纪50年代译介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那样在注释和序言中加入批判性解读以适应出版要求,而完全是一种抛开一切束缚的自由翻译。这充分显示出诗人穆旦在晚年对现代主义诗歌价值的深刻理解与认同。由此可知,穆旦是借助翻译现代主义诗歌重拾他早年创作中的现代主义诗风。与此同时,这种艺术上的回归还体现在诗人坚持“语言刷新”与“思维革新”的诗歌意识上。穆旦在翻译这些现代主义诗歌时采用“异化翻译”的策略,并在翻译中呈现出语言的异质性。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它是一种冲破旧套的新表现方式”[10](190)。他也不再照顾大众所推崇的顺畅、清晰的阅读习惯,坚持用富有创造性的语言译出现代感极强的诗句,诗人坚信这样的翻译能给中国新诗创作带来语言和思维上的变革。由此可见,穆旦这一时期的翻译在选材和风格上坚持了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中所坚持的诗学追求。
郭沫若的《英诗译稿》也是诗人在“文革”期间对“主观”与“浪漫”的一次低调回归。他选择翻译的大多是抒情短诗,虽然诗歌并未完全恢复到《女神》时期那样“绝端的自主,绝端的自由”,但在《山岳是条沉默的好汉》《月神的奶头》《老虎》等译诗中也隐隐显出诗人心中未曾改变的激越与雄壮之情。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多首译诗末尾的附白中也表现出他独特的艺术看法。例如在《爵士约翰•摩尔在科龙纳的埋葬》一诗的结尾,郭沫若说这首诗“好在写得实在而不做作,但很感动人”[15](135)。这简短的评语既显露出诗人追求表达自由流畅、情感真挚自然的艺术风格,又暗指他对“文革”做作文风的不满。在译诗《多浮海岸》的附白中,诗人则批评这首诗“诗意不统一……如在暴风雨之夜,或可使情调统一些”[15](43)。这进一步表明诗人追求情景统一的浪漫主义艺术价值。与穆旦和施蛰存相比,郭沫若的艺术承续显得内隐而不张扬,但同样能彰显诗人所向往的艺术理想。总体来看,这种写作的“复归”在“文革”期间的公开创作中都是无法实现的。而诗人们选择用“以译代作”的方式续接失落的文学理想,在黑暗年代坚持探索诗歌的审美现代性,向艺术缪斯表白自我的良心与勇气。
其次,翻译还代替创作践行了诗人的诗学理念,并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依据。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译诗不仅给新诗创作的内容、表现手法、题材等方面带来了重大改变,而且还在“语言、音律、形式及风格等方面实践或实验了中国新诗的形式观念”[18]。这种“践行”活动一直贯穿于中国新诗自我建构的全部过程。甚至在“文革”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也仍然有诗人坚持用翻译诗歌来实践自己的新诗创作主张,诗人何其芳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他在“文革”期间翻译海涅与维尔特的诗时,“每首诗先译成散文诗形式,然后推敲节奏和音韵,加工成格律 诗”[19](408)。最后的译作成品大多是形式整齐的格律体和半格律体。究其原因,卞之琳先生在代序中说,“他只是在译诗上试图实践他的格律诗主张而已”[13](180)。解放后,诗人何其芳“在自由体新诗以外,感到另有建立新格律体的需要,在自己的探索中得出了以‘顿’建行说”[13](182)。何其芳曾说:“在格律上就只有这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诗,每行有整齐的顿数,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20](56)但此时的何其芳已经被剥夺了创作和发表诗歌的权利,无法再公开创作格律体新诗,他便将这种创作上的格律主张巧妙地运用到诗歌翻译上来,所以他的译诗多采用了格律体形式。例如,他翻译海涅的《给格奥尔格·赫尔韦格》一诗时,全诗都采用了abccb的押韵方式,每行都分为四顿,基本符合他所坚持的“整齐的顿数”和“有规律的押韵”的格律主张[8]。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止于翻译,而是希望借助译诗的格律实践来印证自己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主张。除此之外,何其芳还主动学习创作格律体古诗,并寻求将古诗的格律通过多种形式的转化运用到诗歌翻译和新诗的创作上来。这真是一种曲折漫长且用心良苦的文学活动,从中可见何其芳一颗坚忍不拔的诗心。对于何其芳而言,坚持用格律体翻译诗歌不仅是为新诗格律化寻找合法的依据,而且是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和创作的未来出路而不懈探索。他在黑暗年代通过翻译艰难地摸索出格律体新诗创作的路径,这对于我们当下新诗的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诗人通过“以译代作”尝试不同的文学表现方式,为文学形式的多样化表达寻求可行性。从某种意义上看,“十七年”文学向“文革”文学的转变是一个逐步收缩和窄化自我的过程,这既体现在内容上,又体现在形式上。“文革”期间大多数作家都没有勇气和机会在文学形式的表现上做出突破和创新。面对这样一种“形式荒漠”,郭沫若在翻译外国诗歌时却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体式,既有四言古诗、五言古诗、诗经体,又有自由诗和格律诗。成仿吾在《英诗译稿》的序言中称赞道:“他的手法是多么的高超。”“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沫若是费了一番力气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同样的大诗人之间的几次摔跤吧。”[21](1)这种手法的高超体现在他对各种翻译诗体的灵活运用上。例如,他用诗经体翻译吉姆司·斯提芬司的《风中蔷薇花》一诗,不仅形式整饬,诗句凝练,而且创造出了“水中有鱼/心中有君”“鱼难离水/君是我心”这样的四言佳句,读来朗朗上口。在翻译苏格兰诗人彭斯的《红红的玫瑰》一诗时,郭沫若则使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全诗“ong”韵一押到底,完全遵从七绝的用韵方法,第一句与第三句中对“吾爱吾爱”的连用既表达出原作中情感的真挚,又使得译诗具备了可供歌咏的节奏感,体现出译者高妙的“风韵译”特色。其他的表现形式,如用四言古诗译《月神的奶头》,用五言长诗译《多浮海岸》等,都足见郭沫若的良苦用心。
按常理推测,通常一个译者在翻译一本诗选时会尽量保持风格的统一,但郭沫若却在这本“只译给自己看”的诗选中尝试采用形式多样的翻译文体,这又是为何呢?结合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处境和整个文坛的文体形式所遭遇的瓶颈问题来看,我们就能更充分地理解诗人的深意,他是希望通过翻译形式的多变和创新来尽力维持自己鲜活灵动的创作风格以及自由的创作个性,客观上还能为整个文学创作环境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郭沫若的翻译创新,那他采用古体译诗就是一种遵从内心真实想法的有意之举,其背后隐藏的是诗人郭沫若对文学创作自由的无限渴望以及他对文体形式多样化的执着追求。这也印证了翻译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的观点,当文学处于危机或转折点时,“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得由翻译来提供”[22](30)。
综上所论,“以译代作”主要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翻译作品如创作一样表达了作家内心隐藏的私人情感和现实诉求;二是翻译作品如创作一样践行了作家的艺术主张。这两个层面的合力,强烈地映衬出特殊时期翻译对创作的“替代性”功能。
四
从传统翻译研究的角度去考察上述代替写作的翻译文本,很多译文可能会像卞之琳先生评价何其芳译诗时所说的“译笔还未臻熟练”[13](185)。但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则会对这些译作的价值做出不一样的评价。因为我们重点关注的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而是透过译作,“对文学交流、接受、影响、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23](11),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译代作”现象具有多重文化价值。
在美学家克罗齐看来,“翻译即创作”。翻译无外乎两个步骤,“一是减少剥损,二是取原文摆在熔炉里,和所谓翻译者的亲身印象融会起来,创造一个新的表现品”[24]。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所论述的这些翻译文本具有了“以译代作”的性质,并达到了“替代”的功能和效果。何其芳、冯至、郭沫若等人确实是忠实地翻译了海涅、维尔特和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但更具深意的是,他们将外国诗作的内容、诗歌所呈现出的情景与场域、所流露出的情感倾向和艺术诉求等功能要素也“翻译”到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即通过翻译完成了赫维和希金斯意义上的“文化置换”(cultural transposition)。在这种置换的过程中,原文本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在译入语国得到了完整而清晰的呈现。而且译者还会联系自身的处境和遭遇有意强化和放大某种文化功能,以期实现译者希望在译入语语境中想表达和倡导的内容。这种豪斯意义上的“隐性翻译”可被理解为既翻译了代表“能指”的“语言与声音系统”,又翻译了代表“所指”的“功能系统”。可以说,“以译代作”现象是诗人译者们将“隐性翻译”的两个层次拆开应用,用“译”承载了源语的“语言项”,用“作”来凸显源语的“功能项”,这是属于那个年代诗人译者们的特殊创造。
这样来看,“以译代作”现象就是一种变异的文化形态,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诗歌创作或诗歌翻译活动,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发挥创造性的产物。实际上,它是一种充满撞击、扭曲、变形等力量的诗歌创作与翻译的混合物。从文学演进的层面来看,“以译代作”与当时的“潜在写作”、“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以及早期“朦胧诗”等文学运动共同参与了时代文学的“边缘性”建构,也预示着文学意识的逐渐觉醒,进而开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启蒙”的先声。穆旦、施蛰存等人的诗歌译文还成为“八十年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外来资源。正是在对这些译本的接受和转化中,“八十年代诗歌”才能绽放出异样的光芒。而从文本的历史价值来看,“以译代作”现象透露出“文革”期间中国的文学环境看似铁板一块、密不透风,实际上还存在着较大的时代“裂隙”和自由空间。创作与翻译的“结合部位”正是这样一种还没被政治话语完全吞没的“潜在空间”,它是不断涌动的时代暗流,它的存在表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话语在特殊年代仍有自由发声的可 能性。
“文革”时期“以译代作”现象的存在也展现出诗人们在“当代”语境中面貌独特的“潜在形象”,这样的形象显然与他们在公共领域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有所不同。在面向广大读者的“公共性写作”中,诗人们必须保持较为严肃的态度和较高的政治觉悟,这是源于生存的压力和时代文化的精神重负。而诗人们在“私人领域”中曲折地选择“以译代作”的方式表达自我,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宏大叙事的执着,也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热情,不再以牺牲自我的独立性来换取创作上的合法性,而转向对生命与存在的沉思。这显然预示着文学书写方式的转变,即由“政治”转向“人”,由“集体”转向“个体”。正是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诗人再次获得独立写作者的身份。他们在“以译代作”的过程中提出质疑,展示困惑以及他们身心的悲伤与无奈。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这都是源于诗人们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写作者对于生命个体的认识、尊重和重新发现。尤其是在一个极端的年代,这种通过“以译代作”的方式重新获得的“独立”和“自我”显得极其珍贵。而它所创造出来的潜在文学空间与当时公开的文学界、翻译界之间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张力,也昭示出文学史本身不可想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这些“以译代作”的文本以翻译的面貌出现在文学史中,最终却释放出翻译与创作的双重能量,进一步建构了诗歌的自律性发展历史。诗人王家新曾将穆旦在“当代”以来的文学翻译成果看作是一种“幸存”,这种“幸存”才能真正确定诗人“自己精神的在场,才能辨认出自身的命运”[11]。何其芳、冯至、施蛰存、郭沫若的翻译当然也具有同样的价值,他们用变异的翻译作品让自己在时代中获得了文学的“存活”,免于被时代彻底同化,从而真正地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正如雷克斯洛斯所说,是翻译把他们“从同代人之中拯救出来”[25]。进一步讲,“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中一部分以这种“以译代作”的形式被碎片化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在那个时代中痛苦燃烧着的精神烛火。不仅如此,“以译代作”还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种“言说范式”,即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之下,所有的话语空间都被挤压殆尽时,知识分子如何发声并保存自己的精神命脉和人格尊严。穆旦与何其芳意识到“徒手请愿”(鲁迅语)只能白白牺牲自己,唯有“韧性的战斗”(鲁迅语)才有可能恢复话语的力度。他们不金刚怒目,不以死殉道,也不做无谓的呐喊,而是保持冷静和理智,并竭尽全力在诗歌翻译和文学创作相结合的隐秘区域打开了一条言说通道。他们既言说个人感情和艺术追求,又批判现实,眺望整个国家的未来,为自己、为后人、为时代留下有力的证词,并等待历史的检验。这才是何其芳、穆旦、郭沫若、施蛰存、冯至等人留给当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带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作家如何能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裹挟下,写出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幸存”的作品,如何能够在时代的洪流中保留文学的尊严和自由。
总而言之,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以译代作”是一种重要的创作现象或翻译现象,对它作进一步的拓展研究,会为我们重新理解当代思想史的多元性、当代文学复杂的历史形态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但必须警惕的是,在对这种“替代性”写作史料发掘与解读的过程中,应避免人为放大和过度阐释,毕竟我们需要以公正、严谨的态度去面对民族的文学与历史。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冯至.自传[C]//中国现代作家传略.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3] 郭庶英, 郭平英.整理后记·英诗译稿[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 周珏良.穆旦译文全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 何其芳.何其芳全集: 第8卷[M].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6] 施蛰存.域外诗钞[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7] 贺仲明.何其芳评传[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8] 熊辉.历史束缚中的自我歌唱: 何其芳的诗歌翻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6):102−107.
[9] 冯至.冯至全集[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0] 穆旦.穆旦诗文集: 第2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11] 王家新.穆旦: 翻译作为幸存[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6):5−14.
[12] 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13] 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C]//何其芳全集: 第6卷.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14] 陈明远.追念郭老师[J].新文学史料,1982(4):126−134.
[15] 郭沫若.英诗译稿[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16] 冯至.冯至全集: 第2卷[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7]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8] 熊辉.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J].扬州大学学报,2014(2):83−89.
[19] 卓如.何其芳传[M].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2.
[20] 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M].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8.
[21] 成仿吾.序言[C]//郭沫若.英诗译稿.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22]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3]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24] 王园园.文本翻译: 在互文记忆中的二度写作[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54−157.
[25] 肯尼斯·雷克斯洛斯.诗人译诗[C]//胡续冬, 译. 唐晓渡,西川: 当代国际诗坛.作家出版社, 2012.
On the phenomenon of “substitution of translation for literary cre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1966-1976)
YANG Dong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From the year 1966 to 1976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group of poets whose literary creation was constrained replaced the poetic creation in the form of poetic translation (abbreviated as "substitution of translation for creation"). These poems presented completely diverse cultural traits, of which some poems, under the mask of mainstream cultural perspective, implicitly expressed the translators' sentiments through their translations, while others completely broke free from the aesthetic constraints at that time. In this way, poets, in a roundabout way, expressed their various wishes and artistic appeals which could not be told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at that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existence of this phenomenon reveals the potential image of contemporary poets outside the public space, inherits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intellectuals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n since the times of May 4th, hence providing another kind of more tortuous “Speech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phenomenon of “substitution of translation for literary creation” can manifest its deserved values of thought, culture and literary value.
the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ubstitution of translation for literary creation; translating poetry; adherence to art; the spirit of intellectuals
[编辑: 胡兴华]
2017−10−17;
2018−03−12
杨东伟(1989—),男,湖北兴山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诗歌与翻译诗歌,联系邮箱:554971558@qq.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4.019
I207.25
A
1672-3104(2018)04−016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