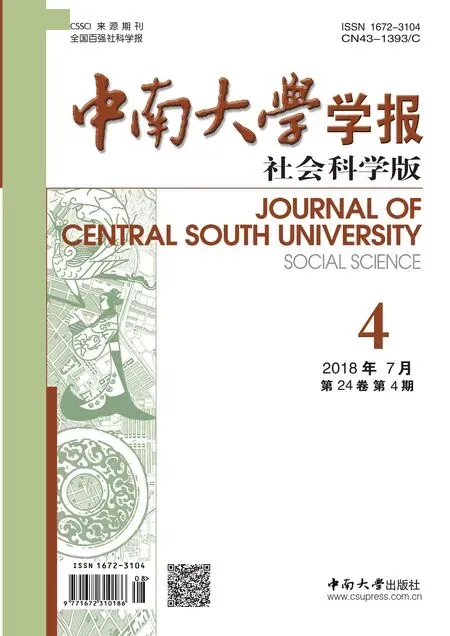天台宗僧诗创作传统考论
2018-08-04张艮
张艮
天台宗僧诗创作传统考论
张艮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天台宗;僧诗;诗僧;创作传统
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园新寺》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耳寄家书。’可谓入作者阃域,岂独雄于诗僧间邪?”[1](136)这是刘禹锡为诗僧灵澈诗集所作的序。刘禹锡少年时曾从灵澈学诗,成年之后又多有交游。刘禹锡称灵澈不仅“独雄于诗僧间”,亦“可谓入作者阃域”,评价甚高。刘禹锡在称许灵澈之外,还揭示了一个不甚为人注意的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即从灵一、护国、清江、法振到皎然、灵澈的天台宗诗僧的创作传统。这段文字虽然经常被研究诗僧和僧诗的学者引用,但是其中揭示的天台宗僧诗创作传统却一直以来因被遮蔽而晦暗不明。本文试着从佛教宗派的角度入手,首先考察隋唐以来天台宗的诗僧的创作情况,然后总结天台宗诗僧宗派背景被忽略的原因,最后讨论天台宗僧诗的创作传统。为显示其鲜明的特色,本文将其与同时期的禅宗僧诗进行对比。
一、隋唐天台宗诗僧队伍考察

神邕(710—788),字道恭,俗姓蔡,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幼时聪悟过人,年十二依法华寺俊师学道。开元二十六年(738),师从著名律僧玄俨,通《四分律钞》,深得玄俨器重。后又从左溪玄朗师习天台止观,深得四教三观等义,吴会间学者从之。天宝后期游问长安,方欲传法而遇安史之乱,复居故乡法华寺,后住焦山大历寺。《宋高僧传》卷一七有传。《佛祖统纪》列为天台八祖左溪玄朗法嗣[5](201)。
神邕亦有能诗之名,其居越州法华寺时,与当时文士交游唱和,并有文集十卷。《宋高僧传》载:“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评事张河、金吾卫长史严维、兵曹吕渭、诸暨长丘丹、校书陈允初赋诗往复,卢士式为之序,引以继支许之游,为邑中故事。邕修念之外,时缀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为序。”[6](422)

尔时一切净光庄严国中,有一菩萨,名曰妙音,久已殖众德本,供养亲近无量百千万亿诸佛,而悉成就甚深智慧,得妙幢相三昧、法华三昧……说是妙音菩萨来往品时,四万二千天子,得无生法忍,华德菩萨得法华三昧[8](55−56)。
慧思在《法华经安乐行义》中谈到欲疾成佛道,须勤学法华三昧。
《法华经》者,大乘顿觉,无师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间难信法门,凡是一切新学菩萨,欲求大乘,超过一切诸菩萨,疾成佛道,须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专心勤学法华三昧[9](697)。
由上可知,法慎诸弟子皆入法华三昧,即是修持此种三昧,则其教属天台宗的可能性极大。在法慎的这些弟子中,法海就被《宋宗高僧传》列入“义解篇”。法海尝谓人曰:“佛法一门,极唯心地,余皆椎轮 也。”[6](115)天台宗宣称止观双运,但又自认为观心法门乃是其区别于其他宗派的一家经教特别之处,法海的重视观心与天台宗教理的一致也可视为其宗派归属的证明。
另外,法慎的“以文字度人,故工于翰墨;以法皆佛法,故兼采儒流”[6](347),也明显与当时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的主张不同。禅宗对语言文字的态度转变为“不离文字”还要等到北宋年间。与禅宗此时对文字的激烈批判态度不同,天台宗因为重视经教,所以一向对语言文字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比如与法慎差不多同时的荆溪湛然在从玄朗学习天台止观后,“即文字以达观,导语默以还源,乃祖述所传章句凡十数万言”[6](117)。二人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何其相似!法慎对天台宗关于语言文字态度的接纳和吸收也影响了灵一。史传称灵一“示人文艺,以诱世智”[6](357),就是将文字作为解脱之径,这与当时的禅门风尚截然不同。

又如皎然,贾晋华曾考其佛门宗系,认为他是一个立身律宗之门而博采佛教各宗义理兼及道教之学的诗僧[12]。不过他与天台宗的关系其实很深。他曾从杭州灵隐山天竺寺守真受戒,亦自称为其门人[13](841)①。守真曾从荆州南泉大云寺惠真学三年苦行,惠真为天台玉泉系重要传人恒景法师的嫡传。同时,《宋高僧传》又载守真为天台八祖左溪玄朗的付法弟子[6](663)。在为守真同门道遵所作的碑序中,皎然也以天台宗后学自称[13](885)②。《杼山集》卷八《天台和尚法门义赞》云:“我立三观,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强欲明因。万象之性,空江月轮。以此江月,还明法身。”[13](851)展示了皎然对天台宗教义的领会和尊崇。《宋高僧传》称皎然“与武丘山元浩、会稽灵澈为道交”[6](728)。“元浩”当是“元皓”之讹误,元皓为荆溪湛然高足,灵澈为神邕弟子,皆为天台宗僧人,与二人为道交,皎然的天台宗派倾向还是很明显的[7](315-337)③。
继惠真之后,在南岳传天台教法的人是其法嗣弥陀承远(712—802),承远弟子中最有名者为法照。法照(746—838),陕西汉中洋县人,俗姓张。十一岁出家,二十岁投承远门下。后于南岳创五会念佛法门。先后为代宗、德宗迎请入长安[14](409)。法照能诗,《全唐诗》卷八一〇今尚收其诗三首。小传云:“法照,大历、贞元间僧。”[11](9135)正是其人。《佛祖统纪》对天台玉泉一系并不重视,所以将惠真、承远、法照三人均列入未详承嗣之类[15]④。
在守真法嗣中越州清江亦善诗。《全唐诗》收其诗一卷,小传称其为“会稽人,善篇章,大历、贞元间与清昼齐名,称为会稽二清”[11](9144)。皎然在《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并序》中称守真有“显名弟子苏州辨秀,湖州惠普、道庄,越州清江、清源,杭州择邻、神偃,常州道进”[13](842)。《宋高僧传》称其“于浙阳天竺戒坛求法,与同学清源从守直和尚下为弟子”[6](368)。守直和尚即是守真法师,《宋高僧传》皆误作“守直”。由此可知,清江亦有天台宗背景。
又如贯休被后人认为是禅僧,但其实他的宗派背景并不那么确定。最早记载贯休属于禅宗的是宋普济的《五代会元》。与贯休同处“未详法嗣”的还有神照本如法师和天竺证悟法师[16](19),不过后二者却是法系明了的天台宗高僧,由此可知贯休虽被列入目录,但可疑的成分还是很大。到元代熙仲集《历朝释氏资鉴》,方将其列入石霜庆诸禅师门下首座[17](213)。
我们若仔细考察贯休弟子昙域所作的《禅月集序》,则不免对禅师之说心生疑窦。《禅月集序》谓贯休乃婺州兰溪人,幼从本县安和寺圆贞老和尚出家,“日念《法华经》一千字”,“年二十岁,受具足戒,后于洪州开元寺听《法华经》,不数年,亲敷法座,广演斯文。尔后兼讲《起信论》”[18](9604)。首先,序文中没有任何文字言及贯休和禅门的关系;其次,贯休在豫章传讲《法华经》和《大乘起信论》,颇不似禅师行事,当是讲师。《法华经》乃天台宗依据的经典,而《大乘起信论》也为天台九祖荆溪湛然所重,援引甚多。这是现存最早的贯休生平资料,且是其弟子所作,可信度极高。
宋初赞宁为贯休作传,在《禅月集序》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新的材料。《宋高僧传》卷三〇谓贯休受具戒以后,“乃往豫章传《法华经》、《起信论》,皆精奥义,讲训且勤。本郡太守王慥弥相笃重,次太守蒋瓌开洗忏戒坛,命休为监坛焉”[6](897)。则贯休不仅精于讲解经论,还擅长戒律和行忏。天台宗一向重视戒律,也擅长忏法。同时,在赞宁的传记中也没有记载贯休从石霜庆诸之事,较之南宋的《五灯会元》和元代的《历朝释氏资鉴》,《禅月集序》为贯休弟子所作,赞宁距贯休时代未远,他们的材料更值得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贯休极有可能为天台宗的讲师,只是因为资料散佚,师承不清,故被后人误为禅师,当然也不排除禅宗有意拉名人入伙以壮声势之嫌。元代僧人昙噩编述的《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二〇贯休传记基本就采信赞宁之说而弃用《五灯会元》的资料,或许也能说明一些问题[19](250)。

二、唐代天台宗诗僧宗派背景被忽略的原因
由上文考证可知,在八世纪,大约自天宝到大历、贞元之间,诗坛上涌现了一批天台宗诗僧,他们与当时诗坛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皎然、灵澈及贯休等人。虽然后人注意到这个时期诗僧层出不穷的事实,但是却又大多将他们视为禅僧。考察这些诗僧的天台宗背景之所以被忽略,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 误解天台宗历史而导致的结果
学界对七八世纪的天台宗的历史有着很大的误解。天台宗自智者到荆溪湛然出世传法的一百多年间,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处于衰微期。《宋高僧传》卷六引梁肃评论湛然之语:“自智者以法传灌顶,顶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发。乘此宝乘,焕然中兴。”[6](118)在《天台止观统例》中梁肃又称:“当二威之际,缄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宝中,左溪始弘解说,而知者盖寡。荆溪广以传记数十万言,网罗遗法。”[5](440)皆认为天台一宗自智者以后渐成颓势,直至湛然出世大力宣弘,才再度中兴。梁肃的观点在后世被广泛接受,现当代学者亦多继承此说。日本学者安腾俊雄认为天台宗在初唐即“一蹶不振而走上日趋没落的命运”,并根据传法谱系,指出“自第二祖章安灌顶殁后,直至第五祖左溪玄朗止,一般通称为天台宗第一期黑暗时代”[20](351−352)。又如演培法师亦认为自灌顶到湛然“可说是天台的黑暗时代”[21](191)。给天台宗贴上衰微不振的标签以后,自然不会认为这一时期涌现的诗僧来自天台宗。
不过梁肃的观点尚值得讨论。南宋志磐就认为梁肃欲张皇荆溪湛然立言弘道之盛,故有贬低二威之嫌,并且指出当时“讲经坐禅未尝不并行也,不然法华听习千众,天宫求道无数,为何事耶?是知‘其道不行’亦太过论”[5](188)。志磐认为智威与慧威之时学徒甚众,讲经与坐禅并行不悖,所以批评梁肃言过其实。志磐所言颇有道理,但“《佛祖统纪》整体立意乃以正统意识梳理天台宗发展史,以法统承接为正统大书特书、以他传为旁支一笔略过,法统承接则以本山系统为正统”[22](29)。所以志磐虽对梁肃之说颇有微词,但由于忽视天台宗玉泉和衡岳支系以及活跃于两京的天台高僧,其所著《佛祖统纪》在客观层面上反而进一步确认了梁氏的结论。
徐文明通过考察天台宗玉泉一脉的传承,纠正了《宋高僧传》及《佛祖统纪》的错误,认为玉泉派在唐代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并且为天台宗的发展及海外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5](239−245)。在《唐中期至五代时的天台宗两京支系略考》一文中,徐文明指出,“到了唐代,唯识宗、华严宗及禅宗北宗等都受到朝廷的支持,而天台宗本山则不受重视,唯有玉泉一支以弘景为代表,进京弘法,也颇受尊崇。两京系天台宗的存在与发展对于维护天台宗的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成为国师的有弘景、楚金、法照等,他们的存在使天台宗得以与诸宗抗衡”[23](120)。俞学明在徐文明的研究基础之上,在《湛然研究——以唐代天台宗中兴问题为线索》一书中继续对自梁肃以来的天台宗“衰微论”提出质疑,认为梁氏之说容易给后人造成两个误解:其一,以为天台宗之传续只有本山一系,因而把非本山系统的天台宗摈弃于研究视野之外;其二,由于只把天台本山系作为考察的重心,所以就判定湛然之前天台宗已经衰微了。为还原史实,她从天台宗的社会势力和影响及天台宗理论的影响和宣弘两个角度重新考察灌顶至湛然期间的天台宗状况,最后得出下列结论。
首先,在诸宗兴起的初盛唐时期(湛然之前),天台宗也并不缺乏高僧大德。其时,天台本山系略显衰微,但京师地区,在以恒景为代表的其他支脉(玉泉系)的天台宗人的努力下,天台宗在社会中依然拥有良好的社会影响,与唐皇室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些天台高僧深受唐皇室推重,其声名影响并不亚于其他诸宗的任何宗师。而天台教观,也广为传布,影响了诸宗理论体系的建设。无论从社会影响还是从思想流布的角度看,都无法得出灌顶至湛然期间天台宗衰微,尤其是属于“黑暗时代”的结论。其次,在八世纪,天台宗之繁荣,表现为各支脉都涌现了一些大师级人物。玉泉系在恒景之后有惠真、承远等支撑门户,有鉴真、法照等活跃于社会,名动朝野,并将天台宗传至日本;两京地区有楚金、飞锡、抱玉、大光等天台高僧光大门庭,受到帝王和社会的礼敬。八世纪天台宗的社会影响力显然大多来自这两处师弟们的努力。天台本山系此时在玄朗和其弟子们的努力之下,比“二威”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八世纪天台宗的繁荣是各地各支脉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独归因于天台本山系。再次,玄朗的诸多弟子虽后来籍籍无名,但现存的史料已经可以证明,湛然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并非是唯一的。玄朗门下的道遵、清辨、神邕等俱为一时之选,他们对天台宗在社会上的普及和深入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22](77)。
通过徐文明和俞学明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学界对唐代天台宗的历史一直存在着误解,所谓湛然之前天台宗衰微不振并不符合事实,习惯上认为荆溪湛然中兴天台宗之说也很不准确。正是因为天台宗这一段历史被后人误解,所以这一时期一大批诗僧的天台宗宗派背景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实际上,其时天台玉泉系僧人在两京地区及衡岳、荆州一带相当活跃,加上玄朗及其弟子们在江南的传弘,天台宗此时影响甚大。贾晋华认为大历江南诗人深受天台宗的影 响[24](143−145),洵为有识之见。不过,笔者觉得考虑到天台宗在当时的影响范围之广,则受天台宗影响的诗人远不止江南这一带的诗人。
(二) 禅宗的兴起遮蔽了人们对天台宗的关注
学界多认为禅与诗有着天然的兼容性,以为禅宗的兴起自然带来了诗僧涌现的状况。如蒋寅就认为“诗僧的出现是与禅学尤其是南宗禅的发展分不开的”,并指出“讲究顿悟的南宗禅尤重禅悟体验的表达,有禅悟而后有禅诗,有禅诗而后有诗僧。自大历以后,历代著名的诗僧大都为禅宗僧人,也可以说明这一 点”[7](299)。南宗禅确实注重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但是他们用来表达禅悟体验的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诗,而只是偈颂、歌赞。比如《景德传灯录》卷三〇所收的《腾腾和尚了元歌》《南岳懒瓒和尚歌》《石头和尚草庵歌》《道吾和尚乐道歌》,前两首为初盛唐时禅师所作,后两首为中晚唐禅师所作,他们和传统的诗歌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禅悟之后带来的禅诗,其实还不能算作诗,只是表达参禅感悟的偈颂。虽然禅师们有些偈颂无论形式上(七绝)还是文字上(富含诗意)都接近诗歌,但实际上它们仍重在阐发佛理,同世俗化的文人诗歌相去甚远。至于诗僧的出现与禅诗的产生更没有必然的关系,相反,诗僧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禅宗偈颂流行的时代。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全唐诗》所收的大历、贞元时期这些诗僧们的诗歌也并不是他们禅悟后所作。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会觉得跟当时文人创作的诗歌没有多少差别,充满了一种世俗的意味。由前文的考证可知,中唐时期那些著名的诗僧事实上差不多都是天台僧。但是,不幸的是,禅宗的兴起使得后人忽略了诗僧们的宗派,大多简单地将他们视为禅僧,以致有些分析讨论似是 而非。
这一时期诗僧们的作品有不少涉及“禅”字,其中有些作品亦有禅味,不少研究者因此将他们判定为禅僧,这也是很大的误会。禅宗虽是以“禅”名宗,但在南宗禅成立之后,他们对传统的坐禅却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在《坛经》中,慧能就对坐禅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25](37)坐禅在这里已经完全不拘于形式,一反传统的做法。到马祖之时,提倡“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在日常生活中穿衣吃饭,行住坐卧皆可为禅。禅门津津乐道的马祖磨砖成镜的公案就点出了南宗禅认为坐禅不能成佛的观念。马祖门下庞居士所言的“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大珠慧海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都是在践行马祖的“平常心是道”。马祖的后人临济义玄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尔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26](498)周裕锴对此分析道:“于一切事不执著,不粘滞,无念无心,顺应本性。这就是南宗禅活杀的自在性,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禅不是体系的逻辑而是贯穿于最寻常的世俗行为的实践。……妙悟的奇迹不再出现于山间的冥想或静室的坐禅,而是存在于尘嚣世俗的生活之中。”[27](10)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触类是道”,而不必再进行枯坐。但与南宗禅相区别的是,天台宗一向重视止观双运,定慧双修,所以他们自智者大师以来一直重视坐禅,在《摩诃止观》和《童蒙止观》中智者大师就对坐禅作了详细的规定和描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诗歌中反复出现关于坐禅的描写以及表达这种趣味的诗僧往往反倒不会是禅僧,而恰恰是天台僧。虽然从马祖的“平常心是道”的逻辑中也可以看出不再执着于“不立文字”的思路[27](11)⑤,但这个思路的真正践行还要等到北宋文字禅时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禅宗要求不落言筌,而诗僧们作品中“禅”字的反复出现与禅宗第一义不可说的精神也是相违背的。我们只要稍稍观察禅师们的偈颂就会了解这一点。
由上文可知,由于天台宗的这一段历史被人们误解,导致此一时期众多诗僧的天台宗背景被人们忽略,也正因为如此,天台宗诗僧的创作传统也进而被遮蔽。考察天宝直至晚唐、北宋天台诗僧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三、天台宗僧诗的创作传统
考察唐宋以来的天台宗诗僧的创作历史及实践,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下这些传统。
(一) 文人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的诗歌内容
天台宗僧侣的文人化程度无论在唐代还是宋代,都较禅僧高出一筹,这和天台宗重视经教有很大关系。早期的禅宗完全是一种农禅,许多禅僧就是失去土地的北方流民,不少人甚至不能断书识字。慧能以后的禅宗诸大师也出现了进一步疏离经教律论的倾向。周裕锴总结为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一,进一步怀疑否定言教经典的作用,由“藉教悟宗”演变为“离经慢教”,呵佛骂祖变得平常;其二,进一步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故多采取有象征譬喻意味的姿势动作来说法,或使用形象直观的方式启人智慧,如德山棒、临济喝,沩仰宗的圆相等;其三,广泛使用俗语口语,或是不合常规的戏言反话,以突破经典语言的拘束,并摆脱经典教义的束缚,强调语言的随意性、自在性,使人们从对语言的执迷中解脱出来,直接体悟真如[28](5−6)。也正因这样的原因,使得禅僧在文人化的程度上远较天台僧落后,当天台宗的诗僧在和文人士大夫们进行诗歌唱和的时候,禅僧们正在忙着搬柴运水,并体会着其中的神通与妙用[29](437)⑥。
蒋寅指出,唐代诗僧灵一“在与僧道俗流的交往中,他的诗就基本不带有释子的色彩了,相反却有很浓厚的世俗情调”[7](302)。比如下面这两首诗。
酬皇甫冉西陵见寄
西陵潮信满,岛屿没中流。
越客依风水,相思南渡头。
寒光生极浦,落日映沧州。
何事扬帆去,空惊海上鸥[11](9121)。
酬陈明府舟中见寄
长溪通夜静,素舸与人闲。
月影沉秋水,风声落暮山。
稻花千顷外,莲叶两河间。
陶令多真意,相思一解颜[11](9127)。
日本学者河内昭圆认为这两首诗显示出的心情、语言、技巧都与一般文人作的酬和诗没什么差别。蒋寅举出《送明素上人归楚觐省》一诗,认为如果不看题目和作者,这首诗和大历十才子送人归觐之作并无不同,从中可看出灵一观念中的世俗倾向[7](302)。而灵一与时人多有来往,在文人士大夫中颇有影响,独孤及《塔铭》记载他“与天台道士潘清、广陵曹评、赵郡李华、颍川韩极、中山刘颖、襄阳朱放、赵郡李纾、顿丘李汤、南阳张继、安定皇甫冉、范阳张南史、清河房从心相与为尘外之友,讲德味道,朗咏终日,其终篇必博之以闻,约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投之以法味,欲使俱入不二法流”[18](3963)。此外,他与诗坛严维、刘长卿、李嘉祐、郎士元等人亦有诗文往来。高仲武云:“齐梁以来,道人工文者多,罕有入其流者。一公乃刻意精妙,与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伟 欤?”[30](143)对灵一评价甚高。蒋寅对灵一诗歌进行考察后,认为灵一主要活动在天宝末至宝应初,他与众多文士的交游为日后大历诗坛的僧俗交流开了风气,“大历时期诗僧的世俗化和诗人对佛教的热衷两种倾向同时由此展开”[7](305)。本文亦赞成这个观点,并认为以灵一为代表的天台宗诗僧由此也逐渐形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第一个特点:生活文人化,诗歌世俗化。本文开篇所引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就是对这一系的诗僧队伍所作的简单描述,也可以看作是对他们创作传统的揭示和认同。
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宋初,九僧及其诗歌就表现得很明显[31]⑦。许红霞在《宋初九僧丛考》中详细考察了九僧与时人的交游,有陈尧叟、陈尧佐、凌策、宋白、朱严、卢稹、柴成务、种放、安德裕、钱昭度、王德用、陈充、魏野、林逋、钱若水、徐任等人,其中不乏当时的著名文人如杨亿、王禹偁等,有些人还身居要职,如寇准、丁谓等[32](65−76)。许氏由于误把九僧当作禅僧,所以又得出宋代的禅僧也已经世俗化了。其实应该是天台宗僧侣世俗化并文人化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一般文士并没有什么差别,在京师与士大夫交游酬唱,分题赋诗,这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现在流传的与九僧有关的故事其实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如惠崇应寇准之邀在池上分题赋诗,足见他们与文人之间的关系之深。同时,他们的诗歌也与一般文人并无二致,而北宋禅僧的文人化还要等到北宋中期。这里略举几首九僧的诗歌为例。
送惟凤之终南山
希昼
阙内寒生早,南山万木凋。
长空人绝望,积雪独寻遥。
静息非同隐,闲吟忽背樵。
几侵峰定月,相念起中宵[33](1443)。
晚次江陵
简长
楚路接江陵,倦行愁问程。
异乡无旧识,多难足离情。
落日悬秋树,寒芜上废城。
前山不可望,断续暮猿声[33](1457)。
池上鹭分赋得明字
惠崇
雨绝方塘溢,迟徊不复惊。
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
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
主人池上凤,见尔忆蓬瀛[33](1466)。
惟凤曾往终南山寻访道友,九僧中多人有诗相送,希昼此诗即是作于这种情况下。“阙内”疑为“关内”之误写,先言关内早寒,南山已是万木凋枯,于此季节送友入关赴远,别离之情颇让人不堪;颈联遥想惟凤在终南山的静修和闲吟;尾联写此后自己每见山巅之月,自会想念起友人。简长之诗则写自己的一次行旅经历。旅途已经疲惫不堪,更兼以于异乡无旧识知音;黄昏之际,一片荒寒之色,“落日”“秋树”“寒芜”“废城”,为诗人所见之景,从中亦可看出诗人心中之愁苦;因此就有了尾联的不敢遥望前山,因为断断续续的猿啼只会让客中的诗人更加难以控制内心的情感。惠崇的诗就是前文提到的应寇准之邀的分题之作。首联点题,并由“雨绝”带出颔联的日暖风清,曝翎引步;颈联依旧扣题而行,白鹭因在池上飞翔,故时时于水中照影,烟霭之中,羽毛依旧洁白明亮;尾联直接表示看到池上之鹭,不由得萌生隐逸之思。
文人化的诗僧也像文人士大夫一样,用诗歌表达对友人的怀念和自己的离愁之苦闷、行旅之艰难,而分题赋诗更是文人之间的风雅之举。这些内容在九僧的诗歌中比比皆是。我们或许会问,此时禅宗大师们的作品又是怎样的风貌呢?下面举几首与九僧差不多同时的汾阳善昭和雪窦重显的作品来作个简单的 对比。
与重岩道者住山歌
善昭
住山须识山中主,不识徒劳山里住。青山绿水眼前飞,白灵散漫山头去。岩又高,岭又峻,曲褶徘徊身自困。临崖石上坐思量,正性不明心躁闷。望林峦,看石壁,满目杉松悬布滴。不知何者是真山,妄念空多元不息。我修行,凭何力,见性未分无道德。将甚酬他施主恩,一米七斤难消得。愿今身,逢知识,决择身心去荆棘。常持法雨润心田,百福庄严俱济益。豁然通,心明悟,这回识得山中主。行住坐卧体轻安,问答随机巧回互。身如山,性如水,山水空花无表里。对境看时似有形,子细推穷从谁起。既分明,心通彻,坐卧山中常快活。不消功力用求真,皎皎青天见明月。照山林,无不遍,一片霞光如白练。飞禽走兽任纵横,皆是向渠影中现。师子王,常独步,百怪千邪离惊怖。龙天释梵总归依,此是妙峰真正主。千溪万壑总唯心,直至涅盘山上路。颂曰:山中有主山中住,山石经行山水语。端坐山林山色心,心外无山山是生。识得山中不死人,觉智圆明自看取。乾坤大地及江河,总是山僧行李处[34](621)。
因读《又玄集》
善昭
因读又玄集,堪嗟错用心。
不除三惑苦,总被四知侵。
献宝亏家宝,求金失自金。
几多迷路者,不解自推寻[34](628)。
送蕴欢禅者西上
重显
金阙路曾遥,行行直开泰。
石房云未闲,杳杳若相待。
高踪逾履冰,何人不倾盖。
早晚承帝恩,再卜林泉会[33](1641)。
送僧之金陵
重显
胜游生末迹,杳自狎时群。
卷衲消寒木,扬帆寄断云。
曙瓶花外汲,午磬浪边闻。
别后石城月,依依远共分[33](1645)。
送道成禅者
重显
曹溪流,非止水。一点忽来,千波自起。直须钓鳌钓鲸,莫问得皮得髓。
君不见石头有言兮,圣不慕他,灵不在己。成禅成禅,谁家之子[33](1639)。
汾阳善昭乃宋初临济宗著名大师,嗣法省山首念禅师,其嗣法弟子石霜楚圆门下开出宋代禅宗最盛行的黄龙、杨崎两派,禅宗有五家七宗之说,七宗就是在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之上,再加上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派和杨岐派,合称为七宗。善昭是宋代“公案禅”的开山祖师之一,他首创“颂古”这种后来被禅师广为接受的文体,颂古就是颂古德遗事,用韵文来对公案进行评说解释,影响深远。这些颂古虽是韵文,但与诗歌的差别还是很明显,因为颂古的目的是“一定要阐明或暗示禅理,使公案意旨‘皎然’”[35](120)。周裕锴在《禅宗语言》中举出善昭对“鸟窠吹毛”和“俱胝一指”两则公案的颂古,分析后认为“汾阳颂古的确是为了使‘难知’或‘易会’的公案意义‘皎然’,利用韵文便于记诵的特点,普及禅知识,因此并不刻意追求辞藻,卖弄文采”[35](120)。不过善昭的“不刻意追求辞藻,卖弄文采”与他作为禅师对语言文字的态度还是有关系的,《因读<又玄集>》一诗就透露了他的观点。《又玄集》乃韦庄所编,其序云:“昔姚合撰《极玄集》一卷,传于当代,已尽精微。今更采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记方流而目眩,阅丽水而神疲。鱼兔虽存,筌蹄是弃。所以金盘饮露,唯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飨醍醐之味。非独资于短见,亦可贻于后昆。采实去花,俟诸来者。”[36](348−349)其序道出了他的编撰缘起和目的。不过善昭从禅宗立场出发,发现无论是编者还是作者,都是“用错心”,让人嗟叹,因为不能认识到自性本空,所以总是不能免除三惑之苦,成为尘世迷途轮回中人。这也说明善昭对诗文本身还是有着一种排斥,认为文字并不能带来解脱,所以我们看《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虽也收了一卷诗歌,但与同时期的九僧及文人的诗歌相比较,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差别都非常大。如《与重岩道者住山歌》,就满是禅语,说教之意非常明显,其中虽也有着禅宗的一种活泼泼的生气,但终究与文人诗歌相距甚远。而《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几乎都是这类布教或劝世之作。
比汾阳善昭略晚的雪窦重显也以颂古闻名于世。雪窦重显(980—1052),智门光祚禅师法嗣,为云门第四世。他既有文学天才,又深契宗门悟境,因此他将诗骨禅心融结为《颂古百则》,成为宗门歌颂的典型。他改变汾阳善昭那种直白的阐释原则,而代之以“绕路说禅”的新阐释方法,深受丛林欢迎,影响了宋代禅宗的走向[35](123−126)。除颂古以外,重显还有《祖英集》两卷传世,上文所引三首皆出自此集。《送道成禅者》乃是杂言,勉励禅师努力参悟,如能得道,则触处成春,并于其中化用宗门语句。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禅宗大师的身份,与前引九僧送别之诗只写人世间的别愁及思念这种世俗的情感差别非常大。这样的送别诗在《祖英集》中所见皆是。当然重显也能写出《送僧之金陵》这一类的作品,但在其诗歌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正因如此,《四库全书总目》虽称其“胸怀脱洒,韵度自高,随意所如,皆天然拔俗”,并举了他的五言如“静空孤鹗远,高柳一蝉新”“草随春岸绿,风倚夜涛寒”等,认为其五言律诗“皆绰有九僧遗意”,其七言绝句“亦皆风致清婉琅然可诵,固非概作禅家酸馅语也”,但依然认为他“戒行清洁,彼教称为古德,故其诗多语涉禅宗,与道潜、惠洪诸人专事吟咏者蹊径稍别”[37](1313)。就是说重显虽然也创作了一些文人化的诗歌,所谓有九僧遗意,但是他的很多诗还是语涉禅宗,多参禅悟道之类的内容,与后来的道潜、惠洪等诗僧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宋人张伯端有《读雪窦禅师<祖英集>》,其中有云:“雪窦老师达真趣,大震雷音椎法鼓。狮王哮吼出窟来,百兽千邪皆恐惧。或歌诗,或语句,丁宁指引迷人路。言辞磊落义高深,击玉敲金响千古。”[33](6468)他认为阅读《祖英集》是可以指引参禅者的,可见他并不将其当作诗集。而从《祖英集》来考察重显的交游对象,可以发现他多是送赠禅者,而少文人士大夫。重显虽“盛年工翰墨,作为法句,追慕禅月休公”[38](417),极富文学才华,他的文人化程度和文学性的创作虽较善昭已有发展,但囿于他禅宗大师的身份,与九僧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及影响比较,二者相去甚远。《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引草庵《教苑遗事》有:“时人语曰:‘法智讲经明觉颂,慈云谈辩梵才诗。’”[39](916)法智乃知礼赐号,明觉是重显赐号,慈云为遵式赐号,梵才即长吉赐号,由时人之语亦可看出,重显之颂古当时极有名,但他并没有被视为诗人,而是被视为禅宗大师,与天台宗大师相对举,而真正以诗而得名者乃是梵才大师长吉。
(二) 天台宗诗僧喜用五言律诗
考察从灵一、法照、清江、皎然、灵澈、贯休到宋初九僧的诗歌,可以发现在众多的诗歌体裁中,他们对五言律诗情有独钟。比如灵一现存诗歌41首,其中律诗占了绝大部分,共有32首,这其中五言律诗又有24首之多。法照所存三首皆是五言律诗。清江现存21首诗歌,五言为12首,其中五言律诗为9首。皎然、贯休才气较大,众体皆备,诗歌留存也比较多。灵澈继皎然之后,亦在诗坛有较大影响,可惜诗歌所存无几,其现存作品中几首五言律诗还是晚年被流放汀州时所作,可知亦喜作五言律诗。至于宋初的九僧,所存诗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言律诗。从这个角度看,天台宗诗僧对五言律诗还是有着比较特殊的偏好。灵一在诗坛发挥影响的时候,李嘉祐、郎士元、刘禹锡等人尚未成为诗坛骁将,灵一与他们的交游为日后大历诗坛的僧俗交流开了风气[7](305),也为大历诗坛和天台宗诗僧选择了一种他们擅长的诗歌体裁。
陈伯海曾专门讨论过律诗在体制上的特点:“与古风、绝句相比较,律诗在体制上有这样两个特点影响到它的美学功能。其一,它的篇幅介乎古风与绝句之间,既不便于象古风那样放开笔力,自由驰骋,也不同于绝句要尽量收缩,集中一些。……其次,如上所述,律诗的特点是格律限制极严,不仅要像近体绝句那样定篇、定句和讲求平仄声韵,还要组织对仗,加长篇幅,从而大大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格律上的规定,同时也就是构成律诗的新的要素,只要运用得恰当,却也可以为诗歌的表情达意提供更为多样化的美学手段,进而使诗篇的艺术天地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展,于是限制便又转化成为自由。而如何实现这一境界,也是历来的诗人和评论者反复钻研的重心。总的说来,律诗可以认定为最难写也最好写的一种诗体。说它好写,因为若不追求意境深广,体气醇厚,只要拼凑起中间两联对仗,再装上一头一尾,即可成篇。这仅需匠师的功力便可应付。……说到难写,则由于要在有限的篇幅和严密的格律限制中开拓广阔的天地,进入自由的境界,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又要求舞步的优雅自如,从容中节。这当然给这一诗体的创作,带来了特殊的困难。”[40](155−156)而后来天台宗诗僧习惯上喜用五言律诗,既和当时诗坛的风气有关,又跟他们多不是才大力雄的诗人相关,因此多不喜欢气势恢宏的古风,也不习惯婉曲空灵的绝句。他们讲究苦吟练字,仔细锤炼中间两联,“其诗专工磨炼中四句,于起结不大留意”[41](1715)。所以我们看到九僧诗歌在当时有许多名句流传,惠崇还曾自选《句图》。同时,写作五言律诗虽然形同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他们长期攻此一体,自然也渐渐熟稔,所以也创作出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引起时人的注意,如唐代的灵一、宋初的九僧等就都曾在诗坛引起较大的 反响[42](34−47)。
与天台宗诗僧不同的是,禅师在写作偈颂之时却是要表达在参禅时瞬间的心灵体验和感悟,这个时候若用讲求格律的五言律诗,往往很难做到。而绝句和杂言体则比较适合进行迅疾的写作,有如禅宗主张的不可拟议,他们在写作偈颂之时往往也是不进行苦吟和锤炼,而是脱口而出。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禅师们的偈颂大都是绝句和杂言体,连极富文学才华的雪窦重显都受到禅宗这一创作传统的影响,其《祖英集》中相当多的诗歌都是杂言和绝句。
(三) 天台宗诗僧的情绪极为节制
天台宗诗僧的情绪往往都极为节制,诗风多显得灰寒和冷寂,这既和他们僧人的身份有关,也与五言律诗这种诗歌体裁有关。作为僧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一般比较简单,多在山林,虽偶涉尘世,但都不是他们的常态。像九僧虽也曾在京师聚集,但他们的笔下还是多模山拟水,又由于刻意雕字琢句,虽也显得精工细腻,但有时也使得整首诗难臻浑厚之境,而多显苦寒清冷之态⑧。举希昼和惟凤二诗为例。
寄河阳察推骆员外
希昼
郡斋邻少室,夏木冷垂阴。
况是多闲日,应悬长卧心。
角当中岛起,樯背远桥沈。
独爱南楼月,终期宿此吟[33](1448)。
寄希昼
惟凤
关中吟鬓改,多事与心违。
客路逢人少,家书入关稀。
秋声落晚木,夜魄透寒衣。
几想林间社,他年许共归[33](1461)。
希昼诗当作于夏季,骆员外之郡斋虽近少室山,但诗称“夏木冷垂阴”,实在有点夸张,这个“冷”字其实更多是来自诗人的心境,所以我们看这首诗并无多少夏日的炎热或蝉噪虫鸣,整首诗倒是有着秋天般的清寂。惟凤之诗作于秋日,其中孤独和寒意更是溢出诗外。
禅宗主张随处作主,强调自我的主体精神,这也反映在禅僧偈颂的创作上,他们的偈颂多张扬、热烈,甚至奔放,有着一种活泼泼的主体精神在其中,与天台宗僧诗面貌迥然有异。再举重显一诗为例。
送清杲禅者
动兮静兮,匪待时出。
云霞闲淡作性,金铁冷落为骨。
知我者谓我高蹈世表,不知我者谓我下视尘窟。
道恣随方,情融羁锁。
紫栗一寻,青山万朵。
行行思古人之言,无可不可,南北东西但唯 我[33](1369−1370)。
其中的自信和对行人的热情期许都完全不同于九僧诗歌的清冷。
四、结语
根据徐文明、俞学明的研究,我们发现学界一直习焉不察的荆溪湛然之前的所谓天台宗衰微不振的历史并非事实,在天台宗本山之外,活跃于玉泉、衡岳以及两京的天台支系高僧对天台宗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徐、俞二人的研究既是本文考察天台宗诗僧的基础,又为这一时期众多诗僧的天台宗背景被忽略提供了一种解释。而本文对天台宗诗僧创作队伍的勾勒,对僧诗创作传统的考察,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再度证实了上述两位学者的结论。

注释:
① 皎然《杼山集》卷八《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序》云:“大师生缘钱塘范氏,讳守真,字坚道。……昼之身戒,亦忝门人。”
② 皎然《杼山集》卷九《苏州支硎山报恩寺法华院故大和尚碑并序》云:“予虽后学,夙聆徳声。”
③ 皎然早年的天台宗倾向确实很明显,不过他后来又遍参禅门诸师,深受江西洪州禅的影响。可参见《大历诗人研究》相关论述。不过笔者觉得如果忽视了天台宗对皎然的影响,也难以全面把握皎然的诗歌。
④ 《佛祖统纪》卷二二“未详承嗣传”第八中有“玉泉真公法师、南岳承远法师、南岳法照国师”,其中真公当是惠真,三人实乃师徒相承。惠真为恒景法嗣,恒景乃灌顶法嗣玉泉道素的门人。
⑤ 周裕锴指出:“既然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是禅的经验,那么,禅也就不再执着于‘不立文字’,离文字是禅,用文字是禅,文字的基础里有禅的世界,禅的表现里有文字的世界。”不过纵观唐宋禅宗史,可以发现,禅宗从“不立文字”走向“不离文字”还是在北宋才真正完成。
⑥ 葛兆光指出晚唐五代开始出现了禅宗的文人化和禅思想的文学化转向。参见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的相关论述。但是,与天台宗相比,禅宗无论是文人化转向的时间,还是文人化程度的普遍性都远远不及。
⑦ 拙作《宋初九僧宗派考》已考订九僧皆属天台宗。
⑧ 九僧也有一些气势雄浑之作,但总体上不以此取胜。
[1] 刘禹锡. 刘禹锡全集[M]. 瞿蜕园,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2] 道宣. 续高僧传[M]. 郭绍林,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3] 项楚. 寒山诗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4] 陈允吉. 古典文学与佛教溯源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5] 志磐. 佛祖统纪[C]//大正藏: 第49册. 东京: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34.
[6] 赞宁. 宋高僧传[M]. 范祥雍,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7] 蒋寅. 大历诗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 鸠摩罗什. 妙法莲华经[C]//大正藏: 第9册. 东京: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34.
[9] 慧思. 法华经安乐行义[C]//大正藏: 第46册. 东京: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34.
[10] 潘桂明, 吴忠伟. 中国天台宗通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11]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12] 贾晋华. 皎然出家时间及佛门宗系考述[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1): 110.
[13] 皎然. 杼山集[C]//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71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14] 刘长东. 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15] 徐文明. 天台宗玉泉一脉的传承[C]//吴力民. 佛学研究: 第7期, 北京: 中国佛文化研究所, 1998.
[16] 普济. 五灯会元[M]. 苏渊雷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7] 熙仲. 历朝释氏资鉴[C]//卍续藏: 第76册. 京都: 藏经书院, 1912.
[18] 董诰.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9] 昙噩. 新修科分六学僧传[C]//卍续藏: 第77册. 京都: 藏经书院, 1912.
[20] 安腾俊雄. 天台学: 根本思想及其展开[M]. 苏荣焜, 译. 台北: 慧炬出版社, 1998.
[21] 演培. 华严哲学的组织与实相论[C]//张曼涛.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第70册. 佛教各宗比较研究. 台北: 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9.
[22] 俞学明. 湛然研究——以唐代天台宗中兴问题为线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3] 徐文明. 唐中期至五代时两京支系略考[C]//方立天. 宗教研究: 第一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4] 贾晋华. 皎然论大历江南诗人辨析[C]//文学评论丛刊: 第二十二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25] 郭朋. 坛经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6] 慧然. 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C]//大正藏: 第47册. 东京: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34.
[27] 周裕锴. 中国禅宗与诗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28] 周裕锴.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9] 葛兆光. 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 从六世纪到十世纪[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0] 高仲武. 中兴间气集[C]//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332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31] 张艮. 宋初九僧宗派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67−73.
[32] 许红霞. 宋初九僧丛考[C]//古典文献论丛.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33]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4] 楚圆.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C]//大正藏: 第47册. 东京: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34.
[35] 周裕锴. 禅宗语言[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36] 元结, 殷璠. 唐人选唐诗十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7] 永镕.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8] 明河. 补续高僧传: 卷七[C]//卍续藏: 第77册. 京都: 藏经书院, 1912.
[39] 宗晓. 四明尊者教行录[C]//大正藏: 第46册. 东京: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34.
[40] 陈伯海. 唐诗学引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88.
[41] 方回. 瀛奎律髓汇评[M]. 李庆甲汇评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2] 张艮. 九僧两宋诗名流传辨析[C]//周裕锴.新国学: 第十三卷.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On the poetry creation tradition of Tiantai Sect
ZHANG Gen
(School of Literature,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Jianxi 341000, Chin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iantai Sect formed a unique Buddhist poetry writing tradition that differs from Zen. Their tradition manifests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iantai Sect advocates the literati's way of life, and their poetry is full of secular contents, unlike Zen poetry. Secondly, Tiantai Sect prefers the five-character octave with emphasis on the two verse lines in the middle, while Zen monks prefer confessions and quatrains to express the sentiments of Zen. Thirdly,Tiantai Sect expresses its emotions in an extremely restricted way, often grey and cold, while the Buddhist hymn of Zen is becoming more prominent and warm. The tradition of the poetry creation of the Tiantai Sect has long been obscured,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a certain period of history after Zhiyi of Tiantai Sect was misunderstood, which led to the negligence of the Tiantai Sect background of many poets during this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se of Zen influences people’s attention to Tiantai Sect, which made the academia misunderstand the "Zen" in the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t sects, the study on the poetry creation tradition of Tiantai Sect can not only reveal and avoid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stud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but also restore the original facet of poetry creation of Tiantai Sec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iantai Sect; monk poems; monk poet; poetic creation tradition
[编辑: 胡兴华]
2017−12−28;
2018−05−10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7)规划项目“唐宋天台宗诗僧与僧诗考论”(17WX14);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天台僧与北宋诗坛研究”( 16YJC751036);2015年度赣南师范学院招标课题“天台宗与唐宋诗歌”(15zb11)
张艮(1977—),男,安徽庐江人,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佛教文学,联系邮箱:2003zhanggen@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4.020
I207.2
A
1672-3104(2018)04−01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