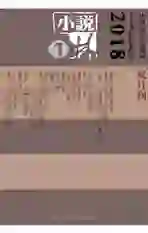肖像
2018-01-09黄大荣
久居小城,俗事缠身,耳边整日价乱哄哄,便觉得憋闷,烦,想寻点儿清静。市郊桃花村人山人海,去一次便告饶了。江南虽有黄花可赏,也就一天来回,便想走得远些。原想买船票东下的,船却早已停开。只好携妻子坐车去省城。首站便是去文联大院寻访旧友。这里傍湖,林木森森,颇有世外之意趣。
大楼三层一间阔大的房子,是F的居所,很简洁,一床,一桌,数椅,角落里似有盥洗器具,看不清,窗外大树的浓荫,让房内也染得浓绿。因事先有约,私人拜访,所谈尽是儿女家常,无一字关涉文学。吴大姐在座,说有公事将去北京。妻子忙说,我这就把儿子的电话给您,我儿子在北京。正待翻看电话本,我说,大姐把电话告诉我,叫儿子打给你,上他家去玩。大姐说,电话早告诉你了。我便为儿子的失礼感觉羞愧。妻子看出我的尴尬,转换话头说,这房子好大,只是也忒简陋了,置几样好家具,蛮享受的。我生怕F听了不高兴,说,这是F君的休息间,所有陈设都是公家的;当初你住机关大院的单身公寓,不也这样么。F坐在一角,只静静地听,矜持地笑。她总这样,含蓄,低调。已近中午,F招呼我们下楼去吃饭。
走出房,却见一间大画室,空空荡荡,不甚亮爽。只在一角,一团人围着,聚精会神观看着什么,悄没声息。吴大姐说,Z又在给人画像。我对看人作画一向颇有兴趣,便向那儿走。F和大姐和妻子也随我走来,围观的人们,闪开一条窄窄的甬道。画家Z扭过头,与我相视一笑。我们彼此应该相识的,他的面孔我很熟悉,矮小身材,很瘦,但精神。五官分开来看,没一样可圈可点,比如,眉毛稀疏,短粗;嘴不成形状,甚至有点歪;小鼻子小眼的,还是单眼皮;但整合到一块儿,不觉得难看,亲切和蔼,还有一点儿鬼祟、滑稽,显出机警灵气,显出心地纯良。年纪三十出头。我与他应该是忘年交。我挤过去,从人头缝隙中看他作画。他好几次偏过头看我,每次我都感觉他只能看见我的半边脸,也不知道他看我是打打招呼,还是想为我也画一幅像。我惊奇他的確是高手,一支速写笔,就是用老式钢笔将笔尖折弯的那种,随意在尺幅之间涂抹,粗细转换自如流畅,一笔到底,很肯定的,不修改,不重复,不用一分钟,一幅肖像完成,神形兼备。先运粗笔,表现素描关系,从眉骨下的眼窝到鼻翼最后到嘴唇,一笔下来,已经将面部骨骼肌肉烘托出来,有了七分神似;再运细笔,勾勒眼眶,画面部轮廓,已得八分成功;第三笔,点睛,笔尖不知怎么一转,一顿,似有无限玄机,人物便活了起来,岂止是活,简直是灵魂出窍。最后大笔勾出头发衣领,收煞干干净净,毫无拖泥带水。
我自然很想请Z为我画一幅肖像。我在文联待了二十年,没好意思找艺术家求一幅“墨宝”——我知道,对他们许多人来说,无异于求他施舍一笔可观的金钱,现在我已经退休,此时此地又是“外省人”身份,更没有勇气开口。但我意外发现,Z几次偏头看我,就是想给我画像,他有惊人的形象捕捉力和形象记忆力,仅凭几瞥之间的印象,就抓住了我的典型特征,这不,此时此刻,他正在洋洋洒洒勾画的,正是我的肖像,而且画得很不错,我不禁暗自窃喜。画毕,他未及署名,站起身,凝视片刻,突然一把将画稿揉作一团,扔进了抽屉。没等大家反应过来,Z套上速写笔笔筒,说一声“开饭啰”便要离开画桌。众人熟知他这德行,也便一哄而散。
Z与我们走在一路。他那稀疏短粗的眉毛,凝作一堆,仿佛无限心事。F说,Z先生,你不是问过我,黄先生何许人么,这位就是。吴大姐说,F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了联想,你们俩性情很有几分相似呢。大姐对我附耳说,问过他读你文章的感受,他只两个字:痛快。Z便停住了脚步。这时,我们竟都随他在宽敞的楼梯拐角处站定了。那里有一张乒乓球台。Z突然从我手里取走一只大信封,里面装的是一本文学杂志。他一边拧开笔套,一边盯着我看,足有两三秒钟。接着在信封上快速勾画起来。这一次比上次画得更生动更传神了。画完,将信封放在乒乓台上,急匆匆奔楼下而去。
我望着他为我画的肖像,惊呆了——
画上的那个“我”似乎说了一句,跟我来!我顿时灵魂出窍,麻木的身子,鬼使神差地跟随他出走了。
渐行渐远,一路所见所闻,越来越陌生。是亦步亦趋,还是大步流星?后来乘坐火车轮船或飞机没有?记不清了,似乎也无关紧要。最后有一点印象,好像穿越了一个类似隧道的幽暗屏障,我与“我”就合为一体了。这是一个陌生的不知名的旷阔之地。万籁寂静,准确地说,是一片深度的宁静或沉寂。蓝灰色的天空,无边无际,银灰色的沙滩,一望无垠。一条大河与蓝天相接,横越天际,却波澜不惊。水,似流不流,无声,又分明并未冻结。一只古旧木船旁,横卧着一位人面兽身的少女,遍体暗红,眼睛正对着一棵枝叶掉光了的枯树,枯树横斜的枝干上,挂着一片软软的橡皮状的东西,细看,是折叠的时钟。一匹马和一个无首男人的骨骼躺在沙滩上,头颅却完好,待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些难以指认的物件,似一些被肢解变形的机械,散落于沙滩各处。“我”并不觉得困惑和惊悚,仿佛自己定格其间,与这一切构成的完整的画面的色彩和形体,都如此的和谐、安详,自然、圆融。天空星星无数,光亮而无闪烁,分不出是昼是夜。一切都是静止的,无语的。我知道,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我突然想到,这里是创世前上帝的试验场?是史后的世界?还是与我们贯见的存在相互对称的另一个存在?是我的现实的映像——“我”的现实?
我和“我”都不见其影了。不过,只要我一闭上眼,稍稍入定,“我”,那幅肖像的“我”,便会栩栩现身。眼睛逼视着我,嘴唇张张阖阖,无声,却犹如闷雷,訇然撞击着我的胸膛……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
我突然看到,“我”的生命如此鲜活灵动,如此富有生气,又如此严肃,如此令我敬畏。
我试图一一回答“我”的提问,一向自以为可以口若悬河的我,竟然失语了,根本无力与“我”对话!
……我在忙忙碌碌中,很少关注自己的形象,偶尔照照镜子,也就梳梳头,刮刮胡子。那是静态的我,从未深究自己的内心。我想,这幅画,乃是“神画”,将“我”从现实中的肉体的实在的我分离开来,让我面对了另外一个人,这人是我,又不是我。“我”向我提出了一个个令我震撼不已的问题:我是谁?什么气质?什么性格?什么思想?我曾做什么,在做什么,将做什么?我为谁活?我活得盲目还是清醒,快乐还是痛苦,值还是不值?此时此刻,这些看似陌生、遥远的问题,汹涌而至,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当时的面色肯定苍白,神情肯定十分瘆人,不然,妻子、吴大姐和F不会一齐呼唤我的名字,声音里充满恐惧……
我使劲眨了几下眼睛,又使劲摆头,“我”才长叹一声,化一缕轻烟,消失在茫茫旷野……
我感到,一个陌生的灵魂,悄无声息地落回到我的身体。而眼前信封上的“我”,突然变得皱皱巴巴,而且脆裂成一块一块的了。我想回到刚才的映像鲜明的“我”里去,已经不可能了。一种刻骨的痛憾与惆怅袭来,头疼欲裂,浑身软绵绵轻飘飘的,像被谁抽去了筋骨。如果不是妻子搀扶,我肯定会从楼梯上一头栽下……
下了半层楼梯,站在又一个拐弯处的平台上,我听见楼下有一片惊呼之声:刚才围观着Z看他作画的人们,将Z簇拥在中间,呈半月形,Z正好面对着转角平台上的我。他笑着,笑得很得意,很自信,还有点顽皮、幽默。他藏在身后的手,慢慢滑到前面,向我展示他的新作——我的肖像,画在一块雪白的硬纸板上,足有一米见方。他故意倒拿着,让我疑惑究竟是不是我。接着,他又慢慢将画掉了个头。我这才确认是我,正是信封上的那个“我”的放大。众人一齐鼓掌,妻子、吴大姐和F也起劲鼓掌。我知道,是为Z的作品鼓掌,也是为我即将获得这件珍藏鼓掌。
我快步下楼,握紧Z的手,言谢的话语怎么都说不出口,眼泪却扑漱漱地直流。F替我连声道谢,却见Z的脸色倏然大变,他望着我,结结巴巴地说,黄先生,这幅画,我不能给你,我还是没有画好,我读过你的文章,我以为……就在刚才与你握手对视的一刻,我又看到了你另外一些东西,更重要的东西……我相信,一个更真实的你,已经印在我的心里了。我知道你马上要回沙市,请放心,我会把画寄给你……
F和吴大姐及妻子连忙说,这一幅已经非常好了,就让他带回去吧。Z不礼貌地瞪了她们一眼,一转身,头也不回地径自离去。
我与诸位道别的时候,已经想好了,我将把Z的作品,我或“我”的肖像,挂在什么地方。
作者简介:黄大荣,男,湖北沙市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先后在电厂、文化馆、文联供职。曾任某刊社长、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国宝》《炎凉世界》《新摩登时代》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小叶女贞墙那边》《金手表》,文史随笔集《不用胭脂媚世人》等。中国作协会员。现为荆州市作协主席,《荆州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