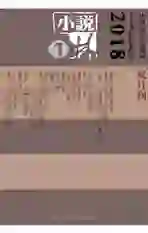疯爷的火车
2018-01-09张伟东
1
明晃晃的日头下,疯爷把裤子褪到了小腿弯,他像一只掉光毛的老猴子,瘦得尖尖的屁股就那么朝天撅着,豆鼠一样的一对黄眼珠滴溜溜地乱转,往四下撒眸着,他是想摸索个趁手的家伙什儿,把腚眼儿抿干净了,好麻溜提上裤子。
疯爷擦屁股是从来舍不得用纸的。疯爷说了,屁眼儿就是用来拉屎的,一臭烘烘的地儿,拿纸擦它,简直就是暴殄天物。疯爷内急的时候,一般都是空着手出门,找个背风的犄角旮旯,就地就解决了。惯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他一边吭哧吭哧地大着便,一边撒眸眼巴前的树枝儿、木棍儿、秸杆儿、包米叶子、石头、包米瓤子、土坷垃,若是连这些东西也划拉不着,摸个砖头瓦块之类的也能将就用用,至于屁眼儿揩没揩干净,那么隐秘的部位,也没人凑近了细瞅。
然而,这次的状况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妙。院落里仿佛刚刚刮过一场狂风,扫得连一根细稻草都摸索不到,害得疯爷抓了瞎,只能尴尬地翘着腚。大白天在自家的当院里出乖露丑,若是被街坊四邻瞧见了,岂不羞死?
瞅了瞅老屋山墙的一角,疯爷有了主意。他像一只老鸭子似的,左一跩右一跩地挪动过去,然后高高地翘起尖屁股,把瘦腚沟一点一点地移过去,移到墙角的棱上,轻轻地摆了那么几下,就算解决了。可能是蹲得时间太久了,疯爷感觉自己的两条腿又酸又麻,有点不大听使唤了,他拿手掌摁住膝盖,哎哟了好几声,才踉踉跄跄地把腰杆抻成了弓形。疯爷的两只手不停地哆嗦着,吭哧了老半天,窸窸窣窣地系紧了腰间的那条油渍麻花的蓝布带。疯爷直起身,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房屋前后用栅栏围起来的这块空地,心里直画魂儿。往时,这院子里脏乱得横七竖八的让他下不去脚,今儿是哪个王八羔子把院子收拾得这么利索呢?
疯爷骂的王八羔子不是别人,正是他自个的儿子满囤。前些日子,有人给满囤的儿子小石头介绍了个对象,女方的父母这两天就要过来相门户,为了给未来的亲家留下个好印象,满囤起了个大早,抡起一把大扫帚,把房前屋后的院子精心地划拉了一遍。犄角旮旯里堆放着的那些没用的碎砖头呀、烂瓦片呀、土坷垃什么的,平日就安安静静地躺在角落里,静物一样与这院子里的其他景致相得益彰,也没觉出来有多余。如今呢,院落里突然间变得干净起来了,那些没用的碎砖头呀、烂瓦片呀、土坷垃的就突兀得碍眼了。满囤从下屋里翻一把铁锹出来,将那些没用的碎砖头烂瓦片土坷垃敛巴敛巴,收进一架小独轮车的车斗里,费了好些力气推出去,倒进村西头的壕沟里。
满囤张罗给小石头办喜事,家里家外的老亲少友都通知到了,只有疯爷还不知情。疯爷上了岁数了,说话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他每天只重复着四件事:睡觉、吃喝、拉尿、唠叨。家里人不再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待,只当是家里喂养着的一只老猫或者一条老狗,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自然也就不会特意告诉他。这话说回来,告诉他也没什么用,啥忙也指望不上他,疯爷在儿女们的眼里现如今就是个老糊涂,是吃白食的老废物。儿女们嘴上虽然没有这么说,但心里个个都明镜似的,疯爷已经九十九了,活到这把岁数,也该到寿了。
2
方便完了,疯爷感觉排空后的身体轻飘了不少,他双手颤颤巍巍地把着墙,像只壁虎一样缓慢地挪动着,他是要挪回到正房旁边的那间下屋去。
满囤的媳妇桂芝开门出来倒刷锅水,一眼就瞄见山墙的一角上抹着黄灿灿的一块粪便,招了一层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嗡嗡地叫得热闹,像是在赶赴一场饕餮盛宴。桂芝拿眼睛向四下里梭巡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在地面上,她发现顺着山墙根往下屋的方向,还有几处将干未干的脚印。这是因为疯爷每次方便的时候,都尿不净,尿液自然就流进了裤裆里,然后再从裤裆里慢慢地渗出来,最后在脚底下积成一洼尿窝窝。这样,疯爷的两只鞋底就泡在尿窝窝里了。等他起身往下屋走的时候,身后边就会留下一溜湿拉拉的脚印。
桂芝一手抓着盆,一手掐着腰,冲着下屋的方向骂道,这老不死的,到处拉屎,还把屎往墙上抹,真是人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桂芝的嘴巴不干净,骂疯爷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这也不能完全怪她,疯爷有时候会蹲在前院园子里的柴火垛底下拉屎。拉完了,图方便,他就拽根柴火揩腚,揩完了,顺手就把揩腚棍子丢进柴火堆里。赶上阴天要下雨,桂芝跑出来往屋里抱柴火,双臂一搂,就摸了一手的屎,桂芝这时就会破口大骂,这老东西,活这么大岁数了,一点人事儿不干,咋就不快点儿死呢,给好人腾腾地方!
疯爷佝偻在下屋里那铺硬邦邦凉冰冰的小土炕上。他的两个细腿棒瘦如干柴,包在外面的暗黄的皮肤如油过的蜡纸,又像是日头爷下晾晒过的猪尿泡,更像是被捶打了多年的蒙在鼓面上的那张皮。别看疯爷老成今天这副德行了,那也曾经是年轻过的,在满囤家堂屋里的那块大镜子上,至今还镶着疯爷年轻时候的一张黑白照,相片上的疯爷看上去五官周正,模样也算英俊,乌黑浓密的头发覆盖住头顶。仔细琢磨,那青春是个啥?那青春无非就是燃烧皮下的那点胶原蛋白,这人呀,一旦衰老了,皮下的那点胶原蛋白就耗尽了,隐在皮肤下面的一块块黑褐色的老年斑渐渐地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再老下去,皮下的脂肪和肌肉也耗尽了,就只剩下一条皮囊裹着一副骨头架子了。到了最后,皮囊也不是从前的皮囊了。疯爷的皮囊就像腊肠的肠衣一样薄得透明,可以清楚地看见皮下的筋骨和丝丝络络的血管。躺在小炕上的疯爷,就像桂芝晾在下屋棚杆上的那块老腊肉,已经风干了。
毋庸置疑,疯爷的身体正在腐烂,这种腐烂不见形迹,是由内而外的腐烂,是潜移默化的腐烂。疯爷的肛门括约肌早就失去了弹性,稀便有时候会毫无征兆地打腚眼儿里溢出来。夜里,疯爷不敢大声地咳嗽和打喷嚏,劲儿使大了,身下面就会有屎尿渗出来,疯爷也没什么知覺,就在屎窝窝和尿窝窝里翻来滚去的。儿女们嫌他脏,从来不动手给他擦洗身子。赶上五黄六月,路过下屋的时候,儿女们甚至捂着鼻子低着头,像躲瘟疫一样打房檐子底下一溜小跑过去。桂芝逢人便讲,我们家老爷子这是坏掉了,坏掉的东西就要隔离,不隔离,就容易传染给身边的人。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桂芝让满囤在下屋里盘了一铺火炕,把疯爷从正房撵进下屋里去住了。到了饭时,桂芝就拿一个瓦盔子,单盛出来一份饭菜,打发小石头给疯爷端过去。
进了下屋,小石头不会把瓦盔子撂下就走,而是将菜饭折进疯爷专用的一只海碗里。那只海碗始终在那铺小炕的炕沿上放着,油画里的静物一般,好像从来没有动过,也好像从来没有刷过。海碗的边沿上渍了一圈黏糊糊的东西,像只猫食碗子。
3
自打满囤跟桂芝当家做主了以后,疯爷就变成了磨道上的驴,只能听喝儿。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就再也没有了挑三拣四的权力。
掰开指头数数,疯爷大概快有十年没上过街了。他的活动范围就是这间下屋,即使扩大一点儿活动范围,也走不出房屋前后栅栏围起来的空地。满囤跟桂芝已经再三嘱咐过疯爷了,不能走出这个院子。疯爷也知道,儿子跟儿媳妇也是一番好意,担心他出门走丢了,找不回来家。
可是,疯爷今天突然有点心血来潮,他想到街上溜达溜达,顺便买点他想要的东西回来。他在下屋里捡到了一枚硬币,是个贰分的钢镚儿,他上街的目的就是打算把这枚钢镚儿花掉。钢镚儿是他偶然在炕席底下发现的。他将钢镚儿捏手里,拿衣服的前大襟蹭了又蹭,然后举高了,迎着小窗口投射进来的一缕光线,眯缝着眼睛细瞅,疯爷就像捡到了一枚银币一样开心,脸上显露出顽童般的一抹笑容来。疯爷将钢镚儿放进衣大襟的口袋里揣好,溜着墙根出了大门,往右一拐,就钻进了一条胡同。顺着胡同走到头,刚好开着一家便利店,疯爷就摇摇晃晃地进去了。他在一节柜台前慢慢地收稳了脚,一只手扶着柜台,另一只手从衣大襟的口袋里摸出那枚钢镚儿,颤抖着递给开便利店的妇女,他瘪瘪着嘴,阴着嗓子,拉着长音跟人家说,给我来一匣洋火。
疯爷着实把开便利店的妇女吓了一跳,她感觉疯爷说话的声音像是从上个世纪穿越过来的。她扫了一眼疯爷递过来的那枚钢镚儿,扑哧一声就乐了,老爷子可真逗,這种钢镚儿多少年前就不流通了,你知道不知道?
疯爷听不明白不流通是啥意思,朝开便利店的妇女抖着两根手指头,颤颤巍巍着说,我当家的时候,经常去供销社里买东西,一匣洋火就贰分钱,你甭想糊弄我!
疯爷执拗得要死,非要买贰分钱一匣的洋火不可。开便利店的妇女简直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商量着说,老爷子,您说的那都是老皇历了,现在没有供销社了,也没人用洋火了,现在都使这玩意了。她随手在柜台里摸出一个打火机递给了疯爷。疯爷快活到黄土埋脖子了,也没见过打火机,颠过来调过去地细瞅,捅咕半天也捅咕不出火苗来。开便利店的妇女拿过来给他做了个示范。疯爷眼前一亮,他发现这玩意高科技,比洋火好使多了,轻轻拿拇指一摁就摁出火苗来了。过去烧炕的时候,疯爷一直拿洋火点柴火,洋火保管不好容易返潮,轻轻一划,火柴头就粉掉了,有时候要划上好几根,才能把灶坑里的柴火引着。开便利店的妇女瞅疯爷上岁数了,就决定把这个打火机白送他,然后将那枚钢镚儿放回疯爷衣大襟的口袋里。疯爷拿手摩挲了一下衣襟上的口袋,感觉里边硬硬的,钢镚儿没花掉,还白得了一个打火机,疯爷就跟占了多大便宜似的,乐呵呵地转身走了。
说起过日子,疯爷绝对是个精细人儿。老邻旧居都说,疯爷精细起来有点不可理喻。譬如饭桌上的一块饽饽不小心骨碌到炕席上了,让小孩子的屁股碾成了一张饼,哪怕是被小孩子的尿窝窝泡软乎了,疯爷也不嫌脏,把孩子屁股一扳,干粮拿手抠出来,麻溜填进嘴里去,鼓动几下腮帮子,就吞咽下去了。有时候,碗架子里放馊了的剩饭剩菜,桂芝要端出去倒掉,疯爷瞄见了,就会一把夺过去,仰脖呼噜呼噜地倒进自己嘴里。疯爷的嘴张得老大,跟个漏斗一样,将生了白醭的残羹剩饭漏干净了,才肯把空碗递给桂芝。桂芝背地里跟满囤叨叨,你爹八成是饿死鬼托生的,生冷不忌,馊臭不嫌,他的肚囊简直就是一口泔水缸,是一只折箩桶,你说也真奇了怪了,他吃完了咋就一点不坏肚子呢?
满囤跟桂芝说,你不明白,俺爹那是过去在挨饿的年头里苦怕了……
原来,疯爷的祖上,是山东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人。建国以前,黄河下游连年遭灾,地里打不下粮食来,为了能够填饱肚子,疯爷就带上自个女人,挑着筐背着篓,里边装着孩子,离开山东老家,流转到关外找活路。疯爷拖家带口,坐最便宜的筒舱小火轮,和好多颠沛流离的穷人挤在吃水线以下最底层的船舱里“浮海”下关东。
他们从大连上的岸,接着又往沈阳走,后来又打沈阳奔往了吉林,一路上要饭,一家人历经了常人不能想象的艰辛,又从吉林流落到了黑龙江,最后在北大荒扎下了根。遗憾的是,疯爷的女人,也就是小石头的奶奶,在逃荒的半路上饿死了。那些年,疯爷是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身边的三个孩子拉扯大了。疯爷直至终老,都没续过第二个女人,到头来只落得个孤苦伶仃,儿女们也不孝顺他,还把他撵进下屋里住着,像饲养牲口一样把他圈养了起来。
4
十冬腊月里,下屋四壁透风,疯爷大概是给冻病了。这次怕是病得不轻,已经爬不起来炕了,老胳膊老腿裹在铺盖卷里一动也不动。桂芝把脸贴在下屋的那扇小窗户上面,偷偷地朝里边观察过好几回了,炕沿上放着的那只大海碗里的饭菜已经冻成一个坨了,她似乎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就在她以为疯爷死了这当儿,那个铺盖卷在小炕上轻微地扭动了一下。桂芝黯然地收回了目光,叹了口气之后耸耸肩膀,将两只又红又肿的大手深深地抄进肥大臃肿的祅袖子里,一边往正房这边扭搭,一边嘟哝着,老不死的这是活成精了,三五天没吃没喝了还能动弹,居然没有死,这个老不死的还真禁活啊!
疯爷如蚕蛹蜷伏茧中一样缩在被筒里面,偶尔会把脑壳露出来透透气。疯爷脑瓜顶几绺碎头发像雪一样白,而且细软,如秋后河套里塔头上的一蓬衰草。疯爷没病倒的时候,身子骨还能动弹,知道去园子里划拉一抱柴火回来,自个儿烧一烧炕。可自打病倒了之后,身底下这铺小火炕就再没热过,睡着拔凉拔凉的,一夜哆嗦到天明。
傍晚的时候,疯爷依旧是伏卧在下屋里的那铺冷炕上,一边哆嗦着一边哼哼。哼哼是疯爷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对外界发出的一种特殊的信号,他是想引起儿孙们对他的关心和注意。疯爷哼哼的声音没有那么响亮,但是听着很绵长,很婉转,很筋道。用桂芝的话说,听吧,“老灯台”哼哼得匀乎儿着呢。桂芝除了骂疯爷是老不死的,再就是骂他“老灯台”了。早年间点油灯那会儿,北方人家在外屋和里屋之间的墙上挖一个方孔,放一盏油灯里外屋共用,这个方孔叫“灯台”。后来生活好了,家里有了电灯,这个灯台留着也就没什么用处了。桂芝骂疯爷“老灯台”,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满囤听疯爷在下屋里头没完没了地哼哼,就喊小石头,抱点柴火过去,给你爷爷烧一烧炕。
下屋的炕沿底下,把墙角的地面有个凹进去的方坑,这个方坑实际上就是个灶坑,只是上头没有垒灶台,因为它是缩在炕体里面的,直接连着炕洞子,不能卧锅,只能烧柴火。小石头抱了一大捆干柴进去,蹲下身子,把干柴架进灶坑里,拿打火机熏着了,烧了一会儿,屋子里见了点热乎气儿,疯爷也就不哼哼了。小石头回头把热好的饭菜端到了疯爷的下巴颏底下,瞅见疯爷的手还能拿动筷子,小石头又往灶坑里添了一大把柴火,然后转身回正屋去了。
临睡前,小石头又跑出来一趟,到柴火垛又夹了一捆干柴进下屋,把柴火一根接一根地往灶坑里塞,塞得差不多了,再鏟几锹灰土盖在上面,把火苗压住了。柴火在没有明火的状态下慢慢地闷烧,这个做法可以使柴火燃烧得更久一点,能让炕热得时间更长一些。
炕烧暖了,疯爷睡得舒坦了。后半夜里,疯爷开始做梦了。疯爷很奇怪,隔三差五就会做情境相似的梦,梦里先是雾蒙蒙的,然后会听见哐嘁哐嘁的车轮撞击钢轨的声音从大雾里传出来,动静越来越大,最后大到震耳欲聋的时候,忽然有一列绿皮火车喷着蒸汽,呜呜呜地从大雾的深处开出来,火车头如同一座大山一样朝疯爷的头上倾倒过来,轰隆轰隆地从疯爷的心口上碾轧过去……
5
小石头要成亲了。
满囤把弟弟满升和妹妹满斗,还有妹夫王孝文全都找来了。几个人坐堂屋里烧得烙屁股的火炕上,围住一张方桌,一边抽着卷烟喝着茶水嗑着瓜子,一边商量怎么给小石头办酒席的事情。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正呛呛得热闹的时候,突然听见疯爷在下屋里歇斯底里大喊大叫起来。
满囤打发桂芝去下屋里瞅一眼。桂芝跑出去看了一趟,回来说,老爷子撒癔症呢,一阵儿哭一阵儿笑的,还满嘴说胡话。
桂芝说完,满囤、满升、满斗哥仨儿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全都沉默着不说话。王孝文拿眼睛扫了他们哥仨儿一眼,然后说,这马上就要办喜事儿了,不能让老爷子这么大喊大叫的,一定要看好他,尤其是正日子那天,千万不能让他跑出来,当着娘家客的面,还不够他丢人现眼的呢。
满囤叹了口气说,正事儿还忙活不过来呢,哪有闲人看着他。
桂芝突然来了主意,干脆把下屋的门和窗户堵死,一能隔音,二能防止老爷子跑出来作妖。满囤寻思了一下说,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哥几个当机立断,说干就干,连夜找了一些松木板子和一双旧棉被,叮叮当当一通敲打,就把下屋门给钉死了,前后的纵墙上有两扇大窗户,也找东西封严实了,最后只留下了外山墙上方方正正的那扇小窗户,小窗户是个活扇,伸手就能拉开,为的是方便给疯爷递饭。
正日子那天早上,满囤嘱咐妹妹满斗抓了几个新蒸出锅的白面馒头,顺小窗户扔进去。疯爷缩在铺盖卷里半梦半醒着,他伸手在枕头边上摸索到了一个又松又软的馒头,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撕咬着,吞咽着,吃一口噎一口,他不断地抻脖儿,尖瘦的喉结突动着。疯爷嘴里一边嚼着馒头,一边眯瞪着。他好久没吃过这么白这么松软的馒头了。
忽然间,外边响起了噼噼啪啪的炮仗声,接着还有喜洋洋的唢呐声,大人和小孩的一片喧闹声也一股脑儿地打小窗口钻进来,钻进了疯爷的耳朵里。疯爷的脑子里有些恍惚,他不知道今天是孙子小石头成亲的日子,他心里还在琢磨,今儿是怎么了,平白无故的,又有馒头吃,又有爆竹声和唢呐声,难道是过新年了么?
疯爷紧着抽搭两下鼻子,他闻到香味儿了。
疯爷再也躺不住了,他挣扎着爬了起来。
睡眼惺忪的疯爷感觉到屋子里的光线比往日暗淡了许多。他试着撞击了两下门,根本就撞不开,他哪里会知道,门已经被儿女们拿松木板子钉死了。他不得不爬回到炕上,把小窗的活扇使劲朝外推了推。窗口的大小,刚好容得下疯爷的脑袋瓜。离远了往这边看,小窗口就像是套在疯爷脖子上的木板枷锁。疯爷的一对黄眼珠滴溜溜地乱转,抻脖子朝外边张望着。他看到院门口并排站着两个人,是一男一女,男的打着呱嗒板儿,女的在咿咿呀呀唱小曲儿。
那些要饭的就跟掐算好了时辰似的,左一拨儿右一拨儿地赶过来,站在满囤家的院门口,打上一通板儿,念叨一套喜嗑儿,然后就等着东家过来打赏钱。为了打发这帮要饭的,满囤今天破费的已经不少了,他不想再招待这些白吃白喝又伸手要钱的穷叫花子了。
满囤刚刚做完了这个决定,眼前就来了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叫花子。老叫花子的手里拄着一根曲里拐弯的木头棍子,肩膀头上搭着个蓝布口袋,弓弓着腰,踮着脚进了院子,他也不打板儿,也不念叨喜嗑儿,老叫花子伸出手掌来,理直气壮讨吃喝,还要钱。满囤很生气,急赤白脸地往外撵他,老叫花子缩缩着脖子,踉跄了几步之后,一屁股跌坐在了下屋的外山墙根下,不想动弹了。
疯爷探出脑袋,冲着老叫花子就喊,老大哎,你是老大吧?
老叫花子仰起脸来瞅瞅疯爷,傻呵呵地乐。疯爷把他手里的几个白面馒头顺着小窗户丢出去,全给了那个老叫花子。这会儿,小石头跑出来了,照准老叫花子的屁股,狠狠地踢上两脚。老叫花子身子一哆嗦,捧着的几个白面馒头就脱手了,骨碌了一地。老叫花子扑在地去抓那些四散的馒头,他捡起来一个,小石头撵上去给他一脚,再捡起来一个,小石头就再撵上去给他一脚。疯爷趴在小窗口不停地叫唤着,老大哎,他是老大!
小石头梗着脖子骂,都他妈要饭吃了,还想当老大,滚出去!
疯爷眼睁睁地瞅着小石头把老叫花子赶跑了。小石头回头伸手用力一推,就把下屋外山墙上的那扇小窗户关死了,同时也把疯爷的脑袋瓜子碰得缩了回去。
一拨儿客人吃完了,下桌抹嘴走人,换另外一拨儿坐上去再吃。满囤家的流水席一直放到夜幕降下来时候,屋里外头才渐渐地冷清下来。
家家户户到了熄灯的时辰了,只有满囤家的窗口还亮着灯。桂芝躺被窝里,哗啦哗啦地数着今天收的礼金,点了一遍,再点一遍,点到手抽筋了,还是没有点出一个准数来。满囤从桂芝手里把黏糊糊的票子一把夺过去,呸呸呸地往手指头上啐着唾沫,厚厚的一沓票子在他手里捻得像旋转起来的风车,点到和礼账上写的数目没有出入了,就搂着桂芝呼呼地昏睡过去了。
6
疯爷躺在下屋里又开始做梦了。
这个梦,疯爷做得格外地漫长。他又梦到自己带着女人,挑着筐背着篓,里边装着孩子,流落到关外找活路的场景。在逃荒的半路上,疯爷的女人连饿带病,就倒毙了。女人临终前嘱托了疯爷两件事:一是把四个孩子全都照顾好,二是不要给孩子们找后妈。疯爷含泪答应了女人,女人才闭上眼。
当时,疯爷身边带着四个孩子。老大满仓、老二满囤、老三满升、老四满斗。四个孩子里,老大有些特别,老大先天脑瘫,是个傻子。老大的饭量大,总喊肚子饿,疯爷的女人活着的时候,自己的那份干粮总舍不得吃,每次都偷着塞给了老大。老大的肚子好像没有底,吃多少也填不满。老大虽然傻,但是力气大,总是抢夺弟弟妹妹手里的干粮。有时候气得疯爷指着老大满仓的鼻子骂,你个吃货,你个傻子,早晚我得把你给扔了!
下着大雾的一天早上,疯爷带着四个孩子,混在逃荒的人流里挤绿皮火车。疯爷怀里抱着最小的老四满斗,身后跟着老三满升、老二满囤,老大满仓在最后头。挤车的人互不相让,现场混乱嘈杂,火车喷着蒸汽,呜呜呜地拉响汽笛了。
疯爷挤上火车之后,身子堵在门口,回身拉了一下满升的手,老三上来,又拉了一下满囤的手,老二也上来了,等准备拉老大的时候,疯爷脑子里一时间犯了糊涂,不知怎的,他就犹豫了一下,伸向老大的那只手下意识地缩了回去。老大满仓跷着脚,仰着脸,伸着胳膊,张着大嘴,带着哭腔喊,爹,拉我呀,你快拉我呀?疯爷闭了一下眼睛,等把眼睛睁开,再想伸手拉老大的时候,老大不见了。
老大在他眼前消失了,人流已经把车门口堵得水泄不通了……
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沉重的粗气,穿破晨曦里的雾霭,碾着没有尽头的钢轨,轰隆轰隆着驶向苍茫的远方。
疯爷在火车上再也坐不住了,拼命地拿手拍打着车窗,疯了一样叫唤着,停车,停车,快停车……老大哎……我的老大……
疯爷答应过女人,要把身边的四个孩子照顾好,一个一个都带大了。疯爷食言了,第一点,他没能做到。抛弃了老大之后,疯爷就中了心魔,愧疚了一辈子。第二点,疯爷努力做到了,就是永远不给这三个孩子找后妈。
疯爷上了岁数以后,夜晚老是做情境相似的梦,梦里先是雾蒙蒙的,然后会听见哐嘁哐嘁的车轮撞击钢轨的声音从大雾里传出来,动静越来越大,最后大到震耳欲聋的时候,忽然有一列绿皮火车喷着蒸汽,呜呜呜地从大雾的深处开出来,火车头如同一座大山一样朝疯爷的头上倾倒过来,轰隆轰隆地从疯爷的心口上碾轧过去……
奇怪的是,这次梦到火车轰隆轰隆地从心口上碾轧过去之后,疯爷没有醒过来,他连着发出几声短吟,虚衰地呓语了两声之后,又续了一个梦,这次梦到的情境和以往不太一样。疯爷梦到他的大儿子满仓,顺着一条钢轨在铁路线上爬呀爬,身后拖出一溜长长的血印子。老大就这样坚持着爬,终于爬到了满囤家的当院里。疯爷趴在下屋外山墙头的小窗户上瞄见老大回来了,就忙不迭地跑出去,下意識地伸双手想去搀扶老大,可怎么扶都扶不起来。疯爷拿手一摸索,老大只剩下了半截身子,下面的两条大腿早就磨没了。疯爷扬起两只手一瞅,手掌上沾满了老大身上的鲜血,嗷的一声就给吓醒了。
7
疯爷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五更天了。
乡村的冬夜,万籁俱寂。高远的天空只有几颗寒星眨着眼睛。
下屋里冷得跟冰窖一样,疯爷的身子在铺盖卷里哆嗦成一团。疯爷想自己下地烧一烧炕,他在枕头底下一摸,就摸到了便利店女人送给他的那个打火机。可是,他已经忘记了怎么使用。他打火机拿到手里,掰掰这儿,抠抠那儿,猝不及防地就捅咕着了,火苗子咝咝响着,打一个小孔里喷射出来,如蛇嘴里吐出来的信子,蹿出去老远。疯爷慌神儿了,手里紧紧地握着打火机,不知道如何把火苗子给熄灭了。疯爷整个人抖得跟筛子似的,火光照亮了他那张惊恐万状的脸。
铺盖卷烧着了,炕上铺的席子烧着了。墙壁上糊的那层旧报纸很快也燎着了。疯爷雪亮的瞳仁里映着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球。火势愈演愈烈。突然,一条火龙蹿上了下屋棚顶。棚顶覆盖的松木板和油毡纸遇火后呼啦一下就烧着了,松木板子燃烧的声音,空空空地响,像极了跑火车的动静。
疯爷在火海里翻滚着。他感觉下屋房子在他眼前哐嘁哐嘁有节奏地摇晃起来了,就像坐在当年的那趟绿皮火车上。疯爷的两只手用力地拍打着炕面子,嘴里不停地叫喊着,停车,停车,快停车……老大哎……我的老大……
第二天早上,人们起来的时候,发现疯爷住的那间下屋已经烧落架了。疯爷的尸首从火后的废墟里挖了出来,晾在满囤家当院里一块白不刺啦的旧被单上。疯爷的四肢佝偻着,筋骨全聚在一起,看着就像一只烤糊了的老家雀。
满囤喊来了村里的小木匠,随便找了几块杨木板子,对付着拼凑成一副小棺材,把疯爷烧焦的尸首殓了,当天就拉出去,草草地埋在了村西头的那片乱死岗子。
疯爷发送出去的第二天,村里的瘸羊倌儿慌里慌张着拐了回来,一脸惊悚地跟满囤说,快去看看吧,你爹从棺材里头爬出来啦!满囤骂了那个瘸羊倌儿,净扯犊子,人都烧成那样了,咋还能活过来?瘸羊倌儿信誓旦旦地说,你爹就在坟头上趴着呢,你不去把他弄回来,过会儿冻死了可别说我没告诉你啊!瘸羊倌儿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满囤跑去乱死岗子一瞅,疯爷的坟头上还真有一人,那人的脸被散落下来的苍苍的白发遮盖住了,有点瞅不清。那人的身形跟轮廓,一打眼儿还真有几分和疯爷相似。满囤感觉头皮麻酥酥的,他咽下一口唾沫,仗着胆子走近了,抽冷子薅起那人的头发一瞅脸,原来竟是讨饭的那个老叫花子。
老叫花子的手里还掐着小石头成亲当天,疯爷送给他的白面馒头。馒头冻得梆梆硬了,老叫花子还在捧着啃呢,啃得牙花子上面都是血,就像吞吃了死孩子。
满囤上去扇了老叫花子一个嘴巴,问他,你他妈谁呀你?
老叫花子咧开嘴,笑着说,呵呵……我……我是老大……
作者简介:张伟东,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绥芬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远东文学》编辑,《独立作家》专栏作家。作品散见《北方文学》《红豆》《在场》《佛山文艺》《满族文学》《太湖》《杂文选刊》《电影画刊》等。小说《毒日头》获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和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全省征文(小说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