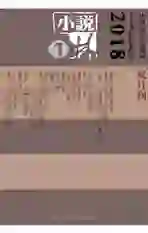环形路
2018-01-09柏川
柏川
一
我从餐厅出来时,他正从另一条长满娃娃萱草的小路上走过来。他扭头朝我这边看。确切地说,是在扭头看我。大概是餐厅外那片空地太过阔大,连一棵树都没有,一个人走出来,会格外显眼。另一个可能是我今天的穿戴有些招眼。一条民族风的层花大摆长裙,上配一件酱红色的中袖短褂,看起来,颇有几分哈尼族女子的风情。我这样穿,并非今天我特意在服饰上下了功夫。事实上,我是个在穿衣上不大讲究的人。这身装束,源自与我同住一屋的晋南女子梅书之手。她说我穿得土气,一大早就把自己的衣服抖搂出来,一件一件让我试穿。当我穿上这身长裙短褂时,她原本就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你看看,她一边为我平整衣服上的褶子,一边说,你自己照照镜子。她一把拉我到镜子跟前。长方形的镜面上立刻映出一个妖艳的女子。我一下愣住了。镜里的人是我吗?我居然可以这么妖艳?多少年来,我的衣服都是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生活也如此。鲜艳的色彩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慌乱。比如我喜欢在夜晚的黑色里,一个人到处走走。而现在,我已经被这个晋南女子的热情烤得出了汗,目光也散乱起来。我甚至懷疑对面这面长方形的镜子是不是一面魔镜。我傻傻地站在镜外,与镜子里的自己面面相觑,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镜外的我还在习惯里寻找那个黑白灰色的自己。而镜面却魔法般造出另一自己,一个陌生得似乎准备重新开始的自己。一种异样的想要挣脱旧我的新鲜感在我的心里盘旋起来。这种新鲜感带着我离开了镜面。我确信自己正在尝试接受梅书的热情以及她为我打造出的新形象。我确信自己在这个异乡的早晨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启开了心窍。是梅书的启发,还是生命自然的演变,我不明白。我尝试着,带着镜中这个妖艳的自己和梅书的混搭艺术走进早晨空气清新的园子里。
此刻,清亮的阳光正漫过台阶和台阶背后的高楼。高楼在我背后成为背景。这个高大的背景让我显得格外的小。即使这样,他还是准确无误地看到了我,并放慢了脚步,像要等我过去。
这是在小镇学习的最后一天。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天虽不能说多么美好但一定是十分宁静的时光。和我一起来的人有几十个。他们是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作家,临时组成了一个作家研修班。这个临时的长度,只有二十天时间。二十天和二十年,只是一个量的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回头一望,二十天和二十年都无非是眨眼之间。吃早饭时,人们用不同的方言道别,有人还流了眼泪。我波澜不惊地看着眼前一张张表情丰富的脸。我想,要不了多久,这些脸就会从我的脑子里一一消失。这一路见过多少张脸,各色各样的五官,表情,好看的,不好看的,欢喜的或悲伤的。有时一个眼神,会荡起一缕微波,一抹微笑或一句暗语,会让人产生某种错觉。但故事往往尚未开始,就结束了。一些细枝末节还不足以激起心底的波涛。可要说一点留恋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我这样胡乱想着,步履散淡地走下台阶,脖子上挂着鲜红的学员证牌子,红丝带缠绕着我家祖传的那块和田青玉。学习期间,不断有人盯着我看,确切地说,是盯着我的胸口看。盯得我准备躲闪的时候,他们突然发出一声令我起鸡皮疙瘩的惊叹,呀,一块好玉。我就下意识地抬起手,护住我的胸口。
此时,那个人离我还有一段距离。他扭头看我,不可能是因了我胸口的这块玉。等我离他很近的时候,我看见他脸上的笑容是为我准备的。他戴一副眼镜。那眼镜不是那种透明的不挡眼睛的近视镜,也不是闪光镜或老花镜(当然他不能算老,可以说还很年轻),自然也不是那种看不见眼睛的颜色很重的太阳镜。他戴的是一副浅蓝色的更像是一种装饰的眼镜。我透过蓝色的镜片很清晰地就看见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荡漾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深情。我相信,他看谁,一定都带着深情,甚至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或幻想。
我们用眼神互相打了个招呼。谁也没动嘴,好像说话是一件多余的事情。顺着培训基地的环形路,我们并肩而行,像一对认识多年的老朋友那样,而在心里,我们大概都在揣测对方的身份。环形路边的娃娃萱草开出金黄的花。环形路的路面涂成了蛋黄色,路两侧长着很多茂密的果树,绿色的草地还有很多开得很盛的花。吃完早饭,离上课还有一小截时间,我们就顺着环形路随意地走着。走到环形路的一个岔口处,我们同时停下来。我先动了一下嘴,问,你是本地人?这样问,是因为我确信,他不是我们这个临时班的学员。在这儿二十天了,几十个人也都陆陆续续认全了。这个人,这张脸,我之前从没有见过。他或是这小镇的人,或是为我们提供赞助的这家公司的人。当我把这一判断换成问句向他提出来时,他在蓝色的镜片后面笑了笑,说,不是。我是特意从另一座城市赶过来听课的。哦,这么说,你也是我们这个圈里面的人。说出这句话,我在心里尴尬了一下。什么是我们圈里面的人,我们圈里面的人是什么人?我们这个圈是什么?它存在吗?想到这里,我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他也笑了。他大概发现了我话中的破绽,风趣地说,自然,我们是一伙的。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可是,这些天,我没看见过你。我扭头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他说,我刚才说了,我今天是特意赶过来听课的。之前,我没来过。你已经不需要学习了吧!我嘲讽地说。他说,不是,我欠缺的很多。接着他又补充道,我是开车过来的,我所在的城市离这里有三百多公里。噢,我吃了一惊,跑这么远,只为听一节的课。如今还有这样为文学不顾一切的人?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看见名片上写着一个名字:诗人轮子。我笑了。他的名字首先让我想到头顶的太阳,之后是脚下这条我们日日散步的环形路,还有我手里拿着的这只水杯。凡是圆的,不,凡是空心圆的,都可称作轮子。这样一琢磨,我立刻觉得眼前的这家伙是个哲学家。我笑了一下,轮子?这名字有意思。他用似笑非笑的表情回应了我,没啥意思,就是一个空心圆。
上课的铃声响了。他看着我,在清脆的铃声里会心地笑着说,铃响了,该上课了。当学生真好!我说。我们说着话,快步走向教室。快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他问我,你的宿舍在几楼?我说三楼,你呢?他说,四楼。有空可以串门。毕竟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我说,只有这最后一天了。他把蓝色的眼镜往上扶了扶,两个黑眼圈从镜片下掉出来,显得略微有些疲惫。他说,一天有很多分钟,很多秒,也可以发生很多事的。一天其实很长。当我们都在为生命短暂焦虑不停时,这个戴蓝色眼镜的家伙却说一天很长。这句话让我准备跨进教室的脚停住了。我扭头望着他的侧面,高高隆起的鼻梁像一座绵延的山峦,让他的脸部显得不同凡响。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突然对他生出兴趣。是的,我应和他说,一天其实很长。他那高耸的鼻梁就转过来正对着我。他说,所以,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还有时间,这句话让我掉进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我说不出这句话包含着什么样的一种意思。但确实,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用如此温柔的口气说出这句话时,它让我平静的心脏突然欢跳了一下。我想,至少他对我的印象不是视而不见的那种。可是,我为什么要给一个陌生男子留下印记,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事实上,我并未觉得有再见他的可能。一天的时间,盛满了很多紧密的安排。分组讨论,交学习心得,还有一些表格要填写。毕业典礼是最后一场表演。没错,生命的每一天都是一场表演。不过是表演的舞台和道具日有所异罢了。比如在这个叫巴普的小镇上,我们的舞台背景,就是这个封闭式培训基地,环形路,天然池塘,池塘旁边的一座土山,土山上的树,还有这几座由教室、餐厅和宿舍共同构成的一个舞台。表演者是组织者和我们这些被组织者,管理者和我们这些被管理者,还有被邀请来的那些名角。主角和配角,每日台上台下,共同合演了二十天的戏,就要接近尾声了,明天就要散场,大家将带着不同的心情离开。路程远的,像我,最迟到明天午饭后也不得不同这里的一切告别,回到我生活了很多年的那个小城去,重新把自己还原成属于另一个舞台上的角色。另一个舞台就是我长久生活其中的一个小城。那座古老的四四方方的小城,居住越久,嵌入越深,它的面貌于我就越模糊,越无法轻易作出某种表达。我所能清晰说出并永远无法摆脱的是我作为一家小报记者的真实身份。这个身份让我无法对生活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我在这家小报社已经工作了十三年。离开它,再从某一处重新开始,对于像我这种视安分守己为天职的人,是不太可能的。我也日渐习惯了这种背着照相机,带着笔记本和录音笔四处奔走的生活。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只长着触须的老鼠,用触须的长毛捕捉那些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被叫作新闻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手艺不怎么精到的裁缝。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把那些政策、文件、领导讲话剪下来,贴到该贴的地方,加上时间地点,拼成一则完整的新闻报道。看起来忙不拾闲,其实并没多少实际内容。这个角色让我既讨厌又留恋。像一只海葵寄生在一块海底砂岩上,我就是那只海葵,我的身份就是那块冒着水泡的海底砂岩。
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与这块代表我身份的岩石暂时分离了。我来到晋中这个叫巴普的小镇上。我以一个没有出处的自然人的样子加入到这个作家群里。我的黑白灰色的生活色彩,在这里被改变。他们说,作家是这世界上没有边界的人群。而此时,我正在这群人中间,每天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散步。特别是同散步,三三两两,我们绕着那条环形路,走了一圈又一圈,好像要一直这样回环下去。虽然不断有人中途脱逃,但这样的散步伴随着每天一句地一句的漫聊,不知不觉中,我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人了。在一个没有藩篱的陌生环境里,一群半生不熟的人群中,我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感。包括这身长裙短褂,这妖艳的色彩,便是这种自由感在服饰上的体现。这种像水一样的流动的自由感,明天就要结束了。
想到这里,我脑子里的晴天一下就暗下来,像一片清亮的树叶突然落上了一层灰尘。我看见自己像一尾黑色的蝌蚪,在酒精一样透明的空气里无力地游动。
二
教室,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报告厅。因了我们的临时入侵,它暫时改作上课的教室。讲台上没有黑板,只有一张白色的投影布。布上头挂着这个班的名字,某某某高级作家研修班。这种摆设,让我感觉像置身于一个大会场里,看到主席台上写着标语或会议名称的大红条幅或电子屏。会场总是让人感到压抑。会场与教室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我认为,教室这个舞台相对于会场,它更逼真更单纯一些,比如可以不挂条幅,可以互相对话。大抵是我在会场上浸泡的时间太久的缘故,看见类似会场的地方,就本能地发酵,眼睛发酸发涩,甚至想打瞌睡。这次来参加这个研修班,原本就是想换个戏台子,换套不同的道具,能有一段时日,重新回到象牙塔,当一回学生,感受一下那种久违的单纯与无邪。可是,最后发现,我还在会场里。一切似乎并未改变。
台上的老师是个长着大胡子的诗人。他声如洪钟,肺活量惊人,不时爆发出笑声,让人立刻从昏睡中惊觉。我坐在靠窗户的地方,窗外是那片椭圆形的池塘。池塘西边的土山和土山上的树映在塘面上,那倒影让人产生幻觉,就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的世界颠倒了一样。
看见池塘,我就莫名其妙想起了轮子。一个女人在某一瞬间想起一个男人,原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即使这个男人只与她有过一面之缘,他也或许会在某刻划过她的脑墙或梦境。那个带着蓝色眼镜的人此时就是这样,在我的脑墙上划过的同时,也出现在我眼睛里。他正坐在我的前两排,讲台下的第一排。他坐得端正,后背挺直,像池塘边那座土山上的一棵树,挡住了我视线。我想,他个子那么高,应该选择坐在后排。而他却偏偏选择坐在第一排。他突兀地坐在那里,就像一棵高出草坪的大树,让我看不到大胡子诗人的表情,只能听到他中气十足的男高音。可我并没有恼恨他。挡在我眼前这只头发乌黑发亮的大脑袋,不时地晃动一下,或静止在空中,都很美,像是映在安静空气里的一抹黑色的刺猬花。大胡子诗人那极具诱惑力的声音,绕过这朵刺猬花,不断撞击我的耳膜。
下课后,刺猬花站起来,去和大胡子诗人握手亲热。看起来他们很熟。我跟在他们后面走进电梯。电梯里挤满了男作家和女作家。大家的表情像从教堂里走出来一般,满脸的祥和和圣洁。我顿时想起林语堂说过的一句话,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吃午饭时,我与刺猬花隔着一张圆形的餐桌对坐而食。我把这句话说给他听。他一边用力地啃着一只发黄的鸡腿,一边认真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吃完鸡腿,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写那些有罪的诗。我笑了一下,说,写诗也是一种救赎。他抬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那眼神空荡荡的,像是看我,又像是在看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对他笑了笑,他似乎毫无察觉,面无反应。眼睛忽而暗淡了下去,眼睑低垂,在蓝色的镜片后,像有一种绝望隐进两片深蓝的湖水里。他不再说话,专注地吃饭。我再次注意到他的头发,那一头浓密的头发,齐整黑亮,黑得让人产生幻觉,像被岸上的树木映黑的池塘,让人对湖面产生怀疑。树和树影对立而存,临了,池塘或许会变成了一个长满刺猬花的黑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