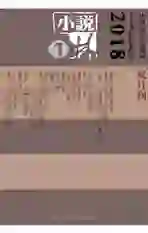为衰老疲惫的乡村中国立此存照
2018-01-09汪树东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篇就曾声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确,离开乡村、农村,就无法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人。但是当华夏大地近百年来不由自已地被卷入现代化大潮中,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迅猛的市场化、城镇化浪潮冲击着华夏大地的每个角落时,乡村的沦陷不可避免,因之酝酿而成的文化悲剧、人生悲剧俯拾皆是。曹多勇的中篇小说《白露降》就聚焦于当前乡村的现实图景,无论是留守乡村的孤独老人,还是远离乡村无法返乡的打工者,抑或是已经定居城市但始终艰难生活的乡村后人,都折射出当前乡村中国衰老疲惫的灰色本相,令人不由得唏嘘感慨。
该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我”父母是农民,生活在淮河边名叫大河湾的安徽农村里,育有一女两子。“我”大姐嫁给农民为妻,患了糖尿病,生活艰难。大儿子“我”考上大学后,留在城市里工作,曾经当过工人,如今是作家,人到中年,女儿也已长大成人,但无权无势,没有大富大贵,只过着磕磕碰碰的日常生活。更为可悲的是“我”二弟,不得不远离家乡,带着妻子到浙江金华去打工。“我”母亲去世得早,父亲独自在家照顾着二弟的一儿一女,侄子初中毕业后也跟着父母去了金华,读了技校,毕业后在金华工作,侄女在老家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侄女高考前,“我”父亲患了白内障,为了不耽误她的高考,“我”父亲不愿意告诉侄女自己的病情,希望在她高考后去做手术。后来,侄女好不容易考上广东的一个二本大学,“我”父亲大喜过望。“我”父亲为了节省钱,做完白内障手术后没有住院,而是直接回家,还要割草喂牛。令人心寒的是,“我”二弟连续几年过年都不回家,即使“我”父亲做手术,他也没有回家,毫无孝心。这引起了“我”妻子和“我”的争吵,“我”也是左右为难。最后,“我”回家帮父亲收割黄豆,感慨世易时移,乡村沦陷。
该小说题为“白露降”,篇首还引用《礼记》上的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为注。这当然是颇有意味的。涼风至、白露降、寒蝉鸣不单单意味着天气渐凉、季节轮替,更意味着时代的更迭、文化的嬗递,传统的乡土世界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因此,在该小说中,只有像“我”父亲、侄子、侄女这样的老弱者留守乡村,至于年轻力壮者、智力突出者都早已经被城市收割,而且他们不敢返乡,不愿返乡,也不想返乡了。至于传统乡土世界最为看重的孝道,在二弟身上早已被日益严峻的生存重担撕碎,丝丝缕缕地飘荡在城乡之间的阔大鸿沟上。作者对乡村的衰败是极为哀伤的,“大河湾土地被煤矿扒塌陷,土地原本就不成样子,遇见大雨天,黄豆成水稻,下半截站水里。”“看来大河湾土地真的像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妇人,衰老得没有一点生殖能力了。”大河湾土地被煤矿扒塌陷,就是一个严峻的象征,即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摧毁了乡土世界的立身之基。大河湾的土地衰老了,乡土中国衰老了,这就是流荡在整部小说中的低沉调子。
当乡土世界无法抑制地沦陷时,乡土世界中的农民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该小说中的“我”父亲差不多是最后一代坚守着土地的、带有悲剧意味的农民形象。“我”父亲面对日益溃败的土地,还是坚持着种地,“我父亲说种庄稼越来越寒心,下一季麦子都不想再种了。犁地、播种、收割,种子、化肥、农药,样样花钱,种地早已是一件亏本的事。我父亲年年说扔下土地,年年还是坚持种上。我父亲对土地的一份复杂情感,我能体会到,却不能明晰地说出来。”像“我”父亲这样的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就是几千年来乡土中国顽强延续的秘密所在。明知道种地亏本,“我”父亲还要种地,这就接近于一种纯粹的信仰了。即使年近八旬,“我”父亲还继续种地养牛,并不存在城市人所谓的退休,或者依靠子女养老。该小说对“我”父亲的这种生活方式曾写道:“我父亲年近八十,喂牛种地,大姐说起来心疼,哭起来鼻涕眼泪一起流。我父亲说,我不喂牛,我不种地,就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吗?自从二弟家的闺女考上大学,我父亲身上的担子轻松下来,我也主张我父亲坐在家里吃、坐在家里喝,全身心地照顾自己。我父亲不愿过这种日子,也不能过这种日子。一个人不管年岁有多大,只要一张嘴能喘气,只要两条腿能走路,只要两只胳臂能活动,每天任啥事不做,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我父亲喂牛,能跟牛说一说话,缓解个人的孤寂与空落。我父亲种地,能下地干一干活,延续一辈子的生活习惯。我父亲过得忙碌,活得充实,不说高血压、高脂肪、高血糖这样的大毛病找不到他头上,就是腰酸背疼这样的小毛病也远远地避开他。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这病那病没有,能吃能喝能睡,我跟我妻子过去不理解我父亲选择的这种劳作生活方式,现在逐渐地理解了。大姐怎么就不能理解呢?”其实,“我”父亲这种劳作生活方式,不就是传统中国农民最基本的劳作生活方式吗?也许从现代城市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劳作终生的生活简直是苦役,可是若从生命的内在意义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为美好合理的生活方式呢?
在作者笔下,“我”父亲具有传统中国农民的种种优异品格。例如他身上的那种传统中国农民式的坚韧品格就颇为鲜明。他能够在乡村独自抚养孙子、孙女,为子女解除后顾之忧,并把照顾孙子、孙女看作一种理所当然的责任、承担;他在刚做过白内障手术后,不住院,直接回家去割草喂牛。他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克己,但是对待子女却极尽呵护之能事。即使“我”二弟连续几年过年都不回家,他也没有多少怨言,只是尽可能地设身处地为他考虑,想着他在外打工生活不易。而且“我”父亲还具有传统中国农民在苦难中保持乐观的坚毅品格,例如他含辛茹苦地抚养、照顾着孙子、孙女时,他就总想着等“我”二弟夫妻挣到更多钱就好了,等孙子、孙女长大就好了。更令人称道的是,“我”父亲即使到老也依然具有梦想,“我父亲是一个不断有梦想的人,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有梦想的人。时下他老人家的梦想,就是在他有生之年,亲手扒倒自家的四间瓦房,亲眼看到自家的楼房一寸一寸地一尺一尺地长起来,长成一座高大挺拔的楼房,跟他梦想的一模一样的楼房。”也许在城市人来,这样的梦想有点渺小可笑,但是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农民而言,这样的梦想实在是生命的庄严承诺,意义非同一般。当然,“我”父亲毕竟是一个年迈力衰的农民,面对的又是一个乡村沦陷的城市化时代,他已经丧失了悠然自得的生活背景,他的所作所为都带有一种壮烈的悲剧意味,就像乡土社会的最后一抹晚霞,虽然明亮灿烂,但终究很快会被黑夜遮掩。
应该说,在《白露降》这部中篇小说中,父亲形象是最生动的,最有富有生活内涵、文化内涵的。除了父亲形象,“我”二弟本来有可能会成为最富有生活内涵、文化内涵的另一个人物形象。但非常可惜的是,该小说把叙述者设定为“我”,几乎有意地遮蔽了“我”二弟更为丰富多彩的出场。但该小说对“我”二弟的几段连续几年都回家过年的内在心理的介绍非常具有深度,值得关注。“究其原因,是二弟离家时间长,这个家他愈来愈陌生,陌生的一个家他待着感到不舒适。村里有许多二弟这样的人,他们漂泊在哪里打工,哪里就是他们的家,真正的家反倒不是家,陌生了,疏远了。”其实,若能设身处地想想,像二弟这样的打工农民远离家乡,漂泊在外,背负着乡土世界的伦理印痕,进入陌生人的都市漩涡,会遭遇多么严肃的生活挑战啊,这里又有多少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啊!“二弟带老婆儿子去浙江金华,一去五年没回家过年。从表面上看,说是手头上紧巴,想省几个路费钱,想省几个过年钱,其实二弟的心理很复杂,想与土地一刀两断,想与老家一刀两断,想与自个的过去历史一刀两断。二弟错了,一个人恰恰与这些东西难以割舍,或割舍不断。这些东西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真的难以割舍清楚,什么都舍弃,没有父母,没有家乡,没有亲情,没有过去的情感与记忆,这样的人跟一具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呢?”打工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一言难尽,盲目地想着和土地一刀两断自然是一厢情愿甚至可能是误入歧途,可是他们渴望成为一个正当的城市人在城市里过上一份安稳自在的城市生活难道不也是合情合理的吗?
与二弟形象相比,小说中的“我”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颇有生活内涵的人物形象。“我”出生于农村,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工作,可是在社会上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既不可能改善家人的实际生活,也无法从容不迫地应付自己的生活。不过,“我”是个作家,是个敏感的人,是个能够充分理解“我”父亲的劳作生活方式的人,是个理解乡土世界沦陷的悲剧意义的人。“我焦虑老家的目前现状。我更焦虑老家的将来看不见出处。那段时间,我差不多隔上一个星期就要回去看一看。看一看日渐破旧的四间瓦房。看一看日渐衰老的我父亲。看一看二弟和二弟媳妇丢下来的两个孩子。看一看,只能是看一看。我帮不上忙,更改不了现状。我一心沉重地去,一心沉重地归。”焦虑和沉重,是“我”根本的生活感受,也是无数像“我”一样来自乡村、定居城市又牵挂着乡村的人的生活感受,“我们”以“我们”的焦虑和沉重铭记着沦陷的乡村世界,表达着深广的文化忧思。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该小说富有艺术韵味的结尾:“我给二弟打电话。几年没见二弟,我与他电话通得稀少。我跟二弟说,我现在在家里割黄豆。二弟在那边回答一声,噢。我说,我在黃豆地里找到了天宝和马泡。二弟依旧回答一声,噢。我问二弟,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俩有一回在生产队地里拾黄豆,黄豆茬戳破你的手,你吃天宝和马泡酸倒牙这么一件事。二弟迟疑一下问,大哥你打电话不会只想问这件事吧?我想说,二弟你今年过年回家吧。话到嘴边,我使劲地咽回肚子里。”“我”回家帮“我”父亲割黄豆,在黄豆地里找到童年时爱吃的野物天宝和马泡,似乎通过不变的野物味道再次体验到了生命和土地之间的永恒联系;但是对于想着割断和土地联系的“我”二弟而言,“我”所体验到的东西实在太过遥远而不切实际了。曾经被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兄弟就这样被时代大潮冲击得天各一方,彼此再也难以沟通理解了,勉强说来也是鸡同鸭讲,这是悲剧,这也是荒诞剧,令人莫衷一是,五味杂陈。
整体看来,该小说关注了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乡村中国的灰色本相,塑造了鲜活而富有文化内涵的留守老农民形象,展示了当前生活中相对严肃的一面,叙事绵密,细节生动,是一部旨趣严正、富有现实警示意义的中篇小说。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