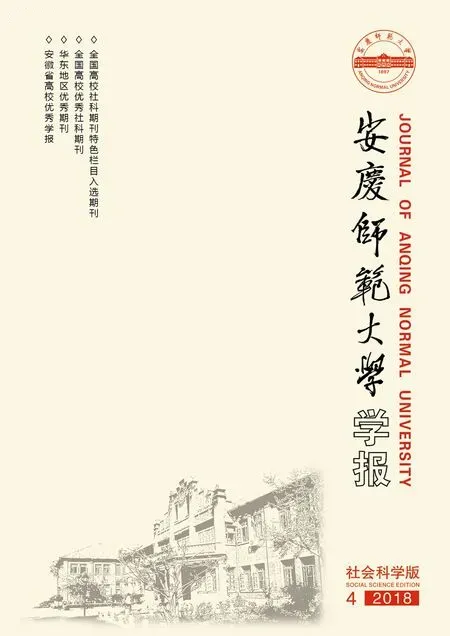汉语成语认知研究述评
2018-01-01刘洋洋
刘洋洋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汉语成语研究历史久远,从本体到文化再到认知,研究在一步步深化。而这一深化,得益于认知的方法和视角。束定芳认为:“认知语言学的魅力在于对语言事实及规律较强的解释力和一定的预测性,以及它对语言使用者心理现实性和相关文化、语言特性的充分考虑。”[1]很明显,成语研究若要有所突破,若要对成语结构的生成、理解模式机制做出深层次的解释,非认知方法莫属。但同时,使用认知的框架合理有效地研究本土语言现象是一条长期的道路。本文概述了汉语成语认知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其特点和成绩,指出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并探讨其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
一、汉语成语生成机理的认知研究
汉语成语言简意赅,其构成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课题之一。对于汉语成语生成机理的认知研究,贡献巨大的首先是徐盛桓先生。徐盛桓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使用“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规推理”为理论框架,以相邻和相似两种关系为中介,成功建构了一个“自主—依存分析框架”[2]。这一框架的建构、推理过程中,所用到的举例多是汉语成语。
2004年,徐先生发表文章《成语的生成》,文中指出成语所具有的四点特性和三种品格,而这些特性和品格并不是成语所独有的,不透明性、不完备性和蕴含力在日常话语中也有体现,只不过这种不透明和不完备在成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集中[3]。所以,徐认为成语这种“表里不一”本质上也是含意现象,可以用含意本体论的“语句解读常规关系理论模型”来做出解释。
之后,为了进一步说明成语形成的机理,徐又发表《相邻与补足》[4]《相邻和相似》[5]两篇文章,把常规关系抽象为[相邻+-]和[相似+-]两个维度,并用以此为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来研究成语的生成。《相邻与补足》指出成语牺牲了语法-语义的完备性来成全其经济性,这同日常话语语句的显性表述通常都是不完备的是相类似的。而且,徐引入“构块”(现多称为“构式”)的概念将汉语成语各种不同的显性表述从不完备表达到相对较完备表达分类为语法外构块、假语法构块、超语法构块、准语法构块、语法构块。这种对成语的再分类,引出了成语形成的推理规则[4]。
《相邻和相似》一文中,徐先生建设性地论证了用构式语法(原文称之为“构块语法”)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汉语成语并不是最理想的。Fillmore等人对英语成语的研究开启了构式语法研究的序幕,对汉语成语的研究有很多的启发,但是徐认为这一事实仅说明成语跟一般句法构型一样,都可以用构式的形式来表征,并不能说明成语形成的机理,而且汉语成语的特点使成语的构式分析产生了一定的困难,成语的生成机理最理想的解释还是以“相邻/相似”为核心概念建构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
徐又将研究推进一步,用“象征性”解释成语结构的“不讲语法”为什么可能。徐先生总结了汉语成语认知研究的主要问题,即成语的语义加工和语言结构的问题,然后从“相似性”、“格式塔转换”角度分析得出成语的结构生成是符合认知特点和认知过程的,最后,结合他前期的“相邻/相似”关系解释,加之于“蕴涵”关系,将成语的语义加工情况分析为两大类七小类,回答了成语生成和理解的语义加工过程为什么可能的问题[6]。
徐先生的跨领域研究可谓汉语成语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首先,徐先生尝试用认知、心智理论来解释汉语成语的生成,打破了以往成语本体研究的套路,他的研究引入了“含意本体论”、“构式语法”、“常规关系”等一系列崭新的解释方法,开创了成语研究的新篇章。而且,徐文在语言共性研究的大环境下研究汉语成语,推导出成语形成和解读的常规关系推理原则和相关推论,跳出了成语研究的窠臼。沈家煊提出,语法研究要以预测和解释合乎和不合乎语法的现象为目标[7],徐先生的研究将汉语成语的研究朝着这个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成语的生成,本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单一的模式所能全面解释的,必然涉及经验基础、知识结构和文化模式等多领域,在认知科学的框架下研究成语的生成必然是有效途径。而且,概念隐喻理论也适用于成语生成机制的研究,值得借鉴。
二、汉语成语语义构成及理解的认知研究
言简意赅的成语能够表达丰富的内涵,并且能够为人们理解使用,所以成语的语义构成和理解也是值得研究的。在这一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位学者是张辉。早在2003年,张先生出版了专著《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以具有双层意义的汉语四字成语为对象,以认知语义学理论为框架,探讨了汉语成语的语义构成[8]。张辉证明了熟语是一种凝固化的常规映现模式(mapping patterns),熟语在产生、使用和理解的过程中,人们无意识地运用了隐喻和转喻的机制,他将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综合为统一的框架,形成了熟语心理空间的概念。张先生还指出,熟语的常规化导致了转喻超转喻化和隐喻的超隐喻化,一个熟语可以同时分析为隐喻和转喻。张先生在研究汉语成语时,主要研究对象是典故成语。汉语中存在许多这样的转喻或隐喻性成语,由于其使用的频繁和常规化的发生,进而演变成超转喻或超隐喻性成语。虽然成语本身的转喻或隐喻性仍旧存在,但是其映射关系几乎已经消失,这种消失并不是真正的消失,一旦有外界因素的刺激,还是会重现的[8][9]。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样的成语已经有了一定的熟悉度,在使用和理解时,会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没有完全消失的映射关系的影响,不去考虑其字面义,而直接采用其喻义。
朱风云、张辉对国外学者的各种熟语语义加工模式进行了思考与述评,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虽然是英语熟语,但对汉语的成语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10]。张辉、季锋考察对象是动宾结构的英语熟语和双动宾结构的汉语成语,研究模式是国外的复合场镜、棱镜和熟语激活模式,考察目标是熟语特性、语法地位、组构假设、语义结构混杂性等问题,指出了这些模式在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11]。
张辉等学者对成语的研究突破了成语本体研究的套路,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首先,这些研究使用了隐喻、转喻、心理空间、概念整合等新的研究框架来探索成语的语义构成和理解机制,解释了诸多以往研究中无法解释的问题;其次,他们的研究引入了世界先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且其研究趋势是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和神经语言学实证研究的结合,这一趋势的开拓必将取得更有效的发现并深入影响语言学其他领域的研究。
对于汉语成语语义构成和理解的认知研究不仅有大的突破,还有点滴的成果。唐雪凝、许浩对现代汉语常用成语的语义研究不仅运用了认知理论,还结合了述谓结构理论。深入分析语料库语料后,他们探讨了成语内部丰富的论元结构关系,继而归纳、解释成语语义构成的规律,总结成语语义结构成分的隐现机制和原则,深化了对成语的研究和认识[12]。
又如叶琳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使用心理语言学实验方法,对英语习语和汉语成语的理解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然后拟构出了适用于英汉习语理解加工的模式[13]。
点滴成果同样可以汇聚为巨大的进步。对于成语语义和理解的认知研究论文层出不穷,其研究趋势亦是走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道路。语义和理解,本就是人脑的复杂活动,开展实验研究,可以更准确明了地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但是,实验研究不仅需要跨学科的扎实理论基础,更需要先进的实验设备以及完备有效的实验设计和操作,所以,目前在国内研究中尚不能普及,尽管如此,语言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相结合进行汉语成语的生成和理解研究,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三、汉语成语变异的认知研究
汉语成语深受使用者喜欢,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唇吻笔端,因此,生活中,为了追求一定的修辞效果,也经常被部分改变其形式或意义来使用,即成语的仿用。以往,学界就成语的仿用研究主要从其分类、修辞效果、利弊和如何有效地仿用等角度展开。自构式语法传入中国,因为成语是构式的一种,用构式语法理论研究成语的仿用应势而生。刘宇红、谢亚军指出成语在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语义压制(semantic coercion),没有被扭曲的成分是压制者,或叫做压制因子,被扭曲的成分是被压制者。压制力源于构式本身相对固化的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语义压制过程是一个认知心理操作过程,其效果受到压制力和抗拒压制力的大小两方面因素的制约[14]。刘文通过具体的成语仿用实例证明:压制因子与构式的结构和意义越接近,压制力越大;被压制者和原语言成分在音系、语义或字形上越相似,抗拒压制力就越小。
构式语法理论是在认知语言学对TG语法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新兴语法理论,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和接受,解释了很多一直以来困惑语言学界的问题。对于成语的研究,借用构式语法理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例如罗远晗从构式的视角解释了汉语成语的活用[15],黄曼借助构式理论对比研究了汉英习语的变异[16]。
沈志和基于封闭语料库对汉语仿拟成语中的语音隐喻进行认知分析。此文重点对仿拟成语的语音隐喻进行分类研究,即语音突显、语音压制和语音隐喻[17]。文章立意新颖,语料搜集科学严谨,详细分类成语语音隐喻仿拟方式,缺憾是未对此语音隐喻机制做出细致的认知阐释。后来,他又以该封闭语料库为基础,对汉语成语仿拟的认知运作机制进行了阐释,改进了前文的不足,理论性更强[18]。
成语的变异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不仅如此,网络的普及还催生了另类的四字“类成语”,如“不明觉厉”“喜大普奔”等。这些新型“类成语”出现时日不长,其接受程度自然无法与“黄粱一梦”等沿用已久的成语相提并论,但是现代社会发达的网络系统为语言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快捷通道,而且已有媒体以“新成语”命名这些四字结构。因此,成语的变异研究亦任重道远。其实,无论是成语的变异体还是新型四字结构,都是非语法性的表达式,都是基于语境产生的,识解这些表达,都需要语境做支撑,结合语境从动态的角度去深入探讨,定会有所收获。
四、汉语成语与英语习语认知对比研究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主要建立在对英语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将汉语成语与英语做认知对比研究会促进理论的检验和研究的深入。对汉英成语的认知对比考察,成果较突出的有王文斌、姚俊。王文斌、姚俊利用“理想化认知模型”(ICMs)和“概念整合”(CB)理论分析了汉英隐喻习语认知机制方面的同与异。人类认知模型的形成和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有关,汉英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是隐喻习语表现出相似的ICM,即汉英习语在隐喻方面会使用类似的源域来隐喻同一目标域。之后,王文重点分析了汉英隐喻习语的异质性、内在的隐喻机制和存在差异的原因。汉语隐喻成语往往借用双源域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而英语隐喻习语则往往借用单源域来映射一个目标域。究其原因有二:第一,汉民族的形象思维和英民族的抽象思维,第二,汉民族的平衡和谐性思维和英民族把一切事物分成两个相对立的方面的思维倾向[19]。以上两种思维差异,体现在语言中,就形成了汉英隐喻习语的双源域映射和单源域映射的区别。
王文对汉英隐喻习语的认知对比研究,对外语教学和成语的汉英互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王文也指出汉语隐喻习语的双源域和单源域映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英语也有双源域映射习语,反之,汉语也存在单源域映射成语。只是从数量上而言,这种差异是明显的。但是这种差异到底存在的比例有多大,值得进一步统计和研究。另外,汉语隐喻成语使用双源域映射是否会使得目标域的特征凸显,反之,英语习语会否使得目标域特征降低?概念整合的过程在两种语言中是否还有个性差异?以上两个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周京励以Geeraerts提出的“棱柱形模式”[20]为理论框架,以汉语和英语中的对等习语为对象,研究了习语中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和隐喻义产生的认知过程。周文以英汉习语为例,详细分析了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并行发生和交替发生的认知过程,并辅以棱柱图示解释了汉英对等习语隐喻和转喻不同的互动认知过程,即汉语成语是并行发生而英语习语是连续发生[21]。周文认为棱柱型模式的隐喻和转喻的三种互动形式在汉英习语中都存在,其中交替发生模式存在数量较少,对等习语中可以用同一种模式阐释的习语数量非常多,但是汉语习语中以连续发生和并行发生为模式的习语数量相当,而英语习语中连续发生模式远远多于并行发生模式。周文大胆地借鉴国外先进的习语研究模式来分析汉语成语,对汉英成语的认知研究、翻译研究和教学都有一定的价值。
无论是汉语成语还是英语习语,都是文化的产物,尽管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但是以同样的大脑为物质基础,以同一个地球为物理环境,决定了人类思维的基本共性,其中之一便是概念隐喻这种人类基本的认知方式。目前的成语认知对比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汉语成语和其他语言成语的隐喻机理的异同方面。本文认为,研究相同之处,可以揭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人类的概念思维是相同的,而研究相异之处,切入点则较多,比如可以就成语进行分类细化研究,也可以从始源域入手,分析总结成语隐喻的始源域,或者就某个主题,分析其作为目标域如何通过隐喻得以认知。
五、汉语成语心理学视角的研究
上个世纪末,周光庆认为在成语的音义结合关系中,有一种意象充当着中介符号。成语的这种“表意之象”,是一种建构性图像,这种图像表达了我们对事物的特定性状特征的一种体验。这种图像的形成主要借助隐喻、示观、象征等方式。周文还认为,成语中的意象之所以具有表达功能,原因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证明的“异质同构”原理。周文在此理论认识上,对现代汉语中约700个常用成语先以内部形式表现的对象特征为标准,划分成了十二个类型,如:神情类、姿态类、行为类、作风类、方式类、途径类等;而后以选取物象的原则为标准分成三类,即自然的、人生的和神话寓言的;最后,以表意方式为标准,又将成语的意象符号分为三类:比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和示观性意象[22][23]。
周文关于成语中介符号的系列研究,已经涉及了成语理解的认知模式,使用了认知、心理方面的原理,是成语表义、理解认知分析的初探。鉴于当时国内认知语言学体系还不完善,详细透彻地使用认知方法来研究成语亦不太可能。之后,周先生提倡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与高度研究汉语词汇,并构建了“认知、解释——文化——哲学”的研究思路[24]。周先生对于汉语成语及词汇的系列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框架,开启了成语研究的多维视角,突出了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
刘振前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了汉语成语的对称特征与认知[25]。后来,发表一系列有关论文继续研究汉语成语。刘振前、邢梅萍指出汉语四字格成语中语义结构具有对称性的占很大的比例,并结合实验,从格式塔心理学、信息论等角度解释了语义结构对称的成语显然比非对称的成语易于认知[26]。刘振前、邢梅萍对四字格成语的音韵复沓形式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并运用心理语言学方法对音韵复沓形式与认知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对汉语语言教学提出了大胆的设想[27]。刘振前研究了汉语四字格成语平仄搭配的对称性与认知,通过实验得出,汉语四字成语按平仄区别不同声调搭配形式有一定理据性,分类呈现总的来说对记忆和保持的影响比随机呈现大[28]。刘振前的系列研究运用心理学理论和实验的方法,以汉语成语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为重点,详细探讨成语本身的对称特征外,对成语的教学和习得贡献显著。
黄希庭等和陈传锋等通过心理实验考察了汉语结构对称性成语和非对称性成语的视觉识别、再认特点和与成语的熟悉度的关系。两次实验的结论显示:在成语的识别和再认过程中,都存在显著的结构对称效应,对结构对称性成语的识别和再认反应时明显短于非结构对称性成语,而熟悉度效应只在成语识别中显著,尤其是在非结构对称性成语的识别过程中;在结构对称性成语中存在特有的“格式塔词素”,促进了成语的识别过程。黄文还指出无法用以西方拼音文字为实验材料所建立的认知模型来解释汉语成语的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认知差异[29][30]。
汉语成语的理解和使用,无论是对本族学习者还是外语学习者,都是有一定难度的。语言学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已经无法满足教学和习得的需要。心理语言学对成语的研究集中在成语理解的潜在认知机制。黄文和陈文的研究成果服务汉语成语习得和教学的同时,无疑对汉语成语的认知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理论模型来解释汉语成语的认知过程?而且,成语的再认反应错误率表明,成语的整体语义超过了格式塔词素结构的作用,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验。再者,成语认知研究的新趋势必然是理论研究结合实证考察,走跨学科路线,而这一点,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六、汉语成语认知研究的优势和发展
束定芳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对语义和广义语境作为语言研究重心的回归,更符合汉语语言的特点。”[1]“认知语法能够挖掘出一些用以往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所不易发现的语法现象。”[1]在汉语成语研究方面,认知语法同样表现出了绝对的优势。
第一,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成语,不仅仅就成语的本体或文化谈成语,而是把成语视为概念系统的产物,结合人类的经验、知识和文化进行研究,从认知思维着手,必要时辅以实证实验,是顺应研究趋势的,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第二,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语言学家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使用的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也愈加增多,为了走出研究困境,部分语言学家开始尝试认知的道路。认知语言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致力于概括性承诺和认知承诺,其语法观以使用为基础,语义观基于百科知识框架,在充分解释语言现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对语言事实及规律解释力较强,因为认知语法对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现实性、相关文化和语言特性做了充分的考虑[31]。汉语成语的文化底蕴深厚,使用灵活,从认知角度研究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第三,用认知方法研究成语,洋为中用,一方面为汉语成语研究注入新鲜活力,另一方面,可以验证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普适性。这样一来,和认知语言学建立最具有概括性的统一理论模式,进行最广范围的趋同证明这一研究目标一致。
从本文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用认知方法研究汉语成语是一条光明之路,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正如以上优势二所述,认知语言学是一种新型的理论框架,“在我国的发展正处于发展、反思与国际化阶段”[1],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钥匙,在研究中汉语的一些个性特征尤其值得思考。比如汉语成语结构上整齐的特点就与英语习语不同,而且,汉语成语使用的频率也远远高于英语习语,这就需要在研究中要细致对比、检验理论的解释力和有效性。
第二,认知语言学是新兴理论,本身处于发展阶段,还有待完备,势必会造成研究的局限性,因此,汉语成语的认知研究也不能不说是处在起步阶段。学者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入手,利用不同的认知概念,难免会出现片面、缺乏系统性的缺点,而且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知网的论文检索结果就可以看出,汉语成语的认知研究重复较多,优秀论文不多,缺乏创新。
第三,就国内汉语成语的认知研究,学者们之间也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徐盛桓认为,“成语是人们头脑中心理模型的类层级知识结构在线加工的结果,不一定都是概念隐喻”[6],而其他学者不都这么认为。类似这些未决的问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我们的任务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建立汉语成语理解和语义加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