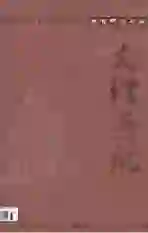冷眼观世、热心警世
2017-12-21王楚乔
王楚乔
鲁迅先生的作品向来振聋发聩,如警世洪钟般冷峻挺拔,犀利透彻。他擅长从第一人称入手进行叙事,《孔乙己》正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与《狂人日记》《伤逝》的内心独白、《故乡》《社戏》的参与型叙事者、《阿Q正传》的全知型叙事者等角度不同,《孔乙己》中“我”的身份,实为咸亨酒店一个不起眼不入流不受待见的小伙计。作者藏身在这个虚拟出的小伙计“我”之后,以其眼目观世,以其口吻叙事,精妙地演绎出鲁迅先生“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作品风格。
一、由小伙计叙事视角切入的优势
先生选择用小伙计“我”的眼睛观察孔乙己的命运、映射整个时代的浮世人生,主要的出发点可归为童真的眼睛、同病相怜的心理和作者隐藏的深心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来诠释何谓“童真的眼睛”。作者特意交待,小伙计“我”十二岁就来到了咸亨酒店当学徒。试想,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纵使社会波谲云诡,他还尚未被炎凉的世相磨钝了清澈的双眼,未被艰辛的生活麻木了本真的心灵,尚且能够用一双童真的眼睛带着特有的热忱观察周围的世界。
童,是指“我”依然保持着小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我”年少懵懂,本好奇心重,却在单调重复、枯燥无聊的伙计生涯中,因为凶脸孔的掌柜、没有好声气的主顾,被压抑得“活泼不得”,每次只有当孔乙己到店,才可以难得的笑几声。因此,“我”会習惯性的观察孔乙己这个对象、这个特殊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真,是指“我”涉世未深、心机难备,按照咸亨酒店老板的理解,就是“样子太傻,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又不够机灵,在“严重兼督下,羼水也很为难”。因此“我”在好奇之余,还具备着最基本的同情心,具备着尚纯真的赤子之心。所以作为小伙计的“我”在看到孔乙己的遭际时会产生一定的同情。
其次是同病相怜的心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即是因他人的情绪状态、处境理解和预期而在情感上有所共鸣的一种心态。此处,我们若将文本中的形象与作者的情感世界相结合,我们会发现这三个人物——孔乙己、小伙计“我”和鲁迅本人,他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彼此观照之间,自然会产生同病相怜的同理心。
孔乙己的设置,符合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侵害下的旧文人知识分子形象。他“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在当时的政治时局、文化环境与社会话语下,自然已经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成为了不被人理解和接纳、举止荒诞怪异的零余人。他存在于小说中的绝大多数意义,也不过是空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年龄上不过是个小孩子,身份上也只是个小伙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视其为少年鲁迅的化身和代言人,但小伙计决不能完全等同于鲁迅自己。这孩子读过书、会写字、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迫于生计小小年纪便出来当伙计,当然有很多的不得已,又因为样子呆傻、不会往酒里掺水而被咸亨酒店话语体系中的权威人掌柜鄙视,认为他不开窍不入流、不讨人喜欢。
众所周知,作者鲁迅在少年时期,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同样是年纪轻轻,便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来回奔波。在鲁迅的身上,有着强烈的因生计煎熬而产生的压迫感和疲惫感。他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药店的柜台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这个过程中,他“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彻底见证了人情冷暖。这段经历对以后鲁迅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综上所述,孔乙己、小伙计“我”、少年鲁迅,都是被看不起的、被冷淡漠视的、被排挤侮蔑的社会边缘人。作者用“小伙计”的视角来进行第一人称叙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再次,我们不妨剖析作者深层的心理状态。鲁迅先生一贯的写作风格是冷眼观世、不动声色的,在这表面的清冷背后,是作者潜藏的热肠深心。这里还是从孔乙己、小伙计“我”和鲁迅自己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孔乙己可视为传统封建文化对纯真的人性摧残、将各异的人性同化的代表。他是传统文化作用于旧时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强烈的映射。因此,孔乙己最后的坍塌和覆灭,正是说明了传统文化的坍塌和覆灭。作者对孔乙己“哀其不争、怒其不幸”,实际上指向的是当时的中国整体的文化格局和国民性,小说中周围人的麻木和愚昧,也正是作者对当时旧制度旧文化的一种否定。
若说孔乙己的形象指向的是传统文化与过去时代的覆灭,那么在小伙计“我”的身上,则体现出了作者对中国未来的幻灭感。小伙计“我”其实已经过早地被拉向成人畸形的社会,在生活当中也势必逐渐地被同化,会逐渐地变得麻木不仁、落井下石。一个孩子如此,那么当时混乱的国家,人人所期盼和指望的未来,还有什么明亮可言。
故而作者鲁迅,一方面觉得过去是覆灭的,一方面对未来也并非十分憧憬和向往,而是觉得茫然和杳然。这与鲁迅先生当时的创作心态相关。先生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孔乙己》这篇文章写于1918年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与当时许多旨在破旧立新的文章一样,有着否定旧文化的共有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心理。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在意识到旧文化对人性的摧残,在对旧文化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着:如果把旧文化打倒了,那么我们的出路又将何在?这种矛盾心理正是鲁迅的创作特点,他从来都是在揭伤口、撕伤疤的同时,也想负责导航向、开药方。那么这个药方究竟是什么、可能带来什么,其实他当时心里也没有万全的想法。所以,鲁迅在创作中否定过去、也否定将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希望何在、出路何在。他用冷峻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但同时更有一种茫然感和无措感,并将之潜藏在《孔乙己》这篇文章里。这种深层的心理状态经过日积月累,到了7年后即1925年他提笔写《伤逝》时,得到了异常鲜明的体现。
由此可见,从小伙计“我”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切入来写,一方面是因为小伙计“我”有着“童真”的眼睛,可以不带世俗眼光地观察主人公形象,还原主人公的生活现实;第二方面是因为孔乙己、小伙计“我”的生存状态有着同病相怜的共鸣感;第三方面,作者创作以笔为枪,此处选择过早地把一个十二岁的小伙计“我”拉入到成人的变形世界,字里行间渗透出作者对旧文化与新文化交锋走向的一种思考。endprint
二、由其他视角切入叙事的欠缺
既然本文择定以旁观者的视角切入叙事,那为什么作者不以其他人的视角作为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呢?我们试从掌柜的视角、酒店主顾(食客)视角、孔乙己本人和作者本人的视角来深入探析。
1.掌柜的视角
读者由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酒店的掌柜有一张凶脸孔、一双势利眼和一副冷心肠。文中交待“掌柜是一副凶脸孔”,可见从外表上看并不平易近人。他有一双势利眼,酒店的食客在他眼中被分成了旗帜鲜明的“短衣帮”和“穿长衫的”,他将其用曲尺形的大柜台隔开,短衣帮只能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就可以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并且他唯利是图,经常往酒里掺水,还因为小伙计做不了此事而加以责备。更为关键的是他有一副冷心肠,他最后惦记着孔乙己,也不过是因为他还欠着自己十九个钱,哪怕是孔乙己死掉后他满心惦记的也是这个。因此在酒店掌柜的眼中,孔乙己的存在价值顶多是他排出的几枚酒钱。他不会注意孔乙己的面容神色,更不會在乎孔乙己的喜怒哀乐。从掌柜的视角展开故事的叙述,小说便失去了可信性与可读性。
2.酒店主顾的视角
文本中酒店掌柜把到店喝酒的短衣帮称作主顾,他们其实正是鲁迅称之为“看客”的那些冷漠的观察者。这类人群的特点是爱围观、看热闹、麻木不仁、迎高踩低。这些主顾们是愚昧的,他们没有同情心,自身生活在社会底层,遭人践踏受人欺压,却偏偏看不起生存更为艰难、状况甚至不如他们的人,并对其幸灾乐祸,靠揭别人的疮疤取乐。如他们调侃孔乙己的新伤疤,高声嚷“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他们背后议论孔乙己的过往,也不是出于对孔乙己的关心,而是在无聊中打发时间,将其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他们观察孔乙己是带着嘲笑轻视的眼光的,和小伙计“我”是截然不同的。
3.孔乙己的视角
那么作者为什么不将孔乙己作为第一人称叙述,将本文写成一篇灵魂自白、心灵剖析呢?个人认为,此中原因很好解释,因为孔乙己这一形象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是活的,孔乙己这个人他肯定不会深刻反思、自我分析的。孔乙己有几个特点,一是爱面子,或者说是爱维持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如他是店里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尽管这长衫又脏又破几年没洗了,他还是觉得是自己身份的象征,以及著名的“窃书不能算偷”。二是真心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时刻以“固穷”的清白的君子来自我要求,即使不被人理解也“不屑置辩”。如他满口之乎者也,要教小伙计“茴”字的几种写法。当他发现小伙计可以和自己在文字上进行交流时,显出极高兴的样子,而小伙计不肯学“茴”字的多种写法,他又觉得很惋惜。三是他心存良善行有原则,他“从不拖欠酒钱”,给孩子们茴香豆。由此可见,孔乙己是保持着最初的些许的善心,又被传统文化禁锢着,被生活逼迫着,最终沦为人们取笑的对象。他一定不会直面自己惨淡的人生,因为他根本不能理性去思考、去把握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也不能深入反思和剖析自己,所以作者决不会从孔乙己的角度写。
4.作者自己的视角
作者第三人称的视角,一般我们可称作全知全能的视角。与之相比,文章从小伙计“我”第一人称视角写显得更真实,反讽意义更为鲜明。孩子眼中的世界,应该是七彩斑斓的,但在小伙计“我”的眼中,却呈现出如此炎凉的世态。理想与现实,素来是反差越大便就越会引人深思。同时,用第一人称视角写作,可以拉近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感,更引人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和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全知全能的视角下,叙述者“他”,可以是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和调度员,但却不是好的参与者和反馈者。如果用全知全能视角来叙述孔乙己的一生,文章就会显得平面,而用小伙计“我”这个角度去叙事,就会形成作者、文章和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小伙计“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随时在观察人物的旁观者,他更对故事的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无意间将自己与所观察的人物融合为一,情感也随之跌宕起伏。从初始的好奇,继而嘲弄(“附和着笑”),继而鄙薄(“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最后同情(“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因此在小伙计“我”的眼里,既有作者眼中的世界,也有读者、旁观者的体验,所以从小伙计“我”这个角度叙事,会使人物更为丰满、形象更立体、文本更为生动可信。
综上,作者以小伙计“我”切入视角进行第一人称叙事,不仅具有观察者、叙事者的“讲故事”功能,更能够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孔乙己的人生际遇,蕴含着作者的深心与潜在的思考,引起读者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共鸣。先生冷眼观世、热心警世的功力,由此亦可见一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