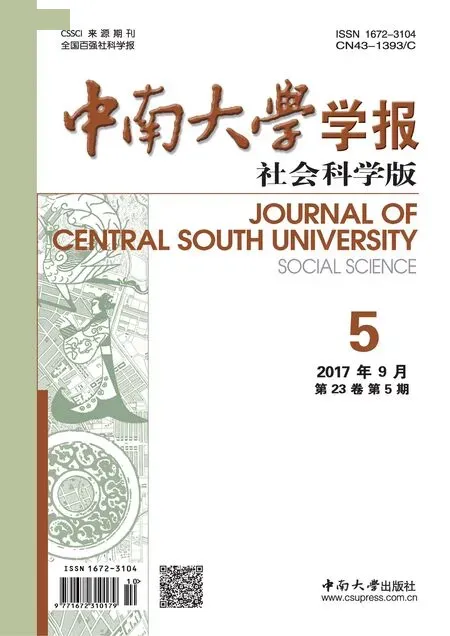论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竞争及其治理
2017-12-13李志锴
李志锴
论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竞争及其治理
李志锴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系行政规制形成的“非市场工资”,长期遁入公共政策空间并成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工具,有违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初衷。如何在保留地方政府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保证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行为的合理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最低工资标准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合理性判断,应当跳出狭义的劳动者保护视角,依据比例原则将审查重点转移至保障经济共同体整体性、流动性和公平性的视角,对劳动者利益进行整体理解,重点在于“协调”而非狭义的“保护”。
最低工资标准;地方政府间竞争;比例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向下竞争”的最低工资标准
2016年初,财政部长楼继伟提出薪酬增长过快,导致企业搬迁至国外,既减低了我国企业竞争力,也最终损害了劳动者就业机会[1]。同年8月,国务院颁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鉴于严峻的经济形式,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方案提升放缓,广东等省市则提出冻结最低工资标准两年。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抑制并非仅是当前应急之策,实际上过去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值与法定的理论值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差距。
依据《最低工资规定》中规定的比重法计算,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统计年鉴收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市”)的最低收入组人均每月生活费用支出和赡养系数,共收集20个省的有效数据。数据样本涉及我国大部分地区。其中,“月消费支出”是该省市最低收入组人均每月生活费支出;“赡养系数”是各省市总人口数与总就业数之比,系就业人口的家庭负担情况;“理论标准”是按照比重法计算的标准,实际标准为该省市一类地区2014年工资标准;“实际标准”是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若该省市最低工资标准分不同类则取最高标准。如表1所示,我国各省市的实际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低于法定理论标准,多为法定理论标准的55%~75%。
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现状,有观点认为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2.8%,其增长速度快于CPI,其调整适当[2]。有的则认为“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一直偏低,大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仅能保障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生存”[3]。张五常教授等甚至主张最低工资标准违反经济规律应当予以取消。对最低工资标准的研究多采用结果导向性的研究方式,此类目的−手段的研究方式作为逻辑起点的“目的”应当是确定的。然而,在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中,“目的”包含保护劳动者、均衡劳动市场、稳定就业等多个需要均衡的目标。基于不同目标可采取的调控手段可能是相反的:以提高劳动者生活、促进利益共享的理由,可以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促进就业、提高地区或企业竞争力的理由,可以压缩最低工资标准。如果说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是有争议的,那么其对地方招商引资的影响便是实在的。换言之,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会确实执行中央的社会政策,因为这些社会政策的执行会影响到地方政府自身的资本积累,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特点是地方可能比中央具有更关键性的影响[4]。在地方政府与纳税企业政商利益共生的格局下会有向下的力抑制最低工资标准,存在“向下竞争”的冲动,这是最低工资标准实际值长期低于法定理论值的重要原因。
无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趋势是“向上”还是“向下”,都不改变其竞争的本质,竞争本身是中性的,对竞争的判断需要结合竞争的过程与结果进行。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有序竞争,可以避免权力的恣意性,促使地方政府均衡各方利益。公平、健康、透明的竞争既可避免地方政府因民粹主义而盲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又可避免地方政府为短期经济利益而压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但是政府俘虏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均证实政府并非当然是大公无私的,政府及政府官员有其依据自身利益进行判断的行为逻辑方式。事实上,政府间不当竞争会导致政府失灵并产生破坏性后果。在单一制国家中,由于地方个体的同质性极大,对资源的需求也极为相同,竞争较之联邦制只会更加激 烈[5]。缺乏法律约束的地方间政府竞争与最低工资标准,极易脱离原有行政规制目的转变为变相寻租,破坏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损害低收入劳动者的利益,对社会资源总量和公共利益毫无益处可言。

表1 全国20省市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表
二、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最低 工资标准拟定及行为逻辑
(一)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1994年的《劳动法》第48条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由各省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3年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第8条规定,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各省市劳动行政保障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家协会等研究拟定后,报劳动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实施至今,各省市拟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得到了中央的同意,未出现申请未予批准的情况。同时,各省市劳动行政保障部门作为各省市政府的下属部门,其拟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需报各省市政府决定,因此地方各省市政府获得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决定权。
不同国家政府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荷兰等国倾向于将工资作为一个社会保护仪表,而爱沙尼亚则将其作为三方谈判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英国政府则倾向于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促进公平和效率的一种手段[6]。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种保障制度,源于《宪法》第42条“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义务。各省市政府负责拟定标准是因为地方政府在信息收集、利益权衡和综合评判上较中央更有优势,也符合行政区域管理负责制的要求。遗憾的是,虽然法律规定了劳资双方有权参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但是我国劳资谈判机制孱弱、工会行政色彩浓厚与地方政府的强势使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权缺乏相应制衡。
(二) 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与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
上下级行政机关间属于隶属关系,下级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应当服从上级的命令和决定,中央拥有对官员评定和升降决定的大权,这种权力资源是下级争夺的极其稀缺的资源。依此推论,地方官员必定会全力执行中央的命令,以取得上级的青睐。然而时间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命令时必定有所侧重,地方政府会选择那些中央更看重也符合地方政府利益的命令执行。事实上,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并非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提出“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实际上,多数省市都无法达到这一要求。例如,2014年北京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 463元,按40%计算已达2 585元,然而至2016年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仅为1 720元。可见,地方政府在调控最低工资标准上并未完全达到国务院的要求和法律拟定的理论值。
依据传统的政治学观点,行政规制作为国家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是“捆绑式消费”,相应的组织和个人只能遵从,但事实是很多的法律制度是可以被选择适用的[7]。《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大量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到内地用工成本更低的地区便是一种行为选择。我国实行国税、地税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企业的税收是地方财政重要的来源,并且影响到招商引资的考评和当地就业率。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考虑,其自身缺乏推动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动力。更重要的是经济分权的背后是政治上的集权,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上级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奖惩主要凭借以GDP等经济数据为核心的绩效考评系统。在晋升机会有限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必须完成提升GDP等经济政绩,才有可能在向上的“零和博弈”中胜出,获得自己的前程[8]。虽然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收入增倍计划等要求不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政府官员显然更加关心地方的税收、就业等指标,因为这些指标直观并容易获得上级认可,更能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带来实际的好处。此外,由于各省市政府间存在竞争关系,只要有一个省市不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就有可能影响周边省市。在竞争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带来降低竞争力的风险。我国竞争实力相近的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看似不谋而合,并非各省市对保护劳动者利益有相同的理解,而是各省市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参考彼此标准。
(三) 地方政府的两难处境及其选择
我国地域广阔,北上广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无异,而西部地区仍较为落后,无法适用统一的保障标准,故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各省市拟定。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失业金等众多财政性支出直接挂钩,在财政分权制下这些财政性支出又多由地方财政承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实际是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财政负担。换言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便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在面对地方政府间竞争、经济转型和日渐加重的财政压力下,一味苛责地方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利可能违反了“无人有义务做不可能之事”的正义原则。
我们应当注意到最低工资标准是一种易升难降的刚性标准。印尼2003年劳动法未明确何为“合理生活标准”,导致地方政府为政治因素而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甚至超过了劳资双方决定的幅度,造成了激烈的劳资对抗甚至演变为大规模示威及罢工事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9]。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设计的目标除《最低工资规定》所确定的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目标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文件还提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内需等目标。其中,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目标是最基础也最易完成的,其他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地方财政状况与经济整体形势。从风险偏好的角度,地方政府的选择多趋于保守,优先选择完成最基本也最容易完成的目标以回复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选择需要根据经济状况和地方财政现状决定的其他目标并不符合地方政府的偏好。此外,最低工资标准过高有可能使地方政府丧失在经济下行时调控的空间,这亦是地方政府考虑的重要风险。判断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竞争的正当性,不应单纯从最低工资标准数值高低进行判断,控制最低工资标准背后政府行为的合理性,才是保证最低工资标准调控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
三、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竞争之法律审视
(一) 行政规制下的“非市场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对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正常劳动后可获得的最少工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劳动基准法。劳动基准法是规定劳动关系基本事项之最低基准的法律,要求劳动关系涉及的责任主体不得低于此基准,是“政府对劳动条件干预、介入之法,故为行政法,对劳动基准法主管机关所为之行政处分,应当按照行政法途径进行救济”[10]。
行政规制是“特定的行政主体所采取的,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的,设立规则、制定政策、实施干预措施等行政活动的总称”[11]。行政规制是政府运用公权力直接干涉市场交易,基于私人选择无法纠正市场失灵,而不得不选择的行政手段。最低工资标准行政规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市场失灵,规制主体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行为的对象是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订立工资的最低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政管理活动,应当将其归为行政规制。以公共管理的视角,最低工资可谓优良的政策工具。最低工资作为政策工具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政府支付很多的行政成本,便可对社会经济产生直接的干预效果,还可以体现政府对弱势群体或劳动者的关爱,树立政府爱民的良好印象,提升政府的威望和稳定执政基础。在公共政策的视野中,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有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就是如何恰当地挑选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过程,最低工资就是一种政策工具与“非市场决定”的工资[12]。
(二) 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竞争之考量
“现代行政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自由空间之时。”[13]如何既保证行政的效率又保证其不肆意妄为,如何在立法机关授权立法不断增多的情况下避免政府失灵,实现对私权的有效保护,是现代行政法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对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学研究较多,公法角度多以宪法为视角。我国宪法中保障人权、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条款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宪法基础,宪法基础的确立固然重要,但是鉴于宪法的抽象性和我国宪法实施基础的孱弱,宪法研究并不能解决对最低工资调控的合理性判断,更无法约束其背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便是通过刺激地方政府与政府领导间相互竞争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样的竞争关系同时也使地方政府重视局部利益,从而引发地方政府间的不当竞争。最低工资标准调控作为行政行为,对其约束应当回归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最低工资标准调控与地方政府间竞争实则都系行政适当性问题。
对于判断行政行为适当性,英、美等国采用合理性原则,德国则通过比例原则进行判断。目前,比例原则不断从德国向欧洲乃至世界众多国家推广,合理性原则在英语国家不断退缩,呈现比例原则替代合理性原则的趋势[14]。比例原则不断扩张的原因是其更适合新时代保障人权的司法需求,其三子项的审查方式具有良好的工具性和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力。最低工资标准的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利益,劳动者的利益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实现的,自由流动、就业自由和社会福利公平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利益。只要劳动力市场是整体并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便可以“用脚投票”选择从工资较低的地方迁移到工资较高的地方。因此,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审查重点在于地方政府的调整行为及其他劳动力市场行政规制行为是否有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性和流动性。只要劳动力自由流动、就业自由和社会福利公平得到保障,那么具体标准的高低应属于行政合理裁量范围之内。
(三) 合比例的最低工资标准竞争
欧盟法院在审理André Mazzoleni vs ISA案[15]时巧妙地避开了人权保障问题和对成员国内政审查可能引发的争议,采取从保障经济共同体整体性、流动性和公平性的视角审查最低工资标准等行政规制行为,并提出合比例调控的判断方法和判断要件。欧盟有26个成员国,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异,人员自由流动、服务贸易自由流动是欧盟的基本原则,是将欧盟凝结在一起的不可妥协的准则。鉴于欧盟现状,比例原则被广泛应用于处理不同国家间劳动政策的冲突。André Mazzoleni vs ISA案是一起审查和判断欧盟不同成员国间以最低工资标准为核心的行政规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案件。在AndréMazzoleni vs ISA案中,欧洲法院指出:
首先,最低工资标准中涉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指对劳动者的利益,重点在于“协调”而非狭义的“保护”。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就业自由和社会福利公平是构成欧盟共同市场的基础。共同市场构建的原理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是一致的,但是强制性劳动标准的制定实际是强行规定了特定民事主体(雇主)对另一特定民事主体(雇员)的法律义务,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认同、政治结构等都对标准的制定和实行产生影响,不同国家劳动政策不可照搬套用。对劳动者的整体保护包括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税收负担等,因此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应当就从整体理解,重点在于“协调”而非狭义的“保护”。劳动者应当指多数劳动者,因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时,从效率角度首先考虑的是多数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因此对法律法规、政策规范的评判无需求全责备,其目的是维护多数劳动者利益,手段“不过分”即可。
其次,欧洲法院认为东道国的主管当局应当评估所有相关的因素,以确定其规则适用最低工资标准是否是必要和相称的。欧洲法院指出全面的评估是必要的:第一,政府必须考虑到,特别是提供服务的持续时间和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成员国间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情况;第二,为了确保在会员国建立的员工保护制度是等价的,他们必须特别考虑到报酬和工作期间涉及的数额的因素,以及社会保障的贡献和税收的影响水平;第三,东道国确立对工人的保护应当与实际情况以及其欧盟成员国的义务相称。
最后,应当采用合比例的评估方法。比例原则的适用作为“目的−手段”的检测方式,如何对行为进行评定是正确适用该原则的一个重要基础。比例原则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在应用时必然包含相应的价值基础,如果这些价值基础和评判标准是可以被任意解释的,那么比例原则规范公权力的作用定然减损。故,比例原则在具体应用中也应当规范。应用比例原则评判最低工资标准是否恰当时,应当注意三性:第一,可预测性。相应的强制性劳动标准应当是可操作、可预测的,“模糊不清”也是“过分”的表现。第二,整体性。比例原则的应用与评定应当从整体出发,在强制性劳动标准领域,应当从劳动者、雇主和社会进行综合考虑,尽可能保护劳动者,也避免“过分”保护。第三,可比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当脱离现实的标准、无视现实的环境,用单纯的理想替代政府决策的理性是有害的。比较表1的最低工资标准便可知,经济发达程度接近的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也类似,正所谓重庆的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四川决定的。反之亦然。
《欧洲社会宪章》第1部分第4条规定“所有工人都有权要求公平的报酬以使自己及其家人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针对跨国劳务合作的兴起而引发的同工不同酬、税收安定和社会安定等问题,欧洲法院通过André Mazzoleni vs ISA案等一系列案件阐述了共同体劳务自由对劳工权利的重要性,以及各国的最低工资规定应当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着重整体判断而不拘泥于具体标准的高低。
四、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优化路径
(一) 地方政府间竞争之比例治理
调控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传统经验是中央通过行政命令、会议协调等方式进行调控,通过中央的权威来约束地方。但是,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始终存在,另一方面这样的调控方式也没有跳出命令型管理的思维定式,并且使得地方政府更乐意于比拼“上层通道”,曾经的地方政府驻京办和现在的类似地方政府机构便是权力命令型管理模式的副产品。最低工资标准调控作为行政行为,对其约束应当回归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最低工资标准调控与地方政府间竞争实则都系行政适当性问题。欧盟法院在André Mazzoleni vs ISA案中实际是运用了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16]的三分判断方式。
首先,适当性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有助于达到其所追寻的目标。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地板工资”应当达到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的目标。其次,必要性是指行政规制在追求相同行政目标时,选择对公民利益损害最小的手段。应当结合社会福利、税收负担等整体考虑劳动者与企业的负担比例,选择利益的均衡点。不反对最低工资标准等劳动基准作为地方竞争实力的一部分,反对为了形成比较竞争优势而刻意控制劳动基准产生螺旋向下的竞争。最后,均衡性原则要求利益均衡,要求实现手段获得的收益不能与受到的损害间不成比例。当前与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挂钩的财政指标太多,使得地方政府变为了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而非中立第三方,在此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相配套,减少地方的财政负担。地板工资保障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是审查监督地方政府调控行为合理性的核心,只要不低于地板工资的地方间最低工资竞争都可以视为合理的。另外,以最低工资标准的方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标,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应当陷入狭义保护,脱离“协调”一味强调数值的增长会割裂社会经济的整体性,这并非最适当、必要和均衡的做法。
(二) 合比例的审查机制与地方政府间最低工资标准竞争的治理
不同于法、德等欧洲发达国家,当前我国存在工会不发达、集体谈判体系不成熟、罢工缺乏明确法律基础等问题,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也主要是采用政府主导下的调研−协商−制定的方法,如何对问题进行评估是行政决策的基础。从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成本−效益”的评估方式成为了英美行政法中较常采用的一种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评估方式。《国务院工作规则》第21条规定:“国务院及各部门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最低工资规定》亦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研究拟定”的。当前,多数省份在拟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会对最低工资标准对雇主和劳动者的影响进行评估,采用了较为简单的“成本−效益”评估方法。然而,劳动者的收入受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地区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等的影响,当前采用的简单的评估方式显然存在不足。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劳动者、雇主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社会影响重大,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程序与依据应当公开。各省在公布最低工资标准时,应当同时公布“成本−效益”的整体评估办法,建立评估体系和标准权重,使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中的利益考虑与利益博弈公开。国务院可以对各省的评估文件进行审查,要求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当具备可预测性,应当整体地对本省市的劳动者状况进行评估。要使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不过分”,应当整体考虑社会福利、税收等因素,在保护劳动者的同时选择对雇主影响最小的手段,避免雇主所失远大于劳动者所得的违反狭义比例原则的制度设计。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种行政规制行为,起到的是劳动市场的“安全网”作用,其标准不应当明显超过工资结构可接受的范围,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目标、过程等亦应受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最低工资标准通过给劳动力市场温和的压力,使得劳资双方关系向良性的方向转化,而非以行政规制取代劳资双方谈判。
(三) 落实行政程序参与原则
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遵循的步骤、方式、空间等要素的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程序的正当性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行政权的不法侵害,必须让个人参与到行政机关行使这些权利的过程中去,越是重要的权利对应的行政权力就应当越严密,或者说更贴近诉讼原则[17]。在拟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程序中,劳资双方应当能够全程有效参与制定的过程。行政程序参与原则落实不足,便容易陷入舆论引导执法的困局。
劳资双方的意见应当能够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政府应当对是否采纳劳资双方建议及其理由和依据给予相应说明,否则行政程序参与权就只是摆设。此外,劳资双方代表应当适格,具备代表的正当性,并能够真实代表其所应当代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诉求。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实行的是一元工会体系,其组织方式和社会背景的行政色彩较为浓厚,在政府主导的最低工资制定程序中我国工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身份特征的影响。要改善我国工会的现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期间更应当保障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过程的公开和透明,迫使工会以其行为显示其代表性。同时,普通劳动者也应当有机会了解和参与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过程,进而督促我国劳资谈判体制的改革发展。
[1] 楼继伟. 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J]. 财经界, 2016, (3): 49.
[2] 白天亮. 最低工资标准10年涨了两倍多[N]. 人民日报, 2015−3−24(8).
[3] 罗小兰, 丛树海. 基于攀比效应的中国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工资水平的影响[J]. 统计研究, 2009, (6): 65.
[4] 郑志鹏. 差序压制型劳动体制——中国两次劳动法在台资企业治理结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台湾社会学刊, 2014(6): 82.
[5] 刘亚平. 对地方政府间竞争的理念反思[J]. 人文杂志, 2006(2): 81.
[6] Lothar Funk, Hagen Lesch. Minimum wage regulations in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J]. Intereconomics, 2006, (10): 89.
[7] 刘双舟. 法律市场视野中的制度竞争与立法行为选择[J]. 政法论坛, 2010, (3): 91.
[8] 靳文辉. 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及其治理[J]. 法律科学, 2015, (1): 141.
[9] 方俊德. 调高最低工资对于劳动市场之影响——以印尼为例[J]. 台湾经济研究月刊, 2014, (9): 104.
[10] 黄越钦. 劳动法新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1] 江必新. 论行政规制基本原理问题[J]. 法学, 2012, (12): 29.
[12] 郑益奋. 政策工具视野中的澳门最低工资[J]. 九鼎, 2014, (12): 12−13.
[13] 余凌云. 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J]. 法学家, 2002, (2): 33.
[14] 杨登峰. 从合理性原则走向统一的比例原则[J]. 中国法学, 2016, (3): 91−93.
[15] NZA 2001, In Case C-165/98[EB/OL]. http://curia.europa.eu/ juris/liste.jsf?language=en&jur=C,T,F&num=C-165/98&td=ALL, 2016−09−15.
[16] 蒋红珍. 论比例原则——政府规制工具选择的司法评价[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17] 章剑生. 现代行政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编辑: 苏慧]
On the improper competition in the minimum wage among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LI Zhikai
(School of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The minimum wage in China is "non-market wage" formed unde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which has been in the public policy space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become the tool of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violating the rational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on. How to ensure the behavioral rational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officials while keep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scre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solve. The reasonable judgment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and the competi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behind should jump out of the narrow perspective of laborers' protec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 the key review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guaranteeing the integrity, the liquidity and equity of economic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interests of laborers, with the key lying in "coordination" rather than its narrow sense of "protection."
minimum wage;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proportional principle
D912.1
A
1672-3104(2017)05−0053−06
2016−12−11;
2017−01−15
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比例原则中国化的原理与应用路径研究”(No.106112016CDJSK08XK21)
李志锴(1981−),男,广西桂林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劳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