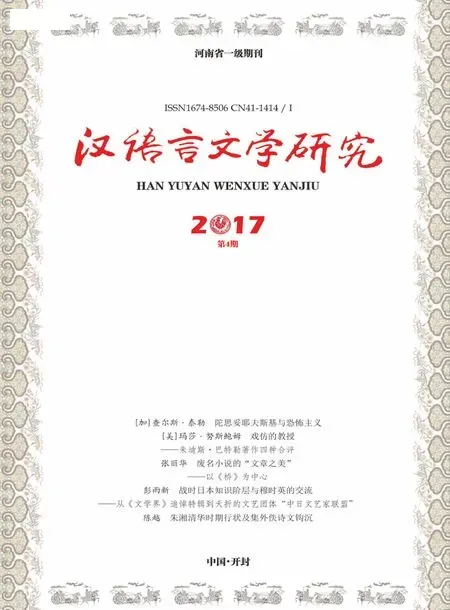听“淞南山歌”有感
2017-12-10吴福辉
吴福辉
在苏南沃原听山歌
前些日子,我曾去苏州大学开通俗文学会,会后承主人热情安排,到离上海地界很近的张浦镇姜里村(按照现名应称“姜杭村”,但古村名“姜里”仍在。其实如论及历史文物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沿用“姜里”更加适当)去听山歌。“山歌”的叫法颇具历史了,据说唐代即有,明末冯梦龙编辑苏州民谣集,题名《童痴二弄》,其中有的卷次已称《山歌》。苏州及其周边地区有什么大山呢?没有,根本就没有大一点的山脉。虎丘、阳山、东洞庭山都是美丽动人、物产丰富的小丘陵小山头,周围是多彩的湖泊平原。但这并不妨碍当地的民众把不是从山谷发生的民谣叫作“山野之歌”。那一天,我们在村中一间二楼的文化室听到的天籁之音,便是请当地的“歌娘”“唱歌郎”来演的。只见四位农妇穿戴着当地极富特色的蓝印花衣衫,蓝白三角包头,紧束腰百褶裥,齐膝围裙,边行边演边唱《月儿弯弯》等,有的歌还要加上道具敲击,配以各种变化的队形。无论是田歌、路歌、情歌,皆用吴侬软语出之,加上女性的歌喉,绵软轻柔,婉转明丽,一股土地的清香味道扑面而来。而男女声独唱的四五位农人,尤其是年高八十的老汉吟唱以女性为主诉体的 《十转郎》(是个长篇,全歌能唱好几个小时),到了紧要处,更是高亢激越,喊出高音,让全场人为之动容,兴奋不已!听毕,我还得了一册张浦镇文联编的《淞南山歌》精选本带回来。
“淞南”是吴淞江之南的意思。吴淞江源起太湖,向东流经上海市区,即是赫赫有名的苏州河,最后注入黄浦江才入东海。这一带是吴地的核心。大的“三吴”概念,应包含苏南浙北及整个太湖流域地区。而我又正好是个吴人,虽然这个吴人因长期脱离江南的关系已不能名副其实。但我的母语是上海话,说过11年。就凭我这点可怜的沪语遗存,我还是能听懂这山歌里的一些句子, 也不会被 “倷”(你)、“伊”(他或她)、“娌”(她)、“嗯伲”(我们)、“覅”(不要)、“纳亨”(如何,怎么样)弄迷糊,就像我也能马马虎虎听评弹或读《海上花列传》的对白一样。因而听的当场,便起了一层亲切感。回到北方家里,还是余音缭绕,禁不住找来“吴歌”的一些集子对照阅读。可这一对照不要紧,居然帮助我纠正了历来的一个错误认识。
这几年我讲演、著文有一个题目,是有感于今日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阅读量的不足,现身说法谈自己的阅读史。这阅读的起点我回忆的都是外国童话故事,是《格林童话》《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梦幻奇境记》里的白雪公主、小矮人、大人国、小人国等等,中国的古典名著反而靠后,是在小学期间读的了。我一贯这么说,从未怀疑过。直到这次“采风”,引起我读吴地歌谣的极大兴趣,突然发现我最初的文学教育真还是中国的,正是长辈亲友在我三四岁时教我念的那些歌谣呀!这些儿歌清一色是1940年代在上海一带流行的。这些回忆一丝不模糊,竟然能够很清晰地勾勒出我最初所受的文学教育,也即整整一代人幼时所上的“听读歌谣”第一课。
幼时所念儿歌即吴歌
现代的“淞南山歌”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想起儿时耳濡目染所接受的歌谣来了。记起的大约有六七首吧,或全篇,或仅留下残句。这已经够我吃惊的了,本来以为完全忘却的东西,原来仍顽固地存于大脑皮层的凹深处。
第一首叫《斗斗飞》。在上海弄堂或家庭里,经常可以看到大人为哄孩子,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而将小孩的两手食指竖起来互相顶住,口中念道:“斗斗飞,斗斗飞,共共飞起!”这就是此歌的全文。前两句重心在“斗”,动作是食指刚刚离开就又衔接上。最后念“飞起”时,食指便往相反的两个方向斜地里“飞”走了。这首歌谣的读、唱、演的传播是如此普遍,以至家里长辈们差不多在我和我妹妹们面前都演唱过,十几年如一日不怕重复。正像凡流传广泛的口头文学都会有多种版本一样,它们在不同的保姆“诗人”那里得到了最大的修改空间,简朴的几句话也变得多样了:
1.鸡鸡斗,斗鸡鸡,鬨鬨飞!(《吴歌甲集》)
2.鸡鸡斗,斗鸡鸡,共共飞,飞到高高山上去吃白米。(《吴歌乙集》。“上”字应读如“浪”)
3.斗斗虫虫飞,飞到南山吃白米;白米吃不着,变了一只大雄鸡。(《吴歌己集》)
4.虫虫斗,鸟鸟飞,麻姐姐家来牵麦粞,粗格烧饭吃,细格烧粥吃,一吃吃子薄隆飞。(《吴歌戊集》。 “麻姐姐”指麻雀;“牵麦粞”指手工磨麦子;“格”“子” 都是衬字;“薄隆”原有口字旁,为象声词)
这些变异,是从形式到内容分析歌谣性质、功能、特色的绝好材料。不过限于本文的题旨,这里只能从略了。
第二首流传更广,可能连北方的城乡都受到影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拨我吃糕糕。”(“拨”即给)现在还有商家用它做品牌、做广告,可见此歌的恒久性。我记得“吃糕糕”后面还有词,但都忘记了,这次我在吴歌里寻到,而且不止是一首,好不开心:
1.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团子还有糕。(《吴歌乙集》)
2.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桥浪跌一跤。咦买团子咦买糕,买条鱼烧烧,头弗热,尾巴焦,吃仔快来摇。(《吴歌戊集》。“咦”即又;“仔”是衬字,也写成“子”。歌谣从口语中来,抄录谐音字会抄出许多异体,这并不奇怪)
我记得的第三首是《排排坐,吃果果》,仅这么一句。这次在吴歌里也找到多首。如:
1.排排坐,吃果果,爹爹转来割耳朵,秤秤看,二斤半,烧烧看,两大碗,吃一碗,剩一碗,门角落里斋罗汉,罗汉弗吃荤,豆腐面筋囫囵吞!(《吴歌甲集》。“果果”是落花生,由方言“长生果”而来。这首歌后面的部分比较复杂,怪不得年纪太小的儿童记不住)
2.(1)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着留一个。——宜兴。(2)排排坐,吃梅果。爹爹买葛好梅果,弟弟妹妹各一个。——宜兴。(3)排排坐,吃果果,吃得肥头胖耳朵。割一只:称称看,二斤半;烧烧看,两大碗。——江阴。(《吴歌己集》。“葛”即衬字“格”的异体。如将1同2之(3)比较,很容易看出它们是可以互相补充的。特别是1的“割耳朵”句,不免突兀,如是吃出“胖耳朵”再“割”,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第四首是《卖糖粥》。这首记得最牢,而且是相对完整的,幼时觉得念起来既有趣,又上口。其词曰:“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格肉,还侬格壳。”在《吴歌甲集》里有《精精阁》一首,其词曰:“精精阁,阁精精,三升核桃四升壳,吃子倷个肉,还子倷个壳。”(“精精”拟铙钹声;“阁”为敲木鱼的声音)幼时读此歌总是想,三斤胡桃为何壳倒有四斤呢?想不通就越是要想。这显然是我念过的那首的变体。
此外,还有几首,只记得残句了。如问答体的:“啥格银?金华兰溪人。啥格话?唐伯虎山水画。”(这是民歌里惯用的谐音造成的机智对答。吴语“银”“人”是同音的。我很长时间不懂哪里是“金华兰溪”,为什么从上海要扯出 “金华兰溪”来)还有一首是说赶火车没有赶上,小朋友常用小板凳一个个连起来当火车,然后坐上去唱。起头的调门“咪嗦嗦嗦啦嗦啦哆啦嗦”,最后一句带叹息地道“火车开脱来”,很能说明1940年代的吴歌已有了现代都市内容,非常珍贵。可惜在我这里只剩断句残片了。
回顾我在“人之初”时期所接触过的歌谣,在在证明民间文学对儿童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那么,在现代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歌谣呢?那既是一个文学的题目,也是一个迫切的儿童教育题目。本文不及展开讨论歌谣对下一代人的教育意义究竟是在哪里,但这很明显。电视里在提倡“朗读”,我看幼儿最适合朗读和吟唱歌谣。我们应该整理传统歌谣,引进世界的歌谣,创作当代的歌谣,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征集吴歌与“五四”之觉醒
姜里村的历史很悠久,大约商周时代就有了。周边还发现了良渚文化、崧泽文化的堆积层,出土过精美的文物,证明六千年前这里就存在人类活动了。姜里村上面的张浦镇建有 “文联”机构,这也少见。所以,“文联”机构的相关人员把搜集山歌的事情作为当地的非遗工作,认真地搞起来:有山歌爱好者俱乐部,有山歌演唱队,搜集整理过1200多首山歌出版发行,件件事做得风生水起。几位搜集传唱者告诉我,他们经过交流学习,已知吴中腹地山歌的来龙去脉,也了解当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活动是与“淞南山歌”直接相关的。这让我不禁另眼相看,因为便是大学里搞现代文学的教授也不见得个个都清楚的。
这段史实的大致情况是:作为准备,早在“五四”之前,“周氏兄弟”就有关于搜集歌谣的提议和行动了。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的时候,1913年提出 “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的建议 (《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周作人1914年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搜集越地儿歌童谣的启事。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1918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破天荒成立歌谣研究会,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教授为中心人物,蔡元培、胡适作后援。刘半农作为骨干,负责起草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后来由他最早将搜集来的歌谣,每日遴选一二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1919年他自己辑家乡歌谣成《江阴船歌》出版,其劳绩不可没。周作人虽处于幕后,但他对歌谣的历史、语言、风俗方面的关注是长久的。他自己整理越地儿歌,20年后出版时写了《〈绍兴儿歌述略〉序》;为别人所编歌集写过多篇序文,如替刘半农写 《〈江阴船歌〉序》,还写了《〈海外民歌〉译序》《〈潮州畲歌集〉序》)等;他对歌谣进行评论,写有《民众的诗歌》《猥亵的歌谣》《读 〈童谣大观〉》《读 〈各省童谣集〉》《歌谣与方言调查》等,理论研究虽还是初步阶段,但在中国已属难能可贵。另一位较早显示这项工作具体业绩的,是原属北大学生辈的顾颉刚。他1918年受学校征集活动影响付诸实践,采集家乡苏州的民歌。1922年北大创《歌谣周刊》,他是积极参与者和供稿人。1926年编辑出版《吴歌甲集》,由歌谣研究会付印,前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疑古玄同(钱玄同)、刘复(刘半农)五序,影响较大。后来的《乙集》至《己集》,或多或少都和此集相关。顾颉刚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因鲁迅的关系负了骂名,也不失为一近现代文化名人了,但他的歌谣搜集与研究的学术成果,知道的人还不多。他写过《苏州的歌谣》《吴歌小史》《写歌杂记》《我和歌谣》等文,是与周作人可以媲美的歌谣研究家。《吴歌甲集》计200余首,据顾颉刚说,这些民谣均是他在苏州养病休学期间从家里和邻里小孩子的口中,从老妈子和祖母的口中抄来的。之后同乡兼同学的叶圣陶诸君也曾助他搜集,初得“一百五十首左右”。后来新妇殷履安“归宁到甪直镇的时候,就从她的家中搜集到四五十首,于是我的箧中的吴歌有了二百首了”(顾颉刚:《吴歌甲集·自序》)。苏州的歌谣也罢,甪直的歌谣也罢(甪直与叶圣陶的关系大家都熟知,此镇与张浦比邻),均是“淞南山歌”无疑。因而更引起我寻借《吴歌甲集》等书,来与手头的《淞南山歌》一书做比较阅读的极大欲望。
我们将周作人、顾颉刚两位的歌谣研究文字稍一浏览,便会发现他们共同的趋向是从歌谣的特性一直讲到“五四”前发生征集活动的历史动因。比如说:“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 ”(周作人:《〈江阴船歌〉序》)“歌谣是民族的文学。这是一民族之非意识的而是全心的表现,但是非到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样发达的时代不能得着完全的理解与尊重。”(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他们强调,歌谣本以直露、简单,经得起咀嚼,善于表达平民淳朴的风气、习俗、心理,成为“社会之柱”的民众晴雨表,方为上品。它长久被统治者的意识文化所淹没,只有在明白了民间为本源,平民的历史地位受到应有重视的时代,才会重见天日。那即是勇猛提倡平民文学的“五四”啊!而“山歌最没有道学气而最多道儿女情致”(顾颉刚:《吴歌小史》),男女情歌之所以流行,“那是礼教的压力太大了,一般民众丝毫没有恋爱的自由,姻婚又多不满意,故不得不另求满足”(顾颉刚:《山歌序》)。以离经叛道的姿态突破旧礼教,并演示得相当勇敢的这些山歌,在“五四”前后才会与一代前驱发生共鸣。这便是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平民的发现,以及爱情自由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等等。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便与“五四的觉醒”一脉相连了。
歌谣足可进入文学史
所谓歌谣入史,便是指民间文学应适当写进文学史。文学史的整个历程是先有口头文学,后有文人文学的,但一旦文人文学在更高的层次上出现,两者的关系就变得复杂了。有时候文人文学会向口头文学吸取不竭的营养,有时候口头文学也需用文人文学来弥补自己粗疏、低俗的一面。今天的歌谣如果追本溯源,或许会在唐宋诗词那里觅到踪迹,而今天的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也会从民间文学那里找到灵感,拜它为“先生”。这就是胡适在给《吴歌甲集》写序时说过的:“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实际上,仅以歌谣为例,它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线迹不断,是始终存在的。刘半农不仅是歌谣搜集的开山人之一,他还用民歌格调和吴语的自然音节,写过仿歌谣:“河边浪阿姐你洗格啥衣裳?你一泊一泊泊出清波万丈长。我隔仔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一记一记一齐捣勒笃我心浪。”(《第十九歌》,收《瓦釜集》)其他“五四”诗人学民歌体几成风气,刘大白等是其中佼佼者。之后,从左翼到抗日根据地的诗坛,吸收歌谣的创作者也不少,成为大众化的一翼。瞿秋白、鲁迅都写过“拟民歌”(自古便有“拟民歌”。家喻户晓的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有人指出可能脱胎于南朝的《子夜歌》),以鲁迅的《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最为简练、传神。到了抗战后方产生《马凡陀山歌》,那种都市讽刺民谣体在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到1960年代,一时跟着政治风向标转悠的文学,将“人民为本”推演成了“人民唯一”,用民间写作把文人创作挤到一旁去的文学史也都出笼了。诗歌界提倡写大跃进民歌,集成的《红旗歌谣》把最朴实的民歌变作最浮夸的文体,极左的思潮将好端端的民歌引向歪路。到了今天,歌谣仍然在民间蓬蓬勃勃地生长,等待我们进一步去继承、发扬、创造。在淞南听到民歌便是生动的一幕。
关于现代文学史中的歌谣线索,以上仅是举例性质,但已能看出“入史”的途径可以有二。第一,是把典型的文学运动和创作成就直接入史。如本文所涉及的“五四”征集歌谣活动,便可融入“五四”文学环境重大改变的章节加以叙写。再如意义不凡的经典歌谣作品的产生,像瑶族长达14000行的创世史诗《密洛陀》,花费27年整理成功而以文字形式问世,是可以写进文学史的;藏族长达100多万行的民歌(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伟大的长篇叙述诗,当然也可写进文学史成为一节。但现在一般都缺席,只在少数民族单独的文学史里才能看到。第二,是将歌谣和文人创作的诗词曲赋甚至故事说唱、小说传奇相互影响的关系,插入文学史的叙述中。这种“影响”的论述将文学连成一片,交织成应有的网状,同时加强了文学经典化过程的演示。这里有各种情境。首先,可以表现为古今歌谣的根源关系,如刘半农辑录的《江阴船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吴歌戊集》),据说在宋代便流行了,可见《京本通俗小说》的引用。再如,顾颉刚《写歌杂记》所引《吴歌甲集》第80首的《牡丹开放在庭前》,指出它来源于唐寅的《妒花词》;而《妒花词》又查出是源于《全唐诗》中的一首《菩萨蛮》,作者无名氏。这种民间写作倒过来反是起源于文人的例子虽然不多,但正说明两者纠缠不休的真实情况。其次,同题(甚至便是同一首)的跨时代歌谣,如把各种吴歌集子与我手头的《淞南山歌》加以对照,可看出“变化”的时代根苗,也是文学史可写入的题目。如《萤火虫》和《萤火虫夜夜红》(前者为历史歌谣,后者为现今《淞南山歌》里的,下同),《再歇廿年做太婆》和《阳山头上小花篮》,《姐伲生来骨头轻》和《一个姐姐骨头轻》等。更突出的例子像“结识私情”系列(指每首开头一句均为“结识私情”),现今的《淞南山歌》有“结识私情隔顶桥”“结识私情隔条街”“结识私情隔块田”“结识私情北海北”“结识私情南海南”等题,均是甜美的情歌;据有人查出冯梦龙明代记录的《山歌》里,却有古代更加大胆、勇敢的女性表露:“结识私情勿要慌,捉着子奸情奴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这引发学者不禁礼赞:“这是何等精神,何等勇气,何等力量!赤裸的人性,率真的心声,只民歌里有”(李素英:《民歌的特质》)。其实那就是“私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反应。压迫愈大,反抗则愈烈也。本来歌谣就是流传的文学,文学史论及文学的传播规律时这就是正面的范例。还有负面“影响”也不可忽略回避,是与我们对歌谣传播的全面看法相关的。比如在流传中的失真,如加深对残疾人的嘲笑(戏弄矮子、麻子、聋子),如因大量采用弹词、昆曲的语汇而使吴歌过于文人化等等,指出这些,我们就不会在认识上对民间文学摆来摆去,无所适从了。最后,还有不同文体互相影响的文学现象问题,可供文学史写作参考。如张爱玲代表性小说《倾城之恋》有个著名的用拉胡琴做开头、结尾的写法,这次读吴歌时不经意竟读出了它的出处。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那段足够烘托全文的妙句:“胡琴咿咿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在歌谣里,已有为现代旅行需要专门介绍上海周围风景的俚曲了。《苏州景致》这样唱:“我来拉胡琴呀,唱只苏州景呀,苏州景致多得无淘成呀。”《无锡景致》的开头则是:“我有一段情呀唱把诸位听。诸公各位净吓净净心。我有一点无锡景吓细细从那头吓说吓说你听。”(顾颉刚:《吴歌小史》)这《苏州景致》《无锡景致》两曲的势力相当之大,它们由沪苏一带的小调变化而成“申曲”,在1940年代上海的娱乐场、茶馆、餐馆、无线电里到处扩散,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听到了。我想,对都市民间歌谣相当熟悉的张爱玲一定也是听到了。她把小调的文字、情趣、意境悄悄做了点移动,从闲适、轻松平添了些忧郁的成分上去,于是,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头尾。文学史可以这样写:张爱玲小说吸收了吴歌的养分!
听唱现代吴歌的随想,先发挥到这里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