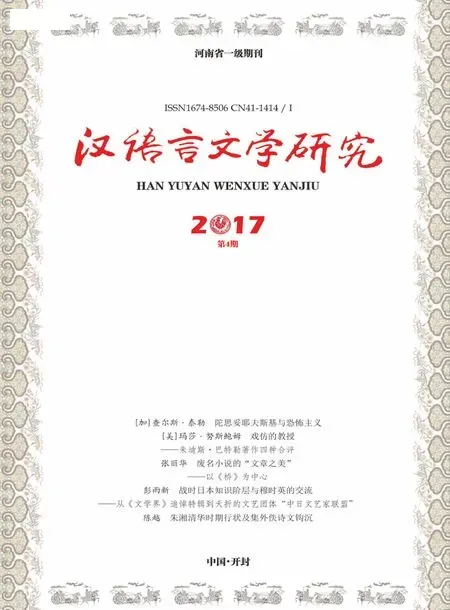茅盾和郑振铎对左翼文学“左”倾思想之修正*
——以《文学》《文学季刊》的创办为例
2017-12-10黄艺红
黄艺红
1930年代初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上海开始成为文坛中心。北方文坛比之于上海文坛的热闹更显沉寂。此时,在上海刚刚成立的左联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作为共产党的外围文化组织,它要求盟员直面斗争,从事具体的革命工作:如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发动同盟罢工等,这使得盟员的身份暴露,难以保存实力,导致开展工作愈发困难。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之下,左联的机关刊物接连被查封,盟员遭到捕杀,左翼文化运动陷入困境。为谋求生存空间,在“文化围剿”中突围,左联必须转变“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作风,打开大门与北方文坛取得联系,释放诚意。此时,身处上海的左联作家茅盾,定居北平与左翼文人关系密切的郑振铎,便发挥了特殊作用。
一、办刊物、求团结——茅盾对左翼文学“左”倾路线的反思
成立初期的左联受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影响,以左翼作家的联合战线自居,但又仅止于强调作家的左翼立场,忽视“联合战线”的扩大。最普遍的做法是:采取阶级分析方法来区分文学的性质和作家的成分,严格与一切“不革命”的作家划清界限。这导致左翼文学生存空间狭小,关上左联对外敞开的大门。茅盾认为,自1931年11月起情况开始好转,左联基本摆脱“左”的桎梏,迎来它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他分析促成这个转变的,是鲁迅和瞿秋白。①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鲁迅与瞿秋白,一个是当时公认的左联“主帅”,一个被认为是共产党派来指导左联工作的代表,他们的合作,使得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仍取得不小的成就。茅盾指出,是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造就了“奇特的现象”;而事实上,茅盾与郑振铎的合作,对沟通南北文坛、壮大左翼力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丝毫不逊于鲁迅和瞿秋白二人。
茅、郑的合作,应该说最早始于1921年,二人筹备发起文学研究会,共同主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之时期;到1923年,郑振铎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茅盾对《小说月报》的影响,仍通过郑振铎得以体现),积极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创作;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茅、郑曾一起创办《公理日报》,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1933年起,凭借着亲密无间的合作经验,在上海的茅盾和在北平的郑振铎,集二人之力,架起南北文坛之间的桥梁:上海《文学》和北平《文学季刊》《水星》等杂志的面世,对消除南北文坛的畛域之见,扩大左翼文化的影响,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选择以办刊的方式为左翼文学争取生存空间,团结除“民族主义”文学以外的非左翼文学,这与茅盾的左翼文学实践及其长期担任左联的领导职务有关。对左翼文学存在的“左”倾思想,茅盾的反思几乎是左翼文学阵营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早在1927年,茅盾就写下《从牯岭到东京》一文,对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队伍之“左”倾盲动主义表示过怀疑。他阐述了“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敌人这一观点,还表达了对“标语口号文学”的担忧。他认为,对于左翼文艺的宣传不能空有革命热情,而忽略文艺的本质。1930年,左联的成立宣告左翼文学阵营的组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左翼阵营的左倾幼稚病得到完全清算,在成立初期,左联各项工作的开展仍以参加不切实际的“左”倾斗争为要。到1931年,左联刊物《北斗》的创刊,成功打开南北文坛互动交流的局面,这与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反思左联内部的“左”倾错误、争取左翼文学生存空间是分不开的。
当然,左联的自我纠偏是长期而反复的过程,其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并未得到有效清理,《北斗》后来越办越“红”,终被查封,就再次关上与非左翼作家对话的大门。《北斗》被禁之后,左联刊物都处于地下发行状态,基本上是内部传阅,很难对外产生影响。1933年3月,郑振铎从北平到上海与茅盾会面,他们提出目下缺少“一个 ‘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写出了作品苦无发表的地方”①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194-198页。。早先鲁迅、茅盾等人创办《北斗》的初衷,就是为了办一个以刊登文学创作为主的左翼刊物,茅盾、郑振铎所说的——没有一个“自己的”“长期的”刊物,指的就是左联办文学刊物的现状。而他们提到青年作家写出作品无处发表的困境,更多的是出于左联负责人和文坛老作家对青年左翼作家的关心。
为再次打开局面,茅盾主动向郑振铎说明必须办刊:“内容以创作为主,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是左倾的,但作者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②同上。此次会面促成了《文学》的创办。《文学》编辑先后由傅东华、黄源、王统照等人担任,但作为实际上的主编,茅盾的编辑思想一直影响着《文学》。这份统战文坛的左翼巨刊,因其既有冲破封锁打开文坛局面的魄力,又有把南北各派作家聚合在一起的能力,成为1930年代生存期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文学期刊 (1933-1937)。进一步说,1931年下半年和1933年下半年,茅盾两次担任左联行政书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北斗》和《文学》出刊。而茅盾在1932至1933年间创作《春蚕》《林家铺子》《子夜》等作品,就是因为左联正从“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创作应成为工作的重点,身为左联的领导核心成员,茅盾率先要求自己以扎实的作品指导左翼作家创作,将左翼文艺运动引向正轨。
至1936年,茅盾撰文批判“两个口号”的论争,严厉指出在论争中出现的关门而内战、“内战之后挤出几个再关门”③茅盾:《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2号,1936年8月23日。的宗派主义做法。谈到左联解散,茅盾认可《萧三致左联信》中指出的,左联存在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他提到:“虽然从一九三二年起,‘左联’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基本上克服了初期的左倾盲动的做法,采取了合法斗争的手段,在文艺的各条战线上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左联’内部的宗派主义,闹不团结,‘唯我最正确’‘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的现象,以及把‘左联’办成个政党的做法,依旧存在。”④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09页。
1946年,茅盾写出《也是漫谈而已》⑤茅盾:《也是漫谈而已》,《文联》1946年第1卷第4期。,这是为批评冯雪峰 《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①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第1卷第1—3期。一文而作,也是他在1949年之前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左”倾思想长期反复出现等问题,做出的全面总结和清算。冯文指出,1928至1936年间的左翼思想和文艺运动,虽存在着文艺与政治“机械的结合”,出现理论和创作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但都属于统一战线的范畴,只是由于工作方式的转变不及时,才导致中间派作家未被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冯雪峰此说,可能是因为全面抗战已获得胜利,接下来又要面临国共相争的局面,因此,有必要加强与左翼统一战线相关的理论建设,但这就将左联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导致的工作失误,全部纳入到统一战线之中。这样的观点自然招致茅盾反对,左联从成立伊始到后来的发展壮大,茅盾是亲历者,甚至是重大事件的主要决策者,他几乎是最有资格写文章批判冯雪峰观点的人。左联成立初期排斥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做法,就表明左联并不是从1928年起就属于统一战线的组织。要说统一战线的形成,并不在朝夕之间,而是由鲁迅、茅盾、冯雪峰、郑振铎等人日积月累的努力一点点争取而来。左联在1932年前后逐渐转变“左”倾作风,建立统一战线的意识由此才慢慢确立起来。从上文提到的,在茅盾主导下改变左联刊物的编辑方针,就能窥见一二。冯雪峰在文中说,左联六年间没有吸引中间派作家加入到统一战线,还说清算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在左联解散后,成立统一战线才开始的,这就无怪乎茅盾要撰文批驳了。
当然,茅盾自己也承认,对于“左”倾错误的危害,“我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开始多半是直觉的不赞成,在理论上彻底弄清楚还在两三年之后;相反,当时的极左思潮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受害不浅”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58页。。但是,为纠正左联政治工作和文艺活动的极“左”倾向,茅盾几乎将其主要的精力都放到建设左翼文学中来,他通过办刊的方式培养左翼作家,并尽最大可能聚合广大的非左翼作家,使他们愿意与左翼作家对话交流、包容互动,并最终站到同一战线,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二、南北两地“起劲干”——《文学》等刊物的重要推手郑振铎
郑振铎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活跃、最热心、精力最旺盛的文学活动家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时,他就是推进白话文的健将,既是《小说月报》的主编,又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从1931年9月起,郑振铎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合聘教授,担任中国小说史、戏曲史及文学史诸课程的教学工作,其间,他悉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他还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和《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其编辑出版的大部头丛书“世界文库”,在当时的文坛产生过巨大影响。
郑振铎待人诚恳热情,对工作充满热忱,他致力于培养青年作家,又“善与人同”③郑振铎这些显著的性格特点,在陈福康编选的《回忆郑振铎》(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与其生前交好的友朋多有回忆。老舍、端木蕻良、靳以等,都是在郑振铎的帮助下走上文坛。季羡林说:“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季羡林:《西谛先生》,陈福康编选:《回忆郑振铎》,第211页)郑振铎“善与人同”是俞平伯语(平伯:《忆振铎兄》,陈福康编选:《回忆郑振铎》,第97页),这精准地概括出郑振铎善于做人的工作,和努力团结人的性格魅力。。无论是在左联成立后团结非左翼人士,大力协助茅盾开展左翼文化运动,还是在左联解散和筹备文艺家协会的过程中,都能看到郑振铎四处奔走的身影。茅盾邀请郑振铎办《文学》的时候,对他说,目下缺少一个自己的刊物,可见茅盾把郑振铎当作左翼阵营的自己人来看待。笔者在翻阅旧刊时发现,当时的国民党刊物《社会新闻》甚至刊文说:“郑与茅盾等极友好,故其思想由古典主义一跃而为布尔什维克主义。”④泉:《郑振铎来上海》,《社会新闻》第4卷第24期,1933年9月12日。可见两人交谊之匪浅。但据陈福康的研究,早在“五四”时期,郑振铎就已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①陈福康:《郑振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3页。,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皆有来往。没有参加左联,并不等同于不具有左翼倾向,也不意味着不能将其认定为左翼作家或要求进步的作家,关于这一点,从来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综观郑振铎在现代时期的文学活动,他始终追求进步,坚持民族大义,立场鲜明,“虽然没有参加左联,但却是十分自觉地作为一个左翼文艺战士在斗争着”②同上,第64页。。他对左联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对左翼文化工作的热情实践,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左联作家。
《文学》的创办,有郑振铎的功劳;《文学》屡次遇到危机,也主要由茅盾与郑振铎共同商讨应对。比如在第1卷第2期《文学》中,傅东华曾以伍实的笔名发表《休士在中国》一文,其中提到:“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完美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的顾忌。”傅东华撰写此文的本意,是为美国黑人作家休士的中国行未得到如萧伯纳来华同样的重视而打抱不平,但正是这几句话引起鲁迅的愤怒。他认为自己身为《文学》的同人之一,却被“无端虚构劣迹,大加奚落”。虽然在事后,编委会向鲁迅承认稿件失检,傅东华专门刊文致歉,茅盾特地登门解释,鲁迅还是辞去《文学》编委一职,一年时间不为《文学》写稿。后来,正是茅盾约同郑振铎一起拜访鲁迅,经沟通之后,终于打破僵局,鲁迅答应再次为《文学》写稿。
1934年初,国民党的书报审查机构对《文学》的“新年号”严格审查,在大抽大砍的干涉之下,《文学》第2卷第1期脱期半个多月才得以面世。鲁迅在与郑振铎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忧虑:“《文学》二卷一号,上海也尚未见,听说又不准停刊,大约那办法是在利用旧招牌,而换其内容,所以第一着是检查,抽换。不过这办法,读者之被欺骗是不久的,刊物当然要慢慢的死下去。”③鲁迅:《340111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为顺利度过书报审查带来的危机,茅盾特地去信邀请郑振铎南下商议对策,他们想出了连出四期专号的巧妙办法加以应对,即后来的《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而《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第2卷第6期)正是由在北平的郑振铎负责组稿。卷首的《文学论坛》以“中国文学研究者向那里去?——中国文学的遗产问题——论文字的简繁——向翻印古书者提议”的形式发论,此部分文字全由郑振铎执笔。该期专号刊有魏建功《中国纯文学的姿态与中国语言文字》、刘复《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郭绍虞《中国诗歌之双声叠韵》、吴文祺《论文字的繁简》、朱自清《论“逼真”与“如画”》、俞平伯《左传遇》、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赵景深《宋元戏文与黄钟赚》、顾颉刚《滦州影戏考》、高滔《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等37篇涉及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可谓大气磅礴。在“五四”落潮之后,如此大格局的论述几乎绝无仅有。连鲁迅也对这一期 《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赞许不已:“本月《文学》已见,内容极充实,有许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柢的。”④鲁迅:《340606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4页。
在短时间内,能向北平的知名学者广泛邀约,并最终刊录如此高水准的文学研究论文,这与郑振铎当时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合聘教授有关。撰稿人与郑振铎基本上是熟悉的同事和师生关系⑤郑振铎曾任清华大学《文学月刊》顾问,被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中国文学会聘请为委员,他长期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在各方面支持学生办的文学刊物。当时还是学生的吴组缃、林庚、季羡林、李长之等人,都曾得到过郑振铎的扶植和帮助。此外,余冠英、吴晗等青年学生能在《文学季刊》发表文章,也是通过郑振铎推荐。,加上郑振铎平素又“善与人同”,约稿自然就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了。而郑振铎自身长期专注于中国文学研究,这就使得他选择稿件,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可以说编辑一期如此高质量、高规格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非郑振铎而不能做到。当然,由此也可以看出,郑振铎立足北平,对于左联团结北方文坛,增进南北文坛之间的联系,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1935年1月9日,鲁迅在回复郑振铎的信中,对郑振铎有意离开燕京大学表示其遗憾之情:“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①鲁迅:《350109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3卷,第340页。为让郑振铎继续在北平工作,发挥其作用,鲁迅还特地致信许寿裳,推荐郑振铎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工作,惜未成,这都是后话了。
茅盾后来写道,郑振铎虽然对于某一形势或决策未必全部彻底明了,但只要开诚布公对他说明,这样的决定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他就会欣然乐从,鼓起精神,来干委托他干的工作”,“这在当时,是要有点牺牲精神的,万一不济,小则坐牢,大则会丢了性命”,“可是他还是起劲地干了”。②茅盾:《悼郑振铎副部长》,《诗刊》1958年第11期。这个评价是不谬的,对于郑振铎的“起劲干”,笔者查阅当时报刊,看到不少与此相关的评价:“郑振铎主编文学季刊,兼主编文学月刊兼主编水星月刊。”③曼因:《文坛杂报》,《当代文学》第1卷第5期,1934年11月1日。“旧人中,比较起来,最活动的当然是郑振铎了,南北两《文学》都有他的名字。”④余异:《北平通讯》,《当代文学》第1卷第2期,1934年8月1日。此处提及的,就是郑振铎为推动南北文坛的交流与合作,创办《文学》,通过靳以沟通《文学季刊》及其副刊《水星》的编辑部和作家群。
据《文学季刊》的编辑靳以回忆,《文学季刊》在创办之初,就以郑振铎为桥梁,与《文学》月刊建立起互通有无的紧密联系。⑤靳以:《和振铎相处的日子》,《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胡风《张天翼论》一文,因为在上海的书报审查处通不过,由当时任《文学》编辑的黄源转寄北平的靳以,最后发表在《文学季刊》。还有巴金的小说《电》,原投《文学》,并已预告发表,因被审查官禁止发表,只好署名欧阳镜蓉,改题为《龙眼花开的时候》发表于《文学季刊》。所以说,《文学季刊》与《文学》乃至与左联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就连卞之琳回忆郑振铎在南来北往之间,为推动左翼文学与非左翼文学的交流付出的努力,也表示出这样的疑惑:“这里是否有一条政治路线的引导(按:暗指有左翼背景),郑振铎也许明白。”⑥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读书》1983年第10期。1958年,郑振铎也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创办《文学季刊》和‘左联’有些联系。”⑦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若结合《文学季刊》的创刊背景,再比较这两份杂志的作家队伍,就能发现二者之间有极大的重合:如鲁迅、茅盾、郑振铎、靳以、老舍、张天翼、吴组缃、朱自清、卞之琳、蹇先艾、冰心、丰子恺、丽尼、王任叔、凌叔华、芦焚、臧克家、李广田、巴金、欧阳山、陈白尘、鲁彦、沈从文、林庚、何其芳、艾芜、蒋牧良等人都在这两份杂志上出现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平的《文学季刊》与上海的《文学》是旨趣相投、携手并进的姊妹刊物。
在朱自清1933年的日记中,记录下郑振铎为推广《文学》和《文学季刊》,常以其个人名义宴请北方文坛作家:
4月22日 晚在东兴楼,应振铎及刘廷芳之招。席间有陈受颐、许地山、魏建功、严既澄、颉刚、绍虞、平伯、杨丙辰等。……铎兄请客系为文学杂志事,余允作一文。
9月15日 晚振铎宴客,为季刊,晤李巴金,殊年轻,不似其特写。冰心亦在座,瘦极。归时与林庚等多人同行。
10月3日 晚饭在振铎处,商文学季刊事。
11月18日 晚赴郑振铎宴,仍《文学季刊》编辑。吴晗拟就历史书中带小说性质材料加以搜讨,又拟作《冯梦龙传》。
12月29日 晚赴振铎宴,为《文季》也。振告我东华君将在《文学》中肃清左翼,如此则《文学》失其续办之理由矣。⑧此处所引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48、254、263、271页。按:12月29日日记所指,正是《文学》决定连出文学研究专号,为转移国民党书报审查机构的注意,以图杂志生存一事。根据朱自清的记载,也能够佐证《文学》正是左联杂志无疑。
由此可见,为促进南北文坛交流和北方学界内部的融洽,郑振铎可谓劳心劳力,他待人并不因作家的政治派别和文学观念之不同而有别,这也决定了《文学》与《文学季刊》重团结而少纷争、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
《水星》常被认为是京派刊物。但因为“《文学季刊》先这样办了,也就给它的附属月刊(按:指《水星》)定了调子”①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读书》1983年第10期。。《水星》编辑部从一开始就与《文学》《文学季刊》的作家群保持着较好的文人交谊,又因为它并不鲜明的政治色彩,成功地团结了北平的学院派文人:“向北平正直而较少明显派系色彩的学院文人伸了手。”②同上。这三份杂志的编辑与创作,都主动寻求与非左翼作家的对话,不但培养出一批左翼新人作家,对扩大左翼文学的影响力、消除南北文坛的畛域、推动1930年代文学的繁荣也起到重要作用。
三、“左翼文学的修正派”:茅盾与郑振铎合力扩大左翼战线
在茅盾大力推动和郑振铎奋力配合之下,上海的《文学》、北平的《文学季刊》等刊物成为北方学界与南方文坛联系的桥梁。他们所做的工作,却并不为左联内部全然了解。就连当时的国民党右派都意识到茅盾为纠“左”做出的努力:“作为左翼文学的修正派而毅然起来修正所谓左翼文学的幼稚病的,有一个茅盾先生。”文章评价这是“茅盾的大‘矛盾’”,讥讽他是既要左翼,而同时又要纠正斗争的“新兴的第三种人”。③柳风:《茅盾的大“矛盾”》,《新垒》第2卷第3期,1933年9月15日。右派文人把茅盾说成是“新兴的第三种人”,显然是用“第三种人”的罪名分裂左翼团体,但他们将茅盾看作是“左翼文学的修正派”,这其实倒是一个很恰当的概念,甚至可以把这当作是对茅盾纠“左”工作的肯定。综合郑振铎在1930年代的文学思想及其与茅盾合力发展左翼文学的行为来看,同样也可以把他列为“左翼文学的修正派”。但郑振铎这个左翼作家,因为没有加入左联,多数时候只被看作是追求民主的中间派。他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为左联做的工作,并不为其他左联成员所理解和认可。
北方左联盟员孙席珍在提到北方左联工作的转变时说:“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总是互相联系的,这表现在对某些人估计不足,争取中间分子不力,比如说当时有好几位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前辈作家朱自清、郑振铎、郭绍虞等在平任教,我们就很少主动去跟他们接近、联系;说是应该留几位有名的中间人物作为缓冲,是一种策略,其实也不过是文过饰非之词。”④孙席珍:《再谈北方左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0页。这里对中间分子的划定,就包括郑振铎,只因他没有加入左联,就忽视他为加强南北文坛的沟通与合作,为纠正左翼阵营“左”的倾向所做出的努力。就连鲁迅也把郑振铎排除在左联人员之外,他在回复王志之的信件中,对其提及北平左联组织文艺茶话会,郑振铎、朱自清皆出席一事,只说“郑朱皆合作,甚好”。⑤鲁迅:《330510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6页。
左联解散后,周扬等左联成员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为能最大程度地争取作家加入,联系作家的工作由茅盾、郑振铎和傅东华出面。出于对左联未发布声明即自动解散的行为之不满,鲁迅坚决不肯加入这个新协会。在他看来,左联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的派系争斗如不能肃清,即使组织了统一战线,作家们不见得就真能站在同一营垒之中。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抱怨道:“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与郑,其积极,乃为救《文学》也。”⑥鲁迅:《360423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4卷,第81页。“此间莲姊家已散,划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①鲁迅:《360503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4卷,第85页。莲姊指左联,毛姑指茅盾,这说明鲁迅对茅盾、郑振铎所做工作的不理解,甚至因为他已身处左联内部宗派斗争的漩涡中,无法跳脱斗争的思维来理解茅、郑二人之行为。茅、郑为消除左联内部宗派斗争的不良影响,为争取非左翼作家的支持,多年热情奔走、殚精竭虑,《文学》获得的成绩就是茅、郑等左翼同人合力造就的。茅、郑的努力当然并不仅只为保住《文学》而已,更是为维持左翼阵营的团结一致。
茅盾与郑振铎所做的工作在当时不被理解,在后来与左联相关的研究中,学界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鲁迅的“主帅”作用与瞿秋白的“如虎添翼”之功,茅、郑的合作对左翼文化运动起到的积极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显然是有失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