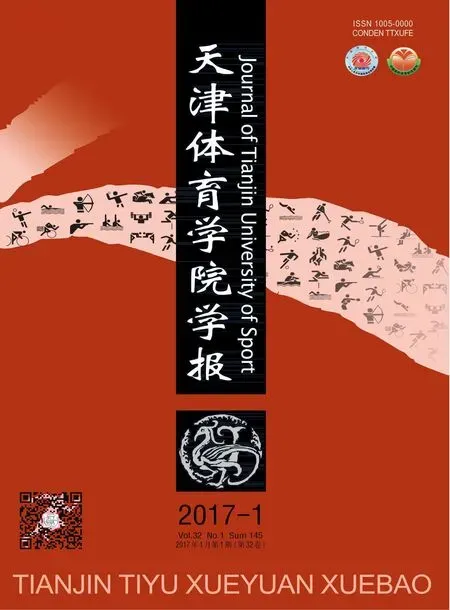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激励结构与约束机制
2017-11-27易剑东董红刚
张 琴,易剑东,董红刚
●成果报告 OriginalArticles
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激励结构与约束机制
张 琴1,易剑东2,董红刚1
在现有的激励结构与约束机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个性化产品以获得政治加分和晋升收益,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成为备选方案之一。然而,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效应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更加重要的是,大型体育场馆的公共产品至少是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建设成本最终还是要公共财政偿还,给下一届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进而违背了社会公众利益和中央政府意愿,而地方政府行为背后体现出的是激励结构和约束机制的一致性或者背离度。此时,中央政府必然以某种形式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加以控制,以避免地方债务危机和过分违背民意,在横向约束机制要素不完备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只能选择以审批制为代表的纵向约束机制。从官员晋升维度解释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激励结构,并在这一解释性框架下阐述我国兴建大型体育场馆中央审批制的合理性,意在指出大型体育场馆能否回归理性取决于激励结构与约束条件的互利耦合。
体育管理;大型体育场馆;激励结构;效用约束;地方政府
大型体育场馆的“超常规建设与大量闲置”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亟待破解的问题和困扰学界的难题。研究大型体育场馆的现有文献基本沿着2条脉络:(1)在“改革论”框架下探讨大型体育场馆的经营绩效,提出的思路有多元化经营[1-4]、财税扶植政策[5-6]、民营化[7]、所有者复归[8]和拍卖冠名权[9-10]等,旨在解决大型体育场馆赛后治理问题;(2)从“存在论”意义上论证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逻辑,代表性的观点有融资模式决定赛后经营开发模式[11],政策工具的本质属性[12],主要回答大型体育场馆的属性问题。其实,世人期盼倾听困境背后的故事。本文从目标指向和行动策略2个维度,探讨地方政府建设大型体育场馆的激励结构;从纵向与横向2个维度,探讨地方政府建设大型体育场馆的约束机制;试图构建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能够将大型体育场馆超常规建设(违背中央政府意愿)与大量闲置(违背社会公众利益)同时加以解释。
1 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激励结构
激励结构引领着地方政府的目标指向和行动策略,而目标指向与行动策略反映出制度的激励力度、评价维度和约束强度。因此,地方政府的目标指向和行动策略是在制度框架内的理性选择,以目标指向和行动策略能够解释我国地方政府超常规建设大型体育场馆的行为。
1.1 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目标指向
地方政府官员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如何获胜?这一政治学核心议题的一般解释是,地方政府官员会不遗余力地对外释放一种信号——其在某些能力上较为突出,相对于其他同级别官员更适合高级别岗位[13-17]。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官员如何选择,以及上级政府如何理解“某些能力”。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某些能力”首先要可度量,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依据是增长、就业和税收等经济指标,虽然当下中央政府已经取消省市GDP排名,开始综合考虑地方政府的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但显然在绿色GDP或者尚不知名的评价体系中经济指标居于主要位置。其次,可行性,为确保上述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央政府保留了任命省级官员的绝对权威,并将每一级政府都纳入竞争格局,让每个地方官员的仕途都与“某些能力”挂钩。这种激励结构的合理性在于,指标体系明确、参与人强激励和避免集体偷懒(合谋),一个清晰可见的事实是,指标优者更易获得晋升机会。然而,在指标相差无几甚至近于中央政府无法评判时,又该如何?一个不可言说的事实是,“特色”成为竞争成败的关键(以“独特性”获得晋升——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18]或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19])。地方政府建设大型体育场馆着力凸显地方文化、经济和社会特色,旨在打造个性化产品,进而获得政治加分和晋升收益。大型体育场馆具备可供考证的实体,还可以充分包装、宣传以获得社会化影响,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2014年山东第23届省运会,嘉祥为凸显“石雕文化”将济宁嘉祥体育馆打造成“石立方”,深受各界好评;曲阜体育馆耗资3.9亿元打造“山高水长”以映衬孔子文化,市政府称其为曲阜的标志性建筑;济南全运会期间,济南奥体中心“东荷西柳”的设计紧扣市花、市树,凸显地方特色,期间城建费用高达1 400亿。“XX大型体育场馆提升XX城市形象”的报道充斥坊间,需知在大型体育赛事成功举办和大型体育场馆好评如潮的背后,相关官员不同程度地获得晋升资本。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安徽省XX市为迎接省十运会兴建奥林匹克公园,随后连续举办2届“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相关领导名声鹊起,调任省委高职(虽然相关领导于2016年“落马”,但这是后话)。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不仅务实地建造了大型体育场馆,也务虚地构建了大型体育赛事。
上述目标指向导致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时间短见效快的个性化产品,官员的升迁欲望越强,个性化产品的短期性越明显。事实上,在这种残酷政治角逐的激励结构中,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机会可能采取激进的甚至是铤而走险的策略。然而,地方政府建设大型体育场馆、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诸多效应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更加重要的是,大型体育场馆的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建设成本最终还是要公共财政偿还。从资源配置的视角看,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将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公共资源提前消耗,从而扭曲了公共资源在代际之间的配置,给下一届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南昌城运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近500亿,会务费用超过1.8亿;南京全运会总投入达到1 600亿,济南全运会增加到2 000亿,打着节俭大旗的辽宁花掉了近千亿;南京奥体中心投资突破22亿,济南奥体中心投入30亿;济南国际赛马场长期闲置,南京全运会赛马场干脆改为停车场[8]。上文提及的安徽省XX市奥林匹克公园,建设之初政府投入6.7亿人民币(2002年,土地费用除外),但连续5年(2010—2014)的运营净利润只有12.91万人民币,并且,支出账目令人费解——本应该是广告收入却成为广告支出。这些尚有据可考,最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留下的是一笔糊涂账,如深圳大运会的开支账目。事实上,地方政府的目标诉求本应该是多重的——政府目标(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公众目标(提供辖区公共产品)和个人激励(获得晋升或者经济收益),并且还要考虑生产者利润、消费者剩余、社会公正、环境污染等问题,上述目标孰轻孰重?确实难以回答或者不便言说。但是,地方官员切不可为了个人目标放弃公众目标,为了自身利益牺牲公众利益,出现那种每一届领导都倾向于选择短期化行为的现象。可见,根治大型体育场馆超常规建设却不断闲置的悖论,不是中央出台文件控制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也不是体育总局压缩大型体育赛事,因为地方政府即使放弃兴建大型体育场馆也会选择其他个性化产品,谁都无法否认南京紫峰大厦观光层与南京奥体中心的相似之处,要证实这一点只需亲临门可罗雀的紫峰观光层即可感知。当然,普通地级市都星罗棋布的“广场”“中心”“商圈”与实体店面业绩的退守,也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证据。因此,构建有效的约束机制以规范、监督、修正地方政府行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1.2 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行动策略
我国自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有权力制定独立的经济目标和选择独特的发展之路,有能力确保采取一致性行动,并且,现任领导有权决定是否延续上任领导的决策。
地方政府一旦决定举办XX大型体育赛事,地方官员就会以建设大型体育场馆为突破口,迅速启动一系列配套工程,在制度、组织、资源配置等方面制定倾向性策略和采取一致性行动。在资源配置方面,地方政府动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舆论资源在项目经费、审批权、相关机构的协调等方面集中配置甚至倾向性配置,毕竟地方政府掌握土地征用、行政审批、贷款担保等关键性资源。在组织体系方面,地方政府会迅速成立“一把手”挂帅的领导结构,通常包括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在组织内部统一思想,达成一致性行动。因此,组织体系的保障和资源配置的倾斜是地方政府建设大型体育场馆的两把利剑。如广州亚运会,组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执行主席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负责总体协调工作;深圳大运会:组委会主席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执行主席黄华华,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负责大运会筹备组织工作;南京青奥会,组委会主席江苏省省长李学勇,执行主席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北京2022冬奥会,申办委员会由王安顺亲自挂帅。可见,赛事层次越高(场馆规模越大),筹备组级别越高,能够调动的资源越多。
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呈现3个特点:(1)法律至上异化为权力至上、依法行政异化为利益行政,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采取行政性一致同意原则,突破了法律框架和依法行政的羁绊,运用资源配置倾斜和组织体系保障2种工具成为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此时法律反而成为兴建大型体育场馆保驾护航的工具;(2)权力运行机制泛政治化,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是政治机制、法律机制和道德机制的共同作用,而在地方官员的业绩与晋升直接挂钩的情况下,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行已然成为定局,这种政治化倾向体现在地方政府对个性化产品的选择、投入和包装各个环节;(3)行动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地方政府承办大型体育赛事一旦获得成功,即可提升城市知名度、展示中华文化、获得国际话语权,又能够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带动房地产、旅游业、文化产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更为关键的是,存在一个以奥林匹克公园为主体的建筑群可供考证,以此获得政治业绩和晋升资格。事实上,3个特点的共同指向是,地方政府在“利剑之下”的行动通常突破制度框架和人大监督,如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的腐败事件,以及近期对体育总局官员的系列调查不可避免。可见,根治地方政府违背逻辑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现象,不仅是建立官员简历追踪问责制度——旨在对任期内地方官员行为导致的后果追踪问责,也不仅是构建多元评价机制——主要是构建以公众和媒体为代表的多元评价主体进而发挥其监督作用并形成合力,而是从顶层系统性构建约束地方政府的机制。
2 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约束机制
既然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是基于激励结构的偏好,那么约束机制是否存在?如何运行?总体而言,约束机制分为纵向与横向,纵向约束机制的核心是确保服从型的上下级关系,横向约束机制的核心是构建权力制衡体系。任何一种约束机制都必须契合现实国情,我国主要采用纵向约束机制,这必然有其合理性。
2.1 何谓约束机制
约束机制回应2个问题:(1)风险控制,即地方政府是否计算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成本-收益,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2)受众指向,即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是否符合当地民众的现实需求和真实意愿。
地方政府在“激励结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目标→地方政府行动”[20]的思路上追求地方利益和个人目标,而中央政府必须确保政治稳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既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利益矛盾,那么中央政府就必须有效约束地方政府,以确保地方政府治理目标不至于偏离中央政府意愿和违背社会公众利益,至少是不要偏离太多;同时,中央政府还要防止约束“过头”导致的地方政府“怠工”。所以说,激励结构是政府内部的契约,约束机制是政府外部的规制,激励结构与约束机制互为条件,内部激励与外部约束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两只手”。显然,只有两手协同发力,即激励与约束相容,才能确保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政府意愿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一致性。
2.2 横向制约与纵向制约:2种不同的约束机制
现代国家为了降低决策风险同时尽可能扩大受众范围,通常选择横向制衡机制,如美国在各个层级构建了充分的横向约束机制;也有部分国家选择纵向约束机制并获得成功,如日本和德国,在社会行为和公司治理层面主要依靠纵向约束机制,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约束机制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21]。
横向约束机制是指,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受到多种力量的制约——西方以地方议会为代表。按照奥茨定理,只要公共品的供给不存在规模效应,地方政府有决策权力和供给义务,但前提是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存在横向约束机制。因此,横向约束机制要把公权力横向划分,构建地方行政机构和地方议会2个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的权力机构。此外,还需具备存在市场主体、债权人、所有者和地方议会等多种约束力量;具备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消费者有“用脚投票”的权力和自由;所有者(股东)有充足的监督动力。按照西方国家的惯例,是否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由地方行政机构决策,而地方议会负责审查、批准、监督,所有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具备充足的监督动力,并且地区民众通过选举权与监督权确保2个权力机构的决策符合自身利益。极端情况下,公众能够否决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议案,如风之城的战争,事实上州政府为了投票也不会过分违背民意。可见,横向约束机制的边界条件是分治结构、均衡权利和信息对称。在我国,法律上已经明确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地方人大)有权监督地方“一府两院”,但我国地方人大是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地方人大、地方党委、地方行政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分工,而不是在利益、职责和组织上平行或者分割,如地方政府在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行动中采用“一把手”挂帅的领导结构,那么地方人大的监督职能被模糊化。同时,我国地方政府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相关性都值得商榷,加之,媒体政治化、社会公众阶层发育程度差异化、投资主体追求外部利润显性化、消费者搭便车心理普遍化,导致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横向约束机制的所有要素近乎失效。
纵向约束机制是指,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制约。如果同一层级内部缺乏对公权力的硬性约束,那么只能依靠更高级别权力主体实施监督职能,一般程序是由地方政府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和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计划报上级政府审查、批准,并监督实施,而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在多大程度上听取民意则无法硬化、无从督查。在我国,中央权威体制汇同地方政府有意排斥地区权力制衡共同导致辖区权力一元化,此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构建以中央审批制度和垂直分层的干部人事制度为核心的纵向约束机制。为何中央政府要保留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难道仅是为了应对“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18],显然,中央政府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决策不当、过度投资导致的地方财政危机和过分违背民意。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出台,明确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不救助原则;12月28日,山东省颁布《关于贯彻国发[2014]43号文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债务实行不救助原则。必须指出的是,在现有激励结构的框架下地方政府的选择是理性的,但违背了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即全社会的总产出最大化、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整激励结构的同时,需以某种形式的约束机制来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此时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是继续进行激励的边际成本等于或者即将超过其边际收益。
2.3 我国采用的约束机制
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背后是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政府这个难题,核心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就此议题,我国现有成果较多关注官员考核制度、地方政府间竞合机制、行政与财税分权制度、地区间财政转移支付等,当然这些都是中央政府治理地方政府备选集合中的一种,但本文着重探讨中央审批制。
在我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基本程序是申报、审批、执行和监督,相应的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管理权限被细化为申报权、审批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地方政府享有项目申报权和项目执行权,而中央政府拥有项目审批权和项目监督权。尽管,我国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没有最终决策权,但中央政府不会无视地方政府的诉求,恰恰相反,中央政府基于某种战略性需求,时常授意地方政府而为之,尤其是青奥会、亚运会、大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即使,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过度兴建大型体育场馆,中央政府也不会轻易否决地方政府的决策方案,而是责令发改委和建设部从技术层面审查地方政府的建设方案,再与地方政府沟通、讨论、磋商,以达成共识进而修改决策方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会尽可能说服中央政府。然而,地方政府承办大型体育赛事是存在很高风险的,其面临的首要投资风险就是兴建大型体育场馆,一旦决策失误,必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为了控制这种风险,即使是具备权力制衡关系的欧美国家也会启动纵向约束机制,即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财政补贴的方式约束州政府的决策行为[22]。
2.4 我国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中央审批制度的合理性
诚如上文所述,地方政府权力一元化是中央政府为避免地方官员以受制于地区内部权力制衡为借口推脱中央政令而有意为之的,也可以说,我国地方政府的权力一元化是中央权威结构的翻版,地方权力一元化意味着地区内部无法通过权力制衡来构建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此时,中央政府面临着潜在风险——为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买单[23],无论是动用中央财政资金还是责令国有银行追加贷款都将导致人民币超发,后果是动摇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心进而威胁社会稳定。那么,在横向约束机制失效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何以控制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投资风险?中央政府只能够以纵向的约束来确保干预地方政府的权力,以便随时纠正地方政府的行为偏离。当然,审批权同样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增加制度运行成本甚至是威胁公民基本权利。因此,审批权要具备实质性的约束力量必须“该审的审、该放的放”,如此政府行为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认可,也才会出现新一轮的政府主动放权。
转换一个视角,从激励结构与约束机制互利耦合考量中央审批制的合理性,则呈现出另一图景。官员晋升激励是一种强激励结构,正是这种强激励导致地方政府在兴建大型体育场馆过程中,刻意排斥地方人大的监督,有意消解实质性的权力制衡,进而将个人政治诉求置于地方政府公众目标之上。约束条件是随着激励结构的建立和发展不断变化的,约束机制的可靠性取决于与激励结构的匹配程度,因此激励结构与约束机制是互利耦合的。显然,如果在强激励结构下采取弱约束必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毋庸置疑,中央审批权具备“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来自体制内部而并非源于具有普世价值的法律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审批权仅是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公权力,也就产生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反复博弈的软约束现象,给权力留下运作空间。因此,才会出现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的公共财政资金可以反复追加的怪现象,甚至是只要不出现过度预算偏离和影响恶劣的腐败现象,中央政府就不会追究责任主体的行为。解决之道,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弱化激励结构,即构建多元化评价指标、搭建多中心评价主体、采取多样化评价工具,虽然这样做成本高昂,但转变唯GDP评价标准如同转变唯竞技体育评价标准一样重要;另一方面,要在优化中央审批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横向约束机制的要素,如在兴建大型体育场馆过程中引入中央政府、地方人大和第三方共同组成的评估机制,构建纵向与横向立体化的约束机制。
毋庸置疑,本文并非一味地寻找中央审批制度的合理性,笔者当然无意与中央政府“放权”政策背道而驰。当下,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简政放权,旨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而还利于民(这与本文讨论的约束机制有着本质区别)。笔者只是在我国制度背景下提出一己之忧,中央政府放弃审批制度的纵向约束,则现有的制度集合中只剩下垂直分层的干部人事制度,仅凭此,能够确保地方政府的公共责任吗?需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激励,那么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在什么程度上对什么主体负责?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厘清,中央政府是不会放弃对地方政府的纵向约束,当然也许是一种保护,即使将来地方政府兴建大型体育场馆不需要中央审批,届时,中央政府也会换一种尚不知名但强度不弱于此的约束机制。
3 结语
20余年来,中国地方政府持续上演超常规建设,却不断闲置大型体育场馆的事件。这种地方官员经验叙事的结局是违背社会公众利益和中央政府意愿,而地方政府行为背后体现出的是激励结构与约束机制的一致性或者背离度。激励与约束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没有任何一种激励/约束机制可以设计到完美地单凭激励或者约束解决所有问题。大型体育场馆能否回归理性,取决于激励结构与约束条件的互利耦合,即任何有效的激励/约束都必须与主体目标一致。显然,如果地方政府超常规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那么中央政府为避免风险外溢必然采取某种约束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大型体育场馆是地方政府内生变量与中央政府利益权衡的博弈结果。
[1]王子朴,梁金辉.“鸟巢”赛后4年运营研究:现状、问题、路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27(06):467-472.
[2]陈元欣,杨金娥,王健.体育场馆运营支持政策的现存问题、不利影响与应对策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06):24-29.
[3]王健,陈元欣,王维.中美体育场馆委托经营比较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01):1-7.
[4]易剑东.大型体育场馆赛后运营的主要理念与方法[EB/OL].http://user. qzone.qq.com/622008260#!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26589 727.
[5]郑志强.我国城市体育场(馆)公共财政问题研究[J].体育科学,2013,33(10):21-27.
[6]陈元欣,王健.体育场馆不同运营模式的税收筹划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3,28(05):208-212.
[7]谭建湘.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企业化改革的基本特征与制度设想[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22(06):480-482.
[8]董红刚,易剑东.卖方缺位:大型体育场馆困境的逻辑起点[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27(05):378-381.
[9]JEAN-LOUPC.Autonomy ofsport in Europe[M].Councilof Europe Pub⁃lishing,2011:21.
[10]CAIGER A,GARDINER S.Professional Sport in the European Union: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M].T·M·C·ASSERPRESS,2000:93.
[11]肖淑红,付群,雷厉.大型体育场馆融资模式分类及特征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5(06):14-18.
[12]董红刚,易剑东.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逻辑及其出路[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05):394-398.
[13]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
[14]周飞舟.锦标赛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9(03):54-77.
[15]乔坤元.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理论与证据[J].经济科学,2013(01):88-98.
[16]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2.
[17]NORTH D C.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J].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0,2(4):355-367.
[18]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J].社会学研究,2012(05):69-93.
[19]俞可平.政府研究的中国经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1.
[20]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1.
[21]GRIFFITH D A,MYERSM B.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strate⁃gic fit of relational norm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5(3):254-269.
[22]KOPPELL J.Political control for china’sstate-owned enterprises:les⁃sons from Americas experience with hybrid organizations[J].Gover⁃nance,2007,20(02):255-278.
[23]PENG I,WANG J.Instruments,Instrumental Purpos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st Asian Social Policies[J].Politicsand Society,2008,36(01):61-88.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RestraintM echanism sof LocalGovernment Building Large Sports Venues
ZHANGQin1,YIJiandong2,DONGHonggang1
(1.SchoolofPE,Anhui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2.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 Economics,Nanchang330013,China)
Under the existing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restraintmechanisms,the localgovernment favors in the choice personalization productobtains political benefits to divide and the promotion income,it choice to hostmajor sports events and constructing large sports venues.However,the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building large sportsvenuesoften takesa long time tobecome apparent;what ismore important is that large sportsvenuesof public goods isat leastqua⁃si-public goods properties determine its construction costswill have to repay the public financeseventually,leaving a heavy burden for the nextgovernment. Furthermore,contrary to public interestand wishesof the centralgovernment,the localgovernment reflects the consistency or the degree ofdepartureof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restraintmechanisms.At this time,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bound to control the behavio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hrough forms of re⁃straintmechanisms,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local debt crisis and excessive disobey of public opinions.In the incompleteness of transverse element con⁃straintmechanism,the centralgovernmentcan only select vertical restraintsmechanismsofexamination and approvalsystem for the representatives.Thisarti⁃cle explains the incentive structureof localgovernments’building large sportsvenues through the promotion dimensionsofofficials,and elaborates the reason⁃ability of centralexamination and approvalsystem on constructing large sportsvenues.This is to pointoutwhether large sports venues can return to rational in⁃centive depend onmutually beneficialcouplingof incentive structureand constraints.
sportsmanagement;large sportsvenues;incentive structure;utility constraint;localgovernment
G 80-05
:A
:1005-0000(2017)01-026-05
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17.01.005
2016-10-21;
2017-01-09;录用日期:2017-01-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6ZDA22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AHSKZ2015D18)
张 琴(1977-),女,安徽芜湖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治理理论、体育产业治理。
1.安徽工程大学体育学院,安徽芜湖241000;2.江西财经大学校办,江西南昌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