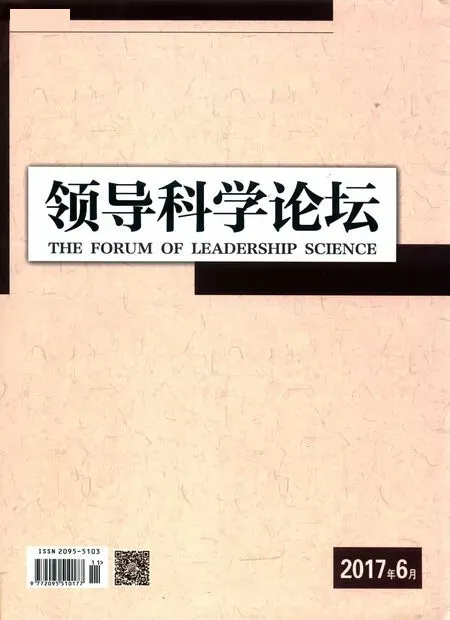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
——兼谈北宋道学
2017-11-26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立华
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
——兼谈北宋道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立华
哲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当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被动摇的时候,它要起来捍卫;当这个时代的价值根基被拔除的时候,它要起来重新为时代确立基础。每一代哲学家,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一定是源自于时代的价值危机的深化程度,价值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哲学就必须取得突破。当这种突破足以解决时代的价值问题的时候,哲学的时代任务就得以完成。
哲学使命;宋明理学;价值基础;儒家;自信
中国是有哲学的,而且中国哲学达到的深度是令人震惊的。有很多人以为中国哲学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直观、一种信念,其实不是。中国哲学是有证明和论证的,宋明理学中张载的哲学论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
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面对的问题。当然,讨论中国文化的特色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特殊论。一说起中国文化特殊论,好像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当中,别人是普遍的,而中国是个例外,这是我们不应该接受的。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是可以普遍而且应该普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谈一谈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创世神话的文明。有人会说女娲造人怎么回事?女娲造人用的原料不是她自己造的,或者说在她造人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了。而上帝创世则是创造一切,“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这种学说超出常人理解的能力。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人这么讲。中国没有创世神话,因此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从起源上就有所不同。
中国文化的根基,我认为可归结到原善论。一切都围绕一个根本的问题展开,就是此世之饱满。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里面,最为根本的是此世性格。我们没有创世神话、没有彼岸、没有末日审判、没有原罪的观念,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文明的根本文化精神是理性的、哲学的,而非宗教的、信仰的。
哲学跟宗教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宗教是相信的才能理解,哲学是理解了才能确认。所以中国哲学经典、哲学家都是在讲道理。无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甚至公孙龙子,都是在讲道理,这是中国文明的根本品格。
人和神的观念在我们的传统当中真的没有吗?以前有。比如《尚书》《诗经》里面就有。《诗经》里早期的诗歌谈到天地这样的概念时,还有人和神的意味。但是至少在三千年前,我们的人和神的信仰已经打消掉了。上帝死后的道德生活如何来安排的问题,中国文明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成功解决了。这实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这几年有很多朋友说,当下中国人的问题是信仰问题,也有人讲中国人正在走向道德沦丧,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今天的中国人有几个能达到道德沦丧的程度?类似于在外面随地吐个痰,不过是一些生活习惯不好而已,最多也就是这些年我们的道德水准有些下滑。还有人说,“道德沦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没有宗教就不可能有道德。”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难道有宗教就能带来道德?人类文明史上大部分罪恶,往往都根源于宗教。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贩卖黑奴,屠杀印第安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这一切都是那些相信上帝的人干的。显然,宗教跟道德之间没有必然关系。道德生活一定源自于根本的看待世界的理性的目光。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宗教,但是我们却依然建立起自己的道德生活,而且这种道德生活构筑了中国文明的基本品格。
二、哲学的发展基于时代的价值需求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自然科学一直在发展,哲学好像没有发展,哲学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这是为什么?
我们能看到上百亿光年以外的地方,能看到微观世界的原子甚至原子以下的结构,对人类自身的身体和心灵的了解也都加深了。在自然科学上,我们一往无前地在发展。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老子和孔子的书?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柏拉图的著作?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哲学的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
上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轴心期。轴心期几乎成了人类文明的回心之轴,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发展到轴心期,以后每一步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不断地回到轴心期的基本理论、基本思想当中去获得滋养和前行的动力。这是雅斯贝尔斯著名的论断。
轴心期这个论断很有意思。当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哲学上我们是不断往回走的,不仅中国哲学如此,西方哲学也是如此。有时候觉得西方哲学似乎是在不断地发展,中国哲学好像总是在回到原点,其实不是。读德国古典哲学像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发现他们这批人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回复,他们要回到的是古希腊哲学的高度,要回到柏拉图所达到的高度。
认识上的“轴心期”和“回复性”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希腊、柏拉图那么早的时期,人类开始以整体的目光来审视、思考世界和人生问题的时候就达到了最高的高峰呢?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自然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经验的不断扩展。但是经验无论怎么扩展,都无助于人类从根本上、整体上来审视世界人生的道理。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讲,以经验来探索世界人生的整体问题,它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早就看到了。
老子说,“为道日损,为学日益”。为道是“舍繁芜求真华”,为学是知识经验越来越“繁茂”。在老子看来,为道日损正是趋向道的途径,人们应以本明的智慧、虚静的心境,去了解外物运行的规律。如果以为学的方式,在知识经验的路上求道,会越走越远。
魏晋时期的伟大哲学家王弼,是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天才,他23岁就去世了,但是他的《老子注》《周易注》等哲学著作留了下来。王弼在解释老子的“为道日损,为学日益”时,说了一句立意非常高的话,叫“转多转离根本”,就是越多越远离根本,越多越靠近枝叶,越少越贴近根本。
孟子讲“心之官则思”,心灵的作用是思想。“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我们以为感官是沟通的,但是中国早期的哲学家却认为,感官对于心灵从整体上、根本上认识这个世界是遮蔽性的。
再进一步看,我们就了解了一个道理,当人类文明发展到开始以哲学的方式整体上看世界人生的时候,它所达到的高度其实就是人类能够达到的哲学洞见的高峰。孔子、老子,柏拉图等轴心期出现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达到了那样的高度。但是,那个思想的巅峰时代是不能复制的,那是需要有很多条件的。
第一,文明充分展开。今天社会生活的大的方面以及主要方法在那个时代都已经完整地具备,而且文化积淀也足够丰厚。
第二,时代问题空前尖锐。哲学的突破一定跟时代问题的尖锐有关。一个以思考为业、以哲学为业的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充满思想问题的时代,既是幸运又是不幸。幸运是说他面对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能有所作为;不幸是说他每一刻都得去思考,都得通过道理的探索,安顿自己人生的同时试图去安顿他人的人生。这是哲学家在一个问题空前尖锐的时代里,所要作的努力。
第三,生活世界足够简单。到底是生活世界越复杂越容易看到生活的本质,还是生活世界越简单越容易看到生活的本质,当然是后者。生活世界越复杂,构成生活的技术性环节就越多,每一个技术性环节都消耗大量的精力。等消耗得差不多了,也就不再能以整全的方式来面对生活,面对这个世界了。
哲学看似不发展,但实际上在发展。根本的哲学洞见上所达到的高度已经成为哲学的时代巅峰,后来者都是不断地回归那个高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似乎是不发展的。但是哲学又在发展,怎么发展呢?读哲学著作有一个经验,就是越早的经典似乎越容易懂,但其实这是表面的。没有比《论语》更难读的书。自以为读一遍就懂了,其实那个懂是假的,读20年以后才明白自己什么地方没懂。有人读过《论语》说孔子的思想不是哲学,那是因为他不会读。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真理。但是这真理孔子是怎么得到的?没有对世界人生最根本的认识,他怎么敢如此自信地把话说出来?他对世界人生最根本的认识是什么?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问题。读懂《论语》不易,后期的哲学著作更难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读起来特别难;读《巴门尼德斯篇》感觉更难;最初读《理想国》觉得好像挺好读的,但《理想国》最关键的部分,今天最了不起的哲学研究者,也不敢说自己真都懂了。
为什么越是晚进的书越难读?实际上,这就是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是什么?哲学的体系化程度在发展,哲学论辩的复杂程度在发展,哲学阐述的严谨程度在发展。洞见始终能够洞见,要回到那个最高的洞见,就需要在论证表述和体系化的程度上一直发展。所以,为什么越晚进、越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著作就越难读,原因是它体系化的程度、论证的严谨程度在发展。体系化程度和论证的严谨程度的发展,意味着说服力的发展。为什么说服力在发展?很简单,要说服的对象越来越麻烦。为什么越来越麻烦?时代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基本上越是早期的人越朴素。随着时代问题的深化,随着思想问题的深化,随着价值危机程度的深化,哲学的体系化程度、论证的严谨程度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因为不达到足够的体系化程度,不达到足够的论证严谨程度,就不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从而让哲学真正做到为时代的价值确立基础。
最近几年一直在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哲学的重要性在哪儿?就在于: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它守护什么?它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当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被动摇的时候,它要起来捍卫;当这个时代的价值根基被拔除的时候,它要起来重新为时代确立基础。
张载有四句话是大家都熟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归结起来就一句话,为时代立根。时代的价值基础需要哲学的努力,哲学要为这个时代确立价值基础,这是最根本的。所以,每一代哲学家,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一定是源自于时代的价值危机的深化程度,价值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哲学就必须取得突破。当这种突破足以解决时代的价值问题的时候,哲学的时代任务就得以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可以用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过程来加以概括和总结。
三、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体系形成
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末年,孔子时代的哲学。第二阶段,战国时期孟子墨子哲学,这一时期虽然与春秋末年相差不远,但是战国时代的思想风格、思想主题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第三阶段,曹魏西晋时期,主要成果是魏晋玄学时代的哲学发展。第四阶段,唐宋时期,特别重要的是两宋哲学的发展。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就是时代问题不断深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春秋末年,孔子时代的哲学。孔子面对的时代问题是什么?是礼坏乐崩和价值基础的动摇。孔子时代还有没有价值基础?有,只不过人们的价值确信已经不那么坚定了。价值基础被动摇了,但是共同的价值基础还在。所以读《论语》时会有一种感觉,孔子每说完一句话,别人就信了,不但信,而且还要照着去做。孔子跟身边人的关系是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关系。有一段特别著名的话,“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听到老师说一个道理,还没来得及去做的时候,生怕老师又说一个新的道理。孔子一生就没遇到过任何意义上真正严峻的思想挑战,他遇到的也就是个别伶牙俐齿的弟子偶尔质疑一下,比如宰我之流。
很多人读《论语》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孔子从来不用冥思苦想,似乎他一弯腰就能捡到真理,就像是一个跟真理同在的人,生活的本质对他来说是赤裸的。《论语》中的孔子,性格饱满圆润,从不需要证明自己。
尼采说“论证是一种颓废的意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不清楚。实际上,读懂了《论语》就会明白,一个人需要证明自己,他就不再饱满了。因为真正自信的人无需证明自己。孔子就是真正自信的人。他无需证明自己是因为他那个时代还有统一的价值共识,有统一的价值基础,因此孔子不用把问题说到根本上,他把问题说到某一个比较深的程度上,大家一听就知道是对的,就明白。所以《论语》里不管多重要的话都不重复,只说一遍。“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过犹不及”,这些重要的论述都只说一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关乎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在论语当中就只出现一次。
第二阶段,战国时期,孟子墨子哲学。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好辩。有一天孟子的弟子公都子说,老师您怎么这么好辩啊?孟子很无奈,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哪里是好辩,我实在是不得不辩。为什么不得不辩,因为孟子时期已到了百家争鸣的时代。百家争鸣是基于价值基础的缺失,价值基础从动摇到缺失,这一步差别巨大。意味着不再有统一的价值基础,每个人认为的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人们认为美好的生活标准也不一样了。所以《庄子》里面有一个问题,叫“故有儒墨之是非”。那时候孟子讲,“今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今天天下的思想言论不是杨朱思想的变形,就是墨翟思想的变形。杨朱、墨翟的思想是什么?“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各走一个极端。什么叫为我?极端的利己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杨朱的名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个人利己到这种程度,确属少见。
孟子好辩,墨翟则讲“兼爱”,爱所有的人。其实儒家也讲爱所有的人,但是墨家不仅讲爱所有的人,还得同等程度地爱所有的人,这一点很了不起。虽然他讲的道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他毕生努力朝向一个做不到的目标,这本身就挺伟大的。历史中记载,墨子的形象——精瘦,瘦到大腿上都没有一点肥肉。他忙忙碌碌地奔走于各国之间,帮着各个国家守城,头发都掉光了,腿上的毛都磨光了。
杨朱“一毛不拔”,墨子摩顶放踵,各追求一种生活的极端。墨子说我这样的生活才是对的,杨朱说我这样的生活才是对的。孟子说你们俩都不对,我们要爱,但是爱要有差等,只能不同等程度地爱,不能同等程度地爱。孟子、杨朱、墨子有没有统一的价值基础?没有了。没有统一的价值基础,没有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没有共同认可的美好生活,就是那个时代的问题。
读《孟子》时发现,孟子其实是论证的。孟子要不断地辩论、不断地说服,所以《孟子》的逻辑严谨程度和说服力比《论语》大得多。因为他不提供足够的说服力、足够的论证的话,他的道理就立不住。但是《孟子》规模看起来比《论语》狭隘得多,而且从整体上看,孟子的格局比孔子的格局小很多。
墨子时代,虽然价值危机已经严重了一步,不再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但有一件事是统一的,就是价值本身在那个时代没有受到质疑。大家都认可“怎么活是有区别的”,表明这个时代的价值危机还没那么严重,价值本身没有受到质疑。
第三阶段,魏晋时代玄学。魏晋时代价值危机的问题更加严重,更加深化了,它的价值危机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怎么活?这个问题几乎已经是一个现代问题了,跟我们今天的价值危机其实已经有共同之处了。魏晋时期突然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时间感和死亡观,死亡意味着什么?是取消一切差别的最根本的力量。活着的时候,不管有多大差别,在死这件事上都一样。在《列子·杨朱篇》里面,有一段体现魏晋时代思想基本倾向的话,“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活着的时候是尧舜,死了一堆烂骨头;活着的时候是桀纣,死了也是一堆烂骨头。烂骨头都一样,怎么活有什么差别呢?想想都挺绝望的。既然都这样了,那就抓紧时间及时行乐吧,反正也没区别。
魏晋这样一个深刻的虚无主义时代,却在哲学发展上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大飞跃。为什么有这个大飞跃?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哲学如果不相应地达到足够深的程度,就根本不足以解决时代价值危机问题。而且哲学要解决时代课题,不仅需要回复到哲学洞见的高度,还需要哲学论辩的程度向复杂有力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回头去看看魏晋时期王弼、郭象的哲学思想,恰好与那个时代的发展际遇相契合。
在传统中国社会,价值危机一定是哪个阶层的价值危机,而不可能存在普遍的价值危机。老百姓想的是我下一顿饭在哪儿,他没有那么多空闲去思考价值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危机实质上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危机。有意思的是,魏晋出现了价值危机,又出现了王弼、郭象这样的哲学家。随着哲学家的出现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力,魏晋时代的危机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四阶段,唐宋之际,宋明理学的发展时期。唐宋时期的价值危机更加严重了。宋明理学实际上根源于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唐儒学复兴运动,意味着儒学在复兴时代开始之前已经达到了极度的衰落,隋唐恰恰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极度衰落的时代。当时,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佛教从汉代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是在民间底层,作为一般的民间宗教之一,没有对士大夫的文化和精神世界发生真正的影响。佛教真正在士大夫中发生深刻影响是在东晋。由于开始渗入到士大夫精神世界当中,佛教的中国化过程、理论化程度就进一步地提高。到唐代的时候,佛教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
道教很有意思,道教的实践是荒谬的,但道教的问题是真实的。道教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古代哲学有个基本信念,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这是中国哲学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洞见,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的认可。既然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时间是无限的,就意味着只有追求永生,人生才有意义;而且人生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追求永生。所以,道教徒的这个问题本身是真实的。
隋唐两代国力鼎盛,文化也非常兴盛,那是一个诗歌、文学的时代,但是在道德跟思想层面,隋唐两代真的不行。唐代士大夫普遍人格分裂,时不时地就宣布“我隐居了”,他隐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朝廷发现自己。如果时间长了没人理,他就会出来,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宣布隐居。诗仙李白都没能超脱出来,他既写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又给达官贵人们写信要官做。其实大部分的“隐”都是姿态。孔子从来不隐,孟子从来不隐,庄子也不隐。
看北宋士大夫,是多么的言行一致,不管在哪儿,都有一股气撑在那儿。靠什么?人家有价值确信。南宋在蒙元铁蹄之下,那么文弱的一帮人能抗争到到十年以上。文天祥被俘后,蒙元皇帝动用南宋投降的皇帝来劝降,都不为所动,原因何在?就在于这个王朝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他有道义之勇,他有道义上的坚持,精神的力量太强悍了。
唐代士大夫是虚无主义价值观,不归于佛教,就归于道教。佛教的逻辑从根本上是要追求解脱,苦来源于执着,破除对“我”的执着和“对象”的执着,关键在于“无我”。而道教主张“我命由我不由天”。简单地说,佛教和道教的虚无主义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世界真的存在吗?我们真的活着吗?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人的行为的价值都是可以虚无化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这个时代的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深的地步,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道德生活真的建立不起来了。
面对这样的价值危机,唐代中叶开始产生一波儒学复兴运动,而儒学复兴运动的开创者就是中唐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韩愈在当时的贡献太大了,所以叫“至宋学者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帅”。研究宋学、宋代思想文化的人,一定要从中唐的韩愈开始,因为整个思想的根源在那儿。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奠基者。而当时的古文运动从属于儒学复兴运动,古文运动为儒学复兴运动找到了恰当的思想表达的风格,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文风,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文体。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虽然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但从理论建设角度看,韩愈的理论建设是远远不够充分的。从《原道》可以看出,韩愈对佛教道教的批判,主要是社会经济理由,而不是真正的哲学上的理由。他的理由非常清楚,大量人出家为僧导致劳动力锐减,这个不行。他解决佛教的方案非常简单,九个字:“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记住了这九个字,你就知道什么叫古文运动。“人其人”,让和尚们还俗;“火其书”,把他们的书都烧掉;“庐其居”,把寺庙都变成住宅,让老百姓进去生活。九个字虽然简洁,用的却是行政手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强力手段、暴力手段、强制手段。但是思想跟文化的问题,还得说道理。因此如何在道理上真正地破除佛道的影响,这是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儒学复兴运动到了北宋的时代主题。
宋朝出伟大人物。宋朝的哲学家是分几派的,除了宋明理学或者北宋道学以外,还有一支特别著名,就是苏氏蜀学。另外还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几支学派都是致力于儒学复兴。除了道学以外,其他各派都是大文学家。北宋道学家认为文学不那么重要,所以北宋道学家一般诗都写得不好。也有极个别写得好的,比如程颢的诗就写得不错,邵雍的诗也好,但是程颐、张载的诗,就不怎么样了。从整体上来看,他们在文学方面不是特别关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关心人的情感的流露,认为这些没意义。他们认为,真正的有道德的人是用道理来驾驭自己情感的人,而不是放任自己情感流露的人。
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颢、张载、程颐,是北宋五个最核心的伟大哲学家。北宋五子其实关系非常密切。“二程”是北宋五子的核心,而且两个人是亲兄弟,哥哥程颢,弟弟程颐,程颢比程颐大不到两岁;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邵雍是“二程”一辈子的朋友、终身的讲友;张载是“二程”的亲表叔,是有血缘关系的。这里面大家最熟悉的是周敦颐。一说起周敦颐,很多人脑子里闪现出那篇《爱莲说》,《爱莲说》是周敦颐年轻时候的作品。《太极图说》和《通书》才是周敦颐真正伟大的哲学著作,确实非常了不起,对朱子的思想影响都很大。
北宋五子要解决的时代的理论主题非常清楚,四个字:自立吾理。其实今天中国人要做的,中国思想家或者中国哲学家应该去做的也是自立吾理。自立吾理这一观点是程颢讲出来的。对佛教道教导致的价值危机问题,不能老是采取行政的策略,而要通过思想和理论的发展,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哲学来支撑。程颢最早明确提出了北宋道学的真正主题——“自立吾理以胜之”。要把儒家根本的道理立起来,把自己真正的体系确立起来,道理立在那儿,它就有说服力。所以要“自立吾理以胜之”。这个主题的明确提出,使得整个北宋道学有了明确的理论发展方向。
自立吾理,实际上是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为合道理的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哲学之为哲学,必须是冷静的,没有任何温情。北宋道学为什么叫道学?程颐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思想根底就是道理。他们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叫新儒学,但是从根底上来看,新儒学在那个时代是超学派的,一切合道理的都拿过来,放在自己的体系当中,这正迎合了哲学的一个主题,叫重估一切价值。没有道理的就应该把它放弃,合道理的就应该坚持,通过自立吾理,为一种合道理的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是北宋道学的主题。在这方面,北宋五子各自作出了自己的理论努力和尝试,都进行了足够的理论化的探索,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在这些理论当中,最具哲学品格的,体系化程度最高、完成程度最高的是张载的著作。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他晚年完成的《正蒙》。
我们今天讲张载,讲张载的论证,就是看他的理论建设朝向哪个方向。佛教道教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根本的虚无主义问题,世界真的存在吗?其实证明不了。但是它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世界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生活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儒家要做的理论建设的第一步是什么?理论建设特别重要的在于,一定要证明这样一个生生变化的世界是实有的;而且这个生生变化的世界不仅是实有的,还是无始无终的。只要这个世界最终一定会消亡,也就意味着你做过的一切痕迹最终都会消失,也就意味着你活着做什么努力其实在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没意义的。
中国哲学的传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无始无终的,要怎么样去证明这个世界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中国哲学家是提供了证明的。很多人说中国哲学不证明、不论证,不证明怎么叫哲学?不论证怎么叫哲学?中国哲学家只是论证得极简单,一般不超过三句话就能证明一个伟大的道理。
我们现在来分析张载怎么证明世界没有开端这件事。先说“有”,什么叫作有?什么叫存有?比如说,这个杯子上面有个盖,这就是有。为什么是有?因为它有属性,它有可以用感官认识的属性。比如,它是白色的,它的硬度、它的质量、它的温度都是它的属性。任何属性都是一个有限的肯定。我说它是白色,是个有限的肯定;但任何有限的肯定同时就意味着无限的否定。因为当我说它是白色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我说出了无限多的它不是其他什么颜色,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颜色是如此,别的属性也都是如此。所以,物体是有限的,同时它又是无限的。它既是有限的肯定同时又是无限的否定。张载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叫“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是知万物虽多,其实一物。”万物再多,其实就一物,其中道理并不难理解。比方说“我之为我”的本性,包含我跟你们所有人的差别,也就是说我跟你们的差别包含在我之内;而这个差别是无限多的差别,所以“我之为我”的本质里,包含了跟无限的万物之间的差别在其中。因此所有的万物的本质其实都包含在我的本质里。既然所有的万物的本质都包含在我的本质里,我的本质又包含在你的本质里,所以最后得出结论,万物虽多,其实一物。这已经涉及到哲学里面特别关键的问题,即有限与无限的问题,同一与差异的问题。
简单来讲,“有之为有”源自于分别,有肯定,有否定,就是有分别。有分别对应的数字是二,不能是一。如果这个世界有开端,有之前得是什么?如果有之前还是有,这个世界有开端吗?没有。有之前必须是无。《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在中国哲学导致了一个传统,就是认为世界有一个完全虚无的阶段,然后再由完全虚无的阶段过渡到有的阶段,所以这个世界就成为有开端。但问题是,有是二,是有分别的,无是一。中国哲学里无不是零,零是印度概念。中国人讲无就是无分别,没有分别就叫无,没有分别是一。所以张载在一段非常简洁的话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从“一”过渡到“二”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从无分别状态过渡到有分别状态是完全没有可能的,逻辑上都不成立。既然无分别状态是可能的,无分别状态是可以保持的,就意味着无分别状态当中没有分别的要素和力量。因为如果无分别状态中有分别的要素和力量,它直接就会体现为分别,不再是无分别。
可能有人会说,那是不是有一种分别的力量,再有一种平衡这种分别的力量,于是暂时达到某种平衡状态。
有了分别的力量,又有平衡分别的力量,请问是有分别还是没分别,不还是有分别吗?所以,从无分别的“一”过渡到有分别的“二”,这在逻辑上都不能成立。所以“有”之前,只要是“二”的状态,分别的状态,之前就永远处在分别的状态,而不可能是无分别状态。
既然我们在无分别状态,也就证明此前一直是无分别状态,这世界就没有开端,没有开端就没有终结。既然世界没有开端,就证明在我之前有无限时间。我现在提出另外一个论题,在无限时间里凡有可能的必然发生,哪怕最微小概率。极微小概率只要在无限时间里它一定会发生。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在无限时间里,没有发生的就意味着在逻辑上完全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之前无限时间里,世界从有回到无的事情发生了吗?从有回到无就是从分别态回无分别态。如果在我们之前世界已经从有的分别状态回归到了无的无分别状态,那岂不就意味着不可能有我们了?既然我们身处于其中的有分别的一个世界,那不就证明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所以世界是没有开端没有终结的。
多么简洁伟大的证明,这就是中国哲学的证明,这个证明太有意思了。中国哲学里面还有很多的非常有趣的证明,有待于大家去逐步探讨。
其实梦的问题也是如此。人在梦中,是分别状态还是无分别状态?如果是无分别状态,说明你那时候连梦都没做。人在梦中也是分别状态。人在梦中有变化没变化?有变化。变化的世界无论是醒还是梦中都是贯通的。
世界的最根本的原理在《易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只有变化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易”字含三层意思,变易、简易、不易。把这三层意思加在一块,基本的人生的原理、基本的世界的原理就出来了。这个世界最简易的道理是什么?只有变易是不易,只有变化本身是不改变的。
中国哲学把变化理解为日新的生生不已的永恒创造。世界无始无终,永远处在生生不已的状态,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证明。这个证明本身已经能够帮我们部分地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一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如果不施加外力,它将永远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我给它个作用力,施加作用力往你那边推,只改变它的方向,不改变它的速度,改变了方向之后,它就开始往你那边飞了。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通过后面的作用,让这个物体回到它原来的运动轨道上,并保持原来的速度,能做到吗?能做到。只要计算精准,物体就能回到原来的运动轨道,而且保持着原来的速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当这个物体又回了原来的轨道上,并保持原来的速度运动,能不能说我对它第一下的作用力在它此后的运动状态当中作用消失,能这么说吗?不能。我对这个事物的第一下作用,将包含在这个事物此后所有的运动和变化当中。这叫什么?这叫作用不灭。其实佛教里讲的“业”,有点接近于这个原理。佛教里面有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献叫《物不迁论》,作者是僧肇。《物不迁论》结尾讲,“如来功流万世而长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果以功业不可朽故也。”这个“功业不可朽”讲的就是作用不灭。说到这儿的时候,对于“不朽”的理解变得真实清晰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做过什么,由于世界是无始无终的,其影响会无限地延伸下去,作用会凝结在世界的相互作用和发展当中,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吗?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以《礼记》思想为基础,或者从儒家理念出发,对人生的意义加以总结,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回答或印证:活着的时候努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死了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活着是有差别的。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四、中国哲学是文化自信的依据和源泉
当今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又到了自立吾理的时代。我们要把中国人故有的世界观的道理讲明白,把中国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讲明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边界,要知道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树立在哪,从而知道我们民族的基本的品格。
中国的复兴不能忽略我们的文化根基,否则国家实力发展得再强大,但面对人家强势文化的时候,仍是喃喃低语似的自我辩解,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今天中国人的自信要真正建立起来,还需要有伟大的哲学家站出来,能真正地把道理说清楚,完成哲学的当代使命。
我们今天过分地强调包容,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明白,连自信都没有的人,怎么可能包容。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才知道从他人那里汲取什么。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哲学自信缺得太多了,以至于很多人自己刚刚说出去的话,马上又觉得没道理。
去年中国一家公司收购了澳大利亚的几家医院,收购之后在进行资产整合的时候,澳方坚持原有的运转体系,中国坚持自己的管理体系,双方冲突了很久。在这种情形下,中方代表就应该明确告诉被收购方,医院被收购的原因就在于它原来的运转体系有问题,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今天的中国人老觉得好像哪儿不对,这种状态导致的结果就是不自信,这是当代哲学要去努力解决的问题。
根据中国干部学习网录音报告整理
责任编辑:范文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