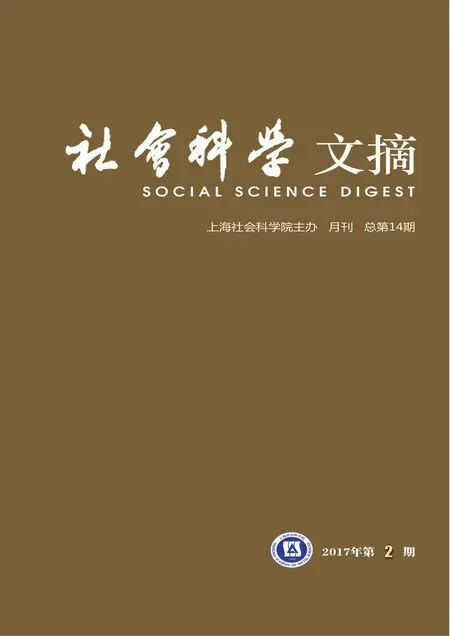二十世纪思想史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
2017-11-21陈来
文/陈来
二十世纪思想史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
文/陈来
林毓生的“创造的转化”
“创造的转化”这个概念本是美国华裔学者林毓生在 1970 年代面对“五四”时代激进的文化思潮而提出来的,他本人也曾说明他对应使用的英文为“creative transformation”。林毓生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家,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据他说,“创造的转化”这个概念,是他根据罗伯特·贝拉对“创造的改良主义”(creative reformism)的分析而提出来的。而贝拉则是受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分析的影响。林毓生最早在1971年纪念其老师殷海光的文章中提出“创造的转化”这个概念,正式提出这个概念是在 1972 年的《五四时代激烈反传统思潮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一文之中。
“创造的转化”这一概念是针对五四自由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而提出来的一种修正。林毓生把五四自由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归结为“全盘反传统主义”,他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只能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得不到任何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反而使自己成为文化失落者。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这一立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区别,他反对“发扬固有文化”“文化复兴”一类的提法,反对唐君毅等港台新儒家的文化思想,显示出他自己对这个概念的使用还是有着自由主义的印记。他还指出,一方面,“创造的转化”这个观念的内涵是重视与传统的连续性而不是全盘断裂,一方面在连续中要有转化,在转化中产生新的东西。所以新的东西与传统的关系是“辩证的连续”。
关于创造性转化这个观念的内容,林毓生多次做过明确说明,如:“简单说,是把那些这个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转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中继续保持文化认同。”他所说的符号主要指概念和语句,他所说的变迁是指以自由民主为主的社会变迁。因此,他对创造性转化概念的定义和说明可概括为三句话:一,把中国文化中的概念与价值体系加以改造;二,使得经过改造和转化的概念与价值体系变成有利于现代政治改革的种子;三,在社会变迁中保持文化的认同。其思想实质,是使社会变迁和文化认同统一起来,而不冲突;其基本方法是改造、转化传统的观念,但不是打倒传统的观念。而其局限性是,对传统观念的转化只是在“有利于自由民主”一个向度上。
这是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明显局限。林毓生认为,仅仅从西方搬来一些观念,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造成我们的危机,创造性转化是指从传统中找到有生机的质素,经过改造,与选择的西方观念价值相结合,而产生“新的东西”。比如,“性善”可以作为这样的资源,经过创造转化,变成自由民主的人性论基础。又如,“仁”在与“礼”分开后,仁成为个人的道德自主性的意义,与外在的民主法制制度进行整合。可见,他所说的变迁始终着眼在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建制。
从美国中国研究的学科史来看,林毓生的这个概念,表现出他的问题意识是与费正清时代关注中国近代“变迁与连续”的主题相一致的。而他的态度则是以自由主义的身份对五四自由主义的文化观的一种反思和调整。他认为五四的经验教训是自由主义没有处理好“传统”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提出“创造的转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态度,要求自由主义不再否定中国文化,重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从而解决变迁与认同的冲突,使二者都能得到肯定。从 1970 年代至今,他对五四自由主义的文化观的批评和对文化认同重要性的补充,已得到不少自由知识分子的赞同。
虽然,“创造的转化”本是自由主义内部在文化上的调整,要求自由主义把五四对传统的“全盘否定”改变为“创造的转化”,但林毓生自己后来也把它的应用作了扩大,使它不仅是对自由主义的要求,也希望使之成为一般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各界的人士广泛积极地利用“创造的转化”这一观念形式,抽象地继承这一观念形式,但是,如果从我们今天对文化传统继承的立场来看,林毓生对“创造的转化”的具体理解,仍有很大局限性,这也是需要指出的。这主要是:第一,这一观念没有表达“继承”的意识,甚至和“弘扬”相对立,这样的立场不可能成为全面的文化立场,如果林毓生把他的观念概括为“辩证的连续”“创造的转化”两句会更好。第二,转化的方向只是有利于与自由民主的结合,完全没有考虑与现代社会道德、伦理秩序、心灵安顿、精神提升、社会平衡的需要结合,这种转化就不能不是单一的、片面的。
墨子刻以“调适”批评“转化”
与林毓生同时代的美国中国学家墨子刻,从一开始就对林毓生的“创造的转化”的观念提出异议,他从英文的语感出发,认为 transformation(转化)含有革命和根本改变的意思,而应当重视改良、调适(accommodation)。所以他提出了transformation vs. accommodation(“转化/调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框架。他认为,中国近代历史中的革命派属于转化性,改良派属于调适型,前者主张激烈转化,后者主张逐渐调适,而民国初年以来革命派代表的转化方向一直居于思想上的优势地位,他甚至称五四思想为转化思想。不过,“转化/调适”这一框架更多地是来处理革命和改良的分别,并不像林毓生的“创造的转化”观念是专对思想文化的激进化倾向而发。墨子刻的学生黄克武在《一个被放弃的选择》中运用了这一框架对梁启超作了新的研究。
在墨子刻看来,“转化”是根本改变,是在性质上发生变化,属于革命派思维;这与改良、调整的观念不同,故墨子刻用 accommodation(调适)来说明与革命思维不同的改良方针。在中文中,“转化”虽然不一定有革命式的决裂意义,但确实没有渐渐改良的意思,而有一种从方向上转换的意思。林毓生自身的立场并不是主张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创造性转化观念的提出正是针对思想革命而提出来的。所以墨子刻对这个概念的反对并不能针对林毓生的思想。但墨子刻提出“转化”这个概念是不是过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由于墨子刻对“转化”与“调适”的分别,主要用于政治思想史的主张,而不是文化态度,所以这里不再多加讨论。
傅伟勋的“创造的发展”
与林毓生等不同,1980 年代初,傅伟勋由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而提出“创造的诠释学”的方法论。其创造的诠释学应用于文化传承发展,是“站在传统主义的保守立场与反传统主义的冒进立场之间采取中道,主张思想文化传统的继往开来”。他强调,继往就是“批判的继承”,开来就是“创造的发展”,所以他的文化口号是“批判的继承,创造的发展”。这个口号较林毓生的单一口号“创造的转化”要合理,可惜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和推广。尤其是,傅伟勋与林毓生不同,不是只从政治改革着眼,而是面对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重建发展,其文化的视野和对应面本来就更为广泛。而且,“创造的发展”这一观念,比起“创造的转化”,也没有墨子刻对“转化”所提出的可能毛病。在该口号中,“批判的继承”应是取自20世纪50 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待传统文化的普遍提法,而“创造的发展”是傅伟勋自己基于其创造的诠释学所引发出来的。其中还特别关注当代人与古典文本的“创造性对话”,以体现“相互主体性”。由于他的诠释主张基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也曾被他应用于道家和佛教的典籍文本的解读,经过深思、实践而自得,故比较有系统性。当然,由于他的这一主张更具体化为五个层次的诠释阶段,往往被认为主要是针对思想文化文本的诠释而言,容易忽略了“批判的继承,创造的发展”具有的文化主张的意义。
应该说,就观念的历史而言,傅伟勋的“创造的发展”为我们今天提出“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基础。就其创造的诠释学的五个步骤而言,即“原典作者实际说了什么”、“原典作者说的意思是什么”、“原典作者所说可能蕴涵的是什么”、“原典作者应当说出什么”、“原典作者今天必须说出什么”,他强调“应当说出什么”的层次就是“批判的继承”,“必须说出什么”的层次就是“创造的发展”。这些说法对古代文化的“创造的诠释”提供了具体的途径,从而也就如何面对古代经典文本进行“批判的继承、创造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法。但其中“批判的继承”是我们 50 年代的口号,不能不含有批判优先于继承的意义,今天应该予以调整。
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
李泽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也提出一个口号“转换性创造”,很明显这是从林毓生的提法变化出来的。李泽厚所说“重复五四那种激烈的批判和全盘西化就能解决问题吗?我们今天的确要继承五四,但不能重复五四或停留在五四的水平上。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如此。不是像五四那样扔弃传统,而是要使传统作某种转换性的创造”,这说明他的提法也是针对五四文化观念而发,其出发点与林毓生也有一致之处。而且,李泽厚在使用“转换性创造”时很强调革新和批判,如他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转换的创造:一个是社会体制结构方面的,吸收近代西方民主、人权,重视个体的权益和要求,重视个性的自由、独立、平等,发挥个体的自动性、创造性,使之不再只是某种驯服的工具和被动的螺钉,并进而彻底消解传统在这方面的强大惰性。第二个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方面,要真正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某些东西,来进一步改造学校教育、社会观念和民俗风尚,以使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也进行转换性的创造。这实际讲的是两个方面的“转换”,其目的是“转换传统”。他说“在对传统中封建主义内容的否定和批判中,来承接这传统心理,这就正是对传统进行转换的创造”。所谓在对传统的批判中承接传统,并认为这就是转换性创造,其实就是以往所说的“批判的继承”。他认为传统只有先得到批判、改造、转换,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承继和发扬。就具体内容而言,他所说的可以承继发扬的是指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道德主义、直觉体悟、人际关怀。
从文化继承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总起来看,历史的解释者自身应站在现时代的基地上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突破陈旧传统的束缚,搬进来或创造出新的语言、词汇、概念、思维模式、表达方法、怀疑精神、批判态度,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去继承、解释、批判和发展传统。他的这种强调破旧出新、怀疑批判的继承发展传统的说法,还是“批判的继承”的思想,强调以批判为前提。他主张“改变、转换既不是全盘继承传统,也不是全盘扔弃。而是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转换性创造”本来的重点应该落在创造上,但李泽厚在这些地方讲的重点都是改换,不是创造,实际是“创造的转化”。所以学术界和知识界都没有对李泽厚的这一概念产生兴趣。
20世纪90年代以后,李泽厚的讲法有所变化,使得“转换性创造”不再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而是对中国道路的一种设想,用以表达其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西体中用”的主张,成为其对“中用”的解释方式,即强调在实践中把中国文化的精华融入于中国现代性的体制建构之中。于是他自觉地把重点从“转换”变为“创造”,强调在“用体”(体即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中创造新形式。他说:“中国至今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许多年。我以为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建设性地创造出现代化在中国各种必须的形式。关键在于创造形式。为此,我提出‘转换性的创造’。这词语来自林毓生教授提出的‘创造性的转换’,我把它倒了过来。为什么倒过来?我以为尽管林毓生教授的原意不一定如此,但‘创造性转换’这词语容易被理解为以某种西方既定的形式、模态、标准、准绳来作为中国现代化前进时的方向。”“我们不能仅仅是接受,转换一下,把西方东西拿过来,使自己的传统作某种转换是远远不够的;我说‘转换性的创造’,强调的是创造。这种创造带有转换性,但重点在新形式新内容的建立。我称之为转换性创造,这种创造不是把原来的东西都打掉,而是就在现有的社会政治基础上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模仿,不是克隆港台,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中国‘用’西方的体,会创造出新形式。从而这个体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那个体了。”这是李泽厚后来讲的“转换性创造”的意义,是要解决怎么“用”的问题。但他也说,重要的是创造,但这创造又是一种转换性的创造,而不能脱离了传统的根本精神。
当代中国文化政策中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来有关中华优秀文化的讲话在国内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个提法就是“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有关传统文化的讲话充分综合了党在历史上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方针,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学术界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加以发展创新,提出了“两有”“两相”“两创”的方针。“两有”即对古代的文化要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两相”即中华优秀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即对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有”是讲继承的区别原则,“两相”是讲继承的实践要求,“两创”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讲话在这些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是对党以往的文化方针的新发展。当然这不意味着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来说,有关继承的理论难题都已经解决,事实上在继承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人停留在以批判为主的思维,需要加以转变;而是说,面对今天治国理政的复杂实践需求,今后的关注应当更多地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集中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提出“两创”的基本前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的价值追求,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道德、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建立合理关系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利用、扩充、改造和创造性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我们所说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发展其现代表达形式,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摘自《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