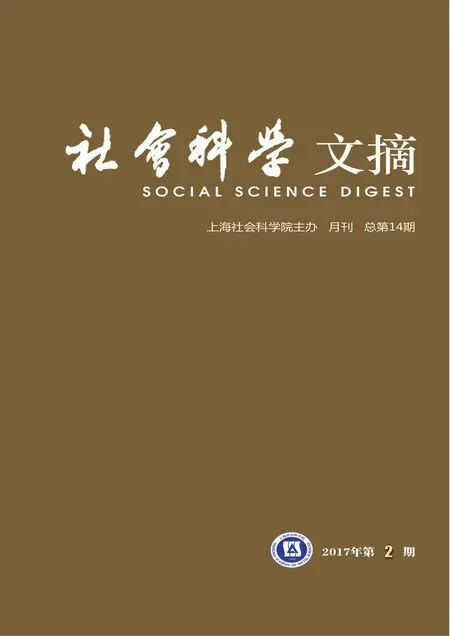“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1950年代美国反共宣传
2017-11-21翟韬
文/翟韬
“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1950年代美国反共宣传
文/翟韬
近年来美国文化冷战研究、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史(又称“公共外交史”)的研究非常热门,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美国政府动员和利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诸如报刊、电影、音乐舞蹈、运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国际公关活动。其中利用文学形式开展对外宣传的活动也渐渐为学界所注意,相关研究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在乔治·奥威尔小说《动物农场》、《一九八四》的翻译、传播、影视改编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真相运动”中美国情报部门策划动员苏联东欧流亡者撰写文学传记小说的活动,美国情报机构和在其欧洲的隐蔽广播“自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动员、利用、传播苏东的“地下文学”的活动等。较为综合性的研究也已经出现,它们观照美国政府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动员和操纵国内外(文学)图书出版界、以服务于美国外交和政治目的政策与活动。本文则尝试把美国利用汉语小说进行反共宣传这一做法的过程完整呈现出来:梳理政策形成情况、描述文本生产过程、分析文本内容,把历史研究缺乏的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缺乏的历史情境研究结合起来。
大陆赴港“流亡者”与美国的反共宣传政策
美国炮制的反共中文文学项目,源于对其针对苏联东欧的“文学冷战”的相关活动。从冷战爆发到1950年代中期,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的是“解放战略”,即通过宣传和心理战发动苏联和东欧人民群众来颠覆、瓦解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体制。杜鲁门时期美国对外宣传最高决策机构心理战略委员会之下有两大项目来具体实施解放战略,一是策反苏联东欧民众的“叛逃者项目”,一是促进苏东人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意识形态战,具体说来是“学说项目”。而“叛逃者项目”和意识形态战是有交叉的,且越来越靠书籍这一媒介结合在了一起:利用叛逃者个人传记文学的形式来进行意识形态心理战,这种媒介形式被学者称为“冷战自传文学”。
冷战前期,为了消除“红色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并配合美国的亚洲冷战战略,美国在大中华区(尤以东南亚华人为主要目标)展开了浩大的心理战和宣传运动。这场反中共的心理战和宣传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以香港为中心展开的。香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传媒资源成为了美国依仗的心理战和文化宣传活动中心。在其中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都扮演了绝对重要的角色。“流亡者”不仅把关于新中国的丰富信息和情报带到香港,而且与美国在港支持的反共组织和传媒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重要的是,香港之所以拥有丰富和雄厚的传媒、文化资源与人才,主要就是由于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的缘故,1950年代香港的传媒业和文化界主要是由大陆赴港移民群体构成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冷战前期美国的反中共宣传运动就是依托香港这座城市的诸多资源、尤其是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开展的,因而关注香港“流亡者”群体,便是抓住了美国反中共宣传运动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从事传媒行业和其他文化行业、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大陆来港“流亡者”,成为了美国驻香港宣传机构——香港美国新闻处汉语宣传材料最主要的稿件和素材来源。美新处在香港遍寻中文作家、编辑、翻译、新闻记者等合适的人选,来进行符合美国宣传目标的创作、编辑和翻译等工作。这对于生活普遍比较窘迫、没有特别稳定的收入来源的“流亡”知识分子来说,是个难得的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美新处主办和资助的各种反共宣传媒介的外围形成一支庞大的“流亡者”媒体人队伍,他们是美国在1950年代的反中共宣传活动的“主力部队”。
反共小说的生产和发行机制
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的十年之间内,美国驻港宣传站点逐渐形成了以书刊纸媒为重点的两大宣传项目:一是以《今日世界》为代表的多份中文刊物,一是包括翻译书籍、原创书籍等在内的“书籍项目”。
书籍项目中以反共小说最有特点。香港美新处自1953年开始策划“反共小说”。美新处评估到,当时很多华侨青年非常反感简单粗暴的反中共宣传作品,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反驳的著作也没多大兴趣。针对这种情况,美新处打算采取一种更加隐蔽和轻松的方式进行反共宣传。美新处官员打算重点开发反共小说,这类作品“通过把个体人物在不同阶段的经历编成小说(fictionalized)、但同时又是写实性的叙述和描写,来达到反共的目的。”当时还没有中国作家专门从事反共小说创作,美新处积极寻找这方面的作家把其作品推销到东南亚市场上去。
于是在美国新闻处的精心挑选和组织之下,一批鲜明的反中共题材小说作品被“创作”了出来。其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正是蜚声世界文坛的华裔女作家张爱玲和她的两部反共小说《秧歌》及《赤地之恋》。除了反共小说之外,香港美新处还策划、创作、编译了一批具有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色彩的反共作品,大部分是以在大陆亲历“苦难”和逃亡为题材,其中以刘绍唐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为代表,该作品被美新处译为16种文字销售散发到世界各地。以反共小说和反共纪实文学为代表的反共文学作品渐渐成为美新处极为倚重的一种宣传媒介,逐渐成为原创类书籍的主要形式。
原创中文书籍的发行环节也是比较巧妙的。美新处主要通过商业出版社签订合约的方式出版发行:美新处每一次想要出版图书,不仅免费给某商业出版社该书的版权,而且还不用该出版社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策划和采、编、译,且发行销售环节还有保障,因为美新处会以成本价收购所有书籍;而且出版社还有进一步获利的可能,美新处策划出版的书籍如果由出版社操作真正进入商业流通领域,所获得的额外销售所得会全部归出版社所有。因而一个常见的现象是,美新处不再回购某书籍之后,该书籍还能继续发行、销售、赚钱。如美新处曾在1955年开发过《故事画报》,制作发行即采取上述机制。1961年准备放弃该媒介。美新处认为出版社就不会再继续出版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却惊喜地发现《故事画报》没有消失,仍以较小的版面在香港和台湾市面上继续出版、销售和流通。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样运作的好处非常多,很愿意合作。这几乎是只赚不赔的买卖,最低限度也就是免费获得一本书的版权,没什么可损失的。对于美国宣传部门来说,其实好处更大,这有些类似变相的“资助出版”。尽管政治力量在商业传媒背后扮演了推动力作用,但不是单纯的资助,而是“授之以渔”,尽最大可能性使每一本书籍成为“纯粹”的书籍商品。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隐蔽宣传手段,是在把宣传品“洗白”、包装成为文学商品。
对小说主题和情节的文化分析
在大陆赴港“流亡者”反共小说中,有两类主题最为普遍,一是“青年对革命的幻灭”的“醒悟体”,二是“逃离铁幕、奔向自由”的“流亡体”。
(一)“醒悟体”小说
在众多“醒悟体”反共小说中,最普遍的一类情节是革命青年由于自身受到政治运动冲击和目睹了新中国政权的种种“黑暗内幕”之后放弃革命信仰。
“醒悟体”小说情节很多样、传达着多种“反革命”道理,但这些小说的共同点可能更加耐人寻味。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毫无例外地都是青少年,而小说情节几乎都是在重复这些青年对革命的产生幻灭感,最后“告别革命”的程式。这与美国在大中华区的宣传对象和目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东南亚华侨青年群体(甚至整个大中华区的青年学生群体),一直都是美国在亚洲宣传的重点之一。反共小说这个宣传手段的出台更是直接和对华侨青年的反共宣传目标有关。在美国对华人青年进行冷战宣传这个大背景下解读以上反共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心理战和宣传题图,可以说是精准地为美国宣传政策量身定做的材料。
这种小说情节的设置,除了反映出政策意图之外,更饶有意味地反映了美国精英看待革命的深层次文化心理。大体而言,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政学两界——对外宣传官员乃至外交精英和社会科学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家群体——有一套高度一致的对革命和革命者的观念、且多以社会科学话语形式表达:革命者多是没有社会关爱和家庭关爱的边缘人群,参加革命是为了克服严重的焦虑和空虚等精神病症。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寄托,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陷入了对自身政治身份迷茫不安的“认同危机”之中,于是加入共产党想要寻求秩序感和归属感。总之,这种观念把革命者视为地位边缘、缺少社会关爱的精神病人。
我们看到“醒悟体”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孤儿,这种人物身份的设置正是典型地反映了上述美国宣传官员对待革命和革命者“社会病理”诊断。《赤地之恋》中的叶占奎、康悌、《出笼鸟》中的陆素绫、《仇恨》中的云峰等等都是孤儿,即这些曾经笃信革命、坚定的共产党员都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的人群。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小说的结局也恰是上述“理论”为“精神病患者”开出的“药方”。上述主人公的一个主要的结局就是最终回归家庭和社会,革命者“回家”的结局颇为符合社会科学家的“社会病理”诊断思路: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爱可以提供秩序和归属感,是替代革命和党组织“医治”革命者孤独不安的精神病症的归宿。
(二)“流亡体”小说
由于香港的传媒业和文化教育界主要由流亡知识分子组成,所以由香港美新处请其捉刀的作品,多是以他们在大陆生活的经历、逃亡过程和到港后的流亡生活为题材。因而“逃离铁幕、投奔自由”的“流亡体”小说,是美国在大中华区炮制的反共文学作品群体中最“主流”题目。香港美新处采取各种手段挖掘和宣传流亡者“逃离铁幕、奔向自由”的题目。美新处认为这种“我在场”、“发生在我身上”个人亲历式的逃亡经历,在大中华区尤其在东南亚华人中是非常有效的宣传素材。美新处把这些素材制作成广播节目,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播放。站点还邀请“流亡者”去海外演讲,甚至还组织大陆“流亡者”去东南亚华人学校从事教学活动。相关信息也被整理成英文提供给东亚以外的美国宣传站点,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大陆“流亡者”的话题。
香港美新处最经常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流亡者素材编辑成平面媒体材料,多以新闻报道、纪实文学、个人自传、小说等形式面世,美新处采取各种手段把这些媒体材料在报纸、杂志上刊载,或是单独以书籍、画报和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由于“逃亡”的主题带有极为明显的个人亲历特点,又多有复杂曲折的情节和较强的故事性,所以最经常被改编和创作为纪实文学与小说的形式,这构成了美国在港炮制的反共文学的主体部分。纪实类流亡文学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叙述,情节比较程式化,主要是三段式:在大陆的悲惨遭遇、逃亡经历、“点题”的结尾,往往是“我终于到达了自由世界”、“我终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之类的结语。题目也多是“我从××来”、“我××(如何)投向自由”。
当然,不仅是铺陈逃亡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把“流亡”这一行为赋予在冷战双方中做出选择的象征意义。在反共文学(也是所有的宣传材料)中,美国宣传部门把香港建构为“东方西柏林”、“自由灯塔”的象征,将流亡行为赋予浓厚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在这里,流亡者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心理恐慌等原因逃亡香港的行为,被赋予高度政治化的解读:是在冷战中“用脚投票的义举”,是一种“逃离铁幕、奔向自由”的行为,是人民在“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正式选择的象征性举动。
美国宣传部门还在把难民赴港建构为一种类似宗教朝圣般的举动。反共小说中描写了很多“生死逃亡”的细节,着墨最多的就是对流亡者“奔向自由”“虔诚”心情的描写。以上这些描写带有一定的宗教意味,甚至美国宣传部门也不避讳把“逃亡潮”说成是“一件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大事,”这是“《圣经》上出埃及记的重演,”也是“一首悲壮的史诗。”美国宣传官员之所以把大陆人流亡香港赋予高度意识形态化色彩,甚至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恐怕是因为美国人把对自身起源的神话和对自我身份的想象投射到了“流亡香港”这个冷战事件中。美国人把祖先从欧洲移民新大陆的历史建构为一种“宗教流亡”的历程,他们“将新英格兰视为上帝为人类准备的一个特殊避难所”。在冷战的高潮时代,当美国人执着地用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想象着冷战的时候,也把西柏林和香港想象成是为爱好自由的人们准备的一个“特殊避难所”,是反抗专制与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涌入西柏林的德国人和涌入香港的大陆人,和心向新耶路撒冷“应许之地”的美国祖先朝圣者一样,也是一群心向自由、虔诚坚贞的“义士”。
结语
美国宣传机构对华“文学冷战”拥有一定的宣传效果。一方面,反共文学作品发行量大,散播范围广,可以大体判断阅读人群数量较多、受众面较宽。另一方面,从中国大陆所见一些史料来看,美国在香港制作的反共文学作品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进中国大陆甚至东南亚。这种效果很大程度上和小说独特的优势有关。比起文化冷战常采取的其他形式如音乐、舞蹈、体育、博览会、教育交流等,文学和小说、尤其是个人传记这一小说形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宣传媒介。其突出特点是可以给读者提供一种“个人亲历性”,通过文学语言和生活情境,小说可以迅速把读者带入作品的内部世界中去,使读者“亲历”作者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密切相关的进程:一是把政治话题“人性化”,即把反共和亲西方的立场与信息通过个人经历、人类情感和曲折情节传达和呈现出来;二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即把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话题简单地和集中体现在个人经历变故之后的思想斗争和人生选择上。这样就把文学传记和政治意识形态渗透这两个本不太相关的事物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所谓的“反共意识形态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of Anti-communist Ideology)。搞清这个本质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对华宣传的技巧。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摘自《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