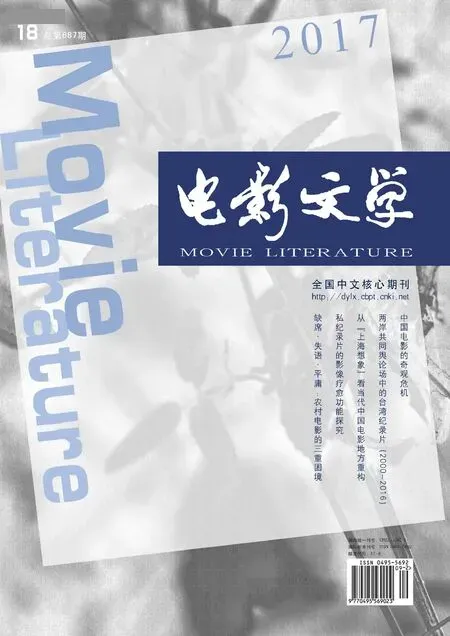中国电影中的癫狂形象研究
2017-11-15冯莉莉
冯莉莉
(河北中医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200)
一、引 言
在中外古典著作中,便存在关于疯癫、痴狂的论述,在中国东汉时期的文论著作《说文解字》中,就有关于疯和癫的释义,即“狂”;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将疯和癫释义为狂暴、凶狠和邪恶,可见在人类古典文明时期,将疯和癫划归为一种病态,而疯癫者也被置于隔离或者边缘的地位。[1]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疯癫这一普遍的现象,在病理层面的研究之外,还将疯癫置于精神层面进行探讨,引入了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认为疯癫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问题,而是人类历史和社会文明的产物,换言之,一些不符合理性价值观的思想与行为都可能会被划归为疯癫。[2]总的来说,人们对于疯癫的定义都离不开非理性,在非理性的指引下,疯癫者的外在形象、内在性格及行为举止都有异于常人,这使他们一直游离在社会主流生活之外,成为一类特殊的存在。
随着对于疯癫问题的理论研究的深入,文艺领域也开始关注疯癫并从其中挖掘更深刻的内涵,就电影艺术领域而言,疯癫者往往承载着丰富的表意作用,在看似玩笑的疯癫外在表现形式下是一重重深刻的隐喻内涵。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逐渐脱离了传统刻板的叙事模式,也不再受制于红色叙事的约束,开始探寻更为丰富的表意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癫狂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中国影坛之上。纵观中国电影中的癫狂形象,不难发现此类人物形象虽形态各异,但均指向了“反思”,其中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有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反思,也有关于人性和民族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或是通过人物形象癫狂化的过程进行阐释,或是通过预设癫狂形象并赋予其隐喻价值得以实现,而这些站在理性对立面的癫狂者的悲剧也成为一面反思历史、反思文化、反思人性的“照妖镜”。[3]本文将以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为研究范围,重点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和王秋赦、《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有话好好说》中的赵小帅、《鬼子来了》中的疯老头及《驴得水》中的张一曼为研究对象,围绕反思这一核心价值,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中的癫狂形象进行研究。
二、历史反思中的癫狂形象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封建社会延续了数千年,在20世纪初,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覆灭,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崭新的生活,而是军阀割据和殖民侵略,战争的硝烟在中华大地上盘旋了半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才成为自己的主人。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的十年“文革”再次将人们推向了生存的困顿之中,可以说自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几乎一直处于动荡和蜕变的阵痛之中,而新时期以来的电影也聚焦这一风云骤变的年代,依托一些生活在落后文化或高压政治桎梏中的癫狂形象言说着伤痛,进行着历史的反思。
在根据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而成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就塑造了一位在封建思想桎梏中的“疯女人”形象颂莲。颂莲原本是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在继母的排挤下被迫嫁入陈家成为四姨太,从最初对这段封建婚姻的不屑到不择手段地争宠再到失宠后的癫狂,颂莲没有逃出封建桎梏下女性的依附地位。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老爷这个甚至很少正面出现的人物形象无疑是整个陈家的权威,在锤脚、点灯、灭灯、封灯的制度下,姨太太们都无可选择地成为陈老爷的依附者,大太太因年老色衰而无奈地忍受着老爷不断纳妾的行为,依靠所谓的贤良和宽容维护着在陈家岌岌可危的正室地位;二太太凭借着过人的隐忍和狡诈的心思周旋在老爷和其他太太之间,并在害死三姨太、逼疯四姨太后成功上位;三姨太因美貌过人而颇受老爷怜爱,但最终却在私情暴露后被老爷刺死;而四姨太颂莲则在经见了大姨太的无奈、二姨太的狡诈和三姨太的惨死后逐渐走向癫狂,最终被老爷封灯,彻底失去了争宠的可能,从陈家太太沦为游走在大院里的疯子。整部影片呈现了颂莲走向癫狂的过程,这一过程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自立自强的女性堕落成为封建社会男权制度下的他者,而癫狂的颂莲也代表着成为封建礼教“祭品”的千万女性。
同样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芙蓉镇》讲述了“文革”等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影片中勤恳致富的男主人公秦书田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而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王秋赦却成为运动中的权力人物。运动中,曾为文化馆馆长的秦书田变成了“秦癫子”;运动后,曾经叱咤风云的王秋赦走向癫狂。在被批斗的日子中,秦书田常常以呆傻的形象示人,并企图躲避更大的灾难,被称为“秦癫子”的他经常说自己亦人亦鬼,唱着包括爱人胡玉音都无法理解的人鬼之歌,还在被捕入狱前对胡玉音说“像疯子一样活下去”,这些看似异于常人的言说事实上却蕴含了对特定时代个体命运的嘲讽,带来了人何为鬼的反思。影片中一直致力于批斗秦书田和胡玉音的王秋赦大张旗鼓地投身政治运动,在运动中极尽媚颜之态,这个曾经被众人所唾弃的懒汉在政治运动中成为一个性情卑劣的小丑式角色。然而在政治运动的风波过境后,人们的生活恢复常态,如王秋赦一般的小丑也彻底失去了立足的空间,在巨大的落差和更为落魄的处境中走向癫狂,成为一个天天叫喊着“运动啦”的疯子。在许多新时期的影片中,有许多书写“文革”伤痕、进行“文革”反思的作品,《芙蓉镇》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通过塑造秦书田这个亦人亦鬼的“秦癫子”形象和王秋赦真正走向癫狂的人物形象对“文革”于个体的异化进行批判和反思。[4]
三、社会反思中的癫狂形象
在上文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在现代社会文明中,疯癫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极端代表,但理性与非理性的定义却源自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而不符合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之上,这些主流文化中的异类在长期备感压迫的文化氛围中逐渐走向癫狂。著名影片《霸王别姬》上映于1993年,改编自李碧华创作的同名小说,由陈凯歌执导,张国荣、张丰毅领衔主演,讲述了京剧名伶程蝶衣和段小楼延续半个世纪的舞台上下的故事,这部影片曾一度打破中国文艺片的美国票房纪录,并荣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金棕榈奖。《霸王别姬》讲述了主人公程蝶衣从学徒小豆子到成为舞台名伶过程中对于戏的痴迷及对于师兄的痴迷。事实上,在深爱师兄的数十载中,这种同性之恋不仅不被世俗所容,也不被其师兄段小楼所接纳,最终在绝望和压制之下,程蝶衣在“霸王别姬”的演绎中自刎于台上,用癫狂的死控诉着自己关于“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的错位一生。在小豆子初入戏班时学习旦角,因经常唱错“男儿郎”和“女娇娥”的唱词而遭到打骂,终于在师兄段小楼将烟袋插入他嘴里后,流着鲜血的小豆子唱出了正确的唱词“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这也意味着小豆子放弃男性身份的开始。在经历了痛苦的学艺过程后,程蝶衣凭借在“霸王别姬”中对虞姬的出色演绎而逐渐成为京剧名伶,观众所喜欢的正是程蝶衣在男儿躯壳下的娇娥之态,这进一步强化了程蝶衣的女性意识,同时对于师兄段小楼的情有独钟也使程蝶衣一直沉浸在“霸王别姬”的角色设定和剧情之中,不愿自拔。事实上,程蝶衣并不是天生的“女娇娥”,而是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成为满足观众观看欲望的虞姬;同时,当程蝶衣以“女娇娥”的身份追寻爱情时,却又遭遇了主流观念无情的唾弃与打压,成为一个性别身份缺失的边缘人,在这种夹缝生存的状态下,程蝶衣变成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癫狂者,并通过极端癫狂的自刎行为杀死了戏中的虞姬,即心中的“女娇娥”,实现自夹缝生活的解脱。
影片《有话好好说》由张艺谋执导,姜文等人主演,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诞却又值得反思的故事。影片男主人公赵小帅在被女友抛弃后,决心找到女友的现任男友刘老板探个究竟,却不料被财大气粗的刘老板叫人打了一顿,情急之下,赵小帅抢过身边张先生的背包以自保,但打斗却使背包中的电脑彻底损坏,为了讨要说法并得到赔偿,赵小帅和张先生“一武一文”来到刘老板的公司。在与刘老板交涉的过程中,冲动的赵小帅执意砍下刘老板的手来发泄愤懑,而文质彬彬的张先生也因极力劝说赵小帅而被其绑在了椅子上,就在争执的过程中,店内的厨师以为张先生是个疯子,并对张先生百般折磨,竟然真的将张先生变成了“疯子”。面对势大欺人的刘老板,赵小帅和张先生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实现诉求,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疯狂砍人的“疯子”和一个被戏弄变癫的“疯子”,这无疑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也是对社会文明的反思。
四、人性反思中的癫狂形象
对于人性光辉和阴暗的呈现及反思一直是电影艺术的核心价值之一,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影坛上也出现了许多呈现人性的作品,而其中的癫狂形象自然成为传递反思价值的重要载体。在上映于2000年的影片《鬼子来了》中,有一个经常大声叫骂的疯老头形象,他看似毫无逻辑的叫骂却是正确之择,而村民们看似理智的选择却最终惹来了杀身之祸。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挂甲台村出现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个受伤的日本军官和他的中文翻译,面对如何处置这两个几乎没有反抗能力的敌人,村民们并没有显示出民族的气节,而是纷纷担心杀死日本军人后村子将惹上麻烦,而此时的疯老头却疯疯癫癫地躺在床上大喊“杀了他”。在村民的胆小懦弱和翻译官的小聪明中,日本军人花屋小三郎已经在村中生活了半年之久,甚至与马大三等村民建立了较为和谐的关系,为了感激村民们的不杀之恩,花屋小三郎提出让村民将自己送到宪兵队并交换粮食,对此马大三等人又开始了激烈的商议。商议中,疯老头还是疯疯癫癫地叫骂众人是“王八羔子”,然而疯老头的叫骂却从未引起村民们的重视。经过几番商议,村民用花屋小三郎换取了粮食,却在不久之后在日军全面溃败前的最后疯狂中遭遇了屠村之劫,在看似理性而实则懦弱而贪婪的人性中,挂甲台村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疯老头看似疯癫却实则清醒的形象凝聚了讽刺之力和反思之意。
2016年,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话剧的《驴得水》在全国上映,这部没有业界大腕出演的影片却在全国引发了观影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影片带给观众令人悲怆的人性反思,影片以民国时期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发生在山村学校的一段令人初看发笑,细观流泪的故事。为了维持学校的教学,校长和几位老师在干旱缺水的情况下将一头驴子虚报为教英语的老师,以此来获得老师的费用贴补学校开销。然而在一次教育部检查中,特派员为了得到美国人的捐款而将这位驴得水老师塑造成了扎根边疆的教育家,在这个巨大的骗局中,特派员和学校老师开始不断编织新的谎言来维持骗局,同时贪婪、虚伪、自私、狭隘的人性也逐一展露。在几位老师中,女教师张一曼看似放荡,却在每次谎言中都选择了牺牲自己来成就大家,“睡服”铁匠伪装驴得水老师,还任凭曾经的爱慕者和同僚辱骂自己来维护铁匠伪装者的身份,在一系列的精神折磨中,恐惧、失落、无助的张一曼终于疯了,变成了一个牢记“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管”的疯子,在学校依靠捐款而重获欣欣向荣之景时开枪自尽。这部影片通过女主人公看似荒诞的走向癫狂的故事展开了一次深刻的现实批判和人性反思,正如影片的宣传语所言:“给你讲个笑话,你可别哭。”或许这就是癫狂形象在新时期以来的电影中的反思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