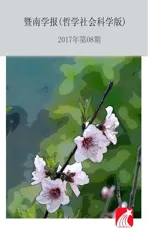扬雄官箴创作及经典化问题探讨
2017-11-13王允亮
王允亮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扬雄官箴创作及经典化问题探讨
王允亮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扬雄的官箴文涉及西汉的官制,根据西汉末官制的变迁,可以推知这组箴文大致作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十二月至二年三月之间。扬雄的官箴文创作受到内外动因的双重驱使,在朝政混乱的情况下,他通过模拟《虞人之箴》的方式,一方面委婉地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劝谏,另一方面则直接与古人角胜,体现出知识型人格处理问题的特点。其官箴文因为符合士大夫的审美需求和创作心理,在六朝时期逐渐被经典化,在官箴文体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扬雄; 官箴; 创作时间; 内外动因; 经典化
扬雄是西汉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他以复古为特点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除了众所周知的大赋创作之外,其模仿《虞人之箴》而写的《十二州牧箴》、《二十五官箴》也非常值得注意。这组作品在后世取得了经典性的地位,引起很多人的仿效,形成了一个官箴创作的系列。尽管如此,对于扬雄官箴的写作年代,由于资料所限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大致有初始元年(公元8年)和元始四年(公元4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之间两种观点。本文从汉代官制改革的角度入手,重新探讨了扬雄官箴文创作的时间,将其定于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末至绥和二年春(公元前7年)三月期间。在对基本史实重新考订的基础上,我们由扬雄官箴作品的创作时间出发,考察了扬雄官箴文创作的时代环境及其内在动因。鉴于扬雄官箴文在后世的重要影响,我们以六朝时期为中心,从经典化的角度探讨了其接受历程,并揭橥其经典化的内外原因,以便更深入了解扬雄官箴作品的价值。
一、扬雄官箴的写作时间
对于扬雄官箴的写作年代,如前所述,当今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初始元年(公元8年),一个是元始四年(公元4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之间的三四年间。这两种观点的主要依据都和扬雄官箴中的十二州箴创作有关。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五年王莽上奏:
莽复奏曰:“……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界,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奏可。
又《汉书·平帝纪》:
分京师置前辉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虽然两处所言时间不同,一为元始五年,一为元始四年,但均提到王莽进行州制改革的史实。由于传统正史帝纪作用以系年为主,其编排当较传记可信,故此处姑从《平帝纪》将其时间定为元始四年。
在说到十二州的划分与扬雄官箴的创作问题时,很多人认为扬雄十二州箴的创作时间在王莽改制之后,甚而由此认为扬雄十二州箴的选择受了王莽的影响,由此上升到对他谄媚阿附王莽的批判,如清朱珔《文选集释》卷二十三云:
近梁氏耆《庭立记闻》谓:翁孝廉尝言:汉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凉州为十二;雄作州箴十二,独缺朔方,可见其为莽大夫也;此亦人所未及。梁氏所引翁孝廉之语,实乃宋明以后诸人对扬雄所作出的诛心之论,此论点发自朱熹《通鉴纲目·汉纪》“莽大夫扬雄死”一语,以后广为传播,此可勿论。但除梁氏之外,后世的很多学者也存在这样的认识,认为王莽元始四年改制是将十三州改成了十二州,并以此作为扬雄百官箴创作时间的上限。
然而,这些说法看似有据,却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除了州制的变动之外,由于西汉还进行过数次官制改革,官箴中的官职名称也应该是我们考察扬雄官箴创作时间的依据。扬雄的官箴中有《廷尉箴》,据《汉书·百官公卿表》:
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复为廷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复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
根据廷尉官制的变动记录,它在汉初名廷尉,景帝中期改称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改大理,至王莽改称作士。元始五年至始建国元年期间廷尉已经更名为大理,如果扬雄这个时期内创作官箴,当名为《大理箴》,而不应该名为《廷尉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矛盾之处,也是以往的研究者很少注意到的地方。
如果根据廷尉官制的变迁来考察,则扬雄官箴创作年代当在哀帝元寿二年之前,而不应该是其后的平帝年间。那么,它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汉代改十三州为十二州,并不仅是王莽时期才有。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曾将天下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朔方、交趾十三州,设刺史以监之。而据《汉书·成帝纪》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汉书·哀帝纪》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夏四月“罢州牧,复刺史”,《汉书·百官公卿表》哀帝“元寿二年(刺史)复为州牧”。在这刺史、州牧的来回变动中,我们认为十三州也极有可能改为十二州,而且其最可能改动的时间则在绥和元年由刺史而州牧的变革中。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成帝末年的复古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成帝绥和元年二月,按儒家通三统的理论分封殷绍嘉侯和周承休侯;四月以骠骑将军为大司马,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益大司马、大司空俸如丞相,以符合古三公之义;同年十二月的罢部刺史,更置州牧,也是这一系列具有复古精神的活动之一。《汉书·朱博传》载:
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
何武和翟方进改刺史为牧伯建议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尚书·尧典》中的“咨十有二牧”,这和元始四年王莽所言的“《尧典》十有二州界”同一出处。我们要注意的不仅是其中的牧伯官职,还有其十二的数目,何、翟二人既然据《尧典》所言“十有二牧”提议进行制度改革“以应古制”,恐怕就不会仅建议将刺史改为州牧,而在数目上仍保持与经典有违的十三州,所谓的“古制”应包括州的长官为州牧,州数为十二这两层含义。既然王莽能根据《尧典》想到将天下划为十二州,难道依据同样理论提出州制改革的何、翟二人就不会想到吗?所以,我们认为成帝改制不仅是将刺史改为牧伯,还同时将十三州改为十二州。除此之外,据《汉书·成帝纪》,武帝征和四年设立的职位与刺史相当的司隶校尉,也已在成帝元延四年二月被撤销,其时仅在改刺史为州牧的前一年。成帝撤销司隶校尉,改刺史为州牧,将十三州并为十二州,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符合《尧典》所言十有二牧的记载,将自己的统治和舜的统治相类比。
那么,十三州是如何改成十二州的呢?据《并州箴》所言,其最大可能是将十三州中的朔方州并入并州,省去一州而为十二州。这一想法并非纯出推测,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据《汉书》《翟方进传》《冯野王传》《平当传》所载,成帝中叶时尚有朔方刺史之职,此后则再未出现,这就说明在成帝末期刺史改州牧的变革中,朔方州很可能同时被取消,变十三州为十二州,以符合经典之记载。由于 “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然其所载州郡中并无朔方之名,这似可说明,在王莽改制之前的元始二年,朔方就已经省去,虽然成帝变刺史为州牧的制度,在他死后有所回复,但改十三州为十二州的制度,似乎仍维持了下来。因而,王莽元始四年的再度改革,可能只涉及到州名及经界问题,对于十二州的数目并没有变动。
如果成帝末年曾改十三州为十二州,扬雄州箴的创作时间就不能仅限定在元始四年以后了,成帝时的绥和元年至哀帝建平二年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时间。再考虑到哀帝元寿二年以后虽然刺史复改为州牧,但其时廷尉已改称大理的情况,那么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二月至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四月,才是唯一能符合既有廷尉又有州牧条件的时间,扬雄官箴的创作就应该在此期间。
又据《汉书·游侠传》扬雄曾经做《酒箴》讽谏汉成帝,其官箴当和《酒箴》大概作于同时,皆为讽谏成帝所作。我们看百官箴中的箴谏对象皆为皇帝,哀帝虽处末世,即位后却有励精图治的决心,《汉书·哀帝纪》赞云:“哀自为藩王及充太子之宫,文辞博敏,幼有令闻。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即位痿痹,末年浸剧,飨国不永,哀哉!”于此可见其重整朝政的决心。而成帝却以酒色荒淫著名,且他在位的时候外戚当政,国势日衰,故而这些对皇帝劝谏性质的箴文无疑是针对成帝而发的。更进一步来说,扬雄这组作品当作于成帝末期,即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二月至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这约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百官箴创作于平帝元始五年至王莽始建国元年这个时间段内,当时朝政一直掌握在王莽手里,平帝不过是一个年幼的傀儡皇帝,没有任何的权威,这样一来文本中对于皇帝的屡屡进谏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地方。而且自哀帝元寿二年之后廷尉即改称大理,扬雄官箴中却有《廷尉箴》,这也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之处。如果将创作时间放至绥和元年十二月至二年三月之间,则无论是官制称谓还是其实际创作意义都不存在任何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其实最早提到扬雄官箴的创作时间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中说:“汉成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亡失九箴。”与后世学者不同,孔氏将州箴和官箴的创作时间置于成帝时期。通过我们对刺史改为州牧以及廷尉官制的变迁考察结果来看,他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成帝末年,分封殷绍嘉侯和周承休侯,存二王之后以通三统;以骠骑将军为大司马,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益大司马、大司空俸如丞相,以符合古三公之义;以《尧典》之义罢部刺史,更置十二州牧,这一系列活动具有强烈的文化建构意义。这种建构以儒家经义为核心,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与自武帝以来,儒家五经立于官学,其思想长期浸润社会,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成帝末年,国家政治面临的现实困局有关。向经典寻求力量,强调统治的合法性,增加民众的认同感,是这些具有仪式化举动的实质。。这一系列的因素,最终体现为复古风气的兴起,这种复古是以儒家经典为指归的,儒家经典文本被崇高化,在当时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其影响,时人也日益注重对经典文本的审定、阐释、模仿,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经典化作为自己的目标。扬雄的官箴创作,也是在这种经典化风气下产生的典型之一。当然,他的创作自有需要申述的独特因素,接下来我们将就这一方面进行分析。
二、扬雄官箴创作的内外动因
扬雄的官箴创作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内外双层动因的驱使下完成的,其内在动因取决于扬雄的创作心理,外在动因则取决于其创作的时代环境。两者相比,外在动因无疑更为显眼,接下来我们便由此开始作一考察。
(一)扬雄官箴创作的外部环境
扬雄这组作品创作于成帝绥和元年十二月至绥和二年三月之间,其诉求对象也为成帝,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应该是文章的接受者汉成帝刘骜。对于他,《汉书·成帝纪》中有这样的评价:
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
这段《成帝纪》后的赞语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班彪写的,班彪的姑姑班婕妤是成帝的嫔妃,所以他的看法来自家族女性与成帝的日常接触,可信度自然较高。
西汉自元、成时期起,儒学开始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不仅朝中大臣儒生的比例越来越高,最高统治者身上的儒学色彩也越来越浓,他们注重用儒家伦理标准来处理君主与大臣间的关系,而不是凭法家的严酷少恩来维持一人专制,这一点可以从汉宣帝与当时的太子元帝间的对话见出一斑。《汉书·元帝纪》载:
(元帝)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可见,元帝与宣帝的最大不同在于其身上多了儒家的人情味,而不是像法家一样强调君主对臣民的绝对权威。成帝与元帝一样,也是一个儒学化色彩较浓的帝王,他虽然有湛于酒色的致命缺点,但一方面却能容受直词,颇有度量。
另外:与君主自身的儒学化态势相反,社会上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西汉后期由于国家长期稳定,统治阶层渐渐流于奢靡享乐,经济层面豪强兼并弱小,普通民众生活难以为继,加之元帝时宦官干政,成帝时外戚专权,故而国势日衰,社会局面几近失控。《汉书·王商传》载“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杜邺传》载“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从这些反常的景象中,可想见社会纷扰不定的情状。
昭帝时晆孟因上书汉昭帝要其求索贤人,禅让退位而被杀,宣帝时作为九卿之一的司隶校尉盖宽饶,同样上书皇帝让他退位让贤,虽然盖宽饶被迫自杀,但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即使家天下的制度实行已久,西汉知识界天下为公的思想却一直存在。至元、成以后社会局面日趋混乱,这种思想又开始抬头,《汉书·李寻传》: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
这个事例足以说明在时人心目中,刘氏统治确乎遇到了至为棘手的难题,所以某些术士才鼓吹用再受命的方式来延续汉家运命,这也反映出成帝时期统治的不稳定。
作为宗室老臣的刘向对此心怀忧愤,不断地向成帝陈奏论事,而且写成《新序》《说苑》《列女传》以启发成帝。朝中的一些大臣也借灾异现象的发生,接连向皇帝上奏章进行劝谏。。由于君主身上的儒学化色彩浓厚,故儒家话语中对君主个人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被大臣们以灾异为借口频频提出,对成帝进行毫不忌讳的谏诤,这些奏疏激烈伉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举例论西汉晚期的上书奏事风气说:
……刘向奏成帝亦曰:“陛下为人子孙,而令国祚移于外家,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
足见当时上书言事风格的激烈,由此也可知当日朝堂上下的紧张气氛。
当然,如刘向给成帝的奏疏中所言,其时汉帝国的权力实际上把持在成帝的外家王氏手中,作为宗室大臣,刘向见及于此,屡次对成帝耳提面命进行谏诤。也有一些士人认识到这个问题,毅然指出症结所在,但很快遭到报复,引来杀身之祸,《汉书·王章传》:
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
另外一些人则避开这个敏感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汉书·谷永杜邺传》:
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
又:
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
作为西汉末期的言事名臣,谷永、杜邺宁愿批评皇帝本人,也不敢撄王氏之锋,足见王氏气焰之嚣张,朝中论政的风险之大。这便是扬雄官箴创作时面临的社会政治局面。
(二)扬雄官箴创作的内在动因
以上所论为扬雄官箴创作的外部环境,那么他创作的内在动因又是如何呢?作为一个知识型作家,扬雄对于政治并不热心,他的主要目的是欲以“文章成名于后世”,故而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知识的探索中去了。所以在西汉晚期朝政扰攘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如其他人一样痛陈时政,只是不痛不痒地写了一篇《谏勿许单于朝》,因为这种做法并不涉及实际的政治利益,不至于使他卷入朝中的纠葛纷争,从而保证他处于一个安全的境地。
那么扬雄的箴文创作又是为何呢?某种程度上,这或许与汉成帝和扬雄的私人关系有关,这一点在扬雄的《答刘歆书》颇能透露出一些信息,其中有云:
而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此数者,皆都水君尝见也。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沉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徭,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如是后一岁,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成帝好之,遂得尽意。
就汉成帝对于扬雄作品的喜爱与欣赏来说,实具有某种文学上的知遇之情,至于他准许扬雄不任职事,得带俸恣意观书皇家密阁,又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襄助其事,这对于不营生产,且写有《逐贫赋》的扬雄来说,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帮助。从扬雄与刘歆书信中透露出的情况来看,他在私人感情上对成帝是有感激之意的。从扬雄的角度来说,在目睹对自己有知遇之情的君主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时,自己无论于公或私都应该尽到谏诤之责,这种心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可以看作是他创作文章的动机之一。
但扬雄对官箴形式的选择,其原因则较为复杂,从外部环境来说,当时朝堂政治氛围凶险,他在朝中无甚根基,王章的前车之鉴证明,谈论具体事务很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官箴文形式复古则无此之虞;从内在个性上来说,扬雄以模拟为创新的创作习性,促成了他对官箴形式的选择。
“箴”作为贵族文学的一种,古代早已有之,《国语·周语》中记载: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此处“师箴”,韦昭注云:“师,小师也。箴,刺王阙以正得失也。”箴在这里作动词用,当时有无文学作品的存在,不得而知。但是《左传·襄公十四年》载:
晋师旷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而,百工献艺。”
这里从“工诵箴谏”一句,明显可见箴谏是一种可诵读的文本,具有文学作品的性质,证明当时已有箴文存在。
古代的箴文不仅只是在典籍中被约略提及,而且还有一篇相当完备的文字流传下来,那就是《虞人之箴》,《左传·襄公四年》: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虞人之箴》与扬雄箴文的句式、风格如出一辙,它对扬雄创作的影响毋庸置疑。那么,扬雄的箴文创作与《虞人之箴》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难道仅仅是一种模仿吗?扬雄又为何要这么做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相对于西汉的其他作家来说,扬雄是一个知识型的作家,从知识型作家的性格来讲,扬雄具有好奇、好胜、好深、好博的特点,他的创作多以模仿为之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无论是模仿司马相如写四大赋,还是模仿《论语》写《法言》,模仿《易经》写《太玄》无不如此。这并不是扬雄才力不够必须模仿,反而是他好胜性格的一种表现,他在各类著作中都选定居于第一位的作品为目标,以自己的才力与古人相角逐,不是一种好胜性格的支撑,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扬雄的箴文创作也是如此,《虞人之箴》作为义据典雅,首尾完备的箴文珍品,在后世具有不容置疑的经典地位,扬雄以其为目标撰写的《十二州》、《二十五官箴》,风格体式丝毫不差,从创作动机来讲无疑具有争胜的意味。
总之,从扬雄官箴创作的内外动因来说,社会环境的纷纭扰攘彰显着时代困境,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给士人以无形的心理压迫,成帝的知遇之情又不容扬雄缄默不言。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愿希颜苟合来赢得政治位势,也不愿直指弊政给自己带来麻烦,通过对经典典作品的模拟来表达政治劝诫,则一方面既让自己与现实政治疏离,不至于卷入政治风波之中,另一方面又顺应了自己与古人争胜的创作心理,同时也尽到了作为大臣的职责。因此,这组箴文可以看作是扬雄在内外因驱动下,对成帝末期混乱朝政给出的独特反馈。
三、扬雄官箴经典地位的获得
扬雄的官箴文对后世颇有影响,在六朝时期便有继起仿效之作,文评予以高度评价,类书多选其篇,使它获得了牢固的经典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它的经典化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其经典地位获得的内外原因当不为无益,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一情况作一考察。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往往与作家经典地位的获得息息相关,扬雄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已被认可,汉成帝以其文类相如而任他为郎即是明证。此外,他的作品更被时人认为是必传之作,这可以两汉之际桓谭的言论为代表:
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杨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
又桓谭《新论》:
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
前者是桓谭认为扬雄的著作必传于后世,后者是桓谭、张子侯以扬雄比孔子,既体现了对其作品经典地位的认可,也显示了他在两汉之际的崇高地位。
至于扬雄的官箴作品,其经典地位的较早体现,是在班固《汉书·扬雄传》中被作为扬雄的代表作品而提及,在传后的赞语中,班固写道: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这里所言的“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是史书写作中以点带面的常见手法,用《州箴》来指代扬雄的全部官箴文创作。扬雄箴文在这里与他的代表作品《法言》、《太玄》、四大赋等相提并论,足以说明其在东汉初已经被当成经典作品来看待了。
除了在史书中对其经典地位认可之外,扬雄官箴的经典化还表现为对它的借鉴与模仿,最早体现为东汉出现的一系列官箴作品,《后汉书·胡广传》:
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胡广之前与扬雄相关的官箴文创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扬雄亡佚的官箴作品进行补苴,另一类则是对扬雄的官箴作品进行模仿,但无论哪一类,都是以承认扬雄箴文的经典地位为前提的。
其实,除了《胡广传》提到的官箴文之外,东汉还有其他的官箴作品,如皇甫规的《女师箴》,崔寔的《谏议大夫箴》,崔篆的《御史箴》,崔德正的《大理箴》,潘勖的《符节箴》等,仅就《后汉书·文苑传》所载,就有崔琦《外戚箴》和高彪《督军御史箴》。虽然这些箴文与扬雄官箴的诉求对象或许已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扬雄的官箴仍沿袭古义,以标题中的职官身份箴谏,其诉求对象为皇帝,东汉箴文的诉求对象则多是职官本人,但它们也都受到了扬雄的影响。我们先来看崔琦的《外戚箴》:
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势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高彪的《督军御史箴》:
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周公大圣,石碏纯臣,以威克爱,以义灭亲。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复无所观。先公高节,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
我们再来看看扬雄的《豫州牧箴》:
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我败。毋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带蔽屏营,屏营不起。施于孙子,王赧为极,实绝周祀。
《将作大匠箴》:
故人君无云我贵,榱题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极游。 在彼墙屋,而忘其国戮。作臣司匠,敢告执猷。
很明显,《外戚箴》和《督军御史箴》中的“无谓”,“无曰”,“勿谓”云云之类的句式,是从扬雄《豫州牧箴》中的“毋曰”,《将作大匠箴》中的“无云”、“毋云”句式变换而来的,说明前者在创作中对后者进行了借鉴。
魏晋时期,官箴创作尤其兴盛,现在能知道的有魏嵇康的《太师箴》,晋齐王司马攸的《太傅箴》,陆机的《丞相箴》,温峤的《侍臣箴》,王济的《国子箴》,潘尼的《乘舆箴》,张华的《女史箴》、《大司农箴》,傅玄的《吏部尚书箴》、《少傅箴》,傅咸的《御史中丞箴》,挚虞的《尚书令箴》,李重的《吏部尚书箴》,王廙之的《保傅箴》等,这些作品均受到扬雄的沾溉,不出其箴文所牢笼。不仅官箴文字,铭文的创作也受到影响,就当时颇负盛名的张载《剑阁铭》来说,《骈体文钞》卷四即评曰:“虽曰铭,其体实箴也,亦是步趋子云。”这说明扬雄官箴文的影响此时已经跨越文类,及于铭文创作了。
南北朝时期,官箴创作也不乏其人,最突出的有袁峻,《梁书·文学传》:
高祖雅好辞赋,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其藻丽可观,或见赏擢。六年,峻乃拟扬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赐束帛。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
这说明直到南北朝后期,模拟扬雄官箴的创作仍在继续,袁峻且因成绩出色而受到梁武帝的嘉奖。
创作之外,在作为文学经典化体现的文艺批评和选本收录上,扬雄的官箴作品也同样受到注意。前者主要体现于集南北朝文学批评大成的《文心雕龙》中,其《铭箴》说:
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可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
刘勰从箴文文体发展史的角度,指出了扬雄官箴创作在其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后者反映为扬雄官箴在中古文学书籍中的入选情况,它们虽然没有入选《文选》,但在初唐的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等书中却多次出现,如果将作者存疑的《交州牧箴》《尚书箴》《博士箴》《太常箴》五篇作品排除在外,据统计《北堂书钞》节选了七篇,《艺文类聚》选录了六篇,《初学记》选入了十七篇。除此之外,通常被认为是唐人选本的《古文苑》也选了二十三篇。这说明时人已将它们当成创作时借鉴取资的典范。
至唐以后,官箴创作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进入了人才选拔的范畴,《四六丛话》卷二十三载:
周辛甲为太史,命百官箴王阙,虞人掌猎为箴。汉扬雄拟其体爲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之作者咸依倣焉。隋杜正藏举秀才拟匠人箴,拟题肇于此。唐进士亦或试箴。显庆四年试《贡士箴》,开元十四年《考功箴》,广德三年《辕门箴》,建中三年《学官箴》。
有了制度性的保障,其影响无疑也就更加广泛了。
通常来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一般具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外在原因。内在原因一般包括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外在原因则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
就扬雄的官箴作品来说,其经典化地位的获得也多少具有这方面的因素。从内在的艺术价值来说,作为一个知识型的作家,扬雄作品以渊博典雅为特色,这一点在熔铸经典而成的官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文心雕龙·事类篇》说:“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这说明扬雄官箴创作注重从经籍中撷取词汇典故,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作品展现出渊雅堂皇的美学风格,《骈体文钞》卷四即评扬雄《十二州箴》为:“子云诸箴,质多于文,源出诗书者也。”又云:“本传以为法《虞箴》而推究盛衰,折衷经调,才学识具备。”又评扬雄的《官箴》为:“《官箴》不及《州箴》之赡炼,而古泽自足。”作为宫廷贵族文学的一支,这种典雅渊穆的风格,符合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受到他们的青睐。从可阐释空间来说,官箴文以政治批评为主题的写作范式,与传统士大夫以政治为日常生活主题的生存形态相契合,他们在感情上对这一主题并不陌生,官箴创作上熔经铸史的特点,又给了作者驱遣词句,较力角胜的空间,因而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群趋从事这一文体的创作,客观上促成了扬雄官箴的经典地位。从官箴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扬雄的官箴创作在模范《虞箴》的基础上扩充完备,使沉寂数百年的官箴文重新焕发了活力,实有兴废继绝的意义,从对后世作者的影响来讲,它的作用更为直接显豁。从外在的接受角度来看,扬雄官箴文的经典化历程经过了史家的认可,它们在《汉书》扬雄本传中被正式提及;作者的接受,东汉以降大量的补苴模仿之作层出不穷;批评家的关注,《文心雕龙·铭箴》中对它的地位高度评价;文学书籍的纳入,《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等书将它们广泛甄录;制度化的保障,唐代科举考试中将官箴创作列为人才选拔手段之一,诸多因素保证了它的经典地位在初唐时期已经完全确立。
综而言之,扬雄的官箴作品并非作于平帝元始五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廷尉已经改称大理,这与扬雄官箴中有《廷尉箴》一文不合,经过细致比勘,我们认为它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成帝绥和元年十二月至绥和二年三月之间。这个时候朝政掌握在外戚手中,社会局面动荡不安。西汉皇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解脱政治困局,通过种种复古举措,向儒家经典寻求力量,客观上形成了社会上的经典化风气。扬雄出于对成帝知遇之情的回馈,顺应时代的复古风气,采用模仿《虞人之箴》的方式讽谏皇帝,既可以让自己尽可能远离政治纷争的是非,又满足了他与古作者争竞的好胜心理。这种情况下创作出的官箴,可算是经典化风气下产生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因为符合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在六朝时期被广泛借鉴、模仿、评价、选录,迅速确立了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池雷鸣]
2016-12-28
王允亮(1978—),男,安徽亳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典化视阈下的汉代文学研究》(批准号:16BZW089)。
I206.2
A
1000-5072(2017)08-01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