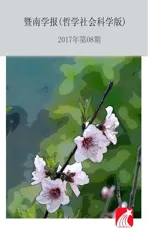约翰献土:中古英国王权与罗马教廷关系管窥
2017-11-13蔺志强
蔺志强
(中山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世界史专栏】
约翰献土:中古英国王权与罗马教廷关系管窥
蔺志强
(中山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1213年,约翰王向教皇臣服,使英格兰王国成为领自教廷的封土,开启了英国王权与教会关系的新格局。封君封臣关系是理解此时双方互动的不应忽视的基础。约翰王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从中各得所需。亨利三世时代是这一新型关系影响最为深入的时期。教皇在亨利三世幼年时期行使了封建监护权,并为亨利亲政后双方的良好关系定下基调。亨利三世认可并履行对教廷的封臣义务,并借此扩展王权,但同时教廷征收高额贡金及其权威过分介入英国引起英国教会及贵族的抵制。从爱德华一世时代起,臣服关系逐渐被淡化,但并未否认。1366年,英国议会单方面终止了这种臣服关系,是当时国际形势变化以及教廷和英国王权实力消长的结果。
罗马教廷; 英国王权; 臣服关系; 贡金
1213年,约翰王在内外交困中将英格兰和爱尔兰王国奉献给罗马教廷,使教皇破天荒地成为英国国王的封君,英国王权与教廷的关系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亨利三世时代到十四世纪中期,涉及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的许多史事,必须放到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得到解释。
对于这一时期罗马教廷与英国王权的关系,国外的相关研究很多,但很多论著仅从税收的角度认可此次事件的长期影响,这一看法的奠基者无疑是伦特。受其影响,学界长期以来对臣服事件的转折性意义强调不够,但事实上它的影响很难一言以蔽之,比如鲍威克就曾感叹没有哪个课题像解读教廷与其臣属国之间的关系这样令学者们困惑。国内的相关论著中,对这一议题也早有提及,如刘城从教职任命权之争的角度论述了英诺森三世与约翰王的冲突及其封臣关系的建立,以及教皇权在中古英格兰的扩张及其引发的斗争。龙秀清从教廷财政的角度论述了13世纪起英格兰向教廷寻求保护与缴纳贡金的具体情况。孟广林论述了约翰王与英诺森三世冲突与和解的史实,指出
政教双方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彭小瑜阐述了中古教会法以及教皇英诺森三世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述及约翰王奉教皇为封君的史实。这些论著在宏观视野下肯定了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不过尚未对这一事件本身及其如何影响此后英国的王权与政教关系进行过专门细致的讨论。本文认为,约翰献土事件在13世纪之后百余年间的英国对外关系乃至国内政治生活的演进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特别是封君封臣关系建立后的影响过去强调不够,因而试图梳理相关史料和既有的研究成果,理清这一事件的脉络,就其长短期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同行。
一、“国王的主人”:教俗关系新格局
英国教会在中古英格兰王国中地位独特,它既有独立的行政与司法体系,又拥有巨大的地产。长期以来,世俗王权在很多方面都难以深入到教会的势力范围内。教会之所以能够维持较高的独立性,除了与世俗贵族一样拥有其地产内的封建特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罗马教廷的力量。中世纪西欧被看作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英格兰教会奉行“教皇权至尊”,接受教皇敕令与基督教大公会议决议的约束,服从教皇的司法权力。
诺曼征服之后,作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王权,英国历代国王不断尝试加强对教会的控制,但在教廷权威和封建传统的双重束缚下成果有限。亨利二世曾发动对教会势力最大胆的攻击,但英国教会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抵制了国王对教会特权的削夺。1172年托马斯·贝克特事件之后,亨利二世被迫裸足而行到坎特伯雷表示忏悔,并向教皇使节屈服。
从1205年开始,约翰王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授任问题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爆发了长期而激烈的冲突。1208年教皇对英国发布禁教令,1209年约翰王被开除教籍,1212年教皇甚至下令废黜约翰王的王位。约翰王最初对教皇的威胁毫不理会,但法国入侵的威胁和国内贵族的反叛使他内外交困,不得不向教皇屈服以换取保护。
从双方达成的协议来看,约翰向教皇的最终屈服可谓干净彻底。他不但接受教皇力荐的兰顿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而且承诺纠正一切侵犯教皇权和教会特权的行为,包括将退还1208年以后侵占的总数达10万英镑的教会收入。更为惊人的是,约翰直接把英格兰和爱尔兰王国奉献给了教皇。在1213年11月4日英诺森三世至约翰王的公函中,完整引述了约翰于5月15日致教皇的臣服书,其中明确承诺:
出于我们的善意与自由意志,基于贵族的共同建议,我们将向上帝,向上帝的神圣使徒彼得和保罗,向我们的母亲神圣的罗马教会,向我们的领主教皇英诺森三世和他的继任者,自由地奉献和赠予全部英格兰王国、全部爱尔兰王国,包括其所有权利和财产,以洗刷我们和我们国民的罪过;并在今后作为封土从上帝和罗马教会领受和持有它们,……为此,我们命令,罗马教会将从上述王国的收入中每年获得1 000马克,不包括任何应付的彼得便士。其中,每年米迦勒节和复活节各付500马克; 其中700马克为英格兰王国而交, 300马克为爱尔兰王国而交;我们和我们继任者的管辖权、特权和君主权不受伤害。
事实上在这封信发出之前的两天,即5月13日,约翰已与教皇的谈判代表潘多夫(Pandulf)达成了妥协协议。根据文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编年史中收录的特许状,5月13日的协议中并不包括约翰臣服献土的条款。但在5月15日,约翰又签署了上述的臣服特许状,并在潘多夫面前举行了效忠仪式,变身为教皇的封臣,英格兰和爱尔兰也就此成为英王领自教皇的封地。数百年后,伏尔泰旅居英国,遍访历史典籍,根据如今已无从考证的史料,记录下了臣服仪式的细节:“于是约翰把钱放到教皇特使手中,作为第一笔缴纳的贡银。他把王冠与权杖也交给特使,意大利人(指潘多夫)把银子踩在脚下,把王冠和权杖留了5天,然后还给国王,作为他们共同的主人教皇的一种恩典。”罗杰的编年史没有这一细节,但他提到,在臣服仪式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耶稣升天节当天,约翰以残忍的方式处死了一位隐士彼得,因为彼得在不久前预言,约翰在耶稣升天节后将“把王冠转给别人,从而不再是国王”。这些记录的真实性难以确定,但记录者关注的重点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约翰王的奉献大大超出英诺森三世对他发出的通牒中的要求,令这位野心勃勃的教皇喜出望外。原因之一,虽然当时已有欧洲君主成为教皇封臣的先例,波兰、阿拉贡、卡斯提尔、葡萄牙等多个地区的君主奉教皇为领主,但他们都从教廷获得实际的回报,像约翰王这样奉献如此富庶的王国然后变身为教皇封臣,且貌似不图回报的君主,实属罕见。原因之二,事实上直到1209年对约翰王处以绝罚之前,英诺森三世对约翰的要求也主要是承认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而1213年2月发给约翰的最后通牒中,教皇的要求除坎特伯雷大主教问题外,也只是加上了纠正“整个英格兰教会”的问题,仍没有提及世俗权力方面的诉求。虽然约翰是否主动献土这一问题,学术界已争讼百年,但是约翰的奉献超出教皇的预期是没有疑问的。
所以当约翰臣服的消息传来时,英诺森三世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在1213年6月6日致约翰的信件中,先前那个冥顽不化、“不足与谋”的背教者变成了“高贵的君主”。他声称约翰的奉献使他“以更尊贵更可靠的头衔拥有他的王国”,因为“王国变身为祭司领地,祭司领地又是一个王国(sacerdotale sit regnum et sacerdotium sit regale)”。在之后的几封信件里,英诺森三世反复论证了约翰奉献国土的高尚意义,其中最能全面地反映他的理念的是1214年4月致约翰王的信。在信中英诺森三世这样写道: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已指定一人作为其在人间的代理,正如在人间、天堂甚至地下的每一个膝盖都向上帝跪倒,所有的人也应服从上帝的代理人,坚持世间只有一个羊群,一位牧人(unum ovile et unus pastor)。出于对上帝的爱,世间的国王如此敬重这位代理人,以至于认为没有对他的虔诚侍奉就不算合格的国王。我的爱子,你深谙此中道理,在主宰每一位国王的内心和命运的上帝的感召下,你决定让你的人身和王国在世俗事务上也臣服于作为它们的精神导师的这位代理人,这样,王位与神职,正如肉体与灵魂,便在基督的代理人一人身上结合(in unam vicarii Christi personam uniantur),此必对二者皆大有裨益。如今,那些曾经在属灵的问题上将神圣的罗马教会作为适当教导者的政治体,在世俗事务上也将之作为特别的主人了,这都是万能的上帝的恩赐……
在此,教皇掌控世俗事务的野心昭然若揭。我们知道,就西欧整体而言英诺森三世并没有提出由罗马教廷统辖教俗两界的思想。不过,对于以封君的身份插手世俗事务,他并不反对,也不陌生。在这封褒奖约翰的信中,英诺森三世也毫不掩饰地阐明了自己的理念。《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关于世间的羊将“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的话,被英诺森三世用来佐证教皇权威的普世性,而且强调精神与世俗事务的最高管理权都应集于其一身。五百年前,著名的丕平献土造就了教皇国,使教皇得以在意大利半岛的核心区域身兼精神与世俗领袖二职。如今这些欧洲各地的王国纷纷臣服教皇,很难不让英诺森三世做起一统天下的美梦。
除了促成教皇在理论上实现自我膨胀,约翰臣服还有更实际的后果。按照约翰的承诺,这一臣服给英格兰带来的最广为人知的后果是每年要为英格兰向教皇缴纳贡金700马克,为爱尔兰缴纳300马克。关于这一钱款,英文一般翻译为tribute,即一种教俗领主向保护者缴纳的贡金,这符合它的引申意义。但在拉丁文档案原文中,它被称为census,而这个词在西欧封建制度中就是指封臣向封君缴纳的地租。因此缴纳这种钱款本身就是封建臣服的标志。伦特也明确指出,缴纳贡金的世俗领主或国王与教皇结成的是封建关系。所以,直到14世纪中期,只要教廷和英国之间还存在缴纳贡金的关系,就不会忘记双方的封建臣服关系,不存在只保留纳贡而淡化臣服的可能。1000马克在当时并不是小数字,著名的狮心王理查被俘事件中,神圣罗马皇帝索要的赎金为15万马克,约合10万英镑,相当于英国两年的岁入,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而且,从一开始约翰献土臣服带来的就远不止纳贡关系的建立。1213年7月6日,英诺森三世同时向约翰王、英国教会贵族和英国世俗贵族发出三份公文。教皇首先声称在约翰的“强烈请求下”,答应立即派遣使节(Legate)前往英国,他是“带来拯救与和平的天使”,要求约翰“和善而真诚地”接待使节,并服从使节的“告诫和建议”。至于使节的权力,英诺森借用一位先知的话,称已经将充分的权力委托给使节,使他可以“根除和摧毁一切他认为应当根除和摧毁的,建立和扶植一切他认为应当建立和扶植的”。为解决约翰的燃眉之急,英诺森特别下令,由教皇使节下达的针对反叛者的命令都不得违抗。教皇同时向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全体英国主教重申了上述内容,强调使节全权代表教皇本人,要求英国教会严格服从使节的告诫和命令,特别是针对反叛者的命令。如果说命令教会服从还算天经地义,那么教皇对世俗贵族的命令就不能说寻常了。英诺森在致世俗贵族的信中首先指出,“英格兰王国现在以特殊的关系归属于罗马教廷”,因此可以正当地“要求和告诫你们,并以教廷敕令命令你们,友善地接待使节,真诚地对待使节,并谦卑地服从他的建议和命令”。
上述证据表明,教皇决定行使封君的权力,派遣使节全权代表自己,其权威置于英国国王和教俗贵族之上,负责指导英格兰的教俗事务,当然也包括要履行保护封臣的义务。
二、王权与教廷的互助与合作
约翰的献国称臣,很容易让人想到“丧权辱国”四个字,而且还是主动登门式的。然而分析当时的形势可以发现,约翰通过臣服教皇不但短期内改变了自己的被动局面,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也从教皇的支持中获益不菲。有史家称之为“一箭双雕”:使国内和国外的敌人同时丧失了合法性根基。
1213年,约翰内外交困,国内北方贵族反叛,但更紧迫的是与法国的一场恶战一触即发。5月10日,法王菲力二世已经组建好的一支据称有1 700艘战船的军队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集结待命,而约翰也组织了号称6万人的大军开到多佛备战。而大战的推动者之一正是教皇。因为多年来的各种威胁与惩罚都不能使约翰屈服,英诺森三世便假手法国来打击约翰。他向菲力二世许诺,如果能夺取英格兰,将把这个王国转让给他作为永久财产,并免除他的一切罪过。这使一直觊觎英格兰的法王终于得到合法的借口,马上行动起来。不过学者们一般认为,教皇不可能真正希望菲力二世合并英法,法王不过是被利用来压服约翰而已。
正在双方陈兵两岸、剑拔弩张的时刻,教皇派出特使潘多夫到英格兰进行谈判。一种说法是潘多夫表面宣称要联络英国贵族与菲力二世合作对付约翰,因而说服菲力暂缓渡海,但到达英格兰后他先找到了约翰。但罗杰的编年史称潘多夫是在圣殿骑士团人员的牵线之下由约翰邀请到英格兰的。谈判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到两天后,约翰便献上了王国和第一批贡金。特使返回法国告诉菲力二世约翰已在教皇的保护之下,菲力暴怒不已,但也不得不暂停其攻打英格兰的计划。随后教皇宣布英格兰的反叛贵族行为非法,兰顿返回英格兰后,在主持的调停下,北方贵族也于当年11月1日同意与国王和解。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约翰又成功地把自己引入绝境。先是倾全国之力组织起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反法同盟战争,并在1214年7月迎来布汶之战的惨败。然后在国内贵族群起而攻下节节败退,被迫于1215年6月15日来到拉尼米德草地签署了《大宪章》。在此期间,教皇几乎成为唯一可以带给约翰温暖的港湾,而教皇插手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保护其封臣约翰以及罗马教廷的封建领地英格兰王国。
1214年8月,英诺森三世促成法王与刚刚在布汶之战中惨败的约翰达成停战协定,使他得以从外患中暂时脱身。1215年,当约翰与英格兰教俗贵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教皇不断下令支持约翰。3月19日,英诺森致信英国世俗贵族,严厉谴责他们反叛其“最亲爱的主内之子”约翰的行径,并以教廷的权威宣布所有针对约翰王的联盟和计划都须放弃,违者处以绝罚。同天教皇致信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对他支持反叛者的行为表示震惊,并要求立即改正。4月1日,英诺森要求英格兰贵族马上向约翰支付拖欠的代役金。
同时,约翰在与贵族代表的谈判中也不忘搬出教皇为自己做后盾。5月1日,约翰提出双方各自指定四名人选组成八人仲裁团,但坚持自己的“领主”英诺森三世对八人仲裁团的任何决议拥有否决权。这直接导致贵族认为约翰缺乏谈判的诚意。5月29日约翰致信教皇,申诉兰顿为首的教会并未按教皇的命令支持自己,反而逼迫他接受贵族的条件。该信7月初寄达罗马,英诺森三世于7月7日向英格兰教会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函件表达了其“震惊与愤怒”。因为对于现在以“领主权(racione dominii)”附属于罗马教会的英格兰王国,兰顿等人不但没有给予帮助,反而成为破坏者的同谋。“看看这些主教们是怎么保卫罗马教会的财产(patrimonium ecclesie Romane)的!”
签署《大宪章》的消息传到罗马之后,英诺森三世于8月24日再次发出两封长信,严厉谴责英格兰贵族的反叛。在致“见信的所有虔诚基督徒”的信中,教皇强调约翰已经通过加盖“金玺(aurea bulla)”的特许状把英格兰奉献给罗马教廷。在受到贵族逼迫认可改革条款时,约翰也提出因为英格兰王国的领主权在罗马教廷,所以他不能也不应在没有教皇许可之下答应做出任何改变,他请求大主教和主教保护罗马教会的权利,但都被拒绝,最终不得不接受贵族提出的“不但无耻、不得体(vilem et turpem),而且非法、不公正(illicitam et iniquam)”的条件。教皇最后宣布彻底反对和谴责他们的协议,有关的特许状(指《大宪章》)无效和非法,国王如果遵守它,或是贵族敢于逼迫国王遵守它,都将被处以绝罚。而在致英国世俗贵族的信中,教皇强调,在逼迫约翰王签署妥协协议的行动中,贵族们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其行为违背了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而且根据“领主权”,这类争讼的裁决权应当属于教皇。因此,不管达成什么协议,都是贵族以“暴力和恐吓”诱使约翰接受的,因而应当宣布无效,并补偿国王和其人民的损失。当约翰宣布《大宪章》无效并导致内战爆发后,教皇又发布命令,将所有反叛约翰的贵族和其支持者逐出教门,并号召所有人起来支持约翰,对抗反叛贵族,称这样的行为可以等同于参加十字军。
臣服罗马教廷之后,约翰王当然也做出了巨大的让步。除了上述的大量金钱付出,还有各种权利让与。如1214年,约翰向英国教会颁发特许状,承认其选举教职的权利不受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侵犯,并且答应英国主教们向他提出的所有要求。
约翰王向教皇与英国教会的屈服开启了教廷、国王和英国教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新阶段,但他本人很快就“功成身退”了,这一新格局的后果深刻地体现在其子亨利三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其影响更是远及14世纪中叶。罗马教廷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强大而几乎无处不在的势力。它与王权既有亲密合作,又有激烈的利益冲突,英国教会夹处二者之间,常沦为被争夺的肥肉,但也并非完全听命于任何一方。英国王权正是在这一复杂多变的博弈当中,为加强自己的权威殚精竭虑。
年仅9岁的亨利三世于1216年10月匆忙即位。在加冕仪式上,他重申了对教皇的效忠,并宣誓将忠实地交纳每年1 000马克的贡金。而对于这个远未成年的封臣,教皇比对约翰王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要按照封建原则,担当起监护幼年封臣的义务。当然他不可能亲自履职,且英格兰当时形势危急,内战未歇,外敌压境,权力应当交给一位有威信、能作战的英国贵族,而非作为封君代表的教皇使节。所以在教皇使节格瓦罗(Gualo,或称Walo)的主导和力促之下,最终形成了威廉·马歇尔为首的摄政体制。教皇还否决了法国王子路易的王位要求,对英格兰的叛乱者发出开除教籍的威胁。失去合法性的叛乱者军心涣散,纷纷倒戈,最终在与威廉·马歇尔率领的王军作战中失败。马歇尔于1219年去世时,力主国王和王国应当托付给“上帝、教皇和教皇使节”,且当时“无外敌需逐,无内乱需平,因而无须军人摄政”,于是摄政权移交给了一年前重返英格兰接任教皇使节的潘多夫,并逐渐形成“三头共管”的格局。随着亨利的年龄增长,教皇也逐渐按封建规则把权力归还给他。1221年潘多夫卸任后未重新任命摄政,事实上就是让即将满14岁的国王准备亲政的信号。1223年4月13日,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向英格兰发出4封教谕,对刚刚年满15岁的亨利三世的权力收回做出安排。根据教谕,亨利将“自由而不受限制地处理其王国的事务,不设障碍地收回在贵族手中监护的王田和城堡”,“没有国王本人的同意不得使用大御玺”。这些安排使亨利三世实现了“部分成年”,也为他两年后的彻底亲政铺平了道路。
亲政后的亨利三世是认可教皇的封君地位的。据马修·巴黎的记载,1237年的一次御前会议上,亨利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指责亨利 “彻底地听命于罗马教廷的意志,受教皇使节的摆布;还宣称如果没有教皇或其使节的同意,他不能对任何公私事务做出决断,这样才称得上是教皇的封臣,而不是国王”。这样的攻击也许有世俗贵族从自己利益出发而夸大的成分,但考察当时亨利三世的实际行动,也不得不承认这并非完全凭空捏造。在缴纳税款方面,亨利绝对是模范封臣。亨利三世曾在1236年就应向教廷缴纳的1 000马克贡金这样写道:“我们已经习惯于向教皇缴纳贡金,以教会的名义,通过持有教皇证明的使节征收。”在王室收支档案中留下的有关令状证实了他的说法。据伦特的考察,从1219年到1261年,有一半以上的年份每年都有一份令状敦促官吏向教廷缴纳贡金,其中绝大多数是直接交给教皇的税收官,仅有两年没有指明付款对象,两年由圣殿骑士团代收,两年由意大利银行家代收。
贡金缴纳是教廷与英国关系的一个特殊的纽带。这一点从征税官的权力安排可见一斑。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当时英国要向教廷缴纳各种税款,教廷委派的征税官一般可以一并征收。其他教皇领地的收税官都是间歇性地前往,但在英格兰,从教皇洪诺留三世开始,教皇的收税官就一直派驻当地。而且,对于由约翰献土而形成的贡金(tribute),征税官每次都要在得到教皇的特别授权后才进行追缴。每次的缴款方式和收款途径也各不相同。教皇还多次任命了专门的贡金征收官到英格兰。这不仅是双方在财政往来上的特别之处,也是英格兰作为教廷封地这一特殊身份的一个表现。
作为教廷封地,英格兰对教廷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贡金缴纳方面。在亨利三世时代,罗马教廷把大量意大利人安插到英国担任教职,其中不经选举直接由教皇委任为英国主教的就有6人。有很多意大利人根本不到英格兰就职,成为英国教会供养的寄生虫。收入方面,1253年,教廷的反抗者说教皇一年从英格兰至少得到5万马克的收入。教皇英诺森四世反驳说事实上只有8 000马克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教会一年税收的百分之五,也是相当庞大的数额。
在教廷的辅助下,亨利三世终其一朝都不遗余力地树立自己的神权形象。马修·巴黎记载了1247年亨利虔诚地、大张旗鼓地迎奉来自圣地耶路撒冷的耶酥“圣血”的轶事。虽然当时人们对圣血的真实性纷纷表示怀疑,但这一级别的圣物能够到达英格兰,与教廷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教职授任方面,亨利三世在教廷的支持下不断地将国王内府的官员以及国王的亲戚安插到重要的、收入丰硕的教会职位上。
总观约翰献土到亨利三世时代的英国国王与罗马教廷,这种封建臣属关系可以说是使双方都大受其益的。教皇更深地介入英国事务,无论在权力层面还是财政方面的收获都十分可观。而约翰和亨利三世也利用教廷的支持稳定或扩展自己的权威。至于最后两位国王都结局惨淡,不是因为这种关系不够紧密,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国王过分依赖这种关系的结果。比如亨利三世与教廷的合作,特别是染指西西里王位的争夺,带来大量的财政负担,就被称为将英国“投入由罗马教廷和英国国王所构成的石磨之中”。亲教皇的政策使英格兰的大量财源外流,遭到反抗也是必然。
三、臣属关系的动摇与终结
爱德华一世上台之后,对祖父留下的这份遗产的态度与父亲有很大不同。他认为这种臣服且纳贡的关系是对国王尊严的伤害。在1274年回国即位之前,爱德华就派使臣参加在里昂举行的宗教大会,代表“国王、贵族和共同体”对向教廷臣服纳贡提出反对。反对的理由之一,是约翰王的献土有害于王国的福祉与国王的尊严,因而不能合法地延续下去;理由之二,是约翰王当时是在绝罚的威胁之下,担心失去生命和王国才被迫献土的,这种情况下的臣服关系缔结是无效的。这一申诉显然没有什么结果,接下来爱德华想尽办法拖延了几年之后,于1277年和1278年先后向教廷缴纳了8 000马克的贡金,包括补交了亨利三世最后几年的欠款。之后爱德华一世又交过三次贡金,分别是1281年4 000马克,1284年2 000马克,1289年6 000马克。也就是说,1289年之前,贡金虽不是按年及时缴纳,但总归是足额交付了的。
但1289年之后,爱德华一世一直拖欠贡金,直到去世再未付款。其中有几次与教廷达成缴款协议,又中途作废。1317年,爱德华二世缴纳了本年度的1 000马克贡金,但之前已拖欠近30年的款项继续拖欠。在1320年又缴纳1 000马克之后,爱德华二世也停止了贡金支付。爱德华三世上台后并无改变,到1330年,教廷正式确认的贡金欠款达到了3万马克。但纵观爱德华三世时代,只在1333年缴纳过1 500马克贡金,之后便再无支付这一款项的记录。总之,从1289年到1366年英国议会正式否认臣服教廷,英国实际缴纳的贡金仅4 500马克,与应缴纳的数万马克相去甚远。
但1289年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转折性时刻。之前,爱德华一世上台伊始就开始质疑对教廷的臣服与纳贡。数次缴纳贡金的背景,都是在对外交锋中得到教廷的支持,或者换取教廷批准国王向英国教会征税。事实上贡金成了英国与教廷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一点在1289年之后也无改变。
另一方面,无论在1289年之前还是之后,教廷与英国双方都没有忘记这种臣服关系与纳贡义务。但在1366年前,双方的分歧一般都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如上文提及,爱德华一世1274年反对臣服的尝试无果而终,教廷与英国的官方文件对后续结果都不置一词。1317年5月,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派使节到英格兰,其任务除了催缴欠款,还获得授权“接受英王爱德华二世为领有英格兰王国和爱尔兰王国而向罗马教廷进行臣服与效忠的宣誓。”但没有任何线索表明爱德华二世对效忠的要求做出过任何的回应。1345年2月,教皇克莱蒙六世派特使到英格兰,要求爱德华三世偿付“自古以来(ab antiquo)”就向罗马教廷缴纳的“数目惊人(mirabilem summam)”的贡金,但显然遭遇了冷处理,因为使者只得到“简短的回复”便返回了。1358年,教皇英诺森四世致信爱德华三世,试图敦促他缴纳拖欠半个世纪的贡金。为了使催款更有说服力,教皇附上了1214年英诺森三世收到约翰王臣服特许状的确认信,以及约翰王承诺每年缴纳1000马克贡金的誓词。教皇的信在议会进行了展示,但记录此事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未提及结果如何。不同的编年史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耐顿(Knighton)的编年史说国王简短而机智地回复说他不会向任何人缴纳贡金,因为他“过去和将来都自由地持有王国,不臣服于任何人”。但另一个编年史说教皇放弃了约翰王承诺的义务。这一种说法显然不足信,因为1365年6月,教皇乌尔班五世又一次致信爱德华三世,敦促他缴纳从1333年以来就拖欠的贡金。
但乌尔班五世的这次催款却成为英国彻底否认臣服教廷的导火索。1366年5月4日召开的议会,几乎可以说是专门为讨论与教廷的臣服与纳贡关系而开的。会上,国王向教俗贵族寻求如何对付教皇要求的建议。第二天,教俗贵族共同给出答复,并得到下院的支持,于是议会通过一项决议(ordinance):
“……已故的英国国王约翰曾向教皇(指英诺森三世)提交一份契据,承诺将为英格兰王国和爱尔兰领地(le roialme d’Engleterre et la terre de Irlande)而向教皇永远效忠并每年缴纳贡金(un annuel cens),现在,基于该契据,教皇将向国王采取法律行动(proces)以恢复这一臣服和贡金;此事已向教会贵族、公爵、伯爵、男爵和下院宣布以寻求其看法和建议,以及国王当如何应对教皇针对他和他的王国的任何行动。教会贵族、公爵、伯爵、男爵和下院在充分权衡之后一致认为,无论约翰王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不经他们的同意(saunz assent de eux)而把他自己、他的王国和他的人民(lui ne son roialme ne son poeple)置于如此的臣服地位;许多证据表明,约翰王的臣服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并且违背了他的加冕誓言。”
贵族和下院还宣称,对于教皇将采取的无论是法律行动还是其他措施,他们都将以其全力予以反对和抵抗。
爱德华三世把此事提交议会讨论,应该是预见到这样的结果的。教皇在英格兰的敛财行动一直受到包括英国教会在内的英国各阶层的敌视。比如在1358年议会上,下院就提出必须首先解决长期以来的教廷敛财问题,他们才会考虑由教皇特使提出的英法合约的批准。所以国王的这一行动实际上表明他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与教廷之间的这种长期以来的暧昧关系。而做出这一决策的背景,正是乌尔班五世与爱德华关系的不断恶化。乌尔班刚刚否定了爱德华之子埃德蒙与佛兰德尔伯爵的女继承人之间的婚姻,转而批准其嫁给法王约翰二世的儿子菲力。这打破了爱德华试图维持与佛兰德尔同盟关系的计划,让刚刚在战场大败法军,并通过《布雷蒂尼条约》重创法国的爱德华极为震怒。同时,教皇从1363年开始禁止有圣俸者的兼职行为,让爱德华政府中的几位重要成员收入大受影响。作为回应,爱德华三世在1365年1月的议会上重申了两项反教皇权立法,即1351年的《圣职授职权法令》(Statute
of
Provisors
)和1353年的《王权侵害罪法令》(Statute
of
Praemunire
)。同时,在英格兰的教廷税收官手中的资金被英国政府扣押。因此,乌尔班五世在1365年忽然逼债也算是其来有自。议会为爱德华三世摆脱臣服与纳贡地位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未经“他们的”同意和认可。这里的他们在当时显然主要指贵族。但约翰献土是否得到英国贵族的同意和认可,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约翰在1213年5月臣服教皇的特许状有13位教俗贵族的见证,但基本是身边的亲信,似乎不能代表全体贵族。但有一个证据表明反对派贵族也是接受献土的事实的。1215年5月,约翰王在罗马的代表写信给约翰,称发现反叛的贵族派遣使团到罗马向教皇控告约翰,而他们如此做的基础就是教皇是英格兰的领主。这些贵族还声称他们督促约翰按时交纳每年的1 000马克贡金。另外有学者指出,在《大宪章》签订的前夜,几个最激烈的反对约翰者仍然盛赞其臣服教皇的行动。不过,约翰王也曾写信给教皇申诉,称贵族反叛自己的原因是他向教皇称臣。13世纪的编年史家在叙述这一事件时也态度各异。分析这些互相矛盾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做出相应叙述的背景,自然会导致各种解读的并存和冲突。1366年议会的决议也没有列举其证明约翰王没有得到贵族和人民同意的所谓“许多证据”。所以这一争论看来无从结案。然而,学者们争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约翰王的决定一定要经过贵族甚至平民的(多数)同意,但事实上,在13世纪初议会体制尚未形成,所谓“全体同意”往往只是一个好听的说辞,并无完善的制度保证。约翰的臣服特许状声称“基于贵族的共同建议”,并有十几位贵族见证,在当时就是通常的做法。至于民众的态度,更加无法衡量,也基本无足轻重。以是否得到臣民多数同意来决定13世纪初政府行为的有效性,显然是不合适的。
但是,到了爱德华三世时代,议会制度基本成型,民众同意和认可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因而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爱德华以议会决议的方式正式否认了约翰献土的合法性,并得到了对抗教皇的有力支持,可以说大获成功。从实际来看,1366年之后,英国再未缴纳过这种贡金,甚至无论英国还是罗马教廷的现存官方档案中,都再没有提到英国的臣服和纳贡义务。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认为约翰献土已被彻底遗忘。最著名的例证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驱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据估计写于1374—1378年之间的一篇作品。威克里夫声称在某次国务会议上听到七位世俗贵族分别陈述了教皇不应当是英王的领主以及贡金不应继续支付的理由。这些理由没有提到民众认可,而是主要集中在对英王臣服教皇不符合封建原则的各个角度的论述。
罗马教廷的合作对中古西欧王权的发展至关重要。从1213年约翰献土到1366年议会否认臣服教皇,英国王权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特殊时期。这种基于封建效忠的特殊关系一方面给英国带来了一位指手画脚的“主人”和大量的财务负担,另一方面也为13世纪英国王权改变其国际和国内处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英国教会、贵族和民众对教廷势力过分介入的体会从一开始就与国王有所不同,所以当14世纪前后王权与教廷的合作也屡现摩擦时,这种特殊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2017-04-19
蔺志强(1973—),男,内蒙古清水河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欧洲中古史的教学与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古英国贵族特权领地研究》(批准号:11CSS003)。
K561.3
A
1000-5072(2017)08-00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