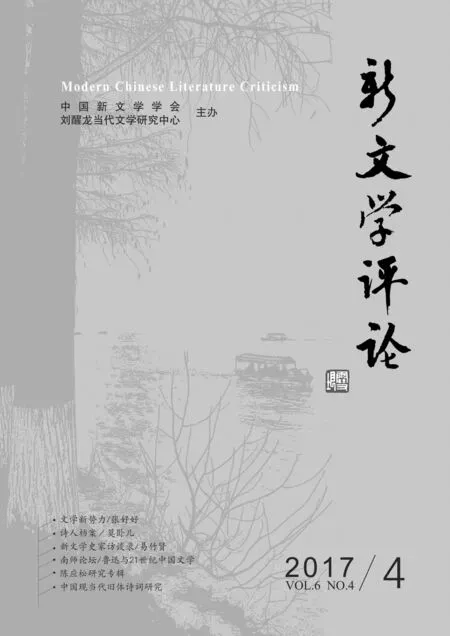作为民族寓言的《黄雀记》
———苏童成长小说的新超越
2017-11-13邓全明
◆ 邓全明
王宏图认为《黄雀记》是苏童小说经过艰难的探索之后的回归,“回归到他初登文坛时大展身手的‘香椿树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狂肆无忌顽童的世界”。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回到熟悉的“香椿树街”,回到“少年血”的成长小说 ,而是回归中的超越。昆德拉曾说,“所有的小说家也许都只是用各种变奏写一种主题”,对于苏童来说,确实如此:苏童最具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都离不开“香椿树街”,离不开那群懵懂而血气方刚的少年。但每一次重回,都是一次新的语言历险、一次对过去的新的理解。《黄雀记》作为最新的小说,也是苏童对香椿树街、对成长问题的书写的一次新的超越。
正如苏童自己所说,他的“成长小说系列的跨度很长”。苏童的成长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桑园留念》,《乘滑轮车远去》、《海滩上的一群羊》、《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刺青时代》都属于早期的作品。苏童这一时期成长小说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青春年少的叙述眼光,张新颖说:“苏童好就好在,当写作和叙述的时候,他自己也是怀有这种不明白的认识。他没有后来长大成人所谓的中年人明白这个世界的优越感”,指的正是他这一时期成长小说的特点。青春的伤感、迷茫,混乱的冲动,无名的血性,构成他这一时期成长小说的基调。《城北地带》的理性色彩逐渐增强,它不仅描写了“文化的废墟和权力的真空”时期,造就的“一代人的欢乐童年”,也揭示了其背后的原因:国家意识形态过分膨胀挤压了民间道德的空间及与民间道德的脱节导致的价值混乱造成了年轻人成长的艰难。作为成长小说,《河岸》的超越体现在将库东亮的成长问题嵌入“文革”大时代中,实现了成长小说与政治寓言的融合。《黄雀记》实现了苏童成长小说的再次超越:将成长问题放到民族心灵史的高度进行审视。
作为成长小说,《黄雀记》中宝润、柳生、仙女遇到的成长问题以及产生这问题的根源与以前的成长小说有相似之处: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父母自身的价值体系混乱,不能为他们提供精神资源,他们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精神必须的营养;学校教育价值观念与民间价值体系脱节,也不能提供切实的精神资源。《黄雀记》的故事从祖父丢魂开始:祖父在一次照相时受了惊吓,他的魂因此丢了。魂在中国文化有着多种寓意:迷信意义上的人死后的魂魄,活着的人的内在精神的魂。祖父丢魂事件可以从民间迷信的角度解释,也可视为一个民族寓言中的重要象征符号——民族之魂的丢失。此在的意义何在,祖父未必做过严肃的思考,以“我思故我在”的标准来衡量,祖父可能只是行尸走肉。70岁后的祖父对于丢魂的重视,与其说是他人生的反思,不如说是惊醒他的后人,惊醒读者,正视我们时代一个司空见惯、触目惊心的现实——我们有灵魂吗?祖父寻找灵魂的努力,其实并不另类、诡异,因为祖宗崇拜、家族延续向来都是中国人的重要的生命意义,只是这种意义体系在前社会主义时期一度被破坏、遗弃,以致其时的年轻人无法从其中获得意义。祖父从祖宗身上寻找意义不被年轻一代所接受,那么,年轻的一代,他们有自己对生命意义的建构吗?
进入香椿树街的日常生活,进入香椿树街众生的心灵世界,寻找他们生活的意义,恐怕我们要失望的。因为也许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灵魂,但如果将灵魂上升到价值原则、信仰追求、儒家的德行和道义,很难说他们有魂,他们的存在其实就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存在、一种没有意义的存在。如果说绍兴奶奶对于灵魂还存在某种敬畏——虽然只是一种形式的,但他们心中还有灵魂的概念,宝润的父母、柳生的父母、仙女的父母则这种形式的敬畏都没有,他们的灵魂空空如也。仙女、宝润、柳生虽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家庭贫富状况、家庭成员的关系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缺乏良好的家教,他们的父辈给了他们肉体但没有给他们灵魂,没有给他们能够支撑起灵魂的类似于信仰之类的东西。宝润家人之间关系本来不是很好,祖父丢魂事件一下让这个家庭显露了真相——义理、价值原则在这个家庭中是脆弱的。宝润的母亲忍受不了祖父的怪异,也是为了物质利益,将祖父送进了精神医院,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义理原则——这一点就是还未成年的宝润都看得出来。宝润的父母不能说没有考虑到或者说不关心宝润,但他们对宝润心灵、精神领域的关心、建设实在太少了。他们不仅无法为他建立一个价值世界,也很少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价值世界,如他的爱情,他对异性的情感。价值混乱导致的成长问题影响宝润的一生,10年后,宝润终于从监狱中出来了。宝润并没有变得成熟,变成一个有自我的人——有灵魂的人,这突出体现在他与仙女恩怨的了结上。是仙女的诬陷,才导致他被冤枉入狱,他对仙女怀有仇恨,我们可以理解,但宝润以和仙女在水塔上跳小拉作为两人恩怨了结的条件,确实让人有些费解。10年牢狱之灾,10年青春年华,就跳一曲小拉就完事了,宝润似乎也太傻了。作者以此告诉读者,宝润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成长——建立理性世界、价值世界。宝润出狱后仍在懵懂地找回他的公平,但“公平是什么,怎样才公平,她猜他说不出来”。他确实说不出来,他找回公平的方式恰好说明了他的无知——他对公平的理解只局限于一种肤浅的形式,他的价值世界一如以前一样空洞。
仙女的家庭更为糟糕,虽然她的养父母对她十分宠爱,但这种缺乏灵魂的爱无法为其建构一个意义世界,仙女无法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不屑一顾、自视甚高的所谓傲气,她玩命式的自我堕落、沉沦,她后来的一系列的悲剧都是因为她没有一个自己的价值世界,没有魂。在水塔强奸案件中,仙女是受害者,柳生和宝润是加害者。不过,由于仙女的父母没有是非观念,因为一点小钱,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指认宝润是唯一侵害人,仙女也由受害者成为加害者。这一事件凸显了仙女成长中最大的问题——她的生活中没有价值原则,她的所有行为或随波逐流或随心所欲。从仙女成年后的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也并非厚颜无耻、十恶不赦之人,她心中仍然残存一点孟子所说的基于仁性之仁德羞耻之心、是非之心,如在对待庞先生的事情上,她仍在维护那可怜的一点尊严。仙女心中那点残留的人性之仁,无法为她提供能让她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如何对付这个世界,如何对付这个世界上的人,除了恨,她并不知道其他的方法”,她以恨对付世界,世界回报给她更多的恨,恨成了她生命的主色调,这就是她悲剧的根源。仙女为什么对世界充满仇恨,这正是她缺乏对生命的正确理解。
三人之中,柳生家境最好,他的父母对他的关爱也较多,但他同样无法逃脱缺少真正有意义的生活的困境。三个没有灵魂或者说揣着扭曲的灵魂的年轻人,因为一个偶然的错误——拿错照片——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的成长之路上演了一幕悲剧,而悲剧的根源是他们没有灵魂。他们为什么没有灵魂,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只能给他们肉体而不能帮助他们铸造灵魂——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世界,以应对外界的各种挑战?这一问题,虽然在《黄雀记》中没有深入探讨,但在苏童的另一部成长小说《城北地带》中得到深刻的揭示:是前社会主义时期各种运动造成的价值混乱、道德失范导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缺失,最终导致这个时代青年人的成长问题。
也许金兰在性生活上、性道德上有一些问题,但不管她在这方面有多大的问题,仍属于个人问题,是民间价值规范范畴的问题。不过,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官方价值体系大大膨胀,将本属于民间价值体系的领域侵占了。“哪天再搞运动,我非要在那骚货脖子上挂一串破鞋,让她挨批斗,让她去游街,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治不了一个骚货?”用无产阶级专政去治一个所谓的骚货,显然是政府权力的越界。这种越界不仅侵害了个人的权力,而且损害了国家权力的威信、公信力,国家权力沦为可笑、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那些被传统价值观念指责的东西,因为获得了官方价值体系的支撑,一下光芒四射。小拐本来是一个小混混,在学校不好好学习,遵守学校制度,亵渎老师;在社会上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无所不为。后来,因他揭发老康为反革命受到市政府的表彰。他回来的那天,“香椿树街两侧时时有人朝王家父子点头致意,那些人的微笑友好而带有几分艳羡,王德基觉得几十年来他在街上第一次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荣耀,这一切竟然归功于儿子小拐”。这样一个无赖、混混,一下成为英雄,将传统价值体系的善恶、是非观全部颠覆了,而老百姓却接受了,这表明他们价值观念本身的混乱。这种官方价值体系过度膨胀造成的价值混乱、失范,也出现在学校。按照社会主义新人的价值标准培养年轻一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将社会主义官方层面的价值标准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全部标准,就有问题了,香椿树街的东风中学的问题也在此。东风中学不是没有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教育,而是这种教育大而不当,对学生根本就没有作用。就拿小拐来说,他的价值观是严重扭曲的,他缺乏作为人基本的、也是人普适的是非、善恶观,也缺乏作为一个中学生所必需的纪律观念,学校应该对他进行的是这样的基本的道德教育。不过,学校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当小拐被开除又重新回到学校时,学校考虑的是如何以小拐作为试点学生,将他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按理说,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应该不能抛弃那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应该是建立在其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没有这些,社会主义新人也只能浮在空中。对此,作者深有认识,为此他设置了老康这样一个人物。当叙德的母亲丧失人性用梳子捅金兰的下体时,香椿树街没有人阻止,他们只热衷于看热闹,只有“老康声嘶力竭地对那里喊:沈家嫂子快住手,你会犯法的”,这表明老康没有丧失一个普通人基本的道德感、责任感和良心。老康还作为一面镜子,照出那时教育的问题。“老康惊愕地望着那群老师,他说,孩子不教不成人,现在学校连《三字经》都不教,孩子们善恶不分,他们怎么会学好呢?”老康对当时教育的批评,也代表了作者对教育的看法。学校连基本的道德教育、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的教育都没有,却大谈社会主义教育、“革命教育”,这显然是本末倒置,最终使大谈成了空谈,学校最终丧失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功能。城北地带价值观教育的另一问题是教育者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思想教育、道德教育都属于价值理性教育,价值理性不存在工具理性那样的客观真理性,价值理性教育的效果与教育者本身的道德、人格魅力有关。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自己首先应该有他认可、信奉的道德规范、道德信条,然后去传播它,这样才有感染力、说服力,让受教育者接受。如果教育者本身没有自己认可的价值或者价值混乱,就很难说服受教育者,所谓“以之昏昏”、“使之昏昏”。“城北地带”的家长和老师都存在上述问题。对于家长而言,他们应该教会孩子如何去爱、诚实守信、友善等与社会和睦相处的道德素养,但我们知道,在前社会主义时期,这些中国传统的为人之道被当作封建意识受到批判,那时主流意识弘扬的是大公无私、爱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做贡献,这些东西并非不好,但它只是国家层面的道德要求,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它不能取代老百姓教育孩子的价值体系。父辈从祖辈那里以耳濡目染承袭下来的道德失去了合法性,而国家层面的那一套东西他们又不甚明了,因此他们不知道应该拿什么教育自己的孩子。教师除了这一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强调教育双方的平等地位,但我们也知道还有所谓向师性就是的问题。所谓向师性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假定了教育者的道德优先地位,即他们是经过社会机构、权力机构认定、授权赋予其具有较高的道德觉悟、道德水平的公众形象。为什么要“尊师”,那时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拥有更广博的知识,还拥有令人信服的更高的道德境界。在“城北地带”的黄金时代,“师道尊严”是封建思想,受到批判的。小拐虽然从不好好上学,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业成绩很差,但他学会了“文革”的那套逻辑,用“资产阶级法权”、“师道尊严是要批判的”半生不熟的政治口号,轻松地击败了他的老师。李老师、教导主任之所以都无法制服或者说教育好小拐,原因就在于教师已经被打成“臭老九”,他们作为教育者的资格首先就受到怀疑,他们能不能承担“革命教育”的任务同样受到质疑。处于如此尴尬境地的教师,当然不能教育好学生。

《黄雀记》不仅以寓言的形式,反映了当代国人心灵史的重大问题,也用寓言的形式呼吁:重建民族的灵魂。
她想,一定是两根死人的骨殖在向她呐喊:
捞起来
捞起来捞起来
捞起来捞起来捞起来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建构性价值取向看诗意江南的失落与重建——以新时期苏州小说创作为例”(090- 2015SJD6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宏图:《转型后的回归——从〈黄雀记〉想起的》,《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②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3页。
③苏童、王宏图:《王宏图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④张新颖:《重返80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⑤张清华:《天堂的哀歌——苏童论》,《钟山》2001年第1期。
⑥苏童:《黄雀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⑦苏童:《黄雀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页。
⑧苏童:《城北地带》,http://bbs.jcwcn.com/thread-37634-1-1.html。
⑨苏童:《城北地带》,http://bbs.jcwcn.com/thread-37634-1-1.html。
⑩苏童:《城北地带》,http://bbs.jcwcn.com/thread-376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