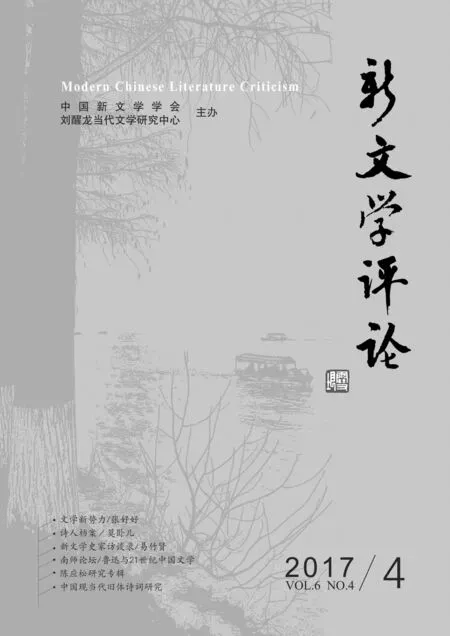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淮水谣》:一曲乡土灵魂的无声挽歌
2017-11-13路文彬
◆ 路文彬
多年来,曹多勇始终未曾偏离过对于大河湾的书写,这片属于淮河流域的富饶乡土俨然就是其不竭的创作源泉。他属于大河湾,大河湾也属于他;他成全着大河湾,大河湾也造就着他。在这漫长的历史书写过程中,我们已然无法将其同大河湾剥离开来。大河湾便是曹多勇的文学符号,是他的精神原乡,而他则是大河湾历史波涛最虔诚的聆听者。在曹多勇的笔下,大河湾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存在,更是一种时间的存在。与当代众多乡土风情的书写者相比,曹多勇的不同正在于他针对后者的高度关注。不难看出,尽管深深扎根于这片泥土,曹多勇的空间意识实际上还是相当淡化的,他极少凭借空间的视觉描述来展开自己的叙事。之所以如此,我想无非是因为曹多勇的文学观是存在性的,而非占有性的。要知道,空间依赖视觉的关注,需要欲望的盛放,但时间等待的却是倾听和耐心。
曹多勇的耐心恰恰来自时间的馈赠,而对于历史的关怀同时赋予了其在文字上的无限深情。他不必刻意去书写爱,还有比耐心更为持久的爱吗?他的空间只能隐没在这爱的时间长河里。河流不可能静止,所有的爱都纠结着逝去的痛苦。基于此,《淮水谣》(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让我们经由空间的脆弱见证了爱在时间中的显现。的确,倘若没有拆迁,我们或许永远不可能知道吴水月对自己清贫家园的这份热爱。在难以抵挡的时代大潮面前,这个不堪一击的女子仍毅然坚持保留着自己最后的一点权利,即死后要能葬在自家的土地里:“她说她喜欢淮河水,不怕淮河发大水淹进棺材里。她说她喜欢听淮河浪的哔嘘、哔嘘声响,死后睡在自家地里就能听得见。”即便活着被迫离开,只要死后可以重归故土,吴水月似乎懂得,活着仅是暂时,而死亡却是永恒;死后无法看见,但却可以听见。那么,是谁在听呢?当然是灵魂。
毋庸置疑,吴水月想用抗争告诉我们,她是一个拥有灵魂的生命。在这个普通乡村女子的身上,我们得以洞见的乃是女性同历史以及听觉的古老原型关系。女人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归属,倾听是她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值得信赖的交往方式。在她所属的家庭里,吴水月无论是作为女儿、妻子还是母亲,从来都不是一个掌控着绝对权力的人;然而,灵魂启示的声音却引领着她权利的方向。权利无需发号施令,它只需倾听和行动,因此,吴水月用毕生的时间行走在履行权利的道路上。她可以不服从某些权力的指示,但是不能不服从权利的诉求,这权利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老天爷的旨意”。吴水月不算是一个多么精明的女人,可却有着女性历史成就的先天慧根。她在进行绝育手术前经历的“过日子不安心,总觉得家里会出事”的莫名焦虑,表明的正是一种潜在的原罪感。冥冥之中,她能够领会那最神秘最安静的真理。她的丈夫韩立海一直无法明白妻子的许多言行,根源即在于他从来就没能懂得倾听,他只会观看,永远驻留于心灵之外的视觉占有。
乡土里没有女权主义,这是一个只信服身体力量的场地,在此,柔弱的吴水月们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再则,为了倾听,吴水月压根也不能多说。可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在吴水月死后,韩立海反倒学会了倾听:“吴水月死去就埋葬在她生前选择的这块地方。夜深人静的时候,韩立海会走过去,站在吴水月坟前,仔仔细细地听一会隔着堤坝远远传过来淮河浪声,哔嘘——哔嘘——一浪推动一浪,节奏感很强,声音很响……”通过这种静听,韩立海平生第一次距离妻子如此贴近,他不知不觉走进了妻子的灵魂。此外,他也因此意外收获了自己的灵魂。在死亡的沉默中,韩立海这个男人终于学会了聆听,妻子用自己的消隐完成了对于他的引领。他在妻子生前所看见的一切,迟迟阻碍着他向妻子向自身的靠拢。从此,能令这个男人感到亲切的,也许只有黑夜和静默了吧。
是的,时代的白昼变得愈发喧嚣,韩立海的内心世界则变得愈发沉静。时间不言,大爱自现,儿子韩新云在工作和婚姻上的不顺着实让他担忧,但这担忧却再也不是烦扰的言说。小说中这样写道:“有一次,大儿子韩新云从古城回家看韩立海。韩立海蹲在灶锅前添火烧锅,韩新云陪着韩立海蹲在锅屋里。爷俩不说话,都伸头看着灶里的火苗,一伸一缩地、一深一浅地舔着黑乎乎的锅底。韩新云忽然地在韩立海眼睛里看见两团明亮的泪光,韩新云站起身不声不响地回了古城。”我不想把此处的父子默契归因为作者情感上的细腻处理,而更愿将其理解为韩立海在作品中的成长。在懂得沉默和倾听之后,韩立海才真正成长为了一个父亲和丈夫。事实上,他作为丈夫和妻子的交流,恰是在后者死后方才真正开始的。吴水月自始至终未曾离他而去,她在肉体上的消失只是为了灵魂永久的陪伴。不然,他的丈夫韩立海又何以成长?成长是认知的过程,认知伴随着爱的理解。韩立海对于妻子的爱,便是在他渐渐认知妻子的进程中得以开始和深化的。
“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歌德这话说得没错。吴水月一直就走在前面,只不过那是她的灵魂,在身体上,她常常是落后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的。她不用去征服,所以不必在乎要去往何处?她也不用操心自己来自何方?因为她的心始终向着归宿。归宿时刻成就着她的服从精神。虽说吴水月可能从未曾想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中心,但归宿却注定了她的中心地位。多年之后,韩立海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一天,韩立海觉察出这么一件早已存在的事实,吴水月死后埋在这里,不只是牵扯住他一个人,甚至连着四个孩子都多多少少被牵绊着。”吴水月每年忌日的阖家团聚,何尝不是一种针对征途的召唤?它让这些被时代裹挟着沉浮挣扎的孩子们稍稍回下头,谛听片刻来自归宿的心声。母亲成为归宿,终是为了不让自己心爱的孩子在征途上迷失。
借助吴水月这一朴素的女性形象,曹多勇写出了乡土的实质,写出了乡土的灵魂,然而她的离去确也暗示了乡土黯然的悲剧性命运。作为归宿,难道它必须以消隐或丧失的结局收场吗?在发出这一质疑之际,曹多勇保持了极大限度的情绪克制,因为他明晓这正是乡土的本色:它不言,它承受。故此,他的叙述是平静的,节奏是不变甚至有些单调的,犹如淮河水浪那时强时弱的“哔嘘”声,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显然,曹多勇深谙听觉哲学的真理,在倾听的世界里,多变和繁复是不受欢迎的。于是,他以敢于拒绝的姿态,选择了看似有限和贫乏的写作方式。但我坚信,这恰恰就是曹多勇的文学价值之所在,在他所提供的文字表象里,其实蕴含着极大的丰富性,只是此种丰富性有时是以某种深刻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罢了。我以为,真正优秀的作家一定是在有限和单一中去寻求无限丰富性的,毕竟自由是在有限而不是在无限中得到保证的;那些盲目追求无限和丰富,从而失去鲜明个性的太多当代中国作家是完全不自信的。可以看出,曹多勇对小说创作有着相当清醒的自我认知,他十分清楚小说和作家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换言之,他了解自己的局限,就像他了解乡土的局限,但在坚守此种局限的过程中,他却将不足转化为了特有的从容和自信。他不温不火,不追随主流,不刻意模仿哪位作家,他只需向自己的大河湾学习,专心聆听淮河深处那永不停息的反复旋律:“哔嘘——哔嘘——”他的不厌其烦,他的不知倦怠,最终使他成为当今文坛一位深刻的乡土书写者,相较而言,那些刻意浸淫于乡土欲望的写作者皆是媚俗的乡土背叛者,他们的写作仅仅属于虚伪的语言游戏,是现代都市心理投射在乡土上的一道疤痕式阴影,这道阴影注定进入不了乡土阳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