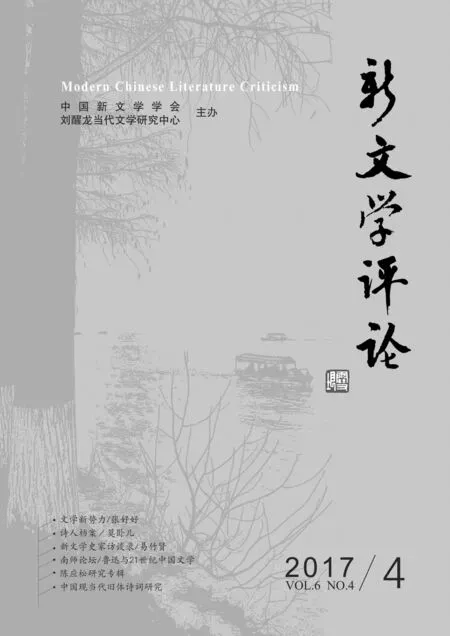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吃人”的复活与永恒的现实精神
———从《狂人日记》到《黑石头》
2017-11-13王学森
◆ 王学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狂人日记》将历史真实的“吃人”转化成文化意象,从历史的渺茫、麻木和陈旧中挖掘出“吃人”的现代意义,树立了人性/非人性、进步/愚昧、现代/野蛮的意识。鲁迅之后,作家们对“吃人”仍有持续书写,其创作模式基本还是延续着《狂人日记》的“批判”特征,把“吃人”看成既定的文化象征和审美资源。但在新世纪的文学界,杨显惠于2004年第4期开始在《上海文学》上连载“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小说,第一篇《黑石头》就写到“吃人”,使用的是纪实手法,大异于《狂人日记》及其类文本。这一对灾难、饥饿、恐惧的直写,在新世纪的创作、批评语境中趋于边缘的位置,但其现实精神却十分明显。无论是文学评论还是文学研究都表现出对作家、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有所遮蔽。那么,当代文学是否真的有了自足的审美语境,而大可舍去对生存基本条件的写实关照?当代社会是否真的已经完成了现实的救赎,而不再需要一种再现的或者是写实性文学的声音?作家的创作应该是个人性的、隐蔽的,还是公共的、开放的;应该是自我表现的,还是社会性的?这些问题一直都有探讨的价值。“吃人”这一题材既触及生命的最初威胁又指涉现代社会的文化变异现象,对其观察既能是社会现实的又能是文学审美的。因此,它本身的多种可能性为研究文学现状、作家心理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也为探讨时代精神、社会文化心理提供了恰当的话语资源。
《黑石头》的写实取向
对于创作资源来说,“吃人”是一个奇绝的素材,非常适合进入人性的深处阐释社会弊端,也非常符合当下小说创作对嗜血、荒诞、虚无、审丑的偏好,但杨显惠却选择了写实的创作手法。《黑石头》描写的是一个关于饥饿、吃人、进孤儿院的故事。这篇小说以小女孩“巧儿”为视角展开描述,其中讲到一位母亲吃掉了自己的孩子的场景。作者分三步塑造了“吃人”场面,渐次丰满,深入人心。第一次是巧儿和母亲给死去不久的父亲“烧纸”回来,刚到家中的场景:
那天我和娘进了院子关上大门,刚进房子,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突然从院子里冲进了房子,拿个灰爪打我和我娘。我娘吓坏了,噢地叫了一声,往炕上爬。虽然天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但是我感觉出来她是谁了,就喊了一声:这不是扣儿娘吗!那人看我认出她来,扔了灰爪转身就走。我心想扣儿娘今儿是咋了,就跟出去了,一边走还一边问她:扣儿娘你打我咋哩?你打我娘咋哩?扣儿娘不说话,拉开门栓走出去了。
第一次读者没能立即进入“吃人”的恐惧中。巧儿娘说:“她是想把我们娘母子打死,吃肉哩!”巧儿不曾震惊,还反问:“庆祥说,扣儿娘把扣儿的弟弟吃了肉了,真事吗?”此处虽然没有写出血淋淋的现场,但是读者从母亲的叹息中,大体猜到“吃人”已成事实,并拥有了“拿个铁爪”、“披头散发”的形象。这一印象对阵于岌岌可危的生命,带来了直接的恐惧感。第二次刻画十分短暂,与第三次“吃人”事实的讲述连接紧密。
那还是我和我娘拆房子卖椽子的时候,庆祥和吉祥到家里来找我,说是拾地软儿去。那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拾地软儿,还叫着扣儿。所以那天我们路过扣儿家的大门,庆祥和吉祥又跑进去叫扣儿了。
我没进去,自从扣儿娘拿灰爪打了我和我娘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她家的院子。我害怕扣儿娘。扣儿娘的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人们都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人们还都说,扣儿兄妹五个人,两个哥哥跟他爸讨饭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死了,白天扔到山沟里了,晚上她娘又抱回家,煮着吃了。
此处添加了生动的相貌描写,“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文中紧接着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这里使生者对死、对人身攻击的恐惧更为形象、可观。“人吃人”是对基本生存环境的破坏,比强盗来袭、官兵屠杀更具威胁性,是人性基础的崩塌,彰显了原初的恶面孔。人类用漫长的时间,用各种方式——价值约束、法律制裁、符号设定来阻止人类流露这一特征,同时又用温饱、舒适、爱、尊重、自由等理想价值来教育、引导、诱惑人类发扬善的一面。可以说人离开了原初的自然竞争,而习得了文明的生存方式,其结果便是我们能够机械化地控制自然,但却丧失了面对野兽、强暴、凶残的还击之力。因此,“人吃人”将会产生无以复加的恐惧感,可想而知,新世纪读者看到《黑石头》会表现出怎样的时代表情。紧接着,第三段的刻画将恐惧感上升到极致:
他(庆祥,巧儿姨家表哥)说他进了正房没找到扣儿,出门一看灶房的门缝往外冒热气,他就又往灶房找去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听见门响,转过脸来问他做啥。他说找扣儿拾地软儿去。扣儿娘说扣儿去舅舅家了。他有点不信,昨天还一起拾地软儿的,便问了一声扣儿啥时间走的。扣儿娘说今早走的。他又问跟谁走的。扣儿娘说,你问这么详细咋哩?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是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话骗他哩,就又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后来扣儿娘又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
文本中扣儿娘的冷静与锅里咕嘟嘟的响声、扣儿娘的少言寡语与庆祥的连连发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深了读者对扣儿娘的恐怖感。同时,文中又通过庆祥的无知、扣儿的辫子与水缸后的空空如也,构成了一幅恐怖的画面,作者并没有将血、头皮等写实,而用简单的几个点和物件架起了剥人的场景,大片的留白给予了读者滋生恐惧的无限空间。他没有设定恐惧程度的顶点,而是让读者自己在想象空间中走向恐惧的巅峰。三个部分描写得十分冷静,一层层地让我们看真了一位吃人的母亲。
与杨显惠同时代的作家中有一位也写到了“吃人”,两位作家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变迁,面对过相同的创作资源,但两位作家作出了不同的文学选择,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吃人”作品。如果说杨显惠展现了真实的人间场景,那么鲁迅表达的是对现实虚伪的怀疑;如果说《狂人日记》尽管迷狂,但尚有一个觉醒者,那么莫言的《酒国》则完全是一个炼狱,只有一条知识分子的堕落之路。《酒国》以“红烧婴儿”事件起始,呈现了“卖婴儿”、“宰杀婴儿”、“红烧婴儿”的细节,同时讲述了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在酒国如何从正气凛然到毫无反抗力,如何被玩弄、陷害,最后走向疯狂、迷失,提出了“官僚吃人”的象征意味。小说比《狂人日记》更加荒诞,语言更飞扬,行文有一股不羁的野性,流露出暴力、血腥、性、丑陋等审美风格。显而易见,这与杨显惠作品的简洁、质朴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
《狂人日记》的伦理现实意义
当然,不能使用单一标准衡量、评价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作品,而应基于创作个性与时代背景展现出各自的复杂性、独特性。尽管有时他们的表达方式截然相反,但本质上还有很多相通之处,即在现实世界拥有近乎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只是面对文学性与社会性的选择时,做出了不同倾向的策略性权衡。
对于《狂人日记》中“吃人”的理解,学界最先提出的是“礼教吃人”的观点,即使他们注意到历来的“吃人”事件,也没有从文本内部阐释其与封建礼教的细微关系;后来有些学者强调了“吃人”的历史现实属性,发展了“吃人”母题的研究,并引用鲁迅与许寿裳的通信来佐证。两种说法在各自的批判视角和伦理目的中展现出充分的合理性。前者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展现了《狂人日记》的文化批判意识;后者则从文学母题的角度,考察“吃人”的社会学意义。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吃人”既是写实又是象征。从鲁迅思想的整体观上来看,这种说法确实合理,但也忽略了文本内部的意义。而在《狂人日记》中,如何用小说方式来填平“吃人”与“礼教吃人”的鸿沟才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即“徐锡麟被吃”、“狼子村挖人心肝”等具体行为如何对立于文化意识。《狂人日记》通过“我”的怀疑和反思——“我”将要“被吃”、“我”已经参与了“吃人”,把外部的“吃人”事件转化成人的心理活动。同时,“我”与家族伦理道德的摩擦,亦形成一种心理活动。心理活动在个人体内的相互融合、印证,便形成了由外而内再向外的价值连接,现实的“吃人”也就比附到了“家族礼教”的身上。对于小说的文学性,鲁迅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显然这里有鲁迅自谦的成分。但从创作意识来说,鲁迅并不局限在现实事件本身,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如此看来,鲁迅并非为了具体探讨“吃人”的人类学意义,只是找到了批判封建传统的武器。因此,鲁迅的“吃人”既不是对历史现实的记录,也不是单纯的象征体现,而是以自我的桥接点进行的伦理现实的重建。


《酒国》的文学性策略

这一策略性选择首先是来自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七十年代末至整个八十年代,文学去政治化以及文学主体性的潮流在学界占据着重要位置,知识分子的回归带来了对“五四”的重新想象,自动区离开主流政治话语,因此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反抗性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由于知识分子、作家已经没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他们对社会现实逐渐表现为失声或策略性表达。同时,西方思潮和文艺手法的一拥而入,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广阔的生存空间,除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手法之外,作者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是“文革”结束后作家梦寐以求的创作理想,并且对于文学手法、文学审美的追求也避开了与意识形态的直接对抗。其次,经济时代与大众文化的盛行扼制了知识分子的话语。信息化时代没有到来之际,文学迎来了短暂的兴盛期,自由知识分子拥有了一定的文学声音。不过,由于经济时代对快餐文化的贩卖,对文化英雄的制造、利用,以及对知识分子从话语权到生存环境的扼制,造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褪色、转化和沦落。它以生活保障、健康医疗等等最基础的生存条件羞辱、调戏、唾弃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尊严,剥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另外,大众文化迎来“盛世”,大众创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心甘情愿为之消费,给国家财政和创业者带来的巨大的财富。而知识分子的创作在经济效益上远远不及大众文化,因此必然会在国家、大众层面失去话语能力。作家们为了“谋生”,习得了血腥、暴力、丑陋、恶心的审丑趣味。他们利用审丑带来感官、心理的刺激,挑逗、吸引、迎合大众读者的阅读品味。当然这种转变过程十分复杂,不是一时完成,亦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但从语境来看,或者从莫言个人及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这一描述基本符合现实状况。这里不是贬低大众的文艺素养,而是说严肃文学已经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创作者和接受者,这对文学史来说意义重大,严肃文学的现实意义不得不走向边缘。

“写实性”的时代觉醒价值

同时,杨显惠没有把“吃人”作为描写的全部,也没有树立以“吃人”为阴暗面的价值观,而是以生命的多样性和广博来生活化地对待每个人。在饥荒的后半时期,国家为了减少死亡人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个是在各地区开办孤儿院,收留失去父母的孩子。“福利院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吃一顿糜面馍馍,后晌一顿汤面,有时候是棋花块块,有时候是柳叶子片片,饭里还有不少洋芋疙瘩。顿顿都能吃饱。”这个消息触动了巧儿妈妈赴死的念头。在死之前,她给女儿赶做了一条又厚又长的棉裤。杨显惠赋予了母亲简洁的语言,就在这简单平淡中流露出生的艰难和无奈。
我换了,把新裤穿上了,但是娘絮的羊毛太厚了,我的两条腿变成两个棉花包子了,上炕下炕弯一下腿都很吃力。我很不高兴,说她:你把裤子做这么厚,我以后怎么跳房房掐苜蓿?腿都弯不下嘛!
娘笑了一下说,你潮着里,厚了不是热吗?
这也太长了呀!你看,裤腰都提到腔子上了,脚还没出来!我怎么穿?怎么走路呢?

巧儿的母亲之前为了保住“后人”而强活,后来看到以死能够换取女儿的活,则义无反顾地去死。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巧儿的娘上吊自杀了。文中说,“人们都说,上吊死去的人吐着舌头,面孔非常可怕,因为是憋死的,死前无意识的挣扎是很剧烈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都扮出吊死鬼的样子:吐舌头,睁圆眼睛。可娘的眼睛闭着,嘴也闭着,娘的舌头并没有吐出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安详”。她的母亲跪在窗台前,后背比平常直了些,脖子也伸得长长的,巧儿说“娘在没挨饿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挺着身板走路,抻着脖子站立,她的脖子平常就显得光滑并且很长”。可以看得出,巧儿娘死得有尊严,她的身上充满了爱的光芒。虽然是有很多的悲哀,却产生了极大的“生”的希望。巧儿肯定是痛苦的,但是这样痛苦是爱所产生的痛苦。设想一下,此时扣儿娘再闯进她的房子来杀巧儿,那种“吃人”行径并不一定有胜算,读者也不一定会产生恐惧。此时的我们已经被生活的“痛”和“爱”注入了充足的力量,面对地狱时愤怒,面对生活时怀有希望。几十年后巧儿回乡安葬亲人,见到了扣儿娘。并且小说最后说:“扣儿娘现在九十岁了。”一个吃人者,一个吃掉自己孩子的女人,作品始终给予她母亲的身份,并让她长久地活着。这是怎样的一个丰富的,十分痛又十分爱且十分平常的世界。这种世界观是博爱,又是充满生的、希望的。可见杨显惠的手法冷静,但不冷漠,相反他还要承受极大的痛苦。作者给予读者真实的生命感,或建立在真实上的生活归所,就必须走进真实的痛苦,与之斗争,然后穿越它走向生命的光芒处。这一斗争和之后的光明恰恰是现实精神的根本所在。因此,对于“吃人”真实的描写,杨显惠必然要承受这种精神的痛苦,并且他还要走向人类的光明之处。这正契合于鲁迅的生命观——“自我觉醒”、与绝望作斗争、期盼青年、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只是他们所处的社会语境不同,表达“现实”的方式自然也就不同。鲁迅的伦理建构与“自我反抗”是时代的现实,也是文学语境的现实;杨显惠的“写实”、对生命痛苦的穿越呈现在当下时代和创作语境中也正是一种现实精神。



注释
:①杨显惠:《黑石头》,《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②杨显惠:《黑石头》,《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③杨显惠:《黑石头》,《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④如茅盾:《读〈呐喊〉》,《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吴虞:《吃人与礼教》,《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⑤如古大勇、金得存:《“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⑥刘泰然、陈雪:《“吃人”话语的建构与还原——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田耳的〈掰月亮砸人〉》,《长江学术》2011年第1期。
⑦巴朝霞:《“吃人”母题的再演绎及人性的叩问——从鲁迅〈狂人日记〉到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⑧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信中说:“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⑨赵江滨:《关于“吃人”的话语逻辑》,《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⑩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