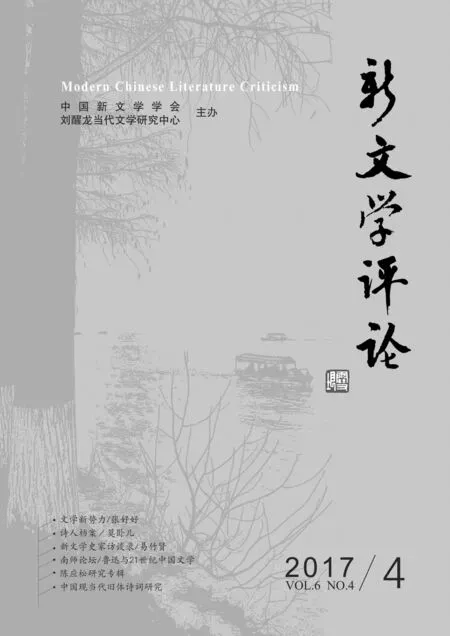猫与妖鸟:超越道德的悲忏
———评张好好的长篇小说《禾木》
2017-11-13◆桫椤
◆ 桫 椤
“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想把隐匿、隐瞒、遗忘了好几个世纪或好几千年的事物显现出来,也不想重新在其他人所说的话的背后找到他们意欲隐藏起来的秘密。我并不试图去揭示掩盖于事物或言说之中的另一层含义。不,我并不只想让即时即刻存在的,同时却又不可见的东西显现出来。我的言说规划是远视者的规划。我想让距我们的目光极近的东西显露出来,好让我们都能看见它,它离我们太近,但透过我们所见之物,我们就能看见另一样事物。让这样的密度成为一种氛围,让这种氛围环绕于我们周身,确保我们能看见离我们很远的东西,让这种密度和厚度成为像透明度那样我们没有体验过的东西,而这就是我们无时无刻不想着的其中的一个规划,其中的一个主题。”
——米歇尔·福柯
一
读张好好的《禾木》,不免令我想起两个人,福克纳和金宇澄。我不是说《禾木》能比肩《喧哗与躁动》或者《繁花》,而在于这些作品中共同充斥着强烈的形式感,它们之间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相近。为什么要谈到形式感,是因为阅读一部作品,我们首先要接触到的就是它的形式而非内容。形式就像一块篷布,我只有揭开这块篷布,哪怕是撩开一条缝隙,才能看到它之下覆盖的东西。对一部小说来讲,形式是先于内容的,我们通过阅读触摸到它的语言形式和叙述的表达方式,之后才可能进入它的意象和情节之中。——形式感!在我的文学观念里,谈到形式,就会产生某种恐惧感,因为紧接形式感的就将是“为艺术而艺术”、“形式大于内容”这样的说法。在并不算久远的时代里,这些观念因为违背或弱化了文学作品被赋予的某种功能而被定罪。在这些观点的角度上,《禾木》就是“有罪”的——它选择了第二人称叙述方式,这显然是一个不常见的写法。关于第二人称,有人认为这并不存在,我也一直没有在各种文学理论词典中找到它的定义,大名鼎鼎的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中它也是缺失的,以至于需要有人通过理论文章证明第二人称的客观存在。这是阅读《禾木》遇到的首要问题,“你”是谁?而又是谁在称呼“你”?是作者在说,还是文中的某个人在说?他们又分别说给谁?
带着这些疑问进入《禾木》,我不得不说作者是个勇敢的小说家。放眼望去,以第二人称书写并进入文学史的作品为数并不多,很著名的一部是法国作家米歇尔·布托尔的《变》。布托尔出身哲学家,所以他选择第二人称叙事与其说是在写一部小说,毋宁说是在进行一种文学试验,来验证文学之中各种不同人称交替写法的可行性。他自认第二人称代表的是读者,用“你”在叙述,是在与主人公交心,对主人公规劝,表达自己的伦理。在华语写作中,高行健的《灵山》也是一个非常少有的第二人称叙事的例子。第二人称叙事的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当下的写作,一贯在追捧顺畅和容易,使用通俗的语言形成平滑、圆润的效果。《禾木》是反潮流的,它的情感基调是出自内心最纯朴的流淌,甚至其“创作感”都不明显,与各种技术流派缺乏必要的关联;它的人称选择则更是一个异类,带给我的就是滞涩和陌生化,辅以绵密的回忆性叙事,整部作品就像一个质量巨大的球体,内里结体紧凑而外形朴拙浑厚。这种特殊的形式选择,决定了这部作品在当下长篇小说写作中的可谈论性。
《禾木》的第二人称写法显然给读者和作者都造成了困难,作者在实施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作为读者遇到的困难,我首先感觉到无法在阅读中摆位,时刻在与作品本身以及作者和人物发生揪扯:我是谁?我是读者还是作者?我如果是读者,“你”显然来自作者的定名,我一面要阅读文本,一面要时时提醒自己,称呼主人公为“你”不是我的意见,而是作者的自作主张。而我如果承认“你”的合法性,则就会成为作者的“同谋”,但作者又有什么权力将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称谓与阅读者联系起来,又代替读者对人物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我揣摩作者在创作中和在文本中的境遇,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作者要克服的首先是作者与隐含的叙述者之间的关系难题,称呼“你”的那个人究竟是作者本人还是叙述者?假如是作者本人,作者就会完全取代叙述者,这是不妥当的,但“你”的称呼则时时让作者陷入身份的迷乱中。作品就在这样的纷乱复杂的伦理关系中被创作和被阅读。我因此有理由相信,作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写法,在于她在进行自我的“设难”:在有可能以传统方式书写的情况下自我设定难度并超越它,从而实现主题的深化——这种深化来自作者本人附身于叙述者对经验进行的独立批判,而并不与依靠经验成长起来的人物面对经验持有相同的态度。
由此可见,是作者的叙事视角决定了文本形式的选择,包括人称问题,也包括讲述和祷告式的叙述语言风格,甚至这种叙述形式本身就接近宗教忏悔仪式的调子。看起来作者置身事外,以一个见证者和“过来人”的角色向一个遗忘了身份的人讲述她过去的经历,但实质上作者的情感态度、道德坚持和审美取向无不体现在每一个词汇和句子中。“设难”的另一个含义是作者对所针对的事物了然于胸,并明白读者的期待,所以敢于独辟蹊径和知难而进。相对于惯常使用的小说表达方式,敢于为自己“出题”,敢于突破自我,《禾木》的选择是一种非常值得称道和讨论的方法。应当说,这种创作的勇气在“先锋文学”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是缺乏的,作家太过于沉迷于自我修筑的金光大道了,可能创新的荆棘之路上人烟稀少。
二
《禾木》从现实入手,讲述了一个寻找和揭秘的故事。“你”通过回忆一个家庭的经历来寻找一个叫“娜仁花”的女人和一个叫“巴特尔”的少年,揭开了萦绕在父母身上隐秘的历史。叙事的重点并不在寻找的过程和结果上,而是用“你”这一代的人生与上一代做对比,反映人性、情感和道德的嬗变。——假如“寻找”的过程用传统的方式当作通俗故事来讲,它再俗套不过:这只不过是一次成功的婚外情。但是,《禾木》在沉静、哀惋和隐忍的氤氲之下,透射出人生对情感的渴望以及对罪感真诚的宽宥和忏悔。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既来自叙事方式的选择对俗世经验的文学性提升,更来自作者所秉持的观念立场。
在我们当下的叙事中,婚外情的出现习惯用来表示人物道德的败坏,或者作为价值多元化、生活庸俗化的证据,但是《禾木》里的婚外情呈现为人性、情感和欲望的自然表达,尽管它应当受到道德的约束,但这种源自本能的情感优先于道德的存在,这是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事实上作者通过“你”的讲述触及了言说的禁忌,即谈论父母一辈的情感问题,何况牵涉并不光彩的婚外感情。在传统小说的伦理建构中,这是一个“雷区”,无论持何种态度,都将使写作陷入两难境地。作者煞费苦心地选择人称和叙事方式与此有直接关系,她的机敏之处在于,将自我的道德意见具体化为某些意象,以此作为自己的代言者,委婉地表达自己对世俗生活的意见,并以悲悯和忏悔替代情感和道德的批判。
《禾木》多次写到动物,实有其物并只作为自然的代言者出现的是真正的动物,但有两种动物的形象超出了作为动物的本身,一是猫,一是虚构的妖鸟。温暖的身体、灵巧的姿态和蔑视一切的神情,猫最大限度地代表着人对情感的向往,而它们对人类无时无刻的陪伴更让走出布尔津的“你”体验到世界的善良和关怀,所以当“你”将猫托运到母亲处,自己回到孤单的现实中时,“你几乎要失声痛哭,你想起十来年的流离辗转,它们一只一只地到来,让你无暇愁苦,让你安然抵达彼岸”。“你”收养流浪猫,一遍遍回忆如何遇见幼小的“六宝”并收留它的过程,它们作为人类感情的代偿者而出现在“你”的身边,它们是“你”情感的寄托。顺着这个思路,我就看到“你”眼里父亲的情感:“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因为一个别的女人慰藉了他的心,他不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拥有过苦难和辉煌岁月的父亲因为承包工程而前往禾木,并在那里结识了图瓦女人娜仁花。“父亲”是善良的,爱家庭、爱孩子,所以他不能选择离婚,而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也不能选择离开娜仁花,就在那样的牵扯中走完他的一生。“你”对父亲的评判是“小平原上的父亲,他从来不够狠。他若狠点,命运一定会好很多”。显然,作为女儿,对父亲背叛母亲的行为是宽容的,“你”也不断说出“谁不热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话来表达对父亲的感情。在血脉亲情面前,道德批判退居其次,情感具有优先权。
人不是猫,世界也并非只被美化为浪漫的情感,作者也不是一个幻想家,因此妖鸟这个意象显示出特殊的意义。妖鸟呈现“鸟”的形象,并被加上了“妖”的属性限制。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猫头鹰和乌鸦有偏见的态度,觉得它们是不祥之鸟,而妖鸟的意象或许从此生发,它被用来被指代欲望。作者数次强调,妖鸟凭借无声的咒语让温良的女性产生邪恶的堕落。一旦被这种咒语击中,“那有获取之心的妇人”就将在劫难逃。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与这个小平原上一个著名的小流氓做了那样的事而退学,成了一个坏女孩,连“唇边笑意里”都“含着毒”;“妖鸟横空飞过”时,“他(父亲)对他的妻说白日里撞见的事。一个妖媚的妇人坐在某个男人的腿上”,“他还说起某年石灰窑里钻进去一个男人,后来另一个女人也钻了进去”。纵然“你”对父亲的感情优先于对他的道德评价,但“妖鸟”这个形象则显示出了作者的道德立场。作者借由妖鸟对传统道德的败落展开了批判,而“世风日下”的社会情境成为父亲情感转移的借口之一,从这个角度上看,妖鸟的背后隐藏的是对“父亲”出轨行为的谴责——但这种谴责因为亲情的存在而很快化作心底的理解,从而获得对父亲的谅解和宽恕——尽管这种理解充满无奈。
妖鸟的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在猫的形象中得到清晰的对照,对温暖的渴望并不等同于现实可行的法则,我因此看到《禾木》并不是一部鼓励或宣扬非道德情感的小说,而是一部忏悔与宽恕之书。妖鸟作为猫的对等意象出现,虽然次数并不多,但其力量足以抗衡故事中非理性情感的蔓延。叙事显然在这里故意走了一段弯路,以隐晦地表达以“你”为代表的作者的态度。如此繁复的书写令人费解,但将“你”放置在传统家庭伦理的位置考量,就看到了“弯路”的必要性。
三
小说应当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仅靠文本力量就能通达到现实世界里看不见的隐秘之所,以“发现那些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作家作为创世者,会站在高远之处为小说选择悬浮运转的宇宙以及它内在封闭的运行规律。所以一个小说世界的品性和温度,比如它是粗犷的苍凉还是精巧的繁密,是感人的温暖还是寂寞的荒寒,取决于它的创世者即作者自身对世界的感觉经验和愿望期待。《禾木》的开头写着三句话:“人类对大自然的悔罪;男人对女人的悔罪;女人对罪恶的悔罪。”我将其看作作者对《禾木》的主题定位。人分男女,作家似乎不应该以性别区分身份,但是能够以忏悔的姿态面对这个世界,女性写作者一定优于男性,男性往往将“无怨无悔”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关于人生罪感和忏悔的书写,这两年最好的作品一是乔叶的《认罪书》,另一个就是张好好的《禾木》了。《禾木》是温暖的,而且温暖的生发是无条件和无界限的。能够将历史的僵硬以情感之火淬炼为温润之珠,甚至将欲望的原罪消解为羞惭的宽宥,这背后作者的女性身份时隐时现——但是诚如陈晓明在论及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表征的文化与美学意象时所说:“很显然,父权制设定的历史动机和目的轻而易举就统合了女性话语。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可能一开始就试图表现女性自身的感情(例如张抗抗、铁凝等),但是宏大的历史叙事所给定的意义改变了女性初始的意向,那些本来也许是女性非常个人化的情感记忆,被划归到历史化的语境中重新指认现实意义。”《禾木》也深陷这种统合和改变当中。
《禾木》是一部女性之书,首先主角“你”是一位女性,所生活的家庭是女性主导的家庭。做裁缝的妈妈带着三个女儿生活在布尔津,唯一的男性是父亲,但是父亲在家庭生活中近乎缺失。计划经济时代,父亲是手工业联合社里的木匠,曾经与母亲同甘共苦,那时的家庭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了,手工业联合社解散后父亲去了禾木包工程。工程完工,父亲不回家,借口还有另外的工程,事实上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了图瓦女人娜仁花。接下来,“你”的家庭就成为一个“母系社会”。在小说中,“你”观察历史和现实的目光呈现出的女性特征,主要在对待父亲和母亲的态度上。叙事焦点对准的是父亲,而将要被原谅的也是父亲,这是一个女儿因女性的本能而对男性父亲保有的无条件的亲切感。相对来说,母亲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你”看到母亲在有关父亲的传闻中一夜老去:“她四十岁开始生白发,不是一根根慢慢生,是百根千根,一夜,她就老去了。”尽管这样,“你”看父亲时还是觉得“不会认为自己的父亲就是败坏的”,而看母亲时则变成“母亲的坏脾气,抱怨语言”。事实上母亲是这场变故的最大受害者,但“你”对此视而不见,对父亲的宽恕是以对母亲的忽视(尽管也多次写到母亲的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或误解为代价的。而对父亲没有离婚的事实,“你”也归因于父亲“不够狠”,而未从母亲的角度做一点考虑。甚至那个因为父亲不伦之爱而被谈论的孩子也被以“巴特尔”——蒙语里英雄或神的名字命名,并视作生命的牵挂,可见对父亲无限度的宽容已近极致,母亲的感觉再次被忽略。
显然,母女间的这种微妙关系明显区别于与父亲的关系,这样的伦理结构创设形成了文章内在的矛盾,甚至导致与作者所宣称的观念的偏离,与“男人对女人的悔罪”这一被宣称的主题相左——父亲对家庭的忏悔表现在这样一句话中:“所以你对他说,父亲的一生不圆满,在最后的时刻,他无人深情致谢,也无人对他深情致谢。”仅此而已——它只是人世间女儿与父亲的正常关系——那仍然是男权社会里的伦理。作者依旧赞同男人的社会地位,男人是家庭的支柱,以至于父亲离家多年及至故去后,女儿仍要寻找母亲之外的那个女人以及可能是他们生育的儿子,事实上是对父亲的牵挂和行为的认同。甚至对娜仁花,“你”也没有丝毫的怨言,仍然设身处地地从她的角度为父亲爱上她寻找理由,“五十多岁的男人也可以是内心脆弱的,是需要人痛惜的”。由此而往,《禾木》中男性是被女性美化的对象,老冲大爷、小曾和布克赛尔的蒙古男人、北戴河遇到的男编辑,“你”的前夫,他们是那么善良,淳朴,宽容,不计较一切得失,甘愿做“你”倾诉的对象,帮助“你”,在“你”想要时给“你”依靠,唯一有污点的男人是父亲——而且他也获得彻底的、宗教般的宽恕。“你”的弹吉他的丈夫与“你”和平离婚并保持友好的关系,这一情节成为父亲与母亲关系的反向对照:徒有虚名的婚姻悲剧没有在“你”的身上上演,这种自我的解放返照的是社会的发展对人性的促进,结束意识形态的禁锢,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感意愿生活的。
我一直在想“你”对待父亲与母亲的态度,假如“男人对女人的悔罪”得以成立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你”站在母亲的对立面,与父亲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向以母亲为代表的女人忏悔。但是因为“你”并不能认同母亲的生活,所以这种忏悔就变得很可疑。“你”这样评价母亲:“她是多么好的妻子,无人能做到。如是你,你会怎样?你说,会离婚。”——“你”已离婚流落四方,而“他”并没有责怪你,在这场分离中“你”对他是心怀歉疚的。从另一个角度讲,父亲、母亲的情感遭遇也成了“你”为自我辩解的方式。作为自足的叙事,我看到其中存在的这些矛盾,但仿佛这些矛盾恰恰才是俗世生活的本来面目,正如福柯所说:“我想让距我们的目光极近的东西显露出来,好让我们都能看见它,它离我们太近,但透过我们所见之物,我们就能看见另一样事物。”张好好在《禾木》之中显然站在现实的远方,与经验形成距离,才得以窥破屋檐下天天发生的无可言表的感情故事,这样由远知近的方法也许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是一种特殊的才能。
四
家庭生活和个人成长经历是张好好喜欢的题材,她的前两部长篇作品《布尔津的怀抱》和《布尔津光谱》也在处理发生在阿勒泰布尔津这个地域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禾木》出现之后,这一组“布尔津三部曲”在反映时代与人的关系,人生成长经历,书写边地童年、少年和青年生活等方面形成了同题异构。关于布尔津的书写也成为辨识张好好作品的重要标志。在当下的生活中反顾历史,通过拉开现实生活与历史的时间距离和生活地理的空间距离,形成对成长经验的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经验进行解构和重建,是小说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责任,也是张好好极为擅长的书写方式。布尔津地处新疆北部边陲,《布尔津光谱》就曾经将小说展开的背景放置在边地开发的历史大幕下,将个人史与民族史和西部的发展史结合在了一起,使得与作者人生经验有着紧密联系的私人化叙事具有了宏大的气象。而在《禾木》中,作者的视野进一步扩大,伴随“你”的成长与迁徙和父母情感变化过程的,是看到道德败坏和自然环境被破坏后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索。所以《禾木》整体上呈现了人类道德进化和生存发展的困境,其中的“寻找”主题则在困境下深化为回归的理想,但似乎小说中这些主题之间存在着矛盾。
在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中,作者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博爱的情感,小说中的“你”对男性怀有美好的憧憬,而对同性也保持了足够的怜惜和仁厚。这一切有一个基础性前提,即在作者看来,发自人类本能的情感和意志大于以道德和法律为基础的社会规约,这在本文中已有论述。这是一种超越性的大胆的思想,并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和政治影响下的社会习俗,这也是《禾木》的特殊之处。在最为基础的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开篇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已经在使用道德标准评判人性,认为人性最初应该是善的。但是人作为自然物之一种,假如不是后世的道德标准,其行为就将无所谓善恶。在人类的进化发展意义上,自然性先于道德性出现,因而人作为自然物的最本能的权利应当首先得到保护,虽然人性应当遵守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但后世的道德和法律并不应该以违反人性为前提。从这个角度上看《禾木》中父亲的情感生活,它是一种天然生发的感情,如果不用道德律条去框定,则它没有罪恶,没有谴责,它甚至是男女之间必要的情感——作者已经在文本中为这种情感的合理性提供了周到的解释——也正基于此,作者才可能以宽恕和忏悔来对待“你”父亲的这段感情,而小说中所有道德视角下不伦的爱情都带有浪漫唯美的一面,甚至全部都是唯美的。在这种观念之下,符合道德要求但是却违反人性的婚姻就成为罪孽,所以“你”的离婚就有了合法性。所以,当父亲和母亲为了孩子和一个形式上圆满的家庭的存在,彼此苦守着一纸名存实亡的婚约,时过境迁之后的“你”重新审视父母之间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时,产生替父亲辩护、替男人向女人赔罪的想法就不足为怪了。
张好好将情感置于道德之上的尝试并非空穴来风,而得自她自童年到青年时代就深受到的自然的影响,自然世界里的客观规律才是作者思想中的律令。从自然地理上看,布尔津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游牧民族信仰中的自然崇拜深刻地影响了作者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所以在作者的笔下,自然永远是美的,而人类成为丑陋的化身。当“你”离开布尔津到内地闯生活,满目所及都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卡莱尔说:“我想我有必要再次说明,自然法是永恒之法:人们决不敢不予理睬这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自然法的和平之声,否则将会受到可怕的惩罚。”但似乎人类已经忘记了这样的警示。这引发了作者深深的忧虑,很多时候小说就在环境被毁坏、草木被破败、动物被虐待和屠戮所引起的作者的悲愤中展开。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表达对自然法的尊崇和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质疑。首先是动植物遭遇灭绝性屠杀和砍伐,“黄羊票”,乔尔泰鱼的洄游遭难,长江野生游鱼减少,圈养黑熊活取熊胆的残忍,对刺猬、青蛙的餐食;“如果有一天大树全毁,即使有大树,但大树顶端全部锯齐,鸟儿无处落足”,“人的心可以坏到见了生灵就杀害”。之后是对物欲横流的人类发展现状的反思,作者说:“人类进程的关键的一百年,文明到来得这样迅疾,大地的腐烂来得太快了”,而“人把九色鹿出卖后,这个世界的灵兽就绝迹了”,随后作者将西天山的美景自然和中原城市做对比,“大家生活在概念里,一句宣言,就糊住了所有的不洁净,黏稠”。而比这更可怕的,是人类对自我的放纵和对自身责任的逃避,人类的狭隘和自私由此可见一斑:“人们把信任交给了城市的创造者,这个‘者’是谁呢?反正掉下去的不是你,不是他,不是她。反正别人的事,永远都是另一个星球的事。”“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善良的,只是观众,‘者’究竟是谁?”在所有的生态文学中,这样直接深刻反思自身,拷问人类道德上的“平庸的恶”泛滥的作品,《禾木》是我仅见。
从自然法到人间法,《禾木》宣扬一种“天赋之权”的自然法则,所以作者引用印第安人的古老歌谣来表达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担忧:“人类啊,最后你只剩下银子,而世界的美好全部消失,这钱你能塞进嘴巴里当食物吗?”但作者所没有解决的,是如何调节人性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从娜仁花到纺织女工,从钻进砖窑里的女人到坐到男人腿上的女人,甚至到妖鸟的咒语对“你”的引诱,在作者看来,天然人性的舒张是以俗世生活中的道德败落为代价的。这是不能简单地用向往“自由”来解释的,因为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自由人,即只遵循理性指引生活的人”,显然,他们谈不到理性指引,而是受到了“妖鸟的咒语”——欲望的引诱,这恰恰是道德所反对的。只有确证了对道德约束的认同,“你”的忏悔和赎罪才有存在的道理;但假如承认情感的超越是道德衰落的表现,对待父亲情感的态度和对父亲的宽恕就显出了悖谬。《禾木》的写作显然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所以通过“寻找”而“回归”的企望变得无所适从。
五

透过《禾木》,连同《布尔津的怀抱》和《布尔津光谱》,我看到了张好好温婉、澄澈又饱含关怀与悲悯的叙事风格。而这种效果的出现,则来自阅读《禾木》的另外一个感受:小说仿佛是自作者心底流淌出来的,没有造作与矫揉,是完全起自自然状态的心灵表达,它或许是诠释人生经验如何升华为文学作品的非常好的例子。尽管第二人称的写法令阅读产生滞涩和陌生的感觉,但私语化的语言又能够对此有所减弱。而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故事性并不强,单从“寻找”这个情节本身来看,甚至都不足以构成一个故事,寻找对象的模糊性使这一行动的完整性受到损害。或者寻找本身只是一个框架,悬挂在这个框架上的部分是父母与下一代彼此不同的人生选择。在作者、叙述者、主人公和读者之间复杂的伦理结构之内,《禾木》开始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展开经验的批判性审美,因为当中牵涉进大量的成长经历,尤其是对幽微的内心世界的描写,使得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发生无可分离的贴近感,作者在其中借助“你”的身影而显形。尽管某些观念的混乱使得叙事逻辑稍有乱象,但保证了小说的客观真实感。在真实性的平台上,两代人无法理清、混沌囫囵的人生被小说浓缩并延展。

注释
:①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kAY1crWkRVjiWo 9OuQzqHztAaDysI1XRidPB_zes8EUIZ9zMk4K_oqMthkaKPrQ2kqVwyTtededCGIA4YmPn_.
②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著,吴松江等译:《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王学勤:《论第二人称叙述存在的客观性》,《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④郑克鲁、董衡巽主编:《新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3编,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⑤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
⑥福柯:《大师之声》第1卷,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⑦张好好:《布尔津的怀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版。
⑧张好好:《布尔津光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⑨卡莱尔著,郭凤彩译:《文明的忧思》,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⑩哈耶克著,冯克利译:《哈耶克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