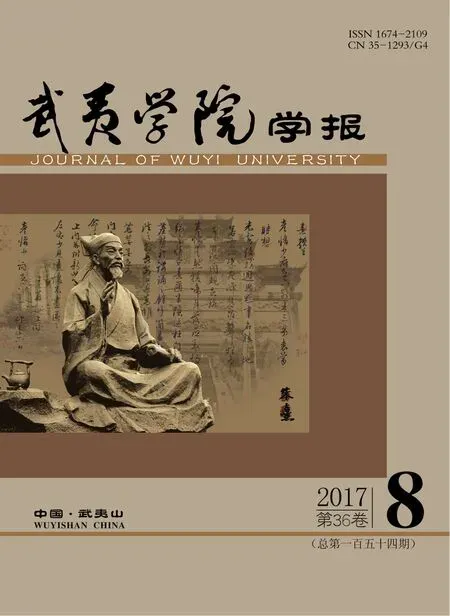清朝后期厦门海防建设论略
2017-11-07许龙波
许龙波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清朝后期厦门海防建设论略
许龙波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厦门是我国海防前线阵地,在海防线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鸦片战争后,厦门逐渐更易原来的海防布置,开始构划近代海防体系。“牡丹社”事件后,厦门海防建设进展迅速,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海防力量。但厦门海防建设主政者的思维还停留在以陆为主的传统基调上,以致厦门并未建成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海防。
厦门;海防建设;清朝后期
鸦片战争,英国人浮海而来,中国战败,厦门被迫开埠通商。战败的创剧痛深,使得厦门的主政者认识到海防对于御敌、强国的重要性。厦门海防从无到有,这经历一个波折复杂的过程。其背后折射出来的历史面相值得深入探讨。学术界对于厦门海防的建设有一定的研究①,但关于厦门海防建设所凸显的观念性问题涉及较少。本文试从清朝后期厦门海防的历史脉络展开讨论,首先对厦门海防的重要性进行分析,继而探讨近代海防危机下厦门海防建设的理念。
一、八闽重镇,海防前线
厦门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九龙江入海口,处于泉州和漳州相交之地,并“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十闽之保障,海疆之要区也”[1],人称八闽门户,闽中咽喉。雍正五年(1727)二月,兴泉道自泉州移驻厦门,管理泉州、兴化二府。雍正十二年(1734),兴泉道增辖永春州,旋即改名为兴泉永道,从此厦门成为闽南政治、军事、经济重镇。
厦门和台湾之间存在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在郑氏统治期间,厦门就是大陆和台湾相互进攻的前沿阵地。郑成功占领台湾后,以金门、厦门作为对陆前沿,“时犯泉、漳”[2]。康熙初年,姚启圣攻占金门和厦门后,就以之为攻台基地。台湾纳入清朝的管理后,厦门更是作为清政府对台湾进行有效管理的中心。康熙22年(1683)清廷设立福建水师提督衙门驻防厦门,康熙23年设立台厦兵备道,管理台湾和厦门两地的政务。一旦台湾发生动乱,厦门往往是清军出发之处,如康熙60年,朱一贵在台湾发动叛乱,朝廷便派遣“施世标由厦门率水师六百艘进攻”[2],七日而克。此外,在军事上,台厦之间,澎湖是漳州和泉州的门户,台湾为澎湖的唇齿,唇亡齿寒,若台湾失守,则“不特澎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3]。而厦门“为漳郡之咽喉……同安三面环海,金厦尤为险要,门户之防也”。[4]可见澎湖障厦门,厦门关漳、泉的这种递进、相依的关系。此外,当时台湾是大陆的粮食储备地,大陆的船只从厦门出发,“配运台谷以充内地兵糈;台防同知稽查运配厦门,厦防同知稽查,收仓转运”[5]。1839年,巴麦尊表示占领福建,以便切断台湾米粮的供应——这种供应是福建人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台湾是厦门商人贩运稻米供应本地区消费的航程最短的地方”[6]。可见台湾与包括厦门在内的大陆地区存在一种“相依为活,合之则两全,离之则两伤”[7]的关系。
就陆地效应而言,厦门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重要的海防地位。“福建用兵海上较他省为多,……岛屿星罗,处处与台澎相控制,故海防控制尤为繁密。”[2]而“泉州重在金、厦二岛。金、厦二门,远控台、澎,近卫漳、泉,为海防重地。”[2]当时的地方志编纂者就充分认识到了厦门的陆地效应,道光《厦门志》称厦门为“洵泉郡之名区,海滨之要地”[8],《鹭江志》也认为厦门“高居堂奥,雄视漳泉”[4]。
从经济角度看,厦门是一个天然的良港,是福建重要的商贸中心。厦门港分为内港和外港,内港深入厦门本岛内部,通过海湾与外海相连;外港沿海岸线展开,是重要的物资进出港。从厦门出发的国内航线分为南线和北线,南线是“贩货至漳州、南澳、广东各处”,而北线“至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登莱、锦州”。[5]可见厦门同南北各地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关系。1832年英人胡夏米在厦门停驻的时候就发现每天“有一二十艘三百至五百吨的帆船进港,装载大米和糖”,他还令人计算船的数目,发现一周时间里入港,吨位在100到300吨的船不下400艘,“其中大部分是从满洲来的沿海商船”[9]。在清朝,厦门同国外的商贸往来也特别频繁,特别是从康熙23年 (1684)到乾隆22年(1757)这段时间清朝开海禁,时“厦门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其地如噶喇吧、三宝垅、实力、马辰、赫仔、暹罗、柔佛、六坤、宋居朥、丁家卢、宿雾、柬浦、安南、吕宋诸国”。[5]不难看出,厦门在清朝前中期与东南亚地区密切的贸易关系。乾隆22年(1757),清政府闭关禁海,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厦门因此而衰落,但是保留了和吕宋的商贸关系。这一时期,大量外国商人通过贿赂本地官员,进行走私活动,清政府的禁海令收效甚微。到乾隆47年,清政府“只好许各国商船按照粤海关则例征税,前来贸易”[10]。
厦门重要的商贸地位,也被英国人所看重。当时有英国人描述:“在中华帝国内,富有而进取的商人,要数厦门最多;他们散居沿海各岸,并在它东面群岛的许多地区建立了商行。大部分名叫青头的沙船是厦门商人的产业。”[6]更有甚者,道光4年(1824)三月,“有甲板夷船在洋游奕,载卖鸦片烟土”[5],后被巡防驱逐。1835年6月,英国商人就致书外交大臣巴麦尊,建议英国政府取得在厦门的通商特权,以此作为对华贸易的基地。
总之,从政治、军事、经济角度来看,厦门都是东南海防极其重要的地区,正如时人所言:“厦门东抗台、澎,北接两浙,南连北粤屯;人烟幅辏,梯航云屯”[11]为东南一大都会。可是厦门却没有建立近代化的海防体系,如《清史稿》所载:“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2]。在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国人的炮火攻击,厦门海防无力还击,最终彻底崩溃。从道光23年(1840)到同治2年(1863)年,兴泉永道被英国人所占据。不过战败为厦门近代海防的兴起提供了动力。
二、近代海防危机与厦门海防建设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形式一变,海防益重”[2]。1863年英国人归还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旧署后,朝廷委任曾宪德为巡道,但因政府认为天下已经太平无事,沿海也是风平浪静,筹建海防之事一再被搁置。直到日本在台滋生事端,意图吞并台湾,面对野心膨胀的日本,为巩固东南海疆,厦门海防建设渐渐提到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国渔船漂流至中国台湾南部牡丹社与高山族人发生冲突,开始派遣军舰从台湾南部琅峤登陆。闽浙总督李鹤年上奏朝廷:“查日本违约称兵之初,臣李鹤年冀其尚可理喻,未敢遽议用兵,现在倭谋显露。恐非大张挞伐,不能戢其狡志,杜其贪婪、为兵釁一开,势必分扰沿海,轮舟往来倏忽,沿海处处可通……先其所急,以厦门、福州为最要”[12]。可见李鹤年是意识到了解决台湾事宜必须靠武力,而厦门防务是解决台湾事件重要的后方支持。当时,清廷派沈葆桢巡台,并且调动7000名淮勇和船政所属轮船舰队赴台,双方相持8个月,日本见难以一时鲸吞台湾,便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要求清政府赔款50万两白银以撤军台湾。
在事件发生期间,李鹤年会同福建大小官员协商,提出了选将练兵、炮台炮位、拦河诸物这三大建设厦门海防的要点。李鹤年指出了厦门海防的情况:“厦门自道光二十二年失守之后,炮台一律毁平,并未重筑。铁炮尚存十余座,炮门皆已钉毁,不可复用。况洋船坚炮利,日新月异,断非寻常炮位所能制胜。……厦门等处,旧址全无。”[12]可见建设厦门海防毫无基础,李鹤年于是派原漳州镇的总兵孙开华会同水师提臣李新燕妥善筹划布置厦门海防。
对于厦门具体的海防建设,李鹤年认为首先必须在军事要冲建当三合土炮台一座,“至于拦河诸物,水雷为最……惟战守必须兼筹,能战而后能守,炮台水雷,须与铁甲船、转轮炮台、铁船、战船相辅而行”。由于“厦门孤悬海中,南北相距不过数里,洋炮、大炮,可以对穿而过,非有转轮炮台,铁船梭巡海口,辅以轮舟五六只,恐不足以恃”。[12]李鹤年认识到了战船在海防中的重要作用,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可惜在厦门日后的海防建设中,我们只看到了炮台的添置,而看不到战船的增加。这固然有经济上的原因,但更为贴切地说,李鹤年的建议未被上级所采用。
“牡丹社”事件后,日本经常派遣“孟春”“日进”“高砂”等军舰肆无忌惮地闯入福州、厦门港。这更凸显了厦门海防的重要性,当时福建官员上奏朝廷:“福州五虎口百余里外,已有该国铁甲船,在彼游弋。是福州、厦门等处海防甚为喫紧。”于是福建地方官员建议“先拟择要紧筑炮台,饬副将杨廷辉将附近渔人招募成军,免资寇兵”。[12]清廷对此表示允可,由此,厦门的海防建设在鸦片战争战败后三十余年才正式拉开序幕。

表1 1899年厦门各炮台火力情况Table 1 Xiamen Fort fire situation table in 1899
据上可知:首先,厦门的炮台建设时间集中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可见外患对于厦门海防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及厦门海防建设起步时期的被动性;其次,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福建官员的海防观仍是停留在“至防海之法,尤重利器”[13]的层面;第三,从炮的来源看,对外依赖严重。这种情况是当时中国海防建设的一个缩影,1895年刘坤一上奏朝廷称:“各省需用轮船,多向外洋订购,中国船政局每欲承揽一、二只而不可得。”[14]以上种种严重制约了厦门海防的发展。
1875年,根据当时福建官员上奏朝廷的奏折,可以窥见厦门海防的建设思路:“海防之法,以水雷据其入,以炮台击其来,以沉船辅水雷之不足,以陆勇辅炮台之不足,更以乡团助陆勇之声势,大要不外此数端。”[15]可见这完全是立足于陆地上的“防”,同“牡丹社”事件发生期间李鹤年的海防观相比,此时福建官员的眼光已大步退向陆地。
1875年,水师提督李新燕向李鹤年报告了厦门海防具体的规划:“大担、小担两口,孤岛难守,稍近而与屿仔尾与白石头相对,最为扼要,仿筑西式炮台两座,各配大炮七尊,守以三百人。再进而为龙角尾、旗仔尾、曾厝垵、湖里汎、鸟空围、武口,六处各筑炮台一座,安炮五尊。此外五通、刘五店两口,为厦门后路,遵路可达漳泉,各筑炮台一座,配炮五尊,守以二百人”。至于炮台所用的炮和弹药可谓“洋味”十足:“拨新购万斤洋炮十尊,大小铁炮五十尊,以资分布,如再不敷,则购西洋钢炮以辅之”。[15]
李新燕对于各炮台的分工和配置也做了安排:“有警则于大担、小担、梧屿、烈屿之间安置水雷,护以红单拖罾”。[15]他同时考虑到若爆发战争,当水陆结合,一部守炮台,一部扼防陆路。这是厦门一地的情况,若战端一起,还须考虑与周边地区相互协作,特别是“金门与厦门相犄角,向无城堡为入泉必由之路。虽孤悬难收守,而关系亦要”因此派员“踏勘地势,添置炮台、炮位,以期声势联络”。[13]
以上的规划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很多工程在中途因为经费掣肘而被迫停止。1876年,新任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就发现,厦门在“牡丹社”事件后,开始办理海防,“经督臣择要详呈,修筑炮垒,嗣因经费支绌,筑完龙角尾、鸟空园、武口三处即暂停工”[15]。考虑到厦门海防力量的单薄,彭楚汉自行筹款,率领驻防军队续修了鱼仔尾、白石头二处炮台。彭楚汉对厦门海防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不过彭楚汉对于厦门的海防还是没有超出前任专注于炮台的观点。由于彭楚汉在落实计划上颇为有力,使其受到了同僚的关注,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上奏朝廷,称“厦门为闽省藩篱,台湾管钥,亦宜兼筹并顾,以副宸厪。水师提督彭楚汉……威望素者。”[16]李秉衡对彭楚汉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他“秉性忠贞……于水师操练之法既素切讲求,更深得兵民之心……方今宿将凋零,水师将才尤为难得。如彭楚汉之忠清亮直,而又胸有韬略,熟悉江海情形,洵属一时无两。”[17]可见彭楚汉被当时的精英所认同,或也显示出其海防理念是当时士林观念的写照。
不仅仅是朝廷高层认同这种以炮为核心的海防布置,光绪年间朱正元在其《福建沿海图说》也提到:“厦门当漳郡之首冲 (县治在厦门北,安海在厦门东北,则亦泉郡之要冲也)。地形如平原,西有鼓浪屿为屏障,遂成泊船稳港。今于胡里山、白石头等处与隔岸屿尾仔、龙角尾分建炮台,亦足扼外海之来路。”可见以朱正元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对炮台的功效是相当认可。不过他也指出厦门“惟四面水道颇深,水轮可以环行,则不恃黄厝一带可抄炮台后路,亦防由五通舍舟登陆,三十里坦途,长驱向西,形势最为吃紧。若绕道北面,经高崎而南,已据厦门上游,海险亦失。”[18]足见朱正元当时已意识到厦门海防仅仅考虑陆地的炮台布置,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海防危机下厦门海防的两个特点:一是,海防意识的觉醒和海防工程的兴建同外患密切相关,外患弥深的压力使得厦门主政者不得不考虑兴建海防;二是,海防工程的筹划从以炮台为中心,辅以舰船,最后转变成以炮台为主导的模式。
三、结语:海防迷思
厦门近代的海防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起步,1896年,胡里山炮台的完工,标志着厦门的海防工程基本形成体系。但是这种体系是前现代的,其主要着眼于陆上防护,这种意义上的“防”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海防。厦门海防实际要维护的是“陆权”非“海权”。美国海军上校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促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19]即是说,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的控制。③这就是对各国制定海洋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海权论”。清末恰是“海权论”兴起的时期,有人在《海军》杂志上发文指出:“观察各国势力,即以其海上权利之大小定之。何以故?海军强大,能主管海上权者,必能海上贸易:能主管海上贸易者,即能主管世界之富源。”④可是在厦门的海防规划中,我们虽然看到了海军的星火,但是很快就被淹没,或许正如时人所言:“我国自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生梦死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进取、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行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⑤看来是长久的陆地情怀,影响了高层决策,士林思维,或者说清朝走到这个时候已是积重难返。
注释:
① 目前有韩栽茂的《厦门海防百年》和《胡里山炮台与厦门海防要塞》以及黄鸣奋的《厦门海防文化》三本专著,三部书分别从厦门海防工程的具体建设、胡里山炮台与厦门海防的关联性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厦门海防。
② 按《福建沿海图说》记载:“屿仔尾炮台光绪二年建置……十二年又于北面添建一所”。故而将余仔尾分为屿仔尾和屿仔尾北两处予以分说。参见朱正元:《福建沿海图说》,厦门大学图书馆藏,1899年,第41页。
③ 杨志本:“序”,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M].安常蓉,陈忠勤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④⑤ 分别转引自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年,第 1126,1129 页。
[1]周凯.厦门志:自序[M].台湾:大通书局,1984:1.
[2]赵尔巽.兵九·海防[M]//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4114,4111,4112,1095,4095.
[3]顾祖禹.福建五[M]//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4518.
[4]周凯.厦门志(卷二)[M].台湾:大通书局,1984:17.
[5]周凯.厦门志(卷五)[M].台湾:大通书局,1984:166,177,183.
[6]胡夏米.“阿美士德”号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R]//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44.
[7]沈起元.条陈台湾事宜状[M]//魏源.魏源全集(第 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5:608.
[8]薛起凤.鹭江志:总论[M].江林宣,李熙泰整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23.
[9]外交部档案,F.O.17/12[Z]//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29.
[10]孔立.厦门史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36-37.
[11]周凯.厦门志:陈序[M].台湾:大通书局,1984:7.
[12]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五)[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1,2,3.
[13]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六)[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24.
[14]刘坤一.刘坤一奏整顿船政铁政片[M]//张侠.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127.
[15]彭楚汉.奉旨出洋督缉并督修厦防炮台恭折具陈仰祈[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六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23,24-25.
[16]孔昭明.法军侵台档补编[G].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52.
[17]李秉衡.奏呈海防紧要密保水师提督彭楚汉[M]//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中).北京:中华书局,2013:607.
[18]朱正元.福建沿海图说[M].厦门:厦门大学图书馆藏,1899:39-40.
[19]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海权论[M].范利鸿,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
A Brief Research on the Xiamen Coastal Defense Construc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U Longbo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Xiamen is in the coastal front of China.It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astal line.After the opium war,Xiamen began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coastal defense system.After Mudanshe event,Xiamen coastal defense construction developed rapidly,through many years`construction,Xiamen formed a certain scale of coastal defense force.But at this time the main politicians`thinking of the Xiamen coastal defense construction is still traditional,thus in the strict sense,Xiamen coastal defense system is not the modern coast defense system.
Xiamen;coastal defense construction;late Qing Dynasty
E295.2,K252
A
1674-2109(2017)08-0063-05
2017-03-27
许龙波(1989-),男,汉族,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苏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