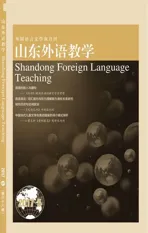理性的合作
——解读合作原则的哲学渊源
2017-10-23孙乃荣
孙乃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131)
理性的合作
——解读合作原则的哲学渊源
孙乃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131)
格莱斯的合作原则自诞生以来所引发的争论和对它的修正从未停止。本文从利奇的礼貌原则对合作原则提出的质疑入手,追溯合作原则背后的哲学渊源,指出从语言使用角度对合作原则提出的质疑忽视了格莱斯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合作原则只是格莱斯意义理论的一部分,意义理论又服务于他的哲学目的,即揭示人的理性本质。合作原则试图揭示言语交际是理性的,合作性是理性的一种体现,对格莱斯原则的正确理解应结合其整体哲学观。
关键词:合作原则;意义;理性
1.0 引言
1967年,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讲座上,英国哲学家格莱斯(H.P. Grice)做了题为“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的讲座,提出了制约交际和理解话语意图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这一原则后来成为语用学界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
格莱斯认为,人们日常的言语交际行为需要遵循合作原则,即根据交际的目的或方向,使谈话的双方符合交际的需要,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才可以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他在康德思想基础上将合作原则之下分为四大类准则(maxim)、准则之下又划分出几小类次准则(submaxim):
(1) 数量类准则:1) 交谈的话语应包含当前目的所需要的信息量;2) 不要使贡献的话语超出所需要的信息量。
(2) 品质类准则:努力要说真话。1) 不要讲你认为是虚假的话;2) 不要讲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 关系类准则:要相关。
(4) 方式类准则:话语要明白清楚。1) 避免表达的晦涩;2) 避免歧义;3) 要简明扼要(避免不必要的冗长);4) 要井井有条。
合作原则的价值在于它系统分析了言外意义的产生,采用了研究语言的新方法,将视角深入触及了话语隐含意义的分析上,为语用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增加了语言研究的实用性,并揭示出交际中最本质的普遍规律。然而,该原则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饱受质疑,不少语言学家从不同视角对合作原则进行批判(Kasher,1976;Levinson,1983;Schauber & Spolsky,1986;Sperber & Wilson,1986;Lakoff,1995;Huang,2004),并试图对其进行修正和改造,先后提出了一些旨在完善、补充甚至替代合作原则的新原则, 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卡舍尔的理性原则(Rationality Principle)、利奇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s)、霍恩的等级原则、斯珀博、威尔逊的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莱文森的会话含义三原则等。本文拟从利奇(Leech,1983)提出的礼貌原则出发,对其围绕合作原则进行的质疑做一简单回顾及分析,在追溯合作原则背后的哲学渊源基础上,指出从言语交际视角对合作原则提出的质疑忽视了格莱斯理论背后的哲学框架,合作原则应结合格莱斯整体哲学观来理解和认识。
2.0 礼貌原则
利奇(Leech,1983:80)认为,合作原则不能充分解释会话蕴涵产生的根源,也不能解释非陈述类型的话语表达的意义与力量之间的关系。为了弥补合作原则的缺陷,解释说话人违反会话准则的根源,他提出礼貌原则以补充合作原则。在他看来,格莱斯的合作原则有助于解释话语的字面意义和语用含义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解释合作原则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违反会话原则的根源,也没有解释听话人怎样推导出话语的特殊含义。利奇把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并列而置,同属于“人际修辞(interpersonal rhetoric)”框架下的第二层次 ,即将格莱斯框架中的抽象总原则作为自己框架下具体原则之一,从而把合作原则的三个层次扩展为四个层次。事实上,格莱斯(Grice,1975)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也提到了礼貌问题,认为讲礼貌(be polite)是参与会话的人通常遵循的准则。只不过他把礼貌准则置于他的四条准则之外,没有进行深入阐述而已。利奇最初也把礼貌当作合作原则的一条准则(Leech,1983:10),后来才把礼貌由“准则”上升为原则,与合作原则置于同等地位。
利奇的礼貌原则包含一系列额外的会话准则,他最初的原则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同情准则、一致准则。随后他提出另有一些重要的准则也应包含在内,如,玩笑准则(banter maxim)、交际准则(phatic maxim)等(Leech,1983:136)。事实上,利奇似乎准备每出现一类实例就增加一条准则。这种数量上的任意性极大地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Chapman,2005:205)。布朗、莱文森认为,利奇的“无限数量的准则”是危险的,这使得他对礼貌原则的补充成为一种详尽的描述而非语用交际的解释性理论(Brown & Levinson, 1987:80)。继格莱斯之后, 解释会话蕴涵的理论一般都是简约论, 尽量缩减会话原则的数量, 以使语用学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给予心理学解释的可能性(Chapman,2005:205), 而利奇增多了语用原则的数量, 因而受到学界的批评。哈伯兰德(Hartmut Haberland)和梅伊(Jacob Mey)就对利奇提出批评,指出格莱斯之后大多数理论趋于简化,而利奇的理论却大大增加了语用原则和类型(Chapman,2005:206)。
礼貌问题受社会影响,与格莱斯的类似语言使用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合作原则界定的是有关言语交流的框架,其基本准则是不能任意偏离于理性,也就是表面看似不合作的行为在深层次是合作的;而礼貌原则正好为偏离提供了原则性(principled)理由。礼貌原则是从语言使用角度推出的,而合作原则是具有哲学基本内涵的高度概括,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类似礼貌原则等 “后格莱斯原则”发端于会话蕴涵理论的某些缺陷,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和利奇一样,将格莱斯的会话蕴涵理论视为语言交际理论,用现实中例子来批驳合作原则的不足,并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这些质疑虽从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语用学的认识,但似乎打错了靶子,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未能领会格莱斯的本真意图。
格莱斯是哲学家,他讨论语言的初衷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主要思想散见于各篇讲稿。纵观其一生思考多,发表少,他所处的写作时代哲学著述缺少背景铺垫,且论述艰深抽象,极少详述。因此,要全面理解其哲学思想就需要研读他的相关著作,甚至需要在字里行间中寻找思想的来龙去脉,而不能仅仅依靠阅读任何一篇孤立的论文。格莱斯曾强调自己的不同研究题目形成一个整体(Chapman,2005:4),我们只有理解格莱斯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将其理论背景和发展脉络梳理清晰,方能对他的任何一个观点予以正确的解读。因此,要深刻理解合作原则就必须将该原则置于其哲学背景下考察,将它与作为哲学家的格莱斯的相关著述联系起来综合考量,才能深入领会合作原则的哲学内涵。
针对格莱斯理论的哲学背景,钱冠连(1999)很早就指出关注语用学研究中哲学背景的重要性,他认为,格莱斯非自然意义理论对于语用学这门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引进其理论不应丢掉其中的哲学色彩。冯光武(2006)指出,格莱斯全部的哲学思想都是以理性为指引的。他从分析语言意义,阐述语言使用着手,其意义理论以人的理性本质为出发点,理性才是其意义理论的主旋律。陈治安、马军军(2006)也认为,理性是格莱斯理论的核心, 既贯穿于其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 也在后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中有所显现。封宗信 (2008) 则对格莱斯原则的概念及哲学方法性质进行了阐释,认为其价值在于为解释非语义学现象提供了方法,为语用学和相关学科构建了难以逾越的哲学框架。王宏军、何刚(2011)指出,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建构在哲学轨道上,是高度概括的理性原则。陈国华(2017)通过介绍格莱斯会话隐涵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追溯其发展形成的整体脉络,肯定其是语用学的基石之一。可见,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侧面阐释了格莱斯理论的哲学背景,强调了其哲学内涵的意义。但就合作原则与其理性哲学观的联系问题还未见详细的论述。从格莱斯哲学思想出发,结合其意义理论,下文将系统分析合作原则的哲学基础及其所蕴涵的理性哲学观。
3.0 合作原则的哲学基础
3.1 格莱斯哲学思想缘起
西方语言哲学在弗雷格之后出现了分流,即分析哲学阵营内部两大分支之间的对立:一派是以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也称理想语言学派或形式语义学派,另一派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牛津学派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转变对分析哲学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格莱斯深受其“意义即用法”的影响,被认为是日常语言学派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在格莱斯看来,语言使用的规律无法完全用形式逻辑来解释,因为语言和生活形式紧密相关,总是处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之中。语言意义不能完全等同于句子的真值条件,他尤其关注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说话人意义之间存在不相对应的现象,主张对日常语言进行严格的分析和深入研究。但格莱斯的观点也并非与日常语言学派完全一致,这体现在他的概念分析法,体现在他对传统日常学派的语言分析模式既有赞同又持一定批判的学术立场上。其实,他对两派的观点都持有不同见解。一方面,日常语言并不像人工语言学派所认定的那样不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另一方面,在解释日常生活语言的实际使用时,语言不仅仅是在语境中的应用,逻辑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当一部分的日常语言还是可以用传统的真值条件语义学说加以解释。在他心里,理想的意义理论应该是既能解释话语表达的不恰当是因为它所表达的命题为假,也能解释话语表达的不恰当是因为其他的原因(Grice,1989:4),即所言和所涵的不同。事实上,格莱斯想建立一个整体框架以解释意义理论,既可以不将意义和使用相提并论,也不将二者彻底脱离开来。格莱斯威廉·詹姆斯演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深入探求这样一个语言理论,能够厘清相关制约因素,并指出它们是如何与意义之间产生互动关系的。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他从语句意义的表达方式出发区别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将意义和说话人的意图、信念和目的三者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既能阐释自然意义、又能阐释非自然意义的统一理论框架,颇具独到之处,体现了一种中庸观,为语用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3.2 格莱斯的意义理论
格莱斯的意义理论首发于1957年的“意义(Meaning)”一文,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3.2.1 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
格莱斯总共采用了五种方法来区别两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用“mean”一词来表达自然意义时不会改变句子的逻辑蕴涵值,他通过以下例子来进行说明:
(1) Those spots mean (meant) measles.
(2) 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of the bus) mean that the bus is full.(Grice,1957:377)
(1)是自然含义,因为句中的mean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事实性的、独立于人的关联,语句所携带的意义具有自然属性。它的逻辑蕴涵值是 He has (had) measles. 非自然意义则是非事实性的,不是单一的意义,自身包含若干个意义,和交际中说话人的意图相关。(2)是典型的非自然意义,是因为三声铃响与公交车客满这一事实之间没有任何自然关联,而是与打铃者的意图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人为约定。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区别可用逻辑的方法把握。当X means P表达的是自然意义时,X means P为真,P就为真,它们之间是一种逻辑蕴含关系,与人的意图无关。当X means P表达的是非自然意义,蕴含关系不存在。“词语或想象”与“意义或事实”之间没有自然联系,仅是人之所为,涉及人的意图和意向。格莱斯重点关注的是与人密切相关的非自然意义,其对后来语言意义的哲学思辨及语用学的诞生发展影响深远(冯光武,2007:25)。
在日常交际中,人们所用语言多属非自然意义,因语句的意义来自于人,体现人的意图及使用目的。格莱斯指出,说话人说出的每一句话,总是意味着要表达的某一或某些意图,其意图在于实际的或可能的听话人,期待对于听话人能产生某些效应(Grice 1957:381)。1968和1969年,格莱斯继续沿此思路深入探讨了基于“说话人意义(Speaker’s Meaning)”或“说话人的意向(Speaker’s Intention)”来建立句子意义的理论,认为句子的字面意义应依据“说话人意义”来解释,而“说话人意义”又应依据“说话人意图”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面顺序表示:
说话人意图→说话人意义→句义
格莱斯认为,语句表达了人们在特定场合下的交际意图,大多涉及了人之意图。因此,其实际意义就等于“说话人的意义或意向”。在他看来,词语的真实意义并非由外界事实决定,而是由说话人的意向决定。格莱斯通过语言使用,通过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和目的以及听话人所做出的反应来阐释意义。他的理论与真值条件论形成了对比,从而开启了语义理论领域的又一崭新的研究范式。
3.2.2 说话人意义的构成
说话人意义属于非自然意义,由所言(what is said)和所涵(what is implicated)两部分组成。所言受制于话语形式,是句子直接陈述的命题,有真值假值之分,包含在说话人意义之中,是说话人本身意图表达的内容。所涵是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的不影响句子真假值的部分,超出或与所言不同的意义。超出的部分与话语的语言形式逐渐远离,但与语境联系却更为紧密,往往在具体语境中是更重要的部分。所涵同样包含在说话人意义中,但又可再细分为常规蕴涵(what is conventionally implicated)和会话蕴涵(conversationally implicated) 两种类型,会话蕴涵又涵盖一般和特殊两类。这种划分形式可用下图来表示(Neale, 1992):

图1 格赖斯对说话人意义的划分
据查普曼考证,格莱斯晚年在写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要研究所言 (saying) 和所涵(implying) 就不能忽略意义(meaning) , 因为所言是基于所涵之上的(Chapman,2005:180)。可见,合作原则、会话蕴涵理论都属于非自然意义体系,也是格莱斯整个意义分析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可见,语言学者把格莱斯的理论应用于语言交际领域,但由于学科背景有别以及关注的焦点不同,往往忽略其理论的哲学渊源。格莱斯所构建的意义理论并非是为了解决语言交流中的实际问题,更不是后来新、后格莱斯原则所阐发的交际理论,以此观之,对于合作原则的种种批评显得有些不着边际,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格莱斯理论的真正内涵。“合作”术语选用又导致其与“合作”一词的日常含义容易相互混淆。合作并不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互相配合,而是人的理性本质的一种体现。只有把合作原则和会话蕴涵论述放在整个语言哲学背景下综合考察,才能领悟格莱斯的真实意图。
4.0 格莱斯的理性哲学观
会话蕴涵理论只是格莱斯意义理论的一部分,并非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事实上,格莱斯意义理论背后更为深刻的是对人的理性本质的哲学思考。这一思想端倪虽在《言辞用法研究》(StudiesintheWayofWords)一书中已有所显现,但直到《理性面面观》(AspectsofReason) 一书才出现较为系统的阐述。此书系根据他1979年约翰.洛克(John Locke)演讲底稿所做的进一步详细阐述而来。
编者沃那(Warner)在整理文集《理性面面观》时发现,原始讲稿中增补了许多格莱斯在不同时期关于理性的探讨,直到1988年他去世的那一年。事实上,早在1966年左右,格莱斯就开始讨论“理由 (reason) ” 的概念,他于1968年和1982年分别发表的“说话人意义、句子意义和词汇意义(Utterer’s Meaning, Sentence Meaning and Word Meaning)”,“再论意义(Meaning Revisited)”两篇论文,对会话蕴涵理论和意义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再论意义”一文更是从理性角度对合作原则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可见,理性是格莱斯长期以来的哲学关怀,在他看来,理性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哲学问题,是哲学家们应该关注的概念。他研究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初衷就是为了从中挖掘出人的理性特征。格莱斯(2001)指出:哲学研究领域内,多数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等都认为较为重要的哲学结论都是从理性人(rational beings)的概念推衍而来的。格莱斯(1986:65)说:“一切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我们自己或至少是我们的理性本质,哲学的不同派别与我们理性本质的不同方面相互关联,而理性本质不能被分离为毫无关系的部分,因为每个部分只有与其他部分相互联系才具有意义。”格莱斯与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观一脉相承,认为理性是知识的基础。理性是实现哲学目标的出发点,是解决哲学问题的途径,因为哲学思辨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探究(rational enquiry)。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作为西方近代哲学两个主要认识论而相互对立。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以个人的感观体验作为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而理性主义哲学家则否定经验的作用,主张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能获取最确实的理论知识体系,认为推理是获取知识的方式。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因此,理性就意味着判断和推理。格莱斯遵循这一哲学研究传统,其理性思想观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最为集中的代表是《理性面面观》一书,部分散见于他对意义理论的论述,“逻辑与会话”一文中也有较为详细的体现。
4.1 理性与说话人意义
在有关意义理论的阐释中,格莱斯将话语字面意义与交际双方的意图结合起来,他认为说话人U通过话语X传递的是非自然意义,对听话人来说,说话人说X是希望使听话人:
(1) 做出某种反应
(2) 识别出说话人欲使其做出某种反应的意图
(3) 依靠(2)做出某种形式的回应 (Grice,1989:99)。
格莱斯从说话人意图的识别角度分析意义,说明话语意义与说话人意图相关。交际就是说话人有意影响听话人心理状态的过程。实现这一目的的最理性的方式是听话人识别出说话人的意图。因此,听话人识解说话人意图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理性是格莱斯意义分析模式的依托,更是贯穿格莱斯整个思想体系的脉络与主线。说话人的意义不是解码意义,它超越句子表面意义,是听话人在正确理解说话人所言的基础上,结合句子所处的语境推理出来的衍生部分,即通常所说的大于言传的意会部分。因此,话语的产生和理解是基于对交际双方理性主体的假设。只有在对方是理性的前提下,其话语并非胡言乱语,理解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就会把话语看作以目的为导向的交际双方在对语境进行合理评估、判断、推理后的理性产物而不是仅仅流于表面,把交际双方的言语合作行为视为用简单的方式提供充足的相关信息。只有在理性的前提下,听话人才能根据说话人的所言结合所在语境,推导出言传之外的内容。
会话蕴涵与理性的联系就更加紧密。可以说,理性体现在格莱斯会话蕴涵理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之中。包括说话人意图的传递与识别,所言的确定,会话蕴涵的产生与理解以及交谈的内容、方式,一一体现出主体的理性特征。在格莱斯看来,一切意义都建立在理性主体假设的前提下。他在《言辞用法研究》的后记中运用理性对会话蕴涵再次做了阐述。他强调:遵守会话准则会提升交际理性,相反,则会削弱;准则不是一堆杂乱无序的会话规章,而是依存于合作原则;最初一轮会话遵循准则体现了理性,而后的交际类似前者同样体现理性;会话蕴涵体现了说话人在追求某种结果时表现出的心理状态或态度 (Grice,1989:368-372)。会话蕴涵的推导依赖于理性的前提,其推理模式是以合作原则为基础,话语的理解不仅仅是获取话语意义和识别说话人意图,而且要假定交际双方在表层或深层遵守合作原则。因此,理性是话语的特征,会话是理性的行为,其蕴涵的推导也是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
4.2 合作原则与理性
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格莱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理性原则,但在合作原则及会话蕴涵中时时体现了其理性观。文中,格莱斯指出:“我们的谈话通常不是由一系列不相关联的话语构成,否则,就不是理性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话语是合作的;每个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会认定一个或一系列目标或至少一个共同接受的方向”(Grice,1975:45)。可见,格莱斯已明确指出合作就是双方有意识地朝着共同目标努力,谈话是相互间有关联的语句,具有合作性的特点。说话人能隐晦曲折地讲话,而听话人又能领会其中的言外之意,正是因为交际双方都遵守合作原则(Grice,1975:46)。其基本含义是:听话人和说话人双方受目标的驱使,都在努力使得各自目标能够实现,也在识解对方的目标。能够实现这一目的是因为双方都认定对方是理性的正常人,为了有效实现交际的目的,通常会用清楚的语言给对方提供适量、真实、与谈话相关的信息,这就是合作原则所涵盖的四个准则。对合作原则和会话准则, 格莱斯认为,合作原则是理性会话的特征。说话人故意违反某一会话准则的同时依然遵守着合作原则是听话人能够推导出会话蕴涵的前提。会话准则是谈话的具体要求,遵守或是利用准则都有可能产生会话蕴涵。但如果不遵守合作原则,谈话就不能进行。合作原则和会话准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能相互替代。合作会话是合乎情理的行为。如果主体关注参与的谈话,只有按合作原则的精神行事才有益。“任何情况下人们会觉得,如果一个人说话前后不相关或模棱两可,令人失望的基本不是听者而是他自己”(Grice,1989:29)。格莱斯密切关注人的理性本质。在其构建的意义理论体系中,合作原则及会话准则展示了会话和自然语言的运作逻辑。这样做并非是对合作原则及准则的归纳,也因此没有多次提到合作的概念。在《逻辑与会话的进一步说明》(“Further Notes on Logic and Conversation”)一文中,理性概念被多次反复提及,会话蕴涵的解释也基于理性主体的认定。
格莱斯(1989:369)明确表示,合作原则不是用于具体的交际,更不能以此来做评判:“只有会话实践的某些方面才是需要评判的对象——也就是那些对理性极其重要的方面,而并非其它别的优点或缺点,所以我们所说的都不能被看作关于会话研究中具体事项的合适性或不适宜的讨论。我所关心追踪的是会话行为是否理性,而不是任何更加一般意义上的对会话充分性的概括。所以,我们期待将会话理性的原则从会话兴趣的具体特征中概括所得。” 从中可以看出,格莱斯更多关注的是交际中的言语行为是否具有理性。他所有的重心都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理性行为是理性人行为的主体部分,而言语行为又是人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合作原则在会话中出现也就合情合理,是对格莱斯整个哲学思想综观的结果。
合作原则揭示的不仅仅是言语行为的本质特征,而是人类行为的理性本质,是理性的具体体现。冯光武(2006)指出,合作原则的基本思想是:言语行为与其他人类行为一样是有目的性的,要实现它,说话人就要理性地判断话语的内容、数量和方式。听话人要将对方的话语理解为目的性的,进而判断他为什么说这些、说这么多、以这种方式说,而不只是认可说话人的目的并帮助他实现。会话蕴涵的产生和理解都基于这样的前提:听话人和说话人将彼此都看成理性主体,并愿意且有能力与之合作。如果不将说话人看成理性的主体,就不能赋予他某种会话蕴涵,无法正确推导出话语的会话蕴涵。因此,合作原则是理性的外在体现形式,是对话语行为中理性方式的描述,是理性人言语行为的指导原则。
5.0 结语
综上所述,格莱斯的合作原则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对其解读偏离的原因多在于对该原则的了解不够深入,未能将其与哲学家的其他著述相联系。合作原则、会话蕴涵从本质上讲都隶属于格莱斯的意义理论,他的意义分析是一种哲学分析,他研究意义为的是构建一种语言使用的统一理论。因此,理性贯穿格莱斯整个哲学思想体系,又指引着会话合作。合作原则是构建在人类理性行为基础之上的。言语行为中的合作行为是有目的性的,受理性制约,是一种理性行为。交际双方会通过判断、推理来决定该采用何种方式去实现这一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常语言交际中种种表面看似“不合作”的言语现象就都是合作了,因为在深层次上交际双方进行的就是理性的合作。
[1] Allan, K. & K. M. Jaszczolt (eds.).TheCambridgeHandbookof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Brown, P. & S. Levinson.Politeness:SomeUniversalsinLanguageU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Chapman, S.PaulGrice:PhilosopherandLinguist[M]. Basingstoke: Palgrave Mcmillan, 2005.
[4] Grice, H. P. Meaning[J].PhilosophicalReview, 1957,66:377-388.
[5] Grice, H. P. Utterer's Meaning, Sentence-meaning, and Word-meaning[J].FoundationsofLanguage, 1968,4:225-242.
[6] Grice, H. P. Utterer's Meaning and Intentions[J].PhilosophicalReview, 1969,78:147-177.
[7] Grice, H. P. Intention and Uncertainty[J].ProceedingsoftheBritishAcademy, 1971,57:263-279.
[8]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Peter Cole & Jerry L. Morgan (eds.).SyntaxandSemantics[C].Volume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41-58.
[9] Grice, H. P. Meaning Revisited[A]. In Smith. N. V. (ed.).MutualKnowledge[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223-243.
[10] Grice, H. P. Reply to Richards[A]. In Grandy, R. & R. Warner (eds.).PhilosophicalGroundsofRationality[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45-106.
[11] Grice, H. P.StudiesintheWayofWord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Grice, H. P.TheConceptionofValu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1.
[13] Grice, H. P.AspectsofReas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14] Horn, L. Towards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A]. In D. Schiffrin (ed.).Meaning,Form,andUseinContext:LinguisticApplications[C].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 Huang Yan.Pragmatic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 Kasher, A. Conversational Maxims and Rationality[A]. In Kasher (ed.).LanguageinFocus:Foundations,MethodsandSystems[C]. Dordrecht: Reidel, 1976.197-216.
[17] Lakoff, R. Conversational Logic[A]. In J. Verschueren, et al (eds.).HandbookofPragmatic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190-198.
[18] Leech, G.Principlesof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19] Levinson, S.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20] Levinson, S. Pragmatics and the Grammar of Anaphora: A Partial Pragmatic Reduction of Binding and Control Phenomena[J].JournalofLinguistics, 1987,23:379-434.
[21] Neale, S. Paul Gri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J].LinguisticsandPhilosophy, 1992,15:509-529.
[22] Saul, J. What is Said and Psychological Reality: Grice’s Project and Relevance Theorists’ Criticisms[J].LinguisticsandPhilosophy, 2002,25:347-372.
[23] Schauber, E . & Spolsky, E.TheBoundsofInterpretation:LinguisticTheoryandLiteraryText[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 Sperber, D. & 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86.
[25] 陈国华. 格莱斯会话隐涵理论的哲学背景与发展脉络[J]. 当代语言学,2017,(1):34-47.
[26] 陈治安,马军军. 论Grice的理性哲学观[J]. 现代外语,2006,(3):257-264.
[27] 冯光武. 合作必须是原则——兼与钱冠连教授商榷[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5):108-113.
[28] 冯光武. 理性才是主旋律——论格赖斯意义理论背后的哲学关怀[J]. 外语学刊,2006,(4):6-11.
[29] 冯光武. 格赖斯的意义理论——老话题 新解读[J]. 外语学刊,2007,(6):19-26.
[30] 封宗信. 格莱斯原则四十年[J]. 外语教学,2008,(5):1-8.
[31] 黄衍. Neo-Gricean Pragmatic Theory: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Looking ahead to the Future[J]. 外国语,2004,(1):2-25.
[32] 梅明玉. 语义蕴涵关系层级类型及推理机制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2010,(3):14-18.
[33] 钱冠连. 语用学的哲学渊源[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6):4-7.
[34] 王宏军,何刚. Grice合作原则的哲学轨道[J]. 当代外语研究,2011,(11):12-16.
[35] 姚晓东,秦亚勋. 语用学理论构筑中的理性思想及其反拨效应[J]. 现代外语,2012,(4):338-345.
[36] 姚晓东. 经典格赖斯语用学研究:一个整体视角[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刘琛)
RationalCooperationAnAnalysisofthePhilosophicalOriginoftheCooperativePrinciple
SUNNai-rong
(NationalResearchCentreforForeignLanguageEducation,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ForeignLanguagesSchool,He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Tianjin300401,China)
Sinceitsbirth,Grice’sCooperativePrinciple(CP)hasbeenheldasaclassicaswellasaconstanttargetforcriticismandrevision.Startingwithcriticismfrompolitenessprinciple,thispapertracesbackthephilosophicaloriginofCP.ItarguesthatthecriticismsfromlinguisticuseperspectivesneglectthephilosophicalbackgroundofGrice’stheory.AcloserinspectionofGrice’swritingsasanintegrativewholerevealsthatitisrationalityratherthancooperationthatiscentraltoCPasaconversationalprinciple.Cooperationreflectsrationality.AcorrectunderstandingofGrice’sprincipleshallbeputinthecontextofhisholisticphilosophicalview.
cooperationprinciple;meaning;rationality
H04
A
1002-2643(2017)05-0010-09
10.16482/j.sdwy37-1026.2017-05-002
2017-05-17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BYY039)和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15YY03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成稿过程中得到陈国华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孙乃荣(1978-),女,汉族,天津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