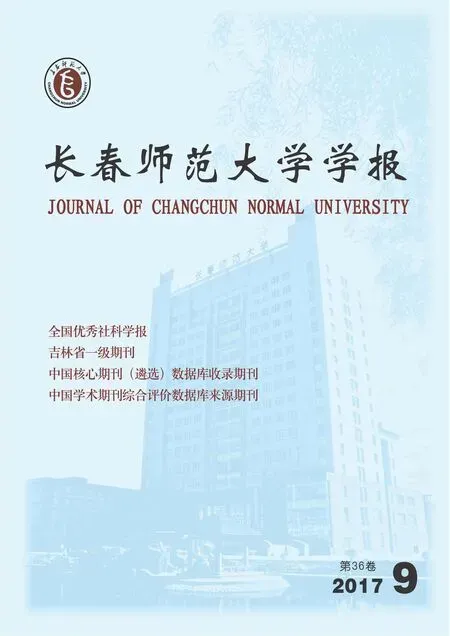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说略
2017-10-20徐高嵩
徐高嵩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说略
徐高嵩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20世纪20年代实验语音学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的语音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原本的“口耳之学”提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刘复的《四声实验录》率先系统地运用西方近代实验语音学理论对汉语声调进行研究并借用乐律进行表达,标志着西方近代实验语音学完成了东方范式的建构。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中国实验语音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至今。
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刘复;声调;乐律
一、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的源流

虽然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有法、美两个源头,但还是以法兰西学派为主要源头。当时的巴黎是世界语言学的中心,法兰西学派显赫一时。刘复、王力(1900-1986)、岑麒祥(1903-1989)等中国近现代著名语言学家都曾在巴黎大学师从法兰西学派的学者,如梅耶(1866-1936)、房德里耶斯(1875-1960)等。若论及谱系,法兰西学派的创始人梅耶曾在1881-1891年于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师从索绪尔(1857-1913)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再向上考求又可知,索绪尔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曾师从甲柏连孜(1840-1893)。所以,可以说近代中国实验语音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法兰西学派。若要追溯谱系源流,虽然甲柏连孜时代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实验语音学,但这些研究都是在普通语言学背景下完成的,也可以说是其思想体系的源头。赵元任一系的实验语音学源于美国哈佛大学,与乐律联系更为紧密,实用性较强。在东亚语学环流当中,同出一源的还有日本的伊泽修二。伊泽早于赵元任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早期实验语音学,所研究的领域同样与乐律联系紧密,实用性强。不同的是,伊泽更侧重于视话术等聋人康复方面的实验语音学研究,这种传统被其弟子浅井春荣等延续下来。
中国实验语音学的两个源头在王力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融汇。他先于1926年在清华大学师从赵元任先生,后于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并师从法兰西学派第二代代表性学者房德里耶斯和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1860-1943)。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在中国实验语音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博白方音实验录》。随着法、美两个源流在中国的汇集,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在这几位先驱的带动下,涌现出罗常培、张世禄、张洵如、吴宗济、白涤洲、周辨明等一批学者,不断投身于实验语音学研究,对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实验语音学。
二、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研究的主要设备
实验语音学的研究设备最早源于生理医学和物理学,美国人E.W. Scripture在他的《实验语音学基础》(1902)中率先介绍了一批早期实验语音学的设备及研究成果。随后,J.P.Rousselot于1924年出版的《实验语音学原理》也对此有所补益。20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相继成立了多个实验语音学研究中心,如德国汉堡大学,它们引入X光照相技术和颚照相技术用以研究发音的原理,对元音的舌位、辅音的清浊以及声调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随着电话的普及,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为了提高电话的通话质量而进行了大量的语音学实验,培养了一批从事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工程师,如Fletcher,他的专著《交谈中的听和说》(1929)一书奠定了当时学界关于听觉和语音之间量的关系的理论基础。[1]
中国近代的实验语音学研究设备最早由刘复系统地传入,由他倡导而成立的“语音乐律实验室”最早开始进行语音实验。实验室所用的实验语音学器材一部分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他根据当时研究需要自己创制的,如声调推断尺、最简音高推算尺、乙二声调推断尺、刘氏音鼓甲种及乙种等。除此之外,当时实验语音学所使用的设备还包括喉头镜、人工颚、唱片灌音、浪纹计、共鸣筒、渐变音高管、齿轮发音器、浊音计等。举例如图1至图4所示。

图1 浊音计

图2 渐变音高管

图3 浪纹计

图4 乙二声调推断尺
以上提及的各种近代实验语音学设备中,在当时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便是浪纹计。浪纹计是利用薄膜鼓动表现声音的仪器,它可以试验声音的长短高低强弱和辅音清浊,是试验四声最简单而又能得到较正确结果的仪器。[2]刘复在《声调之推断及“声调推断尺”之制造与用法》中,就是用使用浪纹计配合音鼓及电流音叉等在烟熏纸上记音的。赵元任、罗常培的方言调查也以当时设计的浪纹计、唱片灌音、渐变音高管等设备记录和分析语音。[3]当时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其设备开发主要是围绕着所要研究的问题而展开的,而基础性的通用设备还比较少。此外,上述仪器有一个共性缺陷,就是只能对语音做静态研究,在动态语音(如复合元音)的分析面前便无能为力。[4]对“决定音色物理属性的究竟是什么”等深层问题也无力解决。后来发明的语图仪等一系列用于研究动态语音的仪器以及计算机的应用对深入探讨语音的本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西方近代实验语音学东方范式的建构
通过对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具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重视对以汉语官话及方言声调为主的音系研究;二是倾向于运用乐律学知识对语音实验结果进行解释。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研究的问题焦点无疑是汉语的声调问题。为什么中国近代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始于声调?众所周知,语音有四个要素——音强、音质、音长和音高。音质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对音的长短和强弱的分析虽然不能够量化,但汉语是不以音长和音强来区别意义的语言,因而传统的音韵学研究并不特别关注这两个方面。音高则是传统音韵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音的高低关系到声调的变化,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自南朝梁人沈约发现四声之别后,大批音韵学家投入到对于汉语声调的研究中来。其对调类的划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在调值方面以及调类分类依据上的研究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基本停留在明代释真空《玉钥匙歌诀》的认识水平,即“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直到近代,中国学者才透过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揭示出汉语声调的本质。
刘复在《国语声调研究》(1926)中谈到:“咱们中国语底声调,已经试验过的,还只有音调跟词调。做过这么一回事的,外国人有Bradley和D.Jones,本国人有赵元任、刘复和高元。Bradley做过几条暹罗字调跟北京音调的曲线;赵验过北京、天津、开封、武昌、重庆、长沙、南京、苏州、福州九种字调跟北京话的词调;刘验过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十二种字调;高元验过北京调上底国音五声,江苏底七声,广东底九声,浙江吴兴底八声等等。他们所验得的浪线都用五线谱表示出来。”[5](图5,图6,图7)

图5 赵元任验证

图6 刘复验证

图7 高元验证
其后,近代中国实验语音学学者从语音实验的角度研究汉语声调的论著蜂出,研究得越来越精细化,如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北平语调的研究》(1929)、《汉语的字调跟语调》(1933);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白涤洲的《关中声调实验录》(1934)、《中国字调跟语调》(1933);周辨明的《厦语声调实验录》;岑麒祥的《粤语发音实验录》(1934);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1937)等。然而运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系统地、整体性地对汉语声调进行研究,应是从刘复的《四声实验录》开始的。
《四声实验录》一书之所以重要,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最早结合了上文所提到的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研究的两个特点,即声调研究和乐律解释。在这一点上,刘复的这本书开创了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研究的一个范式,即西方近代实验语音学研究的东方范式,成为后来学者研究的主要借鉴和理论增长基点。刘复在《四声实验录》摘要部分说道:“这是一本否定四声存在的专著。是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语言中‘四声是甚么’这一重要问题的著作:先述声音的高低、强弱、长短、音质四要素与声音变化的关系;次述所用实验方法及实验结果之如何处理;继列举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等十二种方言中四声之实验,并比较总括之以论定四声之特征。[6]可以说,《四声实验录》一书中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给了当时的音韵学界以耳目一新之感。在这一范式的指引下,借助“辅以口耳”的实验仪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开始在中国语言学界展开。其中,应用较多的主要是对各地方言声调的调值、调类的普查以及对方言音系的归纳,这主要是受到了当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影响。傅斯年在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1分《所务记载》中涉及“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趣旨”问题时,明确说道:“我们还不到抽象的谈一般语言学的地位,但凡不属于上列的三端,而为一些语言的研究所凭借的语言学中工作,我们也免不了兴作几件,尤其重要的是建设一个实验语音的工作室,以便训练出些能认识并且能记录方言的人,这个要即时办的。”[7]
在实验语音学发展的初期,描写音高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如何才能直观地把音高的不同表现出来?其实当时全世界采取的办法大同小异,主要是借助乐音和乐律。刘复在《四声实验录》一书中以胡琴上的凡、工、尺、上、乙、四、合七音为例,论证了乐器对于音高的标示作用。用“三协对照”的方式说明音高的不同,并以乐器的乐音推断人的语音分布。然而,要想通过乐音判断语音高低的具体数值,首先要确定一个标准音值。欧洲曾用中央C作标准音,后来逐渐统一为用提琴A。关于提琴A的标准音A3究竟是多少,早期的数值比较混乱,从370到567不等。直至1859年,法国人R. Koenig将标准音叉在20℃时所发出的标准音A3=435作为标准,这个A3标准数值才在逐渐推广中为大家所普遍接受。测定音高的问题解决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发现音高是复合的、连续变化的,使用乐器和乐律只能对音高进行静态描写,无法表现出音高的动态变化过程,而且描写本身的精确度也不高。
刘复在《四声实验录》中,通过对浪纹计所采集到的十二地官话及方言语音进行研究[8],观察其浪纹波形后提出,为了将声调的显性特征——音高标示出来,要将所采集到的声调的浪纹波形剔除掉来自其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来自音长的影响。也就是说,要把上平声、下平声、入声、去声的音长拉到都同上声一般齐长,或把后者缩到与前者一般短,才能把音高控制为唯一变量,借以讨论音高对声调的影响。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马上发现了这种方法无法适用于入声研究,入声拉长会趋向于平声,其它声调缩短会趋向于入声,所以入声与其它三声都不同。探讨入声时不仅要研究它的音高,也要研究它的音长。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音高高低起落的比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受到个人情绪、发音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发音者所发的音的音高起落的比例不是绝对相同的,也不能因为其绝对音高的不同而判定所发之音的调类不同。对调类的判断应该根据相对音高的起落比例来进行。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赵元任创制“五度标记法”之前,刘复的《四声实验录》已经具备了创制“五度标记法”所需要的所有声调理论,而刘复与赵元任交往频繁,学术讨论较多,因而将创制此法之功归于赵元任一人是不合适的。客观地说,刘复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起码不逊于赵元任。
四、研究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的意义
随着近来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域外视角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而随着域外视角的不断普及,语言学谱系的错综复杂使得关注汉语语言学史的人也逐渐增多。但是,关注的重点多在宏观的语言学史以及汉语语法学史方面,对汉语语音学史的关注相对较少,到了汉语语音学史中的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层面就更鲜有提及。对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的讨论,多散见于诸家的实验语音学著作的前言及序章部分,只是略而述之,以辅叙其源出。作为东亚语学环流中语音学环流的一个重要支流,真正以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为研究目标的著作和文章还十分欠缺。实验语音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语音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科门类,在语音的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罗常培在《汉语音韵学导论》中早就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他曾指出,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解决积疑,可资实验以补听官之缺。举凡声韵现象,皆可据生理物理讲明。从兹致力,庶几实事求是,信而有征。”[9]然而,现在从事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学者论及实验语音学的源流,很少能够理出一个明晰的脉络。一个学科如果缺少了对鉴往知来的源流传统的探求,势必对该学科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通过对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史的梳理,可以看出实验语音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有两个大的趋势,一是“由西向东”的转变,即由“一般”到“个别”的理论扩散趋势。西方的实验理论和实证思想逐步取代了“口耳之学”的传统,转向通过实验仪器来证明的道路上来,并由以刘复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完成了西方近代实验语音学的东方范式的构建;二是“由内向外”的扩散,即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工具的整合和利用。实验语音学的实验仪器和方法最早源于生理医学,后来扩展到了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诸多领域。从最早研究发音器官及发音方法,到绘制声频和声波波形图,再到研究大脑对于语音的控制原理。可以说,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对自然科学实验仪器和方法的整合,在不断推动着实验语音学的进步。这两种趋势分别属于两种层次的变化,即质变层次和量变层次。西方的实验理论和实证思想逐步取代了“口耳之学”的传统,“由西向东”建立中国近代实验语音学范式是根本性的质变层次,而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工具的整合利用则属于量变层次。实验语音学发展至今,已经通过不断整合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和工具完成了基础理论建设,目前更需期待的是未来新的技术革新能够为实验语音学研究带来新一轮质变。
[1]吴宗济,林茂籼.实验语音学概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2]周殿福.介绍几种简单的语音学仪器[J].中国语文,1954(11):36.
[3]王理嘉.罗常培先生与中国语音学[J].中国语文,2009(4):302-303.
[4]王理嘉.实验语音学与传统语音学[J].语文建设,1989(1):55.
[5]刘复.国语声调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1926.
[6]刘复.四声实验录[M].上海:上海群益书社,1924.
[7]傅斯年.所务记载[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15-18.
[8]石锋.论五度值记调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0(3):67-68.
[9]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6.
AnOverviewoftheHistoryofModernChinesePhonetics
XU Gao-s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experimental phonetics in China in the 1920s, i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phonetics in China and provided a scientific and empirical method for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ear and mouth”. Liu Fu’s “Record of Experiments on the Four Tones” first to systematically use the western modern experimental phonetics theory to study the Chinese tones and use the rhythm to express, marking the Western modern experimental phonetics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iental paradig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paradigm,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experimental phonetics has been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so far.
modern Chin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honetics; Liu Fu; tone; music theory
H11
A
2095-7602(2017)09-0067-05
2017-05-3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12&ZD178)。
徐高嵩(1993- ),男,硕士研究生,从事汉语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