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复的幻象
2017-10-16王语行
沈复的幻象
对沈复来说︐小世界和微型山水是心灵自由的幻象︐也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对立︒
■ 闲情与遐思
COLUM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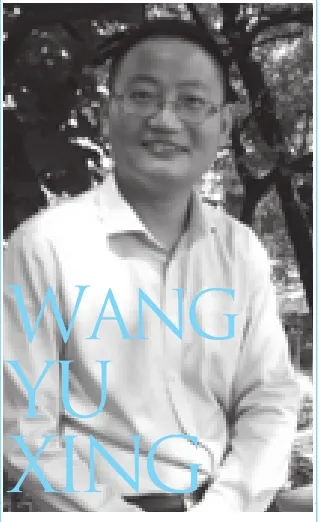
王语行:
作家,青年学者。生长于鲁南,现居重庆。撰有《胡兰成:人如乱世》《吴芳吉年谱》,编有中外诗选《绝妙好诗二百首》
为了纾缓大家庭生活带来的压抑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沈复夫妇移居苏州金母桥东的荒僻之地消暑。这里原为明末张士诚王府废基,景色清丽,“绕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更可人者,屋西有瓦砾堆成的土山,可供登高远眺,颇有野趣。在此客居之地,远离了大家庭的人事繁杂,沈复和陈芸深得居家之乐。
这段恬然自乐、诗酒欢娱的生活虽然短暂,却给了沈复一个幻象般的小世界,一个藏匿自我的温暖子宫。更为浪漫的是,陈芸设计了以后的生活:种植果蔬以供薪水、夫画妻绣以为诗酒之需。沈复对此当然极为向往,这一田园生活的梦想,召唤并诱引着他去营建能够容纳他们闲情乐趣的微型山水。
明清以来,繁华的苏州遍布构筑精致的私家园林,这种返归山水的时代风气为沈复提供了灵感和动力。《浮生六记》极写夫妇二人营建小世界所花费的心血,在此过程中,他和陈芸也得到了无上的意趣。
因财力支绌和条件局限,沈复只能对有限的空间格局稍加变化,“其间台级为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之如行长路,即不觉其窄矣”,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小世界的空间感。还修剪盆景,以叠石为假山,栽种花草,甚至在山中扫墓时亦不忘携来带有山峦纹理的小石头,在宜兴窑出产的长方盆中堆叠成美丽的假山。为让插画盆景更具野趣,捉来蝉、螳螂、蝴蝶之类,“以针刺死,用细丝扣虫项系花草间,整其足,或抱梗,或踏叶”,宛然如生的虫类静物制造了一种虚拟的田园风光,虽然逼真,仍归幻象。
沈复制造幻象的积习可追溯到他的童年:夏天,他将嗡嗡作响的蚊子视作空中飞舞的群鹤,设法将其留在蚊帐之中,在外面喷烟,群蚊向着烟的方向疾飞并不断鸣叫,这时,少年沈复制造了白鹤鸣叫于云端的幻景。
对沈复来说,小世界和微型山水是心灵自由的幻象,也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对立。在这层意义上,沈复不乏知音,最有名就是前辈文人冒襄,在“马嘶草喑”的大乱之后,于优雅的水绘园中构筑了一个极声色、诗文、山水之盛的世外桃源,一面以“遗民”自居伤逝悼亡,绝离于清政权的征召与笼络,一面缅怀着在胡尘中渐远的金陵残梦,秦淮河的桨声不时回荡在耳边。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干脆成为隐秘的象征,它是贾宝玉和周围一群女孩子唯一有意义的世界,与肮脏和堕落的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沈复的情况也如此,即使在最狼狈的时候,他仍不放弃世俗生活的原则:“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他真诚地沉溺于自己所建造的小世界里,并将一生最值得追忆的快乐尽皆寄托于此。
他的闺中之乐与微型山水映衬,增益了夫妻浪漫的兴味:二人于临窗的长廊谈诗论文,以射覆之戏聊助酒兴,在一尘不染的萧爽楼与诗人、画家朋友们吟诗作对……这个小世界本质上是一种逃避,但逃避的是外部世界的敌意,绝非生活本身,他想要的仅仅是回到家庭和田园生活中去。
鲁迅论《红楼梦》提及贾宝玉时时与“无常”觌面相遇。这位贵公子对“无常”的存在和毁灭的必至有着清醒的认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沈复亦如此,命运的悲音时时响起,快乐的“烟火神仙”的生活只不过是巨大不幸的前奏,迂缓的、逸乐的、悠闲的时光不过是人生风暴来临前平静的旋涡。
沈复不止一次地告诉读者,命运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暗示,他已经做好了迎接痛苦来临的准备。当初见陈芸时,沈复惊叹她的才思隽秀,却又“窃恐其福泽不深”,爱慕她的“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却又发现佳人“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复对陈芸的命运始终有惴惴不安之心,“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预言“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更为不祥的玄机出现在一个美丽的七月之望,沈氏夫妇备酒小酌,拟邀月畅饮,陈芸祝以“月轮当出”为白头偕老之象,荧光万点,联句遣怀,调笑细语,静待月出,后至一轮明月涌出,却“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堕”,毛骨悚然中急入房中,陈芸已寒热大作,沈复也继之以病,自述“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这次不祥的征兆在沈复的心中投下了长久的阴影,小世界的笑语与欢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象,“白头不终”之谶像一道命运的裂缝,时刻提醒着沈复为欢不长的时日。
在外部敌意不断的入侵下,沈复的小世界慢慢地坍塌了,失欢于父母亲族、游幕的颠沛流离、家庭经济的窘迫交织在一起,明白无误地证实了小世界的岌岌可危,陈芸的生病与死亡让这一悲剧达到了高潮。陈芸一向不得翁姑欢心,即使生病之后,仍对其“憎恶日甚”,至于病重时换水索汤,更令“上下厌之”。处此恶劣的人际关系中,加之沈复连年失业,陈芸不得不为人绣《心经》贴补家用,为赶工期,昼夜不休,致使腰酸头晕,“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其后,陈芸再次被逐出家门,漂流在外,最终客死扬州,魂归离恨。
陈芸一死,沈复的小世界也幻灭了。如此悲惨的结局,沈复归结为“情痴”太过,致遭天忌。陈芸的病榻遗言未尝不是沈复所思:“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到,我辈何人,敢望神仙耶?强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优游山水的生涯尚且不能久远,那么对感情的痴迷就更飘渺无依了,陈芸因恋慕憨园而发血疾,沈复因痴情陈芸而空余长恨,皆可印证“情深不寿”的奇诡真理:“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语云:‘恩爱夫妻不到头’。”
沈复一直强调,小世界的毁灭和他无关,是造物的力量摧毁了一切,他的痴情不过是加速了毁灭的进程而已。他成了一个安静的旁观者,已知种种不祥,所发生的一切只是悲剧预言的实现,已知幻象不真,只是期待美景和温情能尽量延长,可惜这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色境之为色境,就是因为它生灭迁流、刹那不停,无可常住,犹如电光、瀑水、幻梦。
在最为欢好的时刻,沈复和陈芸发愿来生再结为夫妻——
余曰:“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余笑曰:“幼时一粥犹谈不了,若来世不昧今生,合卺之夕,细谈隔世,更无合眼时矣。
陈芸的死,完全打消了沈复任何关于来世的念头,哀痛已不容他对来世有美妙的幻想。当所有的一切都成陈迹,不仅来生之事不可预期,就连今生这段奇缘艳情也注定会消失殆尽,那么,沈复写作《浮生六记》实为一种深情的挽留,挽留与陈芸共度的时光,以不负闺中良友。这种写作的心态依然使人想起《红楼梦》作者的写作缘起:“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浮生六记》乃招魂之书,为陈芸招魂,为已失去的小世界招魂,在笔墨之间与旧时光悠然相逢,再次进入幻象,重温仙仙欲死或痛苦不堪的过往。
陈芸死后,沈复无法从小世界中解脱出来。更清楚地说,他无法从自己的心念中解脱出来,陈芸、微型山水、小世界,都是围绕他所建立的幻境。唯一可抚平心绪的是,在《浮生六记》里,沈复实现了完全的自主,按照自己的心愿重建了失去的世界,一个更为隐秘、巨大的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