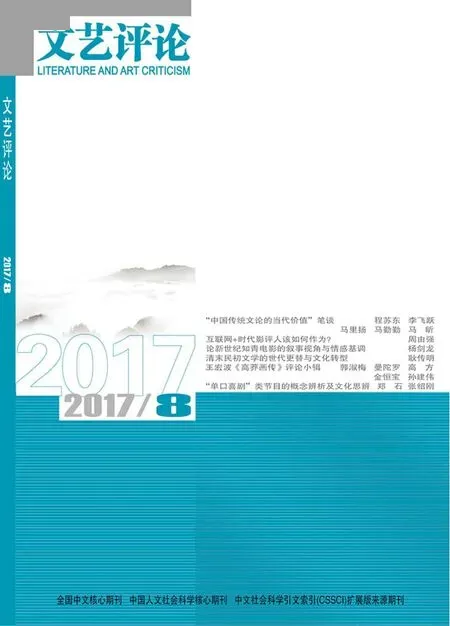语言本体论的写作探索:贾平凹《老生》中的反抒情话语与方言写作
2017-09-28○程华
○程 华
语言本体论的写作探索:贾平凹《老生》中的反抒情话语与方言写作
○程 华
作家创作的成熟,其实是语言意识的成熟。语言作为文学写作的本体,而非客体,其实是说语言不是表现作者思想的工具,而是文学写作的目的。闻一多在《庄子》中谈到,“他(庄子)的文字不只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本身就是目的”[1]。张卫中考察过西方文学语言的本体论观念,“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都是把语言文学看成一个封闭、自律的整体,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来自文本之外,而是来自语言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由索绪尔开创的这种理论称为一种语言的本体论”[2]。汪曾祺老先生从创作者的角度,写过多篇文章,比如《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小说的思想和语言》等,呼吁作家把语言写作提到文学的本体性上,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3]。莫言认为,一个作家最大的追求,主要表现在“语言或文体的追求上”[4]。考量一个作家语言意识的成熟,要看其具体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与文本内容是否契合,语体的选择,语气、语调的运用和语言节奏的控制,与作者的叙述立场和作品叙述话语是否相关。贾平凹《老生》的叙述话语如文坛老生般淡远节制,是反抒情话语的呈现,延续了自《高老庄》以来的方言叙述腔调,其叙述态度、叙事话语和方言腔调自然地融为一体,意味着其语言意识的成熟,可作为根于语言本体论的写作范本来探索和分析。
一、从抒情到反抒情
陈平原曾指明,现代小说受传统“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影响,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话语形式,一种在叙事中偏重客观历史的呈现,写实意味浓重;一种强调在叙事中渗入主观情绪,有浓郁的抒情意味。王德威认为,抒情不仅仅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抒情作为一种文类特征,涉及到话语模式的问题,也即“利用声音、文字和审美的各种资源,形成抒情诗或文学”[5]。王德威的抒情观念不仅超越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拘囿,也超越了文体的限制,叙事类、戏剧类作品中也有抒情话语的呈现,这其实就和陈平原的“诗骚传统”入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借用王德威的抒情观念来观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自出道伊始,基于性格和文学接受的原因,其创作可归入中国现代小说抒情文体一例。《浮躁》围绕金狗的人生起伏和情感经历展开叙述,金狗身上具有改革年代的奋发意识,凸显“浮躁”的时代情绪,具有鲜明史传因素的社会变革等具体事件因过多的故事情境和环境氛围描写被淡化。《废都》中,作者鲜明的情感标记,贯穿在庄之蝶与4个女人的身体沉沦之中,庄之蝶的绝望,其实是作者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个人情感和文化选择的迷惘表现,“废都”意象以及废都城墙上氤氲不绝的埙音也强化了作品整体的抒情氛围。《秦腔》记叙的是世纪末农村的凋敝,但整部小说的叙述节奏围绕虚拟的叙述者引生对秦腔演员白雪的痴情绝恋展开,涉及到的话语表述缠绵而伤感。《秦腔》中最具现实意味的人物夏天义,从土地的捍卫者变成土地的凭吊者,围绕这一和时代同步的角色,不仅写出其子女不孝,传统伦理丧失,其钟爱的土地贬值等很多近于“史传”的事件描述,同时,作者多角度的情感渲染加诸一个时代没落者身上,比如悲怆的秦腔腔调,被土掩埋的巨大绝望,无字碑的无奈等增添浓厚的抒情意味。《带灯》围绕带灯个人情感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裂隙展开叙述,“带灯夜游”寓意带灯情感世界的分裂,带灯给元天亮的27封短信,更是浪漫抒情话语的直接表现。从《浮躁》到《带灯》的写作,其作品都以当下的现实社会为背景,却不是“补正史之阙”的史传文学,这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意象”观念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在写实的基础上,重在张扬作者的情感和想象。具体来说,贾平凹小说中的抒情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抒情氛围的营造,如州河的河流、埙音、秦腔腔调等抒情意象在作品中的一线贯穿;二是叙事者的情感注入,诸如引生、狗尿苔、带灯等极富感情的叙事态度在文本中的体现;三是整体意象的象征手法,诸如“浮躁”“废都”“秦腔”“带灯”等题名都拓展了作品的意义象征空间,再加之散文化的结构和抒情氛围的营造等,作者借助这样的抒情形式,营造出一个多情的话语世界。
贾平凹一路走来,身处历史之中,缺少了远距离的审视,易成为对历史阶段的描绘。在《老生》中,已过耳顺之年的贾平凹,站在历史的高度,远距离凝望和审视历史,也正因如此,其叙述话语经历了抒情话语向反抒情话语的转变。反抒情是抒情的对立面。黑格尔认为,抒情话语,其实就是用诗语完成对自我形象的塑造;米兰·昆德拉认为,抒情的个体“只关注自身,无法看到、理解和清醒地评判他周围的世界”[6]。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抒情者在抒发情感时,沉醉在对自我的爱恋中,无法远距离地看待自我,更难以清醒地认识世界。反抒情就是对抒情的反拨,“远离自己后,带着距离来看自己,惊讶地发现自己并非自己以为的那个人”,[7]不仅如此,带着距离去观察和认识现实世界和他人世界时,也会取得一个超越的视角,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是撕开现实的帷幕,这样,反抒情话语相对抒情话语,表现在对现实更为清楚和深刻的反观和认识中。反抒情话语在《老生》这个作品中,具体表现为超越的叙述视角的设置,叙述者情感的淡入以及寓言和隐喻等客观抒情表现手段的运用等。
二、反抒情话语的呈现
《老生》中,贾平凹第一次将百年历史打通,在反观历史中,注入其对历史的态度。《老生》如同题名,“老”是经验和经历了历史和人生之后,对历史和人生的更为客观的态度。生,即人的生命、生活,历史和人生是在经历中不断成熟的,善与恶、美与丑,苦难与沧桑,愈老愈体会得真实而客观。贾平凹在文学场域中历练四十余年,写下千万文字作品,文学手法老辣,其对历史的态度少了浮躁和玄幻的想象,也绝少个人情感的渗透,更逼近历史的真实。
《老生》最有意味之处,就是叙述视角的设置。《老生》文本叙述的视角是双重的,小说开始和结尾,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这是关于叙述者唱师的介绍,如同倒流河的隐喻,叙述者站在高处俯视百年历史,也开启了历史中的故事。小说中的百年历史故事,是老生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述,这样的视角选择,“借作者和叙事者的间离造成一个潜在的审视角度”[8],这种叙事上的间隔手法,传达的是“对思考者的思考”,间隔的手法如同电影蒙太奇镜头的转换,模糊了具体的时空距离,把百年的故事放在无涯的时空领域中,感受人类在亘古荒原中的渺小存在,这是《老生》叙述视角的特点之一。其二,在具体的故事讲述中,老生作为限知叙述者,不仅是一线串珠的线索人物,突出其在小说结构布局上的优势;作者还借助老生的特殊视角,叙述故事,编制情节,传达其对历史的超越态度。“老生的存在超越了时间、种族、阶级、生死。地主死了他也唱,贫农死了他也唱,游击队死了他也唱,都在唱。超越了这些,才能比较真实地看待这段历史。”[9]其三,在讲述百年历史的故事中,贾平凹引用了《山海经》的故事,《山海经》故事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并无交叉,《山海经》的引用在叙事节奏上起的是延宕故事的作用,在结构方面,《山海经》中所呈现的远古历史和现代历史正相呼应,也是叙述上的间隔手段,将具体的历史拉长到遥远的时空领域中,寄意悲凉的人生感受和荒凉的历史感慨。贾平凹说:“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岗兮深谷行。”作者意欲站在历史的高处俯瞰历史,通过视角转换和结构间隔的手段,通过多层次的超越视角,呈现历史之流的本来面目。
从一部作品中,可见出作者对文学的认识。在《老生》中,作者极力隐藏自己,妥善处理对人物的好恶标准,努力呈现“历史”和人物本身的特征。比如,同样是第一人称叙事,《秦腔》中引生对白雪的痴恋是作品的看点,其叙述话语也多情感的渲染,引生自断尘根的行为,是情感指向强烈的戏剧情景,有绝望的感情在里面。《老生》中,叙事者老生是一个不知年岁的老者,其唱阴歌的身份寓意其窥破了人间的生死密码,游走在阴阳之间既经历着历史又超越于历史,小说中穿插了众多的阴歌歌辞,歌辞的引入并非抒情手段,而是老生生死态度的体现,如同《红楼梦》中僧人唱的《好了歌》。贾平凹在《废都》中借助拾破烂的老头也穿插过类似的看透人间苍生百态的谐语段子。如果说《废都》中老头的谐语中还有着愤世的感慨,老生的阴歌歌辞则表达着对生死的了悟。老生视角下的人物故事是直奔生存本质的叙述,因而其文字表述绝少情感的介入。《老生》人物众多,并不着意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性,而是重点突出小人物具体生存的现实处境。比如,老黑是第一个故事的主角,老生叙述:“老黑有了枪,枪好像就是从身上长出来一样,使用自如。”“他说枪要给喂吃的,见老鹰打老鹰,见燕子打燕子”[10],平淡到简单的话语背后,其实有深厚的思考在里面。老黑与枪的关系,隐喻着人本性中的兽性基因关系。第一个故事中的游击战争,其实就是革命斗争年代下群体的兽性演绎,集中展示了人性的残酷。老黑死亡时的描写,是暴力和血腥的,这是老黑无法摆脱的“斗争”环境使然。多数读者不能接受关于残酷血腥的描写,老生的客观叙述,恰表明这是无是非判断和无价值倾向的进入事物和人物灵魂的描写。再比如,墓生是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在文革环境下,个人命运被大革命夹带携裹向前,被动为生,无处立足。墓生最后还是因旗子而死,并被旗子盖住,“旗子”在文革年代是政治指向鲜明的词汇,旗子虽轻,但对墓生来说却无比沉重,是个人无法知觉的沉重,正因无法知觉,才显沉思的余味。两个人物,两个时代,两种死亡的方式,小人物的具体存在事实,照出了大时代的历史真实。
叙述者情感的淡出,并未弱化文学叙事的文学性,归因于作品中的寓言和隐喻的设置。抒情的表现手段,与自我情感、志趣相联系,在叙事文学中,主要通过创设情境和氛围来实现;寓言是寓于故事中的,寓言中呈现的是对历史的沉思和体悟。比如关于人与动物的寓言。第一个故事中的战争年代,老生在山坳里唱孝歌,唱着唱着,“感觉到不远处草丛里来了不吭声的豹子,也来了野猪,蹲在那里不动,还来了长尾巴的狐狸和穿了花衣的蛇。他们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我也不停唱,没有逃跑。唱完了,我起身要走,他们也起身各自分散”[11]。这段话,俨然人鬼神兽同处一处的情景,老生作为唱师,用歌声穿越了人鬼神兽的世界。四个人物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主角,与四个野兽相映照,隐喻在战乱年代,人性堕入到兽性中;唱师唱《敬五方》《悔恨歌》,是物我同一、众生平等愿望的映现。在佛教的世界里,有人道、神道和畜生道之说,老生俨然如同置身神道的世界,呼唤兽类回归人类世界,而人的世界,应是众生平等。这样的寓言,没有政党批判的因素,只是强化了战争制造的血腥和暴乱使人性迷失,同时通过老生,对美好的人性世界寄予期望。
比如瘟疫。瘟疫是指因某种疾病所导致的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迅即有传染性,难以控制。小说作者叙写瘟疫,多想象的寄寓,如《白鹿原》;也有历史背景的原因,如《十日谈》。《老生》第四个故事中关于瘟疫的故事是寓言中的寓言。商品经济波及到农村后,刺激了人们的拜金欲望,《老生》中众人争先恐后种植危害人类健康的农作物,这是群体意识的盲从现象。群体良知的丧失,道德观念的沦丧,从人类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来说,是一种危害更大的“瘟疫”。贾平凹比别的作者更为高明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通过寓言中的寓言探索“瘟疫”的缘由。良知的丧失,拜金的欲望不仅仅是一种被动刺激,即众人的盲从心理,而是人们内心无意识的呼应,比如“老虎”的寓意。老虎与人类并非对立的存在,人类的发展威胁到兽类的生存,这恰是其《怀念狼》的主题。在《老生》这里,老虎已然绝灭的事实,是人类过渡发展所致,发展的背后是人心的算计与贪欲作祟。贾平凹在这个小故事中写出了人们心理轨迹的演变,在无有的基础上寻找,从虚幻的观念里生发,变虚幻存在为实有,这在鲁迅先生的阿Q那里是精神胜利,但在贾平凹的戏生这里却成为现实的存在。贪欲,尤其是人的算计可以使虚幻变成实有,这是现实人性的演绎。在改革发展的背景下,像戏生这样的普通百姓,其精神世界的病变恰是一种群体的无意识,是一场需要引人注目的精神瘟疫。
比如关于竹节虫的寓言。竹节虫贯穿第三个故事始终,虫混在枯枝中,难以区分,小说叙述墓生在老皮的眼皮底下踩死了竹节虫,老皮走后,墓生又挖坑埋葬了竹节虫,墓生与竹节虫互为表里。墓生是第三个故事的主角,受“文革”文化波及的卑微人物,因为“文革”中强大的文化渗透力量,改变和正在改变着过风楼公社中人物的命运。过风楼每在立夏时节会祭祀风神,祈求庄稼丰收,老皮的到来,原本祈敬自然的行为变成了整治人思想的“整风”行为。老皮在作品中也是具有隐喻意义的人物,其面貌和行为异于一般人,比如双瞳、双排牙,脸上皮肤松弛,其怪异的面貌隐喻的是不正常的畸形存在,但其人却精力旺盛,也正因此,作者写老皮主宰着整个过风楼人的命运。为了强化老皮这一人物,小说中有一情节,老皮来到过风楼公社办公,要住在风大的上院办公,喜欢站在门外的台阶上俯视整个过风楼,作者写道:“他在轰轰嗡嗡的音响里俯瞰着,想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就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挥动。”[12]这一句话有两个词语有双关意义,一是“俯视”,不仅是从高往低看,而是这一人物在过风楼的地位高高在上,是权力的把持者;“挥动”帽子,这典型的动作,不是普通人之间的相互致意,而是某种思想文化的相互辉映,老皮是专权思想文化在过风楼的代言。正是在老皮这样的人物整治下,过风楼里的普通老百姓人性发生变异,刘学仁、冯蟹和阎立本诸人成为老皮不同侧面的化身,或狡黠乖戾、或蛮横残暴,他们是老皮的变种;过风楼公社的老百姓,在老皮们的思想整治之下,也丧失朴素的人情人性。贾平凹在《古炉》中写文革争斗使人使残用狠,在《老生》中,重点写人心作伪,失却本性,这是人心的变异,也是竹节虫的隐喻。文化的畸变,专权的思想,恰是产生竹节虫的温床。故事中,墓生死了,可是覆盖在墓生身上的仍是竹节虫,“竹节虫”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恰体现出作者批判思想的深意。作者不论叙述战争年代、改革时期还是文革时代的故事,都着重笔墨于特定历史环境下普通人性的发展变异,显露了隐藏于民族内部的负面文化因素,并借助寓言的手法,挖掘深藏于民族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是经历历史沧桑之后的贾平凹用文学直面历史的思想体现。
反抒情的叙述话语,使贾平凹在审视历史时,不仅复述历史过程或呈现历史事件,且尽力发掘历史深处影响普通人性变异和人物命运的因素,这恰如王国维所说,是文学家、哲学家眼中心中的历史,而非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在超越的视角之下,历史如同聚光灯,映射出人性的美丑、生存的艰难、存在的丰富性。每一段具体的历史或许不同,但在不同历史幕布下的人的存在是如此丰富,影响人性发展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原因值得人们思考,这是超越历史的视角对历史本质的真实表现。
三、反抒情话语与方言写作
文学叙事中,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手段,且是目的。《老生》语言最为个性的部分,那就是如同从作者身体中生出来的语言,充满着陕西南部的地方方言腔调,与整个小说的反抒情话语相得益彰。反抒情作为一种话语模式,运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也可达到反抒情的效果;若以《老生》为例,这种生活味道十足的来自于民间生活的方言腔调,恰是最适合表现民间历史的语言,是作品反抒情话语最恰当的表现。
纵观贾平凹文学语言的探索之路,从普通白话文写作走向方言写作,是一个逐渐扩大写作范围,超越个人才情和个性的过程。贾平凹文坛试笔时期的语言优美隽永,运用典型的白话文书写自我情感,小说抒情意味浓厚;《废都》中的语言,夹杂着方言古语,但语体表述有明清文人笔记小说的味道,笔记体语言“实质是文人借以逞其诗文才具的手段”[13],庄之蝶形象中有贾平凹的灵魂暗影。《高老庄》的语言是方言土语的大荟萃,是贾平凹摆脱自我形象,用方言呈现现实农村的意图。他的小说语言足以形成方言的洪流,这一方面源于本人日常说话的方言腔调,说话语言和写作语言的一致性,使方言自然地成为观察社会、审视人生、表现生活的手段。另一方面,贾平凹笔下的世界也越来越深广,不仅是故乡生活,而是借助对故乡的书写呈现中国的历史和时代内容。方言写作,不仅是一种语体形式的变革,而是一种文化立场和写作态度的变化。如普通话之于公共语言,是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述形式,贾平凹“用民间语言来表现民间,民间世界才通过它自己的语言真正获得了主体性”[14],这是其民间立场最鲜明和最直接的表现。
再现民间立场下的民间生活,方言比知识分子话语下的普通白话文更为贴切。寻根文学以来,作家们纷纷进入到民间世界寻找文学资源,作家们信赖民间语言,“从几乎无意识地依靠一种混合型的语言背景撤退到有意识地依靠某种旗帜鲜明的单一的所谓民间语言传统”[15],除了民间语言接地气之外,鄙人认为,民间语言(方言)与普通话相比,更适合于表达“我们”而非“我”的世界,“文学写作是从‘我’出发而最终要走向‘我们’的”[16],若从文学语言的发展来,知识分子创造了文言文,用文字遮蔽了言语,扼杀了老百姓发声的可能,鲁迅等五四时代的作家意识到要启蒙国人的思想,必须要接近老百姓的声音,在文字的运用上,就要选择更贴近老百姓的发声方式,即白话语言。鲁迅的白话文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是个人化的知识分子式的发声方式”[17]。到了寻根文学时代,作家们纷纷抛弃五四以来的翻译腔,选择口语化的方言写作,其实是作者语言选择的自觉表现。知识分子普遍向老百姓发声方式的靠拢,将民间生活语言纳入到知识分子的写作过程中,随着民间世界在创作中越来越深入的展现,语言和语言所表现的对象才能够融合。在《老生》中,老生既是民间历史的叙事者,民间历史的观察者和审视者,又是民间立场的代言人。老生视角下的人物始终和多灾多难、有血有肉的民间生活相联系,人物的语言,是充满民间生命力的语言。民间叙述者借助民间语言呈现历史,申明态度,随着作者人生体验的深入和写作对象的扩大,作为“语言的‘根柢’和文学的‘根柢’的方言”[18],才能自然地汇聚成文学语言的河流,承载着作者全部思想和艺术构思,呈现于读者眼前。
叙述态度影响叙述模式,叙述模式也会影响小说作者的语言选择。《老生》反抒情话语通过设置老生视角来表现其民间立场,在叙述结构上也摈弃了抒情意味浓厚的散点透视结构,而以老生作为百年历史故事的讲述者,讲故事的背后其实是有虚拟的听故事者,这种小说结构类于传统的“听与说”的说书人传统。老生娓娓道来的民间故事只有借助如话家常的生活语言才能达到讲故事的效果。贾平凹在《白夜》后记中曾说,小说就是说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话,老生说的是平常自然的故事,过于书面化的语言,达不到如平常说话般的讲故事效果。老生用生活语言讲述民间故事,写作对象、文学结构和文学语言自然融为一体,这是作者清醒的语言意识所致。
《老生》中选择方言写作,恰是为了契合老生的民间视角。《老生》纯然白话,绝少装饰,滤去了情感的成分,语调淡远,语气从容淡定,这是老生作为民间立场代言人的叙述话语。贾平凹将老生对于百年历史的审视态度自然地编织在舒缓简练的方言腔调中,意味着其语言意识的自觉,也彰显着作者的创作态度和创作特征。正是借助方言写作传达反抒情的叙述态度,贾平凹突破自我的限制和束缚,走向对我们这个时代和历史的描绘,并且深入到历史深处,探究民族深处的集体无意识。
(作者单位:商洛学院人文学院)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九)[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张卫中《语言本体论的限度——关于新时期小说语言的探索》[J],《文艺评论》,2016年第 12期。
[3]汪曾祺《小说的思想和语言》[J],《写作》,1991年第4期。
[4]莫言《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学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
[5]季进、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教授访谈论》[J],《书城》,2008年第 6期。
[6][7][法]米兰·昆德拉《帷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第116页。
[8]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9]王佳莹、贾平凹《小说的最高境界不是是非的问题》[N],《北京青年报》,2014年10月31日。
[10][11][12]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第62页,第146页。
[13]郜元宝《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14][18]张新颖《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丑行或浪漫〉》[J],《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
[15]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J],《大家》,2002年第4期。
[16]贾平凹《天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版,第223页。
[17]葛红兵《文字对声音、言语的遗忘和压抑:从鲁迅、莫言对语言的态度说开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商州情结长安气象:地域文化视野下的贾平凹创作思想研究”(15J05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