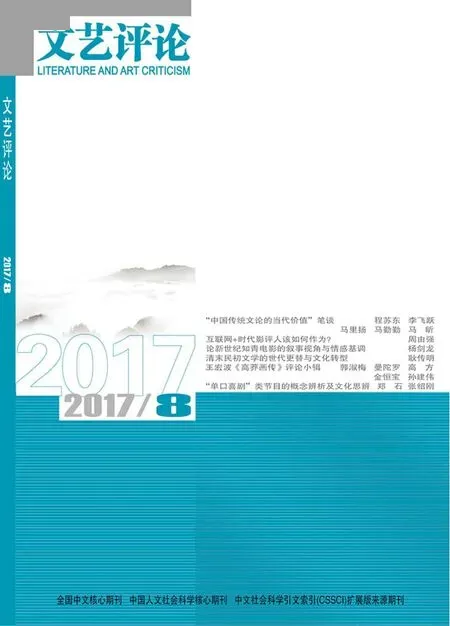定向“翻新”传统的尝试──简评杜立明的诗集《我的诗经》
2017-09-28罗振亚
○罗振亚
定向“翻新”传统的尝试──简评杜立明的诗集《我的诗经》
○罗振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下是一个同质化的诗歌时代,诗坛上流行的大量诗歌文本在构思视角、想象路径乃至语汇风格方面,都可谓惊人地相似,辨识度越来越低,泛滥不已的口水随时都可能把诗和诗人淹没。在如此令人倍感倦怠的艺术时节,我读到了著名的中年诗人杜立明鲜活、稳健、又颇具写作难度的诗集《我的诗经》(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愈发坚信诗这种极其个人化的精神作业,就是为小众的艺术,白居易那种老妪能解的所谓的诗歌理想,也并不那么值得大家推崇,或者说,人人都能读懂、句句都可坐实的绝对称不上好诗,它们也许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因为说穿了诗歌之美,往往就介乎于明白与晦涩之间、懂与不懂之间、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这恐怕也是诗歌和其他所有文体比较所独自享有的权利。如果从这个向度上去考察,和诗人以往灵动清新的诗集《四月》相比,杜立明的诗集《我的诗经》可以说暗合了现代诗歌的本质趋势,又俘获了新的审美气息,它至少有三个长处值得圈点。
一是形式探索的新鲜感和启迪性。我一直以为,在新诗已经拥有百年艺术积累、诗人们几乎“千人一面”的今天,一种艺术可能性的寻找和发现,远比一种技巧和风格在成熟路上的推进更为重要。多少年了,新诗界一直倡导要在新诗文本中强化传统的因素,可是囿于各种原因,又有多少人在切实地进行这种实践,就非常值得怀疑了。在这个问题上,杜立明似乎从来没有表白过什么,但却在《我的诗经》中身体力行了。他的诗集《我的诗经》按照《诗经》的“风雅颂”的体例、顺序和篇数,分别对应着创作了305首新诗,然后以新诗大字、古诗小字的方式,将《诗经》原作和《我的诗经》新篇在同一页码内,并置排列,这样“新”“旧”两个文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既民族味浓郁,容易唤起蛰伏在读者心中的传统的审美记忆,又收到了巴赫金倡言的那种“对话”妙处,达成了古与今、虚与实、传统与现代、继承与超越的互动互补,并使文本的结构意蕴能够从平面趋于立体的高层,诗歌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获得了飞翔的可能。比如《周颂·振鹭》:
今夜太过匆忙,白鹭忘记了飞翔//我的王,我是你的女人/不是唯一的女人,而你是我们唯一的王//趁阳光明媚,我们和大地都穿上衣裳……白鹭高飞/万民激昂//借一件白色的衣服穿着/和另一个世界的人们交流思想//神灵左右我们的幸与不幸/一直到死我们都没有见过神的面庞//就只有白鹭/高声叫着,挂在天上。
且不必说语言的干净洗练,也不必说意境的神秘清幽,单是白鹭意象的纯净高雅,即可视为《诗经》传统之美的现代闪烁。可以想见,没有对《诗经》中305首“风雅颂”原作无数次的阅读、浸淫和领悟,没有对《诗经》中305首诗歌、作者情感与艺术的体贴、回味和深切应和,杜立明若想建构起自己的精神王国《我的诗经》,完全是不敢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我的诗经》既是对《诗经》的体会与解读,又是诗人自我情志的抒放和表达,每首诗不只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在攫取《诗经》原作某个意象或一点情绪线索基础上的生发、拓展,更是跨越古今时空的特殊的精神对话与艺术创造。这种新颖的形式在《我的诗经》中已经不再是无谓的存在,它有时本身即是意味的外化,有某种程度的增值作用,甚至有时形式本身即是意味。我们还不能说,《我的诗经》的每一首都无可挑剔,但是它新鲜的探索,至少可以给人一种陌生的审美刺激,进而启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如何自然地结合传统因子和现代质素,使传统达到翻新的效果,这也许正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
二是对诗歌写作难度的挑战。如今写诗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常人高不可攀的事情,尤其是低门槛、高产出双向刺激下的网络诗歌的推波助澜,更令诗歌写作变得不辨男女长幼,人人可为,容易得总让人觉得哪里有点反常。诗人杜立明亲身经历了诗歌写作这一变化过程,并时时保有必要的警惕,自觉地从两个方面遏制诗歌写作的平面化倾向,用以维系写作的难度。一方面,关于爱、死亡、孤独、命运等经验乃至灵魂视域超验思想的咀嚼和介入,使《我的诗经》打破了诗歌只是激情流露或只是生活表现的迷信或圭臬,这本身让读者接受起来就已经不那么直接。以往我们的教科书上都明明白白地写着,诗是生活的反映,或诗是情感的抒发,顶多诗是感觉的状写;但是随着诗歌创作实践的深细化,诗歌本体内涵的不断拓展,人们越来越发现白纸黑字上面印着的不全都是真理,至少关于诗歌本质的论述就太过狭窄。因为在卞之琳、冯至、穆旦、北岛等一系列新诗史上的主知诗人那里,诗歌就已经晋升为一种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一种提纯和升华了的思想经验。像杜立明的《我的诗经》中的一些诗歌也已经成为某种思想和智慧的发现,如《周颂·清庙》写到:
我有一座小庙,无砖无瓦/盘膝而坐/垂头像一株青草/祈求神灵。最后还是自己把自己喂饱//有一天供奉的和被供奉的在街上遇到/视而不见/祖先把自己的神庙烧了/子孙们只能在山谷里种植包谷和云朵//有教养地活着/和道路学会奔跑。
该诗就不再仅仅追求情感的冲击力,而能给人以心智和思想的启迪,道出了许多人共同的深层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事物的本质,“最后还是自己把自己喂饱”,清庙里养的原本是一个无神论者,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和神灵。只是情感哲学与经验说,也不能完全涵盖杜立明《我的诗经》的写作,它的情思漫游有时已经进入了情绪、思想之外的超验领域。如《邶风·击鼓》:
故意把时间拖得如此之晚/悄悄打将军的墓穴里/扛出那面被敲击了无数遍的大鼓/一个人擂响/宋国和陈国成为两个名字/那匹迷路的马,已经无家可归/旷野之上听见鼓声的土地开裂/能够站立的灵魂重上战场/每一场战争都当作和你最后的诀别/绝不,我决不向任何苦难缴枪/我就是那个提着自己的头颅奔跑的战士/爱你,是我一生的信仰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因为鼓声而颤栗/原始的冲击,像奔跑的牛羊/当决定爱你,决定接受审判/我就为你收割了今夜冰冷的月光。
很显然,诗文本观照的绝对不仅是现实世界具体、实有的存在,宋国和陈国是两个“名字”、灵魂重上战场、提着自己的头颅奔跑、收割月光等虚拟、超验的意象、事态,因为都过于隐秘和私人化,和大多数人具有一种不可通约的个性,所以一般的读者接受起来难以直接与顺畅,而需要一定的过程。也就是说,阅读时需要凭借一定的积累去“悟”,才可得其要领。当然,悟多悟少、悟对悟错也就很正常。必须正视,《我的诗经》对经验乃至超验领域的涉足,在无形中对传统诗歌本体的内涵构成了一种必要的扩疆和拓容。其实这种现象说起来一点也不奇怪,诗歌创作和文本日新月异,诗歌批评和研究的本质内涵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否则一味地跟在诗人后面阐释,必然被动和滞后,还将遭遇诗人和读者的轻视。
另一方面,诗性思维的跳跃与断裂,也给《我的诗经》增加了阅读难度的系数。杜立明的诗歌充满理性色彩,这一点熟悉的人无不称道,但好在它绝对不单纯凭借智力去认识,而选择走了一条非逻辑的感性表达的诗之路。诗集整体上的托物言志,已经使情感与意象的关系结构不那么直接简单,其中即蕴藏了一种含蓄的可能;而诗人超拔的想象力和悟性的思维方式遇合,更使诗获得了一种不时时受物理逻辑支配的自由空灵的属性,情思完全随着诗人自由自在的悟性思维起伏、游走,自然又给读者增加了一重解读的障碍。如《郑风·风雨》:
连绵不断的是雨抑或是另外的东西/说不清楚,就把自己的心空出来了//我们总在失去什么/甚至活着自身//和神秘的事物交流/必须脱了世俗的衣服//用一个大院子饲养鸡的声音/鸡用声音孵化上空的乌云//用一生的寂寞供养一个美人/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秋雨打捞鸽子的心/你总是不说话,若有所思//月亮感觉不到欣喜/风雨清洗了远方。
全诗宛若诗人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又好似小说中的意识流的淌动,虽然整体的诗意脉络尚可理清,但是时而雨,时而东西,时而心,时而衣服,时而鸡时而鸽子,时而月亮时而远方,节与节之间、句与句之间明显地断裂、跳跃,至于前后连接的链条却又都被诗人给省略掉了,这种写法在揭示出诗人隐秘而活跃的心理动感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其思维的转换得过于突兀随意,诗的意味自然也就迷离闪烁得不易把捉了。它好像在说人总在失去中成长,只有本真地向事物学习才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又好像在说人的情感有时说来很神秘,只要值得寂寞也在所不辞;抑或是另有所指也未可知。总之,它提供给你诸多的联想方向,哪一种似乎都对,又似乎都不完全对,诗就是在这种“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起伏中,拥托出“不平”的艺术妙处。对这样的诗不能以一目十行的方式浏览,只有仔细品味才能体会其深意。
三是我很看好杜立明《我的诗经》的沉稳的写作态度。确切地说,写作是对作家心性的磨练和养成,一个诗人成就、风格的高下,和其心性之间有着隐秘而深刻的内在关联。如今诗人们的创作速度远超大跃进时代,十年磨一剑的耐心早已被一年磨十剑的浮躁替代。在这种时代快节奏的整体情境下,真正的诗人应该增加经受寂寞的定力,这是更深的功夫训练。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风度,更是一种写作规律,只有慢才利于静观默察,潜入事物的根部和深层,夯实、提纯情感与思考,让表达趋于秩序和精确化,最终打造出艺术精品。在这一点上,杜立明《我的诗经》的做法能够给人提供一定的启示。不说别的,仅仅是仔细参悟《诗经》的每一篇作品,再按风雅颂的格局和秩序一一对应地写出305首新诗,建构起一个相对自足的逻辑体系,那份耐得住寂寞的沉静和执着,就非一般诗歌作者所能做得到的,就值得敬佩。而像其中的《周颂·烈文》一诗:
八百诸侯受封之后/学蒲公英的子孙四下分散/有的骑马有的乘车有的步行还有的就地打坐/快的已经穿越了死亡的城池/慢的一直走到今天//我们的王,去和黑暗谈判/带走了周公、御事、司徒、亚旅、师氏/我一个人在睡梦里和敌人交战/和存在于灵魂深处的杀伐声,怒睁双眼/我是走得最慢的诸侯/眼看着王的国土被陌生的面孔侵占//我们的王,去和黑暗谈判/黑色的战士将像阳光一样铺展/席卷你们这些不遵守法度的人群/我是最后的诸侯,坚守着王留给我的爱和孤单。
诗人自称“我是走得最慢的诸侯”,但也是最“遵守法度的”诸侯,所以能够坚守住“王留给我的爱和孤单”。在诗里,诗人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和表现对象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距离,以沉稳的笔调,将众诸侯的表现、自己与其他的诸侯和王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姿态、表现和情感,传达得清晰自然,从容不迫,表现出一定的艺术风度。当下的诗人经常去比速度,比数量,急就章居多,如果我们的诗人都能够像让写作快起来一样,学会让写作慢下来,那诗坛就真的蒙福了。
也许有人会说,和无数先人的智慧支撑的《诗经》相比,杜立明一个人写下的《我的诗经》境界没有那么阔达雄浑,从情感到艺术还嫌纤弱和稚嫩,这也是实情。他与《诗经》跨时空对话的意图着实可嘉,也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某些艺术的生长点,但不是出于情感的驱动,而完全靠理性和毅力去督促自己进行写作,其发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不无可疑的因子;自我始终饱满地在场,强化了文本的现代品质,可是能否吻合、能吻合多少《诗经》的内里规律,也就打了一些折扣,无论如何对传统的超越应该先从贴近开始;思想的阐发与思维的跃动,增加了文本内涵的深度和高度,却也因诗人主体的过于内敛,不时让读者感觉其文本的言说方式过于“硬”,如上述还不错的《周颂·烈文》人称、视点的频繁转换,段落、句子、语汇间超出一般人想象的跳跃,就使一些读者望而却步,摸不着诗的头脑,缺少应有的柔软度。但是,我想这些局限或许和杜立明诗歌的优长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取消弊端的同时闪光之处也就不复存在了,《我的诗经》的难度写作之路,因为思维和艺术的奇僻把许多读者挡在了文本门外,但却又提高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这恐怕就是艺术选择的两面性症结所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