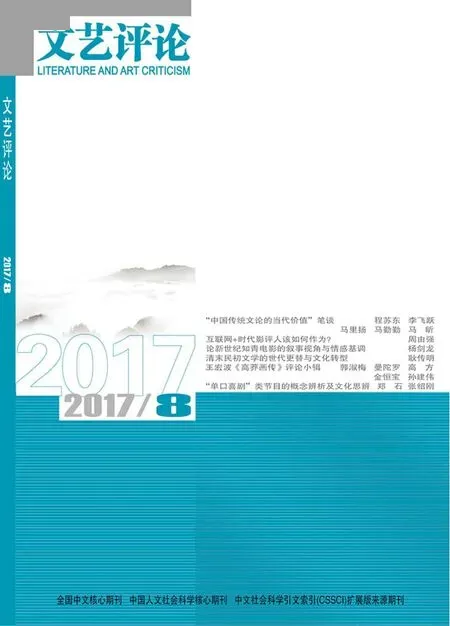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影评人该如何作为?
2017-09-28周由强
○周由强
互联网+时代影评人该如何作为?
○周由强
毋庸置疑,在健康的文艺发展态势下,评论和创作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这是常识,也是真理。但是,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往往常识容易被忘记,真理容易被颠覆。比如,近些年来,随着资本强势进入电影产业后,除了借助大数据的“豆瓣式”评论外,影评特别是专业影评的作用却日渐式微,观众和创投团队更习惯于用简单的“评分”去选择欣赏(消费)和投拍电影作品,专家评论显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值得欣慰的是,今年我国的电影市场在经过前几年的高歌猛进之后理性回落,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中国电影要健康可持续发展,客观科学理性的电影评论不能缺位,电影艺术领域的创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事实上,从中外电影发展史看,影评(主要指专业评论)从来都是沟通创作者和消费者的桥梁纽带,为推动电影艺术健康发展和电影产业的良性运作提供了可靠的智力支持和清醒的舆论环境。中国电影评论几乎是伴随中国电影的引进而产生的。1896年8月,作为现代电影艺术传入中国。[1]1897年出现电影评论,1920年诞生电影杂志。[2]上世纪80年代,载有大量影评的《大众电影》的最高发行量达960万份;《芙蓉镇》等影视作品问世时,评论往往直接影响一系列作品,各大报刊副刊的影评专版专栏一时“洛阳纸贵”。及至目前,受市场和互联网技术等强大影响,电影评论队伍正在“裂变”,电影评论阵地不断“移位”,电影评论传播方式、途径和形态在变化,中国电影评论进入了多元多变多样的格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电影产业与欧美国家相比,本身就存在技术上的落后与理论上的先天不足。我们还缺乏连贯的媒体影评传统,几乎连职业影评人也没有,与西方影评文化相比明显缺乏厚度。而且,在中国庞大的电影产业体系里,与产业的扩容和创作的活跃相比,电影评论工作对于创作者和欣赏者来说,都还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影评人这一专业群体的力量明显不足。
简单回顾一下欧美影评人如何在电影艺术发展历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对我国影评人如何作为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欧美的影评人这一职业和从业者的发展伴随电影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欧洲电影评论还传承了18世纪以来艺术评论的深厚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电影市场走向和观众审美趣味,并逐渐成为电影评奖和国际电影节选片的重要力量。法国新浪潮的影评人能为全球电影输出理论武器,对世界电影史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影评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影的票房走向。总的看来,欧美国家已经构建起包括学术影评、通俗影评、网络影评和电影评奖在内的比较完善的电影评价系统,四者并行发展,又相互碰撞,共同影响着电影市场的发展。
学术影评以其专业性引导电影创作。学术影评主要是接受正规系统的电影学教育的研究学者们,立足于挖掘电影的艺术性撰写出来的理论性电影评论,它能为电影创作提供全局性的指导,为电影创作指明趋势和方向。在欧美很多国家都有专业的影评人及人才培养院校。美国电影学院、纽约大学提斯克艺术学院、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等高校都为美国电影工业和电影评论输送大量人才。职业影评人独立并且专业,常常引导观众取得一致口碑,他们的差评电影往往成为“烂番茄”,他们的影评书籍甚至获得普利策艺术评论奖和国家图书奖等。[3]从机构来说,影评人协会遍及英法美等国各省区州,这些协会历史悠久、影响力大。[4]影评人协会会员大多数是媒体的专职影评人,少数来自大学等科研机构。[5]在世界电影中影响很大的国际影评人联合会(国际影评人协会)于1930年在巴黎成立,是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影评人的联盟。他们经常专门由影评人评选出各种奖项在世界各大电影节期间颁发,由此对电影创作产生影响。
通俗影评以其大众性直接作用于观众。不同于学术影评的小众特征,那些广泛出现在传统大众媒介上的通俗影评能够直接作用于观众,从电影杂志到主流报纸再到电视,通俗影评能够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每一角落。[6]通俗影评人以电影审美启蒙为己任,培养了观众的电影观赏能力。如美国王牌影评电视节目《西斯科与伊伯特电影评论》的主持人罗杰·伊伯特所说,“当我们在节目中评论某部不会同时在全国一千六百家电影院公映的影片时,我们的评论很可能就成了这部电影在许多地方唯一的曝光机会。当我们表达对于某部电影的观点时,它很可能就‘叮’地一下启发了某个志向远大的年轻人,让他明白每个人都可以对电影有自己的想法”[7]。同时,通俗影评还能够通过“在观众耳边持续不断的耳语”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对于票房有着直接的影响。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通俗影评的主要阵地——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日益衰落,使得其影响力有所减弱。
网络影评以其互动性颠覆了传统影评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崛起催生了电影网站、电影论坛、电影博客等,网络影评随之兴起。以美国为例,网络影评主要包括传统影评网络版、社交网站中的电影评论、电影论坛及评分网站、专业影评网站等。网络影评提供了更加自由、独立的平台,并且为影评人与观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值得一提的是,欧美的网络影评并非只是“酷评”的代名词,传统媒介中著名影评人的加入,使得网络影评的专业性也不容小觑。如美国第一位获普利策奖的罗杰·伊伯特自2004年起就开通了个人影评网站,收录了他撰写的上千篇影评及几百条电影名词等,并且保持与影迷之间的互动。
电影评奖成为电影审美与市场的风向标。欧美电影节展往往采用艺术交流与市场交易兼具的双轮驱动模式。一方面,欧美电影节展以其专业性引导着电影审美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且将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传递出去。例如,美国奥斯卡以其强大的影响力锲而不舍地宣扬着美国主流价值观,并尽力促使其成为全球的公认的“世界价值”。另一方面,电影评奖以最直观的方式对电影的市场表现给出明确判断,反映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它们成为观众走进影院的向导,从而成为电影市场的风向标。
反观中国的电影评论生态,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全面启动电影市场经济和电影产业化的尝试,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转型时期。可以说,中国电影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发展时期。2016年通过、2017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无疑是对中国电影业最重要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同时,作为电影屏幕拥有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逐步放开对进口电影的限额,中国电影要和世界优秀电影包括好莱坞电影同台竞技,很难相信如果缺少专业影评人的有效参与,中国电影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和发展。当然,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环境较之前已有较大改善,电影市场的泡沫已经开始得到挤压,电影投资创作生产正朝着理性状态回归。在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重要节点,战略合作、并购融资、原创内容、增进票房、催生周边市场,互联网正给电影行业带来深刻创新与变革。电影产业链上主要包含制片商、发行商、院线和影院四大环节,每个环节都在被互联网化,传统的影视公司、院线和影院都在按照互联网模式转变,同时互联网公司与消费者也成为了这个产业链中的参与主体。在这个新的市场环境和产业链条中,电影评论该如何有效作为?
互联网+时代,电影评论正在经历多重转型。评论主体在由精英评论向大众评论转型;评论载体在由单一的报刊评论向多元的社会评论转型,微博、微信和豆瓣等自媒体上影评如云;评论取向在由专业化评论与娱乐化评论并存向专业评论为主转型。虽然在当今国际领域,影评人同样面临职业危机,电影评论的阵地在日益萎缩,但在中国更为尴尬的是,在学术评论尚不能引领电影创作的审美趋势、通俗评论尚不能培养观众的审美能力、电影评奖尚未成为市场的风向标时,网络评论身着草根性的外衣被暴力话语裹挟着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传统的单向度、碎片化、定性评价式评论,需要转向高效、全面、科学的电影评价系统,各种电影评价主体需要重新认识自身价值并发挥独特作用。
虽然在互联网时代,学术影评(或者叫专业影评)的声音容易被淹没,但事实上,越是众声喧哗的时代,学术影评的专业化导向和美学追求才愈加重要,而要使其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就需要同欧美一样,将学术影评置于整个电影工业的链条顶端,而非单纯的电影美学的学理性阐释和探讨。学术影评人应该意识到,“电影,无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是一种娱乐方式,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有这些电影的职能都是建立在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基础之上”[8]。同时,学术影评还是电影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为将直接影响着包括电影评论在内的电影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所以,学术影评需要在与电影市场保持“一臂之距”的过程中,冷静理性思考和发声,引导电影在文化艺术而不仅仅是工业产业的道路上前进。在大众媒体日渐发达起来后,无所不在的“大众影评”是最为接近消费者的电影评价方式,它们对培养观众的电影欣赏能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众影评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媒体记者手里。然而这些年的大众影评的角色和作用屡遭诟病,一些媒体记者为了夺人眼球或者“服务资本”,把自己的笔头或者镜头更多用在了挖掘演员绯闻等八卦新闻上,让观众消费了演员,而不是消费了电影艺术,瓦解了电影可能起到的文化滋养的功能,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使社会各界对媒体刊发的娱乐影评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经常出现口碑与真实票房倒挂现象。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更多具有专业背景的影评人加入到大众影评的写作队伍中来,他们不仅要有文字功底、电影知识、审美判断,更要有独立专业的职业操守,要诚实体现艺术专业性和时代洞察力。尤其是随着网络影评的兴起,网络影评作为新兴力量已经改变了大众看电影、说电影、评电影的方式,尤其对青少年影响很大。但目前我国网络影评的现状令人堪忧,各种力量都借助网络发声,动机各异,真假难辨,如同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网络影评“众声喧哗,没有主流,没有权威,以至于六神无主”。更为糟糕的是,由于缺乏必要制约和海量信息监管的极大难度,语言暴力泛滥,“酷评”盛行,网络评论的生态还很不健康。因此,要发挥网络影评正向作用,推荐法律和制度规范势在必行。借鉴欧美发展经验,传统媒介中专业影评人如果能充分运用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积极引导年轻一代创作者的内容创造和观众的电影消费习惯,也会大大改善网络影评“六神无主”的现状。
笔者以为,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视听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融合特征;电影作品作为工业化产品,具有和书法、美术、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不一样的产业特性和组织化特征。所以,如果评论要对整个电影工业产生更大影响,必须针对影响电影生产的各种因素(包括学术、艺术、技术等)和各个环节(编、导、演、服、化、道、剪、录、美)进行全面关注,这就需要提高电影评论的组织化程度,否则容易出现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抓其一点不顾其余的不良现象。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各种组织机构都越来越重视提高电影评论的组织化,都会通过组织各种论坛、研讨会、看片会等形式,积极发挥评论在电影创作与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通过组织各类学习培训和专题研修班,加大电影人才的培养力度,提升电影从业者的整体水平。国内各种电影节展,按照国家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的改革要求,压缩评奖数量,更加注重评论的有效介入,“以评代奖”,通过各种媒体的融合传播,不断放大评论特别是专业评论的声音,促进了电影艺术生态建设的健康发展。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逐步建立起包括学术影评、大众影评、网络影评、电影评奖在内的比较科学完善的电影评价体系,我国的电影艺术和电影产业的发展将会迎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中国传媒大学)
[1]1896年8月11日,上海闸北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私家花园内的“又一村”在表演的娱乐节目中间穿插放映了由外国人带入的影片,这是电影在中国放映最早的记录,距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诞生仅半年多时间。当时,中国人把它称为“西洋影戏”或“电光影戏”,以后统称为“影戏”。
[2]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到上海放映电影。同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刊登文章《观美国影戏记》,是迄今我们看到的我国电影观众写的第一篇电影观后感。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当时放映电影的情况、影片的内容及作者的印象。1920年1月,中国电影史上诞生了第一本电影杂志——《影戏杂志》,在之后的20年里又陆续诞生了近百种电影刊物,其中包括《明星月报》《文艺电影》《时代电影》《现代电影》《明星半月刊》《电声》《电通》《联华画报》等著名电影杂志,这些刊物绝大部分诞生于上海。
[3]美国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的电影评论都是带有倾向性的,富于探索、独特原创。她的第四本书《深入电影》是第一部荣获国家图书奖的电影书籍,她被认为是有力量成就或者毁掉一部电影的人。
[4]例如伦敦影评人协会始建于1913年、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成立于1966年、在线影评人协会奖成立于1997年;美国广播电影影评协会,是由美国和加拿大199家电视台和电台联合创办的影评组织,也是目前北美地区规模最大影评组织。
[5]例如美国影评家协会会员JOHN ANDERSON是《综艺》和《华尔街日报》影评人、RICHARD BRODY是《纽约客》影评人、TODD McCARTHY是《好莱坞报道》影评人、KENNETH TURAN是《洛杉矶时报》影评人。伦敦影评人协会目前拥有一百多位会员,主要来自英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影评人,自1980年开始,每年年初都颁出伦敦影评人协会奖。
[6]对市场和观众有影响力地主要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电影评论,如美国《综艺》《华尔街日报》以及法国电影理论家与影评家巴赞1950年创办的《电影手册》等。
[7][美]罗杰·伊伯特《在黑暗中醒来:罗杰·伊伯特四十年精选》[M],黄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77页。
[8]贾磊磊《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道德失序与话语重构》[J],《艺术百家》,2006年第 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