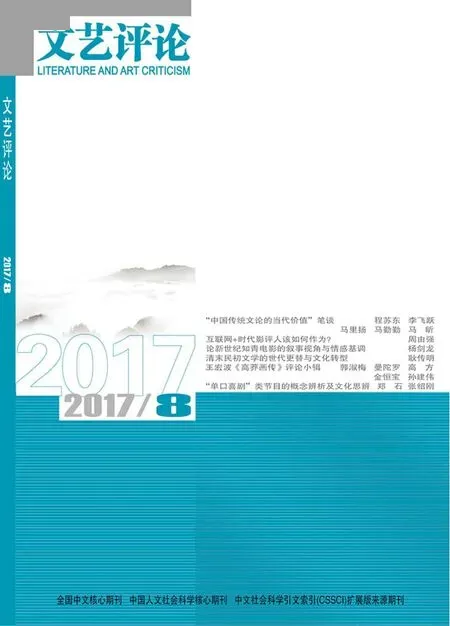传统文论当代意义的百年话语掠影
2017-09-28马勤勤
○马勤勤
传统文论当代意义的百年话语掠影
○马勤勤
有关传统文论当代意义的讨论,早已珠玉在前。一些学者从大处着眼,站在重塑当代中国文论文化身份认同、构建核心价值话语体系和重建民族美学自信的高度,阐述作为本土资源的传统文论;[1]有人甚至指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论作为华夏民族审美体验和艺术实践的历史结晶,在全球化语境中日益显现出普世价值;[2]有的研究者直面目前文学理论合法性危机,剖析传统文论“当代化”有无可能及其实现途径;[3]部分学者在主体性、修辞、结构、命题、虚实等不同层面,具体发掘传统文论在理论阐释方面的生命力与启示性;[4]还有研究者通过坚实的历史钩沉,揭示传统文论当代意义的话语形构过程。[5]本文参照最后一种研究思路,致力于从学术史的视角进入,尝试对传统文论当代意义这一话题的历史建构过程补充性的话语追踪,以期丰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
传统文论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然而其作为一个学科的生成却是现代的产物。晚清时期,受经世学风兴起与西学传入的影响,学术门类开始了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而这“实际上就是从中国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的转变”[6]。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自此“文学”开始在官方学制系统中立科。按照《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的7项主课里,有2项带有鲜明的“文论”色彩,即“文学研究法”与“古人论文要言”[7]。“文学研究法”似乎被视为“中国文学门”最重要的课程,不仅排在课表第一位,而且章程对这个主课的说明最为细致,大体和其他6个主课的解说量总和相近。
在“文学研究法”的课程解说中,其所标举的41则“研究文学之要义”,近半数显示出了经世致用之意。如“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国家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文学与外交之关系、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等。解说的最末还明确指示:“集部日多,必归湮灭,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8]可见,传统文论在其学科化之滥觞期便已着力于对其“当代性”意义的召唤。
对于清末民初的知识者来说,面对民族国家深重的危机,回到传统文化的内部寻找可资利用的资源,恰是常见的文化策略。如果深研这些策略,或许也可以获得一些有关传统文论“当代”意义的细节。1904年,林传甲编写了国人自撰的第一部颇具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该著本有意借鉴了“文学研究法”的内容,使其兼含“文学史”与“文学概论”双重角色。林传甲自言:“《大学堂研究文学要义》,原系四十一款,兹已撰定十六款,其余二十五款,所举纲要已略见于各篇,故不再赘。”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里格外重视文学与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并时常引入对晚清当下状态的评判。如讲“六朝词章之滥”时说道:“今之尚词章,尚不若六朝之甚;然国民文弱,亦甚自奋于竞存之世乎?”谈“论治化词章并行不悖”时称:“中国杂职武弁,多不识字者。外人恒见而非笑之。良由词章之士,务艰深而不务平实也。日本明治维新,说者谓其黜汉学而醉欧化。今读其战争文学,见彼陆海师团、走卒下士所为诗歌,或奇崛如李,或雄健如杜。中国词章之士,苟读之而愧奋,中国庶几中兴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在新文化运动后常因其“杂文学”观而被“后见之明”讥以迂阔无知,殊不知著者的国族救亡意识甚是激烈。在林氏看来,最重要的是经世致用,挽大厦之将倾。这何尝不是在传统文论中寻找“当代”意义的尝试,只是时过境迁,当年著者的苦心孤诣早不为人所见。
民国以降,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渐趋成形,传统文论也逐渐从“诗文评”的原初形貌变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状态。朱自清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然而,今人谈及传统文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惯于举出《新青年》同人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声讨。这固然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但同时传统文论也作为可以依托的本土文化资源发挥着它的“当代”意义,1916年前后胡适文学改良思路的形成即为一例。前人容易只意会胡适借助了域外经验,但如果细致考察胡适文学改良动力的话,传统文论恰恰也是介入性的文化力量。细读1915年至1916年的胡适日记可以发现,对他文学变革观念的形成最有帮助的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论的阅读与体悟。如1915年6月6日,他通过赏鉴秦少游、辛稼轩、陈同甫等人的词,形成了“词乃诗之进化”的观念,想到“诗之不自由而词之自由”。同年8月受白居易《与元九书》与王安石《上邵学士书》的启发。至1916年4月,胡适梳理出中国文学史上的6次革命,他愤慨于“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同年7月,当他与梅觐庄为白话文学问题争论不休时,读到了袁枚的数篇文章,并选择若干文字摘入日记中,赞袁氏有文学革命思想。直到1917年前后,胡适已经完成了《文学改良刍议》的写作之后,才读到了“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附注明“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更可证该文的写作并未直接受到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而是由中国旧有学术内部生发而得。[9]新文学运动获得合法性之后,胡适很快转入到“整理国故”运动中来,也并非偶然的。
而在20世纪20-40年代对传统文论学科化贡献颇巨的多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大体上是“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论领域延伸出来的成果。1927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通常被视为传统文论学科雏形的确立。陈钟凡在《十五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一文中便将该书列入到文学类的成绩中。其《自传》也称20年代的他“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10]。笼统地说,民国时期传统文论的研究思路整体上不脱胡适“整理国故”的学术设想,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1]就传统文论研究目的上看,此一时期更多一份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反倒缺乏清末民初知识者对于传统文论经世致用的标举。
二
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古为今用”,但复杂之处在于如何理解与评价“用”。1949年之后在“厚今薄古”的革命语境下,传统文论的“古为今用”之路也并不平坦。新中国最初的几年里,“文艺学”的讲授基本照搬苏联模式,传统文论的地位亟待彰显。1957年,在“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氛围中,邹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批评了讲授“文艺学”不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怪现象,提出:“在蕴藏丰富的文学理论宝库面前,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还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言不称中国古代,对之报以轻视与回避的眼光?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研究、讲授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呢?”同年《新建设》上刊出应杰、安伦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遗产》与之成呼应之势。1958年,为了推进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遗产批判性继承的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
1960年,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大会上的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专门论述了“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的问题,特别提到了“文艺的民族化”。1961年,毛泽东提出了文风问题,周扬当时也倡导对古代文论要加以重视,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张光年筹划开讲《文心雕龙》[12],并在当年第五、七、十一期《文艺报》上开辟了“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专栏,引来宗白华、俞平伯、王朝闻、王瑶、郭绍虞、游国恩、朱光潜、陆侃如等大批学者参与其中。然而,在文艺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得到相当普遍的重视与讨论后,关于继承的实质、原因、内容、方式都产生了广泛的争议。在传统文论价值定位方面,有的认为继承文艺理论遗产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文艺的民族化问题,而古典文艺理论在今天只有参考价值,它决不能指导今天的文艺运动,也不能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有的则认为继承遗产就是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13]随后,“厚古薄今”倾向开始遭到清算。一直到1966年,更为激进的主张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时期对于传统文论“古为今用”的探索。“拨乱反正”后,周扬在一次关于传统文论的答问中反思说:“批判,我们有时把它用坏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批判都是否定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改革,就是简单的否定,就是毁灭。”[1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方面。伴随着对“四人帮”的清算,传统文论与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关系又重新被提起。1979年3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而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是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会议一致认为:解放以来的文论教材都很少民族特色,这个缺点是和忽视古代文论研究分不开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历史任务已提上日程,必须认真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批判继承,推陈出新。[15]同年,郭绍虞亦撰文指出研究古代文论是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还可以总结文艺创作的历史经验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借鉴。[16]
20世纪60年代,周扬、张光年等人重掌文化界,“双百方针”驱动下的“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的思路也得以复归。1979年11月,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外国输入的,但又必须在我们自己民族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艺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和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我国有两千年来悠久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传统,出现过不少文论、剧论、乐论、画论、诗话、词话、评点小说传奇等著名论著,历代大作家、大诗人、大画家、大思想家、评论家都曾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精辟见解。这是我们民族的美学思想的珍贵资料。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整理研究和批判继承这些宝贵遗产,以利于发展我们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17]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对传统文论研究者而言,真正助推了他们关于自身研究目的与意义展开热烈讨论的是“十二大”的召开。当年《文史哲》杂志便筹办了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为主题的座谈会。在会上,王元化表示:“在十二大上,小平同志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很重要的话,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问题,不只限于哪一个方面、哪一条战线,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各个方面,两个文明的建设都要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所以我们搞文论研究,也应该走自己的道路。”[18]于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了传统文论界热议的宏伟目标。[19]当时一般认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短板正是对传统文论的研究不足,甚至希冀以传统文论来构造思想体系大厦的基石。
几年的热闹讨论之后,借助传统文论以打造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尝试并未获得有说服力的研究实绩,反而还遭到部分研究者的质疑,认为:“‘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个不科学的口号。”[20]总的来看,建国后近四十年的时间中,传统文论最初遭冷遇而亟待正名的状态难免影响到了学者们对于其“用”的过分强调和追求,这一时期对传统文论研究目的的阐述体现了极强的政治性特征。
三
1987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五次年会召开,重点讨论了传统文论当代性的问题。与此前传统文论研究的高度政治化相比,本次对当代性的讨论更多源自学科的内在危机。学者们注意到:“搞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创作的人和不少青年学生,对古代文论缺乏兴趣,这并不是古代文论本身没有价值,而是我们的研究缺乏当代性与现实感,不能强烈地吸引他们。”[21]
1989年至1990年,有关传统文论当代意义的讨论又重新热闹起来。对此,这两年的《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大概可观其端倪。1989年的最后两期,陈良运和徐中玉先后专门撰文提出了“古代文论的当代接受”和“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第二年,《文艺理论研究》连推数文,如杜黎均《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实生命力》、贾文昭《古代文论与时代》、蔡钟翔《以古为鉴和中西互朴——漫议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罗立乾《中国古代诗论的理论价值及其当代作用》等,颇成阵势。后续又有南帆《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等文章。
1989年是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重要时刻。古代文论研究者们组织召开了“回顾与重建——四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反思座谈会”。会上,敏泽作了题为《关于古代文论的进一步发展》的发言,强调古代文论“在研究方法上,要有现代意识”。时任《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在会议总结发言《深入反思,发展文论研究》中,亦提及“现代意识”的问题。他反对“用现代思想去生硬地解释古代文论,或者从现代词义角度去简单地理解古文论中的某些语词”,也提醒研究者要注意“自身却被对象所淹没”“思想上跳不出古人樊篱,行文上以古证古”的倾向;他所期待的是,“主观上能够重视现代意识的养成,并妥善贯彻到研究工作中去”,增强时代气息,把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22]
1989年,《文学遗产》在刊发《回顾与重建——四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反思座谈会发言》的同一期上,还重磅推出了罗宗强与卢盛江合作的一篇学术综述《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该文力图将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从机械式的为现实服务解救出来,在肯定古文论对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服务的同时,更多表达的是对学术自为状态的追求和为“不是面对现实的纯粹的研究”的辩护。文章指出: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而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传统文论研究的目的也并不仅仅是为“今天”,它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不少更是为将来所用的。这种对学术价值自身的努力彰显映射出传统文论学科的渐趋成熟。其反思视角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时期十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学科意识的调整。
199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专门召开了主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及其在当代的作用和意义”的研讨会。朱桦在发表于《社会科学》的综述文章中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立足当代,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深入地挖掘中国古代理论宝藏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因素,使之与当代文论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近年来古代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23]可知,本次会议大体上是前几年讨论的一种总结和延伸。
目前,做传统文论文献述评工作的学者,梳理传统文论当代意义的研究现状时,一般会从1996年谈起,但实际上是不够的。1996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会上,钱中文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的开幕报告。他提出:“要站在当代社会历史的高度,将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我国古代文论融入当代文论之中,这种融入应该既是继承的,也是超越的;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同时是有机的,而不是寻章摘句点缀式的。具体说来,就是吸取其思维内在特性,选择其合理的范畴、观念乃至体系,并在融合外国文论的基础上,激活当代文论,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24]倘若眼光向前追溯的话,可以为这一学术思想的浮出找到显豁的学术史线索。
1997年年初,《文学评论》开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专栏,一时之间,耆宿与新锐纷纷登场,上演了唇枪舌剑的精彩交锋,影响很大。对此,相关学术梳理已相当充分,不必在此重复。倒是可以立足远景,对未来研究的某种可能性做以简单的瞻望。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崛起,西方的文学理论也进入到了阐释困境之中。中西方的既有理论都面临着失效的问题。而看似无路可走的同时,恰恰可能四处是生机。
面对网络世界这样一个新兴的文化空间,传统文论如若能够找到切入的方式,则其当代意义便更加有的放矢。传统文论在20世纪中国遭遇边缘化。除了“传统”在一个革命中国内部的危机之外,传统文论自身的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的文论话语系统,例如概念术语使用的随意,分体文论不平衡,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等。[25]
不过可期的是,未来网络时代的文学与现代印刷术支撑下的百年中国文学将会产生巨大的裂变。奉白话为圭臬的新文学,本就是崛起于新媒体的出现。其激进如钱玄同者,将国之贫弱与汉字繁复、文言分离、教育难以普及相联系,径直主张废除汉字。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这在新知识界是一种有相当认同度的想法。正如识者所言:“语言文字改革各个阶段的不同派系,其努力的方向基本都是字母化(拉丁化或罗马化),也就是要废除文言分离的象形方块字,改用文言合一的拼音文字……语言学从来不认为语言文字有着普遍适用的优劣新旧评判标准,尤其是汉字计算机处理技术的开发应用日新月异,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象形汉字的模糊逻辑属性,可能比逻辑语言具有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更加适合于计算机时代的发展。”[26]随着全球网络时代的到来,汉字的优越性或许会越发明显。而互联网思维的模糊性、交互性、交叉性、重体验性等,似乎与传统文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可以深入讨论下去的地方,从而生发出新的学术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如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J],《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陈良运《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代文论》[J],《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党圣元《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民族美学自信的重建》[J],《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秋之卷;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J],《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传承与延续:叩问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J],《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2]如殷国明《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J],《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再论》[J],《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 6期。
[3]如胡大雷《关于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J],《文学评论》,2003年第 1期;李春青《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可能途径》[J],《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曹顺庆、付飞亮《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有效性——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反思》[J],《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4]如毛宣国《主体性、经典阐释与修辞批评——浅谈当代文论建设中的传统文论资源利用》[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张惠《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5]如罗宗强《20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A],罗宗强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黄念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C],上海:上海出版中心,2006年版;李春青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党圣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祁海文、贾伟《略论传统文论的现代际遇》[A],梅新林、黄霖、胡明等主编《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三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N],《光明日报》,2000年8月11日。
[7]在具体的课程说明中,课名“古人论文要言”改为“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并注明“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奏定大学堂章程》[A],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8]《奏定大学堂章程》[A],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364页。
[9]关于胡适文学改良动力的辨析,可参见宋声泉《民初作为方法——文学革命新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139页。
[10]陈中凡(原名钟凡)《自传》[J],《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1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7卷第1号。
[12]张光年《研究古代文论为现代服务——在〈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J],《文史哲》,1983年第6期。
[13]《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讨论文艺理论遗产的继承问题》[J],《文史哲》,1963年第3期。
[14]《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周扬同志答〈社会科学战线〉记者问》[J],《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15]《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J],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2页。
[16]郭绍虞《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
[17]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A],《周扬文集》(第五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18]《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纪要)》[J],《文史哲》,1983年第1期。
[19]如吴文治《试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民族化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 2期;汪正章《关于建立中国式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浅见》[J],《渤海学刊》,1985年第 12期;张兵《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述评》[J],《齐鲁学刊》,1985年第 1期;牟世金《古代文论研究现状之我见》[J],《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20]金惠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化异议》[J],《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21]曹顺庆《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起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五次年会综述》[J],《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306页。
[22]《回顾与重建——四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反思座谈会发言》[J],《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23]朱桦《弘扬古代文论精华、推进当代文论建设——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及其在当代的作用和意义”讨论综述》[J],《社会科学》,1991年第 9期。
[24]屈雅君《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1997年第 1期。
[25]陈洪、沈立言《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 年第 3 期。
[26]桑兵《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J],《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 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