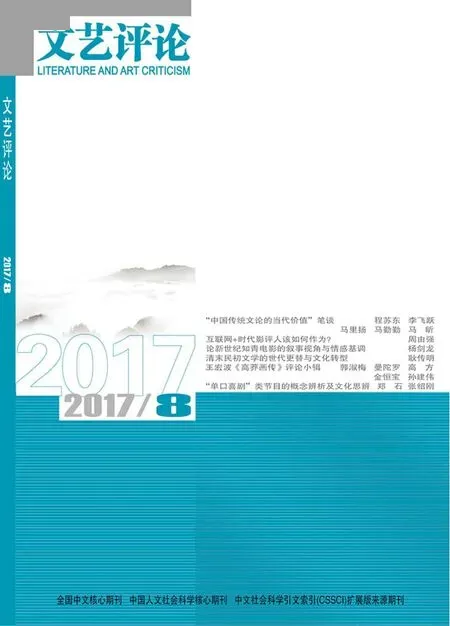传统词学新释三题
2017-09-28马里扬
○马里扬
传统词学新释三题
○马里扬
在宋词批评当中,可以见到的专门术语就是诸如“挑刷”“虚实”“开阖”“点染”“顺逆”,等等,不一一列举,这些其实就是古人所谓的“用笔”之法。它们在“诗话”“文话”“曲话”中,也并不缺席。因此,如果运用它们来展开“词”的文体批评,则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限定性,即“义界”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技法用语的意义限定,是它们进入“词学批评体系”中自然而然生发出的“专指性”;而“词学批评体系”的出现,也不是到了近代才有了自觉。清初人沈雄编纂的《古今词话》,虽然有着种种的缺陷,但由于是“古今词话”的集成之作,因此他有选择地对自宋代以来的论词之语的抄录,实际上隐含了“词学批评体系”的建构意识。该书“词品”下卷专列有“品词”一类,[1]不妨就他所收辑的词话作一初步的总结;至于落在他身后的“词话”,自然是他无从知晓,但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却也是可以纳入他“品词”所隐含着的批评体系之中,是下面需要作的补充。
一、释“词要清空”
张炎在《词源》中提出的“词要清空,不要质实”,由于张炎本人既用它来推尊姜夔,又只是打了一个比方,说“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因此,“清空”二字很难落实到具体的词文本批评之中。其实,“清空”并不是玄虚的。在沈雄征引张炎论“清空”之前,他引了论“情”与“景”配合的文字;如“云间派”宋徵璧说:“善述情者,多寓诸景。”沈雄自己也说:“词有写景入神者。”那么,所谓“清空”,应该是根基于一种“情景论”,它的要求即“寓情于景”“写景入神”。如果只是写景而不动情,便走向了“清空”的对面即“质实”。而“清空”“质实”之分,也不是指字面上是否含混晦涩,应是指词中写景的句子,能否融入灵活飞动的情感,所谓“景以情妍,独景则滞”。如此说来,所谓“清空”,不也就成了“借景抒情”一类的陈言。当然不是的。张炎专提出“清空”来,是立足于词所具有的特性。所谓词的特性,借用孔颖达的话,可以说是“言邪而意正”(《毛诗正义》“诗大序”),也就是说,词借用的语辞,是不庄重的,多是涉及艳情的。因此,“清空”便是针对这类艳情内容甚至字面的歌词而发的,即能够有超出内容与字面之外的精神存在。如此,“清空”所要求的“写景入神”,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景交融”,而是“情在景外”“情不关景”。
二、释“词贵离合”
离合就是“著题”的程度与分寸。沈雄先引了宋征璧的话说:“语不离则调不变宕,情不合则绪不连贯。”像是说的是“语离情合”,也就是词中措语可以和主题偏离,但情绪则是连贯的。又举出柳永为反证说:“每见柳永,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此是其病。”用这样一条标准来评述柳词,不免是偏颇的;但由此可见“离合”的所在,即不要求“句句联合”,也就是每一句都围绕着主题来展开,但于“意”上却不能有更大空间的拓展。接着,又引了毛先舒的话说:“如行乐词,微著愁思,方不痴肥。怨别词,忽而展拓,不为本调所缚,方不为一意所苦,始有生动。”这便说的很明白了,“乐词”可以著“愁语”,“怨词”也可以故作排解,这都是“离”。接着又引了黄山谷的话说:“好词惟取陡健圆转。”(不详沈雄所本)“陡健”是“离”,“圆转”是“合”。除了沿袭宋征舆对柳永能“合”不能“离”的批评,还举出苏东坡来,说他“滔滔漭漭,不能尽变”,从上下文推测,应该是说苏词是能“离”而不能“合”才对。下面,沈雄又举出的几个例子,并不算高明惬当,也就不再一一征引了。
以“离合”进入诗学批评,最早的应该是见于南唐僧文彧的《诗格》中的“论诗势”(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作者订正为“神彧”)。[2]这部《诗格》是收在被罗根泽称为“诗格丛书”的南宋人陈应行所编的《吟窗杂录》之中,[3]其云“先须明其体势,然后用思取句。诗有十势”:“八曰离合势。诗曰:‘东西南北人,高迹此相亲。’”[4]唐人诗格一类的著作,最喜欢谈“诗势”的问题。这里所谈的“十势”,其中若“狮子返掷势”“龙潜巨浸势”,也见于同样收在《吟窗杂录》中的齐己的《风骚旨格》之中。再往前追溯,旧题王昌龄的《诗格》中,竟有“十七势”之多。唐人谈“势”,本自《文心雕龙·定势》。刘勰说:“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又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他举例说:“圆者规整,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5]看来“体势”是不可分的,有一“体”方有一“势”。而“体”又与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性格作风以及他在创作之际所选取的文章形式相关,因此,“势”归根结底是可以谈到“风格”上去的。但唐人谈“势”,多是就诗篇造句言之,落到了技术层面。
“离合”进入词学批评话语当中,已经不同于局限在谋篇造句的“诗势”之一种,而是一个特指性质的词学概念。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曹掌公(鉴平)说:“词贵离合,不粘本题,方得神情绵邈。”[6]周介存《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沉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次则讲色泽音节。”[7]蔡嵩云《柯亭词论》说:“意境神韵无论矣,字法句法章法,一毫松懈不得。字法须讲侔色揣称,句法须讲层深浑成,章法须讲离合顺逆贯串映带。”[8]与沈雄同时的曹鉴平说“离合”二字,是最准确的定义,所谓“不粘本题”。他与毛先舒都说“词贵离合”,与宋徵璧说“妙在离合”一样,都说明了“离合”在词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当然,这种创作的重要性也延伸入批评之中。周介存对“离合”在创作过程中的定位,即“用心——片段离合——色泽音节”,则是关于“离合”在词学批评过程中最为准确的定位。对于作者,则是如周介存所说的这样一种次序,但对于批评而言,恰恰倒置了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首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色泽音节”,也就是造语措辞的问题。其次便是“片段离合”,也就是组织成文本的“词”如何“达意”的问题,最后才是作者的用心。后来,蔡嵩云干脆将“离合”视为一种章法,与他同时代的陈洵在《海绡说词》中屡屡使用“离合顺逆”来批讲周邦彦、吴文英的词——虽然这样不免将“离合”从批评术语拉回了创作手法,但大体上也是无误的。
现在要解释的一个问题,还是清初人提出来的“词贵离合”。如果“离合”只是晚清民国的学者所认为的片段章法的安排,是称不得这个“贵”字的。与本题的不粘著,也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宕开一笔,是在“文法”与“诗法”中都能见到的,为何就成为了词学批评的专有概念?这还是要从词的特质说起。词以“艳情”为“本色”,但第一流好词,往往不必局限于此,但又不能不有所照顾于此,这是其它的文体所不能有的尴尬,也便造就了“词论”当中独有的主题处理方式——“离合”。它在南宋词人的咏物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但发端实际已在北宋中后期苏轼及其周围的士大夫词中。这对“词”的创作而言,不啻为一次新生命的注入。盖伤春怨别,陈陈相因,终将会走到穷途末路上去;而完全改头换面,徒留下长短句的形式,则“词”也非“词”,完全成为了长短句诗。旧题之中贯注新意就是“离”,新意又不至于改变本质,便是“合”。故词的评赏,情景之外,能有“清空”之想;春花秋月之中,复得“离合”之趣,自是独特的境界了。
三、“新寄托”释
这个“新”,不是沈雄引的杨守斋《作词五要》所谓的(1)须作不经人道语;(2)翻前人意;这两者都算不得上是词学批评当中讲的“新”,也不是明清之际的词家狺狺争辩的“本色”“意态”与“自然”,这都落到了第二层。王国维《人间词话》之五六则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9]这至少用以笼罩明清之际词家对本色自然之词的推举,是毫不费力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重复了这一段话:“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10]之所以不惮烦地重新引一遍,是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明清之际的词学家所主张的本色自然,实际上是混词入曲的结果。尽管王国维说“明以后,其思想结构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元人所独擅”,但这不是事实,只是他一人之见而已。以王国维对“意境”的定义来看,其实就是“本色自然”“深于意态”,如《古今词话》中录江尚质(他同时是该书的编者)所云:“花间词状物描情,每多意态,直如身履其地,眼见其人。”这与王国维之推重元曲,标准无殊;第二,王国维明确地讲此即“意境”,他在《人间词话》中虽没有这样讲得明白,但这段言情沁人心脾,写情豁人耳目的话,则并没有删去。看来,王国维对自己在词话里面倡导的“词以境界为上”的“境界”之内涵,与评论元曲时所言的“意境”,相去并不太远;只是研究对象的改变,让王国维面对歌词时,已然感觉到这种本色自然的批评难以完全奏效。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王国维可以信心满满地说戏曲研究是自他开端,但对“词学”则完全没有了这样的“话语权力”;甚至他的所谓境界说,并不能超越常州派的寄托说。
在沈雄所引的批评资料中,所谓“张炎”的“不求新而自新”,才是词的新意的所在——但这不是张炎的原话,而是沈雄所引资料中的发挥添加。尽管如此,“不求新而自新”在这里也没有作进一步阐明,还只是从张炎原话中举出来的正反例证。如苏轼的“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之处便是,这连刻意求新语新意的周邦彦、秦少游都非敌手,更无论辛稼轩、刘龙洲等人的一味专作壮语,甚至将雄奇演变成怪怪奇奇、滑稽游戏了。举例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往往取其一端,不可太认真着实,以为周、秦、辛、刘就是如此。但举出苏轼来说明“出新意”,却是不二人选。其实,宋词批评中所讲求的“新意”,应该就是沈雄下面引到的毛先舒所谓的“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以及贺裳所谓的“用意浅淡,愈翻愈妙”、王士禛所谓的“翻来极浅,反入人情”。这样几段话,貌似有些矛盾,实则不然。由于他们站在的角度不一样,更由于他们选择的批评对象有差别,方才会出现这样貌似矛盾的话。略过这样矛盾的表象,选取它们相交会的部分,则这里的指向应该就是“语浅意深”。
“语浅意深”,是词学批评当中所特有的要求,它同样来源于词的特质——语辞内容上的“伤春怨别”而内在精神上的阔大深广。贺裳与王士禛所谈的“翻”的问题,是局限在了语句构造的技法方面,只是这一批评术语的极为浅层次的内涵;毛先舒的“层深”与“浑成”,较之贺、王,要更进一步,触及到了“新意”形成的本质,尤其是他举出的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更是十分准确地选择了批评的对象。这个例子可以视为“新意”的典范。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则不是清初学人所能的,它要等到张惠言以“寄托说词”之后,方才有了更加充实的内涵。周介存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咳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11]
这仍旧是迄今为止讲“词”作为一种独特文体之批评讲得最好、最具概括力的一段话,虽然他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谈,但还是可以将他讲得次序颠倒过来,反方向来探寻与领会这位一流的词学批评家的严密体系。这段话最后打的譬喻是“赤子随母笑啼”与“乡人缘剧喜怒”,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诗学批评当中讽刺没有自己看法的话,叫作“矮人观场”。诚然,周介存并非就此言之。但“矮人观场”与“乡人缘剧喜怒”从喻体来讲,的确是一回事,那么它们的指向,也就是本体所在又有若何不同呢?这便是“词之为词”的妙处所在。我们读一篇文章、一首诗,总是能够从文中、诗中获得一些“意思”出来,无论这“意思”是深是浅,总是有些的;但“读词”或者说“词的读解”与“批评”,并不以获得“意思”为目的。它有一些“意思”,可以符合“诗言志”“知人论世”的度量,这诚然是可以的;但它没有一些“意思”,也是“词”的“常态”。但“词”中的“没有意思”,不等同于“没有意味”。继续逆着周介存的话向前,他打的两个譬喻,一个是说“读词”,像在水边观鱼,而鱼的来去游动,让人捉摸不定,这一条是鲂鱼,那一条是鲤鱼,只能得到个大概而已——这个譬喻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庄子》里面那个著名的“子非鱼”的故事来,如果把“鱼”比作批评对象即“词”,而我们这些读者在面对“词”的时候,还真的就是庄周与惠施的角色——“鱼”究竟如何很难讲,但不妨碍观鱼的人先来一番争论。另一个是说“读词”,像半夜里睡得正好,突然被一阵闪电惊觉,一时间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也就是不知所云。如此,凡读词所获,则不是得其仿佛,便是不知所云。那么,或者要问“词”有这么难读吗?说“难”与“不难”,是从“理解意思”的角度说的。也就是说,如果要说一首“词”在表达什么内容与情感,这一点并不难读。但问题是,“读词”不以获得“意思”为目的。你拿一首词来读,总有一些东西是要逾越于“词”中这“意思”之外的。
在中国诗学沉淀下来的批评中,有所谓“言外之意”。不过,这“言外”是由“言内”生发出来的,不是独立的,其实是文本包含着但未发出来的“不尽之意”。欧阳修《六一诗话》引述梅尧臣的话,曾举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说“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者便是。[12]“词”的批评当中,当然也有这“言外之意”的存在。不过,它的“意”不仅是在“言外”,更是“无主”。或又以为这“无主意”,岂非“诗无达诂”?在诗学批评中,莫说有阮嗣宗的《咏怀》、李商隐的《无题》,难以确解;纵然是《诗经》以及老杜的诗,究若是“美”是“刺”,也难以有“主意”的。此言虽不虚,但要看到“词”在表达上的特性,便是“语浅”。周介存说:“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是站在创作者的地位的甘苦之言,也是词学批评的重要一环。“诗”中那些“无达诂”之处,成因的确是复杂的,有些也与“词”是相通的,比如“香草美人”传统的承继。但“词”相较于艳情内容的“诗”来,它的呈现却是平淡而浅近。周介存从创作角度说,那些平淡与浅近之处,实则是出自创作者的“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用谭复堂的话说,就是“作者之用心未必然”。其实,何止是“未必然”,简直就是“不知所然”——连作者也不曾知道,他为何要选用此类浅近而平淡的语辞来组织成“文本”。那么,这是不是和宋人所主张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诗学相通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或以为“读词”是“得其仿佛”“不知所云”,“作词”是“全无主意”“不知所然”,难道所谓词学批评,岂不成了玄之又玄之事?话还得要说回来,即这里所探讨的词学批评的出发点,便是要从词本体的特质出发。以上所言,其实尚未能深入词本体的内部,只是围绕它的外在呈象而有的印象与困惑,简言之,便是“语浅”与“非庄语”的“词”,传达出的艺术力量,决不限于它的语辞涵义。这一点,是无可争辩与质疑的事。上面曾引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作为例子,类似的例子,在宋人词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断章举证那些名句。可是,难题也便在此出现了。“词”之“外在呈象”的浅近与平淡,并不足以涵括“词”的所有——除非作泛泛的阅读或只是从“宋词”当中寻找社会文化史的资料。但进一步,“词”的“内在精神”又如何能够探取呢?周介存只是从创作讲,这一问题,他完全可以略过。但实际上,也暴露出在传统诗学的势力下,批评家不得不作出的一种妥协。他说的“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就是这个妥协的结果。“词”中的“内在精神”,当然不是忠爱缠绵、香草美人的寄托可以涵括的。不过,我们还是十分地敬佩这位一流的词学家,他虽然沿用了“寄托”一辞,但为这个批评术语扩展了内涵——他将“词中寄托”扩展了范围,是处在“触类多通”“意感偶生”“冥发妄中”的状态,也就是不能确指,想通过“知人论世”和“香草美人”的比附,并无法完全获得。
周介存的理论,借用他自己所说也是“以无厚入有间”,即把词的“外在呈象”与“内在精神”的关联剖析得最为确当、严丝合缝。晚清民国的词学家,无论有意无意,几乎是无人可以逃出他的理论;虽然至今还是用“寄托”两个字来概括周介存的学说,但这里更希望是用“新寄托说”来划清他与传统诗学比兴寄托的泾渭分别。不过,正如上述提到的“难题”,周介存是将词文本内外的关联呈露了出来,至于批评实践当中如何由外入内,返回来又将浅近平易的外在呈象重现出另一番光彩,至今日仍还是一个“难题”[13]。无论是况周颐还是王国维,他们都是各自从一个方面切入部分回答了这个“难题”,其它的则大可以归入自桧以下了。从这一角度说,很多人都认为王国维提出“境界说”是词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理论创见,现在来看恐怕说得有些晚——真正意义上的划时代,应该就是周介存的“新寄托说”。
关于这“新寄托说”,还可以征引两件词学掌故,见出它的接受状况。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8月1日载:“得孟劬翁函,论四声。又谓王静安为词,本从纳兰入手,后又染于曲学,于宋词本是门外谈。其意境之说,流弊甚大。晚年绝口不提人间词话,有时盛赞皋文寄托之说,盖亦悔之矣。”[14]按,张尔田(孟劬)对王国维的词学,评价不免低了些,但记王国维晚年悔其少作即《人间词话》,这是事实,有王国维与陈乃乾的1925年的书信可证。[15]至于这里提供的另外一条主要信息即王国维盛赞张皋文寄托说,也不是虚语。王国维治词学,让他心有戚戚之感的,便是周介存的著作,现有王国维写于1905年的跋语为证。[16]只是无论张尔田所记还是夏承焘的存录,甚至包括王国维本人,他们对寄托说的体认,无例外还是老一套的传统学说——如《天风阁学词日记》同年9月1日载:“过吴眉翁谈词,谓北宋已有寄托,东坡我欲乘风归去为不忘爱君。王安礼不管华堂朱户,春风自在扬花为诮安石。予意诗人比兴之例,其来甚古,唐五代词,除为歌妓作者之外,亦必有寄托,惟飞卿则断无有。后人以士不遇说其菩萨蛮,可谓梦话。常州派论寄托,能令词体高深,是其功,然不可据以论词史。”[17]吴庠(眉翁)与夏承焘的一席谈,是到今天还延续着的对寄托的理解,即属于传统的寄托说,也是对包括周介存在内的常州派词家的不可撼动的看法,实际情况则要有所辨证。
结语
上述说清初学者沈雄的《古今词话》的“品词”是建构起来了“词学批评体系”,其实也是无心插柳罢了。但他也不是一股脑地不加分别地钞录前代与同辈的词学批评,沈雄自己也将他的《柳塘词话》不失时机地安插其中,是颇有些个人观点的。那么,沈雄钞录这一批词话,他自己要表明的批评体系是什么呢?简单地讲,便是“情景——章法——语句”,也还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谈谈欣赏的问题。不过,他以及江尚质的辛勤收辑,为我们今天探索词学批评自身的体系提供了方便,毕竟在我们之前,晚清民国常州派以及受到常州派影响的词家,将词学的批评推向一个高峰。
由此,清空、离合与(新)寄托,从历史上看,亦即它们产生的时代是有先后的:“清空”是宋元之际提出的,“离合”则在明清之际运用于词学批评,“(新)寄托”距离我们最近——周介存在那篇《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末署的是“道光十有二年冬十一月八日”,这一年西历是1832年。其次在词学批评体系当中,三者起到的作用与能够发挥的效用,并不是一致的:“清空”与“离合”是决定“词”是否能够在相似的情景内容中产生独特的风格,至于下一步是选用西方批评的术语——新批评学派对文本的细读,围绕着一些构成文本的要素展开,如情境(sit uation)、形象(image)、语气(tone)、隐喻(metaphor)、象征(symbol)、主题(theme)以及韵律(metrics),叶嘉莹讲词就移用了这些术语,而不再使用情景、章法、片段、句法、用字等传统的文本分析要素。如叶嘉莹在《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18]即曾有意识地借用;而在谈及判断一首词有无寄托的三项标准时,将作品叙写之口吻及表现之神情列入(见《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19],应该是无意识地受到了新批评派理论中对“tone”的分析影响。这种无意识,正说明了中西方诗学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更为直接的例证,是叶嘉莹对纳兰性德词的研究,据作者自言是经历了如青原惟信禅师从“看山是山”到“看山只是山”式的证悟,同时作者又借用姚斯阅读视野三层次说与之相互发明(《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20]。其实,新批评学派在诗歌读解的过程中,也正沿循着这样一种从“innocent”到“innocent”的过程。[21]
现在来看,是否借用外来术语和传统批评,都需要与这清空与离合两项“义界”打交道。至于第三项,则是超出了文本要素的分析,进入到更高一层次的分析。但它在批评实践上,目前的困境不小。我们认为,虽然作为历史的、思想的或者社会文化文本的“词”,自然不能排除“旧寄托说”以及相当数量的完全没有寄托的作品;但应该正视的是,施用“新寄托说”的文本批评,是可以最为完满地呈现出作为“文体”的“宋词”之特质。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1][6][8]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 849-852页,第 1940页,第 4902-4903页。
[2]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页。
[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二)》[M],北京:中华书局上编所,1962年版,第215页。
[4]陈应行编《吟窗杂录》卷12[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7页。
[5]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 529-530页。
[7]顾学颉点校《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9][10][15][16]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卷,第477页;第3卷,第114页;第15卷,第702-703页;第14卷,第527页。
[11]周济编《宋四家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页。
[12]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28[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52页。
[13]马里扬《清代常州派词史说新诠——兼论近百年词学阐释理论之建构》[J],载《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四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页。
[14][17]夏承焘著,吴战垒编《夏承焘集》第六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第332页。
[18]叶嘉莹《古典诗词讲演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 1-40页。
[19][20]叶嘉莹《清词丛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172页,第115页。
[21]Cleanth Brooks&Robert Penn Warren:Understanding Poetry(《理解诗歌》)[M],北京:外语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上海师范大学文科一般项目(A-0502-00-005024);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4S041);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13CG4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