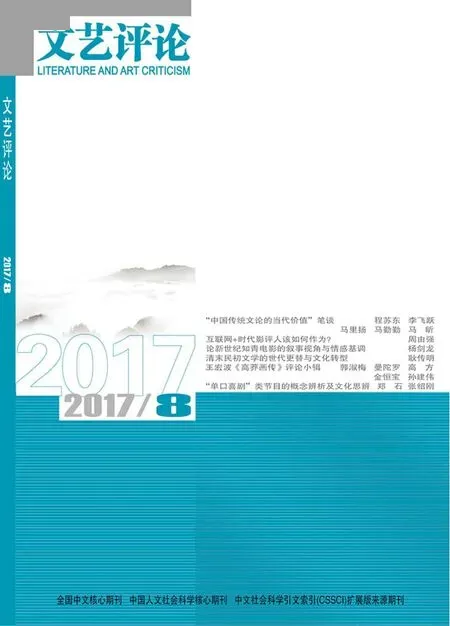也谈战国秦汉时期“作者”问题的出现
2017-09-28程苏东
○程苏东
也谈战国秦汉时期“作者”问题的出现
○程苏东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热门的学术话题之一,“作者”问题曾经吸引了西方最重要的一批思想家、哲学家加以讨论,“保卫作者”(E.D.赫施)、“作者之死”(罗兰·巴特)、“作者是什么”(福柯)等论断或追问早已成为西方文论史上的经典命题,[1]至今仍影响着中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展开。不过,这一话题似乎直到本世纪初才被系统引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视域中。笔者大致调查了上世纪初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多部经典著作,发现在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论述与资料汇编中,大多对“作者”问题并未特别关注,但事实上,无论是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问题的阐述,还是司马迁、王充等对于“作”“述”“论”“文儒”等概念的细致剖析,战国秦汉时期发生的这次“作者”问题讨论确实与西方文论界关注的“作者”问题具有若干层面的相关性。看起来,当前学界对于早期中国“作者”问题的关注是在西方“作者”理论的影响之下重新发掘的一个本土传统,与民国时期基于辨伪学立场而产生的“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古书不题撰人”等观念虽然陈述略近,[2]但在方法论意义上存在明显差异。
据笔者所见,普鸣(Michael Puett)的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2001年)似乎是最早对“作者”问题的“中国个案”进行梳理的著作。通过对孔子“述而不作”这一概念及其接受史的论述,以及墨子、孟子、陆贾、贾谊、司马迁等人对于“作”的不同解读,普鸣建构了关于“作者”问题的中国传统,并论述了在这一传统中“作”所具有的神圣性与权威性问题。随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2006年)一书中也关注到汉魏古诗的“作者”问题,并特别强调了“作者”观念对于文本解读所具有的约束性问题,基于汉魏古诗“作者”常常无法确定的考证结果,宇文倡导“作者”的离场与“文本”的中心地位,显示出汉学界对于“作者”问题的关注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于“作者”功能的弱化乃至消解之间的密切关系。柯马丁(Martin Kern)在他近年来关于《诗经》《尚书》《楚辞》等早期文本的研究中同样贯穿着对于“作者”问题的关注,他的The“Masters”in the Shiji(2015年)、《汉代作者:孔子》(2016年)等文章均旨在论述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初士人对于“作者”这一观念之形成的关键作用,并由此对学界对于先秦文本的传统认知方式提出了反思。[3]可以说,“作者”问题已成为当前欧美汉学界关于早期中国文本生成与传播研究中最富争议性的话题之一,相关论述涉及“作者”的神圣性与主体性、言说与书写的权利与个人化、“作者”功能与文本阐释的边界等问题。可以说,尽管“作者”问题已不再是当下西方文论界关注的核心论题,但对“作者”问题的“中国个案”进行梳理和反思,却成为近年来欧美汉学界和国内文论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可以预期,这一讨论不仅将有助于解决早期中国文本生成研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似乎也可以为整个“作者”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新个案。在这方面李春青的研究颇具开拓性的意义,[4]值得关注。
不过,笔者在阅读上述论著的过程中,也感到目前学界对于《孟子·滕文公下》等部分涉及“作者”问题的关键文献在解读上多少受到西方“作者”理论的影响,在强调先秦时期“作者”观念之神圣性的同时,似乎忽略了孟子时代对于“圣人”的认知与秦汉以后颇有不同。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孟子对于“作”之必要性的强调、以及司马迁、王充等对于“作”的神化与回避,早期士人对于“作”的论述虽有不同,但其背后对于言说与书写的个人化这一权利的声张却是一以贯之的。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王充等汉人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孟子尤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涉及到我们对先秦文本生成方式的认知问题,故笔者不揣谫陋,以下略作申说。
一、以“立言”而“不朽”的早期传统
在早期文献中,有一位名为“迟任”的言说者令人印象深刻。虽然我们对于他的德行、成就一无所知,但在盘庚迁殷的重要场合,他的名言得到了盘庚的徵引,并与这一历史事件共同见载于《尚书·盘庚》:“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5]在《左传》与《论语》中,又先后三次引述一位名为“周任”者所言之语,不能确定是否与此“迟任”即为一人。不过,无论是迟任还是周任,除了他们所说过的话语以外,没有任何具体行事得以传世,他们仅仅因为自己的言语曾被盘庚、孔子等圣贤引用而名垂青史,这似乎正显示了《左传》中叔孙豹以“立言”而“不朽”的表述并非虚辞。换言之,在叔孙豹的时代,“立言”不仅被视为贵族公卿普遍拥有的权利,而且是一种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文化行为。在“立言”的过程中,不仅其所说之“言”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这一行为本身也与“立功”“立德”一样,直接关乎言说者个人名声的确立。可见,虽然在西周、春秋文献中并无关于“作者”问题的实质讨论,但无论是迟任、周任的留名,还是叔孙豹关于“立言”的论述,均显示言说作为一种个人的权利与价值实现方式,至晚在春秋中前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观念。近年来,先秦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便是对早期文本中“公共素材”的揭示与看重,[6]而由前论看来,“个人话语”同样是先秦文本生成的一种重要方式,如何对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关联加以辨析,是未来文本生成与传播研究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此外,在《论语》中也有两段关于言说的论述值得注意,一段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另一段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7]。这两段材料都涉及言说者的主体性问题,第一段材料强调“言”并非“人”之附庸,两者具有各自独立的价值标准,“言”既非某一社会群体所拥有的专利,其优劣与否也不足以证明言说者自身的品格高低;而第二段材料则塑造了一种不同于“大人”的“圣人”形象,他们无关“天命”,也不掌握“大人”的政治权力,但因为他们的道德、知识,特别是他们的“言语”,使其得以与“天命”“大人”分庭抗礼,并为“三畏”。两段材料看似矛盾,却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孔子的知识世界中,无论是“圣人之言”还是“恶人之言”,“言”常常是伴随着“人”而出现的,所谓“君子不以言举人”,这恰恰说明在孔子所处的现实社会中,“以言举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认定方式。由于春秋时期私家著述尚未出现,叔孙豹、孔子所论的这些“言”大多恐怕是以口传方式流传的,如同上举《盘庚》篇对于迟任之言的征引,“史佚有言曰”“臧文仲有言曰”“仲虺有言曰”“先大夫子犯有言曰”等是《左传》中常见的征引方式,凡此足见在书写文化普及之前,关于言说主体的个人化问题已经得到充分的关注。“言说”不仅是公卿、士人等各个阶层普遍拥有的权利,而且有可能成为其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方式,在《尚书》《左传》《论语》对这些言语的征引中,这些言说者显然已初步具备了“作者”的意味。
二、“作”以成圣:孟子对于“作者”的塑造
从现存文献看来,孟子大概是最早在书写文化的背景下对“作者”形象进行塑造的士人,相关论述见于《孟子·滕文公下》: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乎,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于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8]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以“作”字描述孔子与《春秋》之间关系的文本。众所周知,孔子对于“作”曾有过著名的论调:“述而不作。”[9]孔子之所以自称其无所“作”,皇侃《义疏》言:“所以然者,制作礼乐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无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则礼乐不行;若有位无德,虽为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则礼乐不行。故必须并兼者也。孔子是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也。”[10]这里从“德位相配”的角度论述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因,多少受到汉儒“素王”说的影响,不过其强调“作”具有高度的仪式性与象征性,则颇合孔子原意。[11]简言之,孔子将“作”界定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方式,具有变古开新的意味。此外,孔子又反复强调“慎言”的重要性,相关论述广见于《论语》之中,这些无疑会给孔门后学造成一种颇具压迫感的“言说”气氛——既然先师孔子都不敢言“作”,则孔门后学如何敢妄造篇辞,如何敢骋说胸臆呢?
在《孟子》中,正是为了回应公都子所谓“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的质疑,孟子提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命题,并展开了系统性的长篇论述。这一问对的语境非常重要,它显示出孔子“作《春秋》”之说从一开始就与“言说”的权利与方式有关。对于孟子而言,这段论述主要不是为了阐明《春秋》的作者问题,而是旨在强调孔子有所“作”的事实,从而揭示出其所谓“述而不作”只是夫子的谦辞而已——孔子通过“述而不作”的陈述将“作”这一行为神圣化,而孟子则借助这一逻辑的反向推演,在将孔子本人神圣化的同时,[12]也进一步确认了“作”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从而最终为自己的“言说”争得了合理性。
具体而言,孟子通过两种方式对孔子“作《春秋》”的象征性意味予以强化,首先是将其置于从大禹治水到武王伐纣、周公攘夷的“一治一乱”演进过程中,通过“孔于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结果呈现,强调“作《春秋》”这一文本书写行为与上述圣人之功同具拨乱反正的历史效应,从而在论述的最后自然而然地将孔子与大禹、周公并称为“三圣”。在这一论述逻辑中,孔子正是通过“作《春秋》”的方式进入了圣人的行列,《春秋》成为确认孔子圣人身份的关键标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的经典化不仅与孔子的圣人化过程相始终,而且其本身就是孔子圣人化的实现方式。
其次,为了渲染孔子“作《春秋》”这一“成圣”之事的仪式感,《孟子》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复述了孔子的一段感叹:“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我们当然无法考证这一说法的可靠性,不过类似说法又见于《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其词则丘有罪焉耳。”[13]同样是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出现,这显示出强调孔子“作《春秋》”可能存在的“获罪”风险,是受到战国儒士青睐的一种叙述方式。一部文本的书写何以会带来“获罪”的风险呢?从孟子的论述来看,是因为这一行为是“天子之事也”,而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亦言:“词有褒与贬、绝,假天子之事,故谦以为罪也。”[14]正如柯马丁所言,“孔子所‘作’,不仅是一篇文本,而是一种新的王权模式,取代了过去的王权,因为他僭擅了‘天子之事’”[15]。孟子虽未明言,但联系上一点,我们足以注意到,无论是大禹治水、武王伐纣,还是周公攘夷,几乎每位圣人的“成圣”之路上都伴随着高度的危险性,但也正是这些危险,才凸显出“成圣”之路的不易与辉煌,而这些危险除了现实中的自然、军事威胁以外,还包括其行为自身的道德风险: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弑君”之嫌,直至汉初尤未完全褪去,[16]而孔子以“从大夫之后”代行“天子之事”,自然也就具有了“革命”的嫌疑。尽管其“革命”的方式只是“制作”一部文本,但其性质则可与汤、武等量齐观。在《孟子》所引的这段感叹中,我们体会到一种临危受命、大义凛然的风范,“作《春秋》”被赋予了某种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使得孔子的“成圣”之路与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圣一样,充满了危机与挑战,而孔子“圣人”的形象,也由此显得高大而悲壮。简言之,“作《春秋》”不仅是彰显孔子“圣德”的重要方式,而且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孔子成为“圣人”的途径和证明。孔子不是以“圣人”的身份来“作《春秋》”,而是通过“作《春秋》”而最终获得了“圣人”的历史认定,“作”不是圣人的专属权利,而是普通士人成为“圣人”的一种方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的时代,“成圣”虽然具有明显的神圣性指向,但这种神圣性与西方神学背景下的“神圣性”(Divinity)显然不同,事实上恰是对人间社会中美好人格的一种确认。《论语》中孔子与子贡曾有一段对话: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7]
这里孔子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称为“圣”,显示在孔子心目中,“圣”除了自身具备美好的人格以外,尤能博施于人。基于孔子一向自谦的言说风格,他认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18]将自己排除在“圣人”与“仁人”的范畴之外,但熟悉孔子言语风格的子贡就曾经指出: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19]
事实上,当孔子称其“岂敢”时,意味着他已经将自己放在了“圣”与“仁”的标尺上进行丈量,而这就表明无论孔子本人是否真的达到这一标准,“圣”与“仁”都是适应于人间社会的一种价值标准,是对于“人”才有意义的标准。这与秦汉以后“圣人”逐渐超离人间,成为神格化的“往圣”有重要的分别。从子贡到孟子、荀子,正是在他们的不断言说中,孔子才由一个仕途蹭蹬的“从大夫之后”跻身“圣人”之列,而孟子心目中的圣人除孔子以外,还包括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汉代以后至多被称为“仁人”的士人。[20]随着现实中王权的崩解,一批“德”“位”分离的道德权威、知识权威得以出现,而对于孟子、荀子等战国士人而言,这种“造圣”不仅是对前代圣贤的尊崇,事实上也是对于他们自身历史地位的一种预期,这是在大一统的国家权力长期出现“真空”状态时才可能出现的一种舆论环境。在这段论述的结语部分,孟子提出以“言距杨墨”而跻身“圣人之徒”的问题,这种通过言语来实现个人价值的思维方式与孔子“作《春秋》”而“成圣”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足见言说不仅关乎王道兴衰,也关乎个人的历史地位。因此,“作”虽然被赋予神圣性意味,但这种“神圣性”非但不是不可模仿、不可接续的,反而是具有高度吸引力和正当性的。《孟子·离娄下》以“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引出孔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陈述,[21]这里塑造的孔子形象正是挣脱了王权对于文本书写的垄断后获得的一种紧张的自由感。经过《孟子》对于“作”之必要性、迫切性与正当性的充分论述,言说与书写再次被赋予鲜明的个人化色彩,并成为一种带有高度理想性、批判性与创造性的行为。在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王权式微背景下,《春秋》由“公共史料”逐渐被视为反映孔子私义的“个人话语”,诸子文本亦大量得以编纂、书写与传播,从“立言”到“著述”,“作者”的光环赋予书写这一行为以特别的魅力,以至身为秦相的吕不韦也对“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的盛名羡慕不已。[22]
三、圣统告终与“作者”的重塑
对于孟子而言,借助于对孔子“作”以“成圣”的形象塑造,言说与书写获得了一种令人向往的吸引力,这一思路在《荀子·正名》中同样得到延续。[23]但入汉之后,随着儒学逐渐成为帝国尊奉的国家意识形态,包括孔子在内的“圣人”开始成为一种不可模拟、无以接续的神格化存在,这就使得具有成圣之道意味的“作”同样也具有了不可模拟的禁制性。
从传世文献看来,“圣统”是否告终一度成为西汉士人特别关注的问题。司马迁上距孔子去世不过三百余年,但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却借其父之口声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24]显示出有意通过文本书写接续圣统的野心。然而,在帝国的文化体制之下,这一行为显然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国家虽然崇儒尊圣,但其管理体制却无法容许在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以外出现其他的学术权威,无论是西汉的石渠阁会议,还是东汉的白虎观会议,虽然与会者是一时之“儒宗”,但最终却需以天子“称制临决”的方式予以裁定,显示出圣人虽是道统之管,但皇权才是现实中经典阐释的权威性来源。在这一制度中,如果出现新的“圣人”,则显然将无法处理“圣人”与“皇权”关于经典阐释权的纠纷,所以,随着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整个“圣人时代”事实上也就告终了。与孔子、孟子在广泛意义上使用“圣人”这一概念不同,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已经将“圣人”明确限定在儒家“圣统”的范畴之内。
与此同时,汉儒对于“圣人”的神格化塑造也逐渐兴盛,古老的“五帝”被纳入“五德”谱系而获得神性,孔子则被塑造为“黑龙”“水精”,其“作《春秋》”更被公羊家赋予了离奇的神学色彩,凡此都使得“圣人”逐渐脱离人间社会,成为不可模仿的神格存在,这也就构成汉人关于言说与书写问题的新挑战——“作”不再是言说、书写者的至高荣誉,而是圣人专享的一种沟通天人的方式,对于“作”的模仿不仅是对“圣统”的觊觎,更是对现实皇权的挑战。孟子塑造的“作者”观念不仅无法成为汉人声张其书写权利的依据,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作”对于普通士人的禁脔意味。在此背景之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刻意强调其书写行为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25],而在《对作》篇中,王充亦强调“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26]。通过将自身行为定性为“述”“论”,司马迁、王充为其著述重建了合法性,[27]而在他们的语境中,“作”已近乎成为一种指控的罪名,这恐怕是孟子始料未及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通过将“述”与“作”彻底加以区分,对于司马迁而言,其“述”除了如孟、荀一样需承担“言辟杨墨”“说行而天下正”的公共使命以外,同时也可以承载他作为个人在“意有所郁结”的情绪下“发愤著书”的宣泄功能。[28]言说与书写至此不仅成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之一,更成为每一个生命主体都拥有的当然权利。在汉儒对于“作者”的重塑中,狭义的“作者”虽然被神格化了,但言说与书写行为的个人化色彩却愈加强烈了。
总之,无论是叔孙豹所谓以“立言”而“不朽”,还是孟子对于“作”的神圣化叙述,抑或汉人对于“作”的神格化,以及与对于“述”“论”的正名,战国秦汉时期士人对于“作者”问题的讨论虽然对“作者”的权利来源、社会地位等认知有所不同,但事实上都一以贯之地强调个人言说与书写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逐渐构成早期文本书写中的“子学精神”,并最终以“古文”之名构成后世不断追慕的一种文学典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相关论述可参张永清《历史进程中的作者(上、下)——西方作者理论的四种主导范式》[J],《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第101-110页;第12期,第120-136页。
[2]罗根泽《罗根泽说诸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 200页。
[3]Martin Kern,The“Masters”in the Shiji(《〈史记〉中的诸子》)[M],T'oung Pao,2015,101(4-5):335-362;《汉代作者:孔子》[A],王能宪等编《从游集:恭祝袁行霈教授八秩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4-133页。
[4]李春青《中国古代“作者”观的生成演变及其文化意味》[J],《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87-94页。
[5]《尚书正义》卷 9[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9页。
[6]徐建委《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J],《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9页。
[7]程树德《论语集释》卷23《卫灵公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 1106页;卷 33《季氏》,第 1156页。
[8][20][21][清]焦循《孟子正义》卷 13[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 446-461页;卷 20,第 672页;卷 16,第572-574页。
[9]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3《述而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1页。
[10][梁]皇侃《论语义疏》卷 7[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3页。
[11] Michael J.Puett,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2001,p.49-51.亦可参李春青《中国古代“作者”观的生成演变及其文化意味》[J],《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12]柯马丁在《孔子:汉代作者》中指出:“这里,尤其是
‘作’字,是称孔子为圣人的间接方式,他在过去圣王的意义上‘作’。”柯马丁《孔子:汉代作者》[A],王能宪等主编《从游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2-113页。
[13]《春秋公羊传疏》卷 22[M],《十三经注疏》[Z],第 2320页中栏。毛起认为《公羊传》的这段论述受到《孟子》的影响,但具体论证略粗疏,可备一说而已,毛起《春秋总论初稿》[M],杭州:贞社,1935年版,第3页。
[14][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昭公第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15]柯马丁《孔子:汉代作者》[A],王能宪等主编《从游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 114页。
[16]《汉书·儒林传》载景帝时黄生之言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汉书》卷 88[M],第 3612 页。
[17]程树德《论语集释》卷 12《雍也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7页。
[18]程树德《论语集释》卷 14《述而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0页。
[19]程树德《论语集释》卷 29《宪问中》[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11页。
[22]《史记》卷 85《吕不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30页。
[2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 16《正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22-424页。
[24][25][28]《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M],第 3974 页,第3977页,第3978页。
[26]黄晖《论衡校释》卷 29《对作》[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1页。
[27]关于汉儒重塑“作者”的具体论述,可参李春青《中国古代“作者”观的生成演变及其文化意味》[J],《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8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