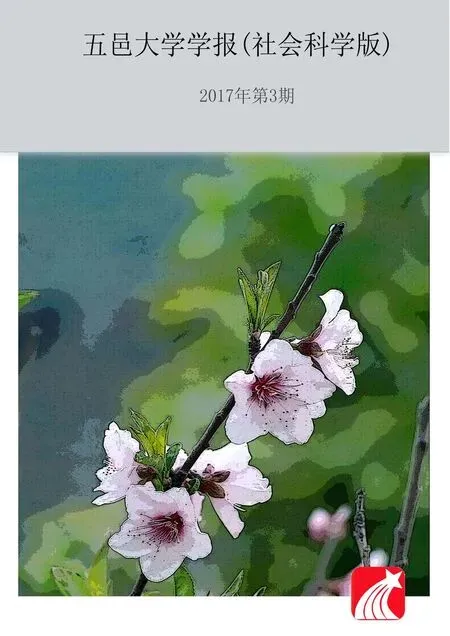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口音、口音歧视及影响
2017-09-08冯舒欣
冯舒欣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口音、口音歧视及影响
冯舒欣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口音歧视的本质只是一种人为的阶层化概念,却演变成了英语学习者真实的学习障碍。探讨口音的本质、了解口音歧视的负面影响,对减少广大英语学习者的学习障碍以及公平看待英语语言相关从业人员至关重要。
口音歧视;英语口音;社会阶层;学习障碍
196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窈窕淑女》里面,男主角语言学家Henry Higgins给卖花女Eliza Doolittle进行了一系列的发音训练,最终让女主角成功地消除底层英语口音,说出了贵族口音英语。社交网络上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在下议院舌战反对党科尔宾的“美妙英式英语”在新浪微博大受追捧。英式发音或美式发音无疑是大众心里最“标准”的口音,无论是主流社交网络、新闻媒体、教学材料和语言机构,都无时无刻地把这么一个概念植入英语学习者的脑袋里:要学就学英式或美式英语,而说“不标准”的英语,是要贻笑大方的。久而久之,英语口音是否“标准”已经成为了一个判断人英语水平高低乃至职业技能与受教育程度高低的标准了。更危险的是,这样的口音歧视,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一群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进程:他们母语中的、自小熟习的口腔肌肉发音习惯让他们的英语夹杂着轻微或浓厚的“非标准”口音,以至于他们在若干次被纠正、被嘲笑、被无视后,选择不再开口说英语。口音(accent)到底是什么?它存在标准吗?笔者拟在Lippi-Green对英语口音的探讨的基础上,结合Coulmas对说话者如何做出选择的研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英语口音歧视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用图表显示口音歧视对英语学习者的负面作用。
一、研究背景
(一)国内外口音歧视研究现状
语言学家Lippi-Green在其著作EnglishWithAnAccent中对英语口音标准化和英语语言标准化提出质疑,通过剖析美国国内教育机构的英语标准化、教师队伍口音标准化,以及社会主流媒体、就业市场对英语口音的标签化,指出主流社会和教育机构对标准化口音这种谬误观念(myth)的种种推广和强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深入探讨了诸多社会现象中折射出的口音歧视,以及这种歧视所带来的不公。她的研究中还提到,在美国大学里面,对说外国口音英语的老师的抵触是相当公开的。Rubin针对62个美国大学本科在读学生的研究表明,教师“非标准”的英语口音(而非教学水平)会导致学生不良的学习体验[1]。Lippi-Green解读Rubin的研究,认为导致学生不良学习体验的并不是教师的“非标准口音”本身,而是教师的口音并不符合学生们对“教师应该说的口音(perceived accent)”的期待。[2]78-99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从侧面印证了大众对口音的歧视是一种对口音所属的社会阶层和种族身份的综合歧视。然而,即使社会语言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了用口音来区分人并不公平,但他们的声音只是止于象牙塔内。
国内对英语口音歧视的相关研究已经展开,但与如何淬炼出“纯正”英语口音的研究相比较,关注度还太低。一线英语教师更是缺乏对口音歧视的正确认识,导致相关研究成果无法对实际英语教学产生作用。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英语口音歧视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段永州提出了许多学生过度关注自己的英语口音是否像美国人,而忽视了语言表达的内容,更别说关注其他的英语使用能力了。[3]李耕砚的研究中也提到,国外教师认为中国学生只关注模仿口音而忽视了语言内容,认为自己的口音“不标准”并为此自卑,抵触带口音的英语。[4]刘东彪和刘怡针对英语教师做的调查结果,更是反映出许多一线英语教师都对口音歧视毫无知觉,认为美式英式英语才是标准英语口音,而对汉语式英语口音持消极态度。[5]
(二)国内英语教学材料、商业化语言教学机构与娱乐化社交平台对口音歧视的强化
三人成虎,如果认同“英美口音才是标准音”的只有一小撮人,那么口音歧视的影响不会那么深远而广泛。事实是,英语学习者日常所身处或接触的英语教学材料、语言学习机构和娱乐社交平台都在告诉他们同一个事情:你的口音是否“英美”(标准),非常重要。即使在非英语母语的中国,同样的谬误也在轮番上演,演变成英语学习者的学习障碍。
英语教学材料是大部分英语学习者进行学习时最初接触的材料,而这些教学材料里面,不乏对“英美音即标准音”的暗示。中国最大的免费英语学习资源网站之一——沪江英语网,在其口语发音首页的6个课程推送中,有3个英式发音课程与一个美音课程。而另一个同类学习网站——普特英语听力网上,英语演讲音频首页的35个推送里面,只有4个是非英美籍演讲者的演讲;而另外的31个英美演讲中,更是有若干个被冠以“纯正皇室腔”等字眼作为标题。刘莹对网络语料库的研究里就提出过,我国的语言教材并没有提供语音辩题的训练,导致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标准移植以“标准”英美发音为主,让学习者对“非标准发音”较抵触,对自己的语音状况也自信心不高。[6]
商业化语言教学机构传播“英音美音=标准发音”的手段更直接,因为这是商业噱头,可以兑换成实际经济收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外教参与教学工作的语言教育机构就一直以向老外学英语为主打广告,并在宣传画和宣传视频中反复出现高加索人的面孔。这在无形中用“标准种族身份”加持了“标准口音”,加强了这样的心理暗示:只有(白皮肤)的外国人讲的才是“纯正”的英语。
社交平台对于这个观念的传播则稍显娱乐化。人称“东北英语哥”的张旭,在2012年于视频网站上传了一个自己录制的视频《模仿10种方言的Chinglish》,在优酷网上的播放次数逾90万,一夜成名。视频中,张旭把中国从东北到台湾等10个省份地区的“口音”(accented)英语绘声绘色地演示了一遍。随后张旭又陆续发布了《伦敦奥运会各国总结》和《五国妈妈经典语录》等,也是以模仿各国口音为噱头,皆受到网民追捧。而在2015年,综艺节目《世界青年说》8月6日这一期,在搜狐视频网上点击量达到127万次,当中也出现了各国口音英语的展示,而主要噱头是日本口音与泰国口音“让人捧腹的英语对话”。而在优酷网、土豆网以及其他视频网站上搜索“英语口音”,按播放次数从高到低排序,就会发现出现在高排位的无一例外都是模仿各种非英美口音的视频。这些只是社交媒体上主要受众对英语口音看法的一个缩影:人们普遍认为非英美的英语口音是带有娱乐性的、好笑的。
二、口音是什么?
在社会语言学中,口音(accent)被归类为语言变异(language variation)的一种。语言变异是说话者的语言在发音、语法、词汇使用等方面的形式变化,通常分为地区变异、社会变异和功能变异三种。[7]206-218口音主要指说话者在说话时的发音习惯,是语言变异的其中一种。口音又分为第一语言口音和第二语言口音:第一语言口音(L1 accent)通常是以地理来划分的,但也有按照人们投射于某群体的社会特征来划分,形成了诸如美国本土口音、黑人口音,或者各种按性别、种族、收入水平和地区划分的口音。第二语言口音(L2 accent)则是一个非母语的说话者在母语语音体系中的发音习惯影响到了他学新语言时候的发音,继而产生的口音。他越能革除这种口音,他学这门语言就越算“成功”。[2]44-54本文中说的英语口音,正是非英语母语的学习者在讲英语时由于母语的发音习惯而产生的口音。非英语母语的人说英语的时候可以模仿“本地口音(native accent)”,甚至高度模仿以至于别人都以为他是英语母语者,即使他没办法换一种非常“本地(native)”的发音系统(即口音),他的英语使用能力仍是不容置疑的。[2]44-54
然而,Norton的研究表明,把个人英语水平甚至个人教育程度、专业能力与英语口音挂钩、认为口音“不标准”即个人能力低下的案例,不在少数。[8]人们总会尝试从说话者的话语中寻找他身份信息的蛛丝马迹。除了用词和语法外,口音也是一种非常直观的信息标志,即使说话者不自我介绍,人们也能从他的口音中猜测到他大概来自何方。当然,口音透露的远不止地理信息,它还能体现出说话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从20世纪初开始,人们就开始对口音有超出语言本身的理解:他们认为一个说着英国地方口音的人不会是上流社会的人,因为上流社会的人接受的是上流社会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之下,他们只说“受接纳”的英语(Received English)。[7]139-150
三、口音歧视的本质是什么?
纵使现今的英语教学中、娱乐平台上以及就业市场里都认同非英美口音不如英美口音纯正、优越,事实依然不容否定:广受吹捧的“英美口音”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充满谬误的。段永州回顾了美国由于各地区的移民来源不一样而有三个方言区的区分:接近英式发音的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接近苏格兰、爱尔兰发音和被苏格兰发音影响的中部地区和欧洲、非洲移民聚居的南部地区。而在地理划分之外,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等等因素,都会造成口音的差异。正如工人阶层和中产的口音、黑人和白人的口音,都是有区别的,于是美国的口音并不能用单一的“美式口音”来归纳。[3]然而,把“英美口音”作为标准口音,并把非英美口音与之对立,标签为“非标准口音”,并认为说“非标准口音”英语的人英语水平更低、综合竞争力更弱——这种公然的口音歧视,却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着。
发音并不天然具有权威,只有社会评价才能让发音代表权威或招致厌恶。[9]口音歧视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阶层的投射:你说什么样的英语,你就是什么层次的人。听者对说话者按照“口音标准”和“口音不标准”进行了区分,并把自己对两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猜测投射到说话者身上,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优越。这种投射包含了听者眼中的、说这种口音的人群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的高低、掌握社会资本的多少等。比如,曾大举扩张殖民地、构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其国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长期高于被殖民的印度,于是英国口音英语被认为比印度口音英语更“悦耳”。同样,被侵略过、奴役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获得的社会发展机会低于高加索人的亚洲人和黑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低于白人,于是他们的口音就不如白人口音“悦耳”(明明中国口音和法国口音都是“非本地”口音)。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从事可替代性强的工作的人与技术密集型工作的人、工薪阶层与中产阶级,三组对比中都是前者地位低——于是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技术密集型工作的白人的口音才是最悦耳的口音。
虽然哪个群体说的是哪种口音的英语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并不是现实的完全反映,但歧视就是基于刻板印象而存在的。口音歧视之下的社会阶层区分,在人的交际中不断被重复、被强化:你虽然是中产阶级但你说的是中国口音的英语,于是你“暴露”了你的“出身”;你虽然是黑人但是你说的是伦敦口音的英语,于是你“明显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说到底,对“英美口音”的认同,不过是对发达国家、“优秀种族”、高教育程度、高工资、多资产等标签的认同;而对“大碴子味儿”口音的歧视,不过是对落后地区、“低等种族”、低教育程度、底薪、少资产等标签的歧视。无论是认同和歧视,与口音、语言、语言能力本身关系不大。有时候口音歧视会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总体趋势是不变的:向更高的社会阶层顶礼膜拜,对更低的社会阶层嗤之以鼻。
四、英语口音歧视对英语学习者的影响
Lippi-Green对美国本土标准美式英语(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SAE)的研究中探讨了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对说非标准英语的师生的影响[2]78-99。教师在SAE的语言意识形态下认为SAE才是受欢迎的、符合礼节的、体面并广泛使用的语言,而其他的语言都是狭隘、不体面的语言。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学生认为非SAE英语是耻辱的(stigmatized)。在英语口音有标准、“标准”口音即英美口音的意识形态之下,非“标准”口音无疑也是“耻辱”的。这种意识形态对学习者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有的学习者期待教师说“标准口音”的英语,而当这种期待不被满足的时候,就产生抵触情绪,有负面的学习体验,这在Lippi-Green[5]55-65和Norton[10]的研究中可见一斑;有的学习者因为说的是“耻辱”口音的英语,受到了不友善的对待,为了不再让别人对自己的能力做出与口音捆绑的、不公正的评价,从此陷入沉默[8];有的学习者因为能说出“标准口音”的英语而受到肯定,于是止步于模仿“地道口音”而不再关注语言内容,也不再提高其他英语能力[3-4]。
中国口音英语本无问题,然而这样的英语口音在中国就业市场、媒体平台和教学场所都是饱受歧视的。身为曾是英语学习者、现是一线英语教师的笔者,在20年的英语学习、实习和工作中,饱历英语口音歧视的发生与影响,也从歧视的施加者转变成歧视的承受者。在此,笔者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案例与一线英语教学经验,把口音歧视对国内英语学习者的影响用简单图表展示出来(如图1所示),以说明这种谬误观念如何不知不觉中成为英语学习者的学习障碍。

图1 口音歧视对英语学习者的影响路径图
图1展示了说“标准”口音英语和“不标准”口音英语的学习者在口音歧视之下的四种受影响路径:
一是当学习者在课堂说出教师所期待的“标准”口音时,会受到教师的肯定和朋辈的赞许。学生会因为被肯定和赞许而获得学习自信,激发对英语的学习热情,从而促进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又能帮助他说出“更标准”的口音,让他的英语学习进入良性循环。
二是当口音“标准”的学习者在课堂说出教师所期待的“标准”口音,并受到教师的肯定和朋辈的赞许后,学生获得口语表达的自信,并强化了说“标准”口音等于英语水平高”的想法,把重心放到模仿“标准”口音上面,忽视了语言的内容和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使英语学习进入止步状态。
三是当口音“不标准”的学生在课堂说出老师认为“不标准”口音的英语,不时被教师纠正、被朋辈嘲笑,失去口语自信,因而对英语口语任务甚至英语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导致英语综合能力不再提高。
四是当口音“不标准”的学生被教师纠正和被朋辈嘲笑后,失去口语自信,并想停止别人基于口音的、对自己能力和社会价值的不公评价,于是而彻底陷入沉默,不再参与英语口语任务,英语综合能力止步于此。
图1反映出口音歧视这种虚妄的概念是怎样给英语学习者带来切实影响的:无论学习者本身是否被判定为“口音标准”,这种名为语言标准、实为社会阶层投射的歧视都可能成为他们提高英语综合水平提高的障碍。
四、结 语
并不是非要把英语口语中的“非标准”口音革除,才算说得一口好英语。前人和笔者的探究都表明,英语口音歧视这种谬误的概念正在确实地给一线英语教学活动带来负面影响。怎样才能消除口音歧视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呢?Coulmas在其著作Sociolinguistics:thestudyofspeakers’choices中总结了前人的观点,给出一点启示:有人用的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Henry Higgins的方法,把“低级”的口音革除,加倍努力模仿标准口音,才能消除“低级口音”对人的影响——当然,这种方式在Lippi-Green看来是艰难而非必要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则是,改变人们对口音和说话方式的想法,解除口音与社会阶层的绑定。如果学生和教师能认清口音歧视的本质,师生就都可以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多元的口音,从而提高自信,进入良性的教学互动。
[1] RUBIN J. The special relation of Guarani and Spanish in Paraguay[M]// WOLFSON N,MANES J.Language of Inequality. 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85:111-120.
[2] LIPPI-GREEN R. English with an accent:Language, ideology,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3] 段永州. 大学生过度关注口音对英语学习的影响[J]. 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181-182.
[4] 李耕砚.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音对《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的启示[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04):329-330.
[5] 刘东彪,刘怡. 大学英语教师对待不同英语口音的观点研究[J]. 前沿,2012(04):180-181.
[6] 刘莹. 网络英语口音语料库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2007(01):41-45.
[7] HOLMES J.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 3rd ed.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8] NORTON B.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Gender, 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Change[J]. Tesol Quarterly, 2000,35(3):504-505.
[9] 吴海彬. 批评视野中语言的社会意义——以英语方言和口音为例[J].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3(02):82-85.
[10] NORTON B,KRAMSCH C J.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 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J]. Mcgill Journal of Education,2014,49(1):255.
[责任编辑 文 俊]
2017-02-24 基金项目:本文为五邑大学2016年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基于能力提升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批准号:JX2016008)的部分成果。
冯舒欣(1989—),女,广东恩平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教育学(英语作为外语/第二语言教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
H0
A
1009-1513(2017)03-00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