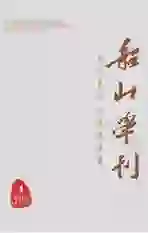曾国藩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儒耶对话
2017-08-10张乐
张乐
摘 要:曾国藩家族成员作为曾子后裔,一直以捍卫儒学为己任。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基督教却逐渐嵌入以儒学为治家之本的曾国藩家族。辛亥革命之后,曾国藩家族出现了第一批“叛教者”,他们背离儒教,纷纷受洗入教。他们利用自身扎实的儒学背景,使得曾國藩家族内部出现儒耶合流与互补的现象。此举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性尝试。
关键词:曾国藩家族;基督教;儒耶对话
以孔门弟子自居的曾国藩家族,为秉持儒家学说、塑造清廉家风,曾立下祖训:“不信僧道,也不许唱戏饮酒,赌钱打牌。”①曾国藩也曾以“八字三不信”教育子弟:“八者曰:早、考、扫、宝、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②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曾国藩家族中出现了一股背儒入耶的风潮,不少成员纷纷受洗入教,由孔门弟子转身成为耶教门徒。因此,曾国藩家族成员与基督教接触甚至受洗入教一事,堪称是近代中国儒耶对话的经典案例。
一、曾国藩、曾纪泽父子的基督观
中年以前的曾国藩志在修习义理之学,并不热衷于洋务,遑论当时被视为“洋教”的基督教。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粤匪窃外夷之续,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③因此,曾国藩甚至告诫曾国荃等人:“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④
当然,《讨粤匪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曾国藩有意歪曲基督教的产物,其意在争取当时的士绅以对抗太平天国运动。因此,1862年,曾国藩去函王家璧时特意检讨其在《讨粤匪檄》中文过饰非的问题,并进一步批评反教者借助《讨粤匪檄》制造教案:“昔年所作之檄文,偶及粤匪之教,天父天兄,昆父祖母,大紊伦纪,文字粗浅,不足称述。近乃有好事者,为檄痛诋天主教,词旨鄙秽,展转传播,颇滋事端。璧意我苟求胜于彼,不必锱铢较量,尤不在语言文字——今审时量力,茫无足恃,一时快意,不过扬汤止沸,将来招侮,仍不免掩耳盗铃。”⑤
随着曾国藩对基督教认识的不断加深,其逐渐分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甚至对于世界大势(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源流与现状)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仍未曾丝毫改变其作为孔门弟子的立场。1867年,曾国藩写道:“查天主教之始专以财利餂人,近日外国教士贫穷者多,彼之利有所不给,则其说亦将不信。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而佛教渐行。然佛教兴于印度,今日之印度,则所从回教,而反疏佛教。天主教兴于泰西,今日之泰西,则另立耶稣教,而又攻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有周孔之道,万古不磨。”⑥同时,曾国藩建议朝廷改革,使“修政齐俗,礼教昌明”。如此,纵令传教士如何开拓传教,终难有信奉者。不过,紫山川崎三郎却据此认为曾国藩对于来华传教士“持不偏不倚的见解”,持论最为平正⑦。
晚年曾国藩承认天主教的教义在于劝人为善,并在奏折中特意指出:“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⑧因此,此时的曾国藩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已经日益客观化,也是一种典型的“去妖魔化”的渐进式过程,而远非《讨粤匪檄》中所折射出的儒、耶冲突。纵然如此,曾国藩的认识水平也仅停留在反对传教士庇护教民,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行径,并未关注基督教教义及其精神内核。当然,其作为孔门弟子的身份认同也始终未曾改变。因此,在华洋杂处的中西对视之下,曾国藩既维护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既保守旧物又冲撞了旧物⑨。
与乃父不同,曾纪泽年轻之时,即已醉心西学,并在守制期间依靠英文词典和《耶稣书》等自学英语⑩。出使期间的曾纪泽,则多次参观教堂、教会学校和教徒的婚礼。在他看来,教堂在西方所承担的角色类似于中国的宗庙,“自天子至于庶人,典礼仪文皆举行于教堂。升冕之典,盖合教庙为一礼也”B11。他在参加法兰亭(法国人,信仰天主教)婚礼之后,在日记中指出:“教师祈祷,手舞足蹈,秉铎挥塵,默诵经咒,间以乐歌,与中华僧道大致相同。或言天主教缘饰佛教,殆有据也。”B12曾纪泽认为基督教与东方佛道相似,并承续佛道思想与仪式,老子西出流沙之后上古三代的思想西传之说亦不无道理。为了比对中西文化,曾纪泽还特意“将二十八星宿、生肖禽兽写记一图,以证西洋礼拜七日分配日月五星之恰相符合也”B13。曾纪泽也曾阅读传教士所赠之基督教经典,如他就曾详细翻阅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所赠送的《福音书图说》一书B14。同时,曾纪泽对于民教冲突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各省难办之案,常因民教不和,若能撤去邀誉于绅民,阳遵条约,暗拒教士之成见,专论其事之有理无理,不问其人之是教非教,则棘手之事,亦当减少。”B15
此外,曾纪泽也与李佳白(Gilbert Reid)、德贞(John Dudgeon)、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等传教士过从甚密。曾纪泽将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德贞并称为“四君子”B16。虽然曾纪泽频频与传教士交往,亦曾阅读基督教义书籍,但其并不认同基督教,甚至认为《旧约》“可笑之至”B17。但是,他在论及基督教时却又指出:“教者,所以束缚凡民,使不为恶。贤智拔萃者创其说,而邦国之君师,因之义劝惩百姓。举天下为天堂、地狱之说者,立旨虽异而本源实同。上智不为教所缚,然亦不肯昌言攻之,以其有益于政治,可以补赏罚之不足也。”B18
总体而言,曾纪泽主要将传教士视为学习西方器物与制度的一种媒介,希求从传教士那里获得处理洋务和总理各国事务的技巧,因而与当时在京城的诸多颇有才华的传教士密切交往。但是,他与父亲曾国藩并无二致,也没有对基督教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其认知水平也停留在表面而未曾深入肌理。
二、辛亥前后曾氏族人的受洗入教风潮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社会纷繁复杂、人心陷溺,曾氏后裔或去职还乡、决意仕途,转而研究基督教义;或在教会学校求学,深受基督教氛围的熏陶;或与传教士和基督徒相交,得以窥见圣经奥义。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也使得社会风气大变,儒家士绅及其子嗣入教阻力大减。因此,高伯雨曾言:“在前清,入教还有些体制上的不便,到了民国,没有拘束,号称典型的名门宦裔,也就首先信起教来了。”B19于是曾国藩家族内部出现了一股受洗入教的风潮,不少成员弃儒从耶,实现由孔门弟子向耶稣门徒的转变。
曾国藩家族最早受洗入教的基督徒是曾宝荪。曾宝荪(1893—1978)字平芳,号浩如,曾国藩长曾孙女,曾纪鸿孙女,曾广钧之女。早年求学于教会学校,虽佩服基督徒办事的精神,却认为他们的传教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有较大出入,所以尚无法接受基督教B20。但她认为《圣经》的人伦哲学远不及儒教的详细,虚玄理想又远不及佛教的奥妙,至于文字的美则更在二者之下,外加又认为多数基督徒都是不爱国的,所以她根本看不上基督教。大体而言,曾宝荪对于基督教由完全无知、排斥的态度转变成信服、最终受洗入教的思想变化的轨迹,反映出了晚清民初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过渡型现代女性对于基督教认知的现代转型。曾宝荪深深佩服耶稣的人格,并认为耶稣的社会观念、博爱精神等都在儒教精神之上。耶稣伟大的人格使得曾宝荪想到了人类伟大的可能性。此时的曾宝荪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上帝的灵性,而心中高尚、诚实而又博爱的我,便是上帝的返照B21。在1911年圣诞节前夕,曾宝荪在杭州圣公会正式受洗,是曾国藩家族的第一位基督徒成员。但是,曾宝荪受洗入教时所受阻力甚大,她曾感慨:“在这样的家庭里,旧礼教之深,旧风俗之重要,要一个女子来摆脱,是很不容易的。”B22
紧随其后的则是曾广钟。曾广钟是曾国藩家族成员接触基督教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向曾纪芬等人宣讲基督教教理,还力促曾宝荪等人离湘赴沪、杭等地教会女校求学,进而受洗入教。曾广钟(1875—1924)字君融,号季融,曾纪鸿之子。甲午战争时期,他曾率忠、恕两营出關援助朝鲜,以候补道员的身份分发浙江杭州任职,于辛亥年归田。曾广钟曾用五言韵语将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的要义编撰成《圣经提要偈子》B23。事实上,曾广钟最初接触基督教却十分偶然。任职杭州期间,曾广钟的子女在教会学校求学并常携带《圣经》回家,他翻阅之后,甚觉有理,不到半年便决志信主B24。1912年元宵节(1912年3月3日),曾广钟与妻子同时受洗礼于长安里之小教堂B25。
再次则为聂其焜夫妇及其子女。聂其焜(1888—1980)字潞生,聂缉椝之子,曾任恒丰纱厂董事长、总经理,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主席等职。义和团运动期间,聂其焜基于仇教的心理,认为基督教是中国之祸阶,并以孔孟学说驳斥《圣经》B26。1905年,聂其焜返回长沙,经由李提摩太之介绍,认识雅礼会胡美夫妇。此外,伦敦会孙荣理夫人也曾任聂其焜英文教员,但不取束脩,基督徒的这种为人服务的精神让聂其焜甚为感动。聂其焜还在孙荣理家中认识了循道会任修本牧师。武昌起义之后不久,聂其焜与颜福庆组织红十字会分会,并率领颜祥生、李清茂等数十人前往作战区域拯救伤员,可是无端被捕,且生命堪忧。聂其焜向上帝祷告并最终获救,自此之后,他通道之心日渐笃深B27。自武昌返回长沙的聂其焜,因弟弟聂其贤患肠热症而逝,悲痛无已,感叹人生如朝露之淹没。聂其贤丧事结束以后,聂其焜请任修本牧师至其家讲解圣经。任修本牧师“学贯中西,讲解明显,于是圣道奥义乃能略窥一二,愈研求愈生兴趣,始知耶稣基督为何如人,崇拜信仰,至于极端”B28。1913年12月25日,聂其焜在长沙西长街循道会受洗入教。在聂其焜的影响下,1914年4月,其妻黄蕴仁率领五个子女(聂光地、聂光堉、聂光增、聂光琛、聂光坡)也领洗于循道会。
曾国藩家族辈分最高者的基督徒当属曾纪芬,她幼年深受儒教教育,60岁之后笃信基督教B29。其接触基督教,主要是受曾广钟、聂云台的影响。曾广钟多次自杭州到上海聂家宣传基督教义,所以曾纪芬晚年回忆道:“渠常来为余说基督教真理,余深为开悟,遂有服膺之志。”B30因此,曾纪芬受洗之前,“读经尤为恳挚,规定日课无有间断,卒能豁悟真道”B31。1915年2月14日,曾纪芬与聂云台、萧敏春同时受洗。当日他们三人来到昆山路监理会礼拜堂,杂坐群众之间,直至牧师讲经结束,乃至台前接受洗礼。施洗牧师是袁恕庵,整个受洗仪式相当简单。正是基于他们的特殊身份,玛丽·盖姆威尔(Mary N. Gamewel)认为他们的洗礼:“关系中华教会,实非浅鲜。吾人可目之为特殊之礼拜日。”B32甚至记者也感慨:“从此教会多一柱石,天国得一栋梁,不禁为吾道庆得人也。”B33
聂云台(1880—1953)名其杰,为聂缉椝第三子。1919年筹建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聂曾前后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等职。1915年受洗入教,1924年改宗佛教。聂云台之妻萧敏春(1881—1917)字新云,江西泰和县人。祖萧芸浦、父萧惠农皆为孝廉。萧家以盐业起家,席丰履厚。18岁之时,萧敏春嫁给聂云台。在聂家,萧敏春“习礼通经,兼长簿记,治家相夫,雍雍如也。且天性敦厚,事亲尽孝,训子有方”B34。1914年12月,格蕾丝在其信件之中指出萧敏春参加了由雅各小姐在家教授的圣经班一事B35。萧敏春“平日天君素然,无所愧怍,通道纯笃”,临终之时对聂云台言道:“能输财济无告者,庶不负上帝好生之德。妾所有珍饰,当尽变作慈善事业。妾常念夫子多病,请祷祈祝,愿以身代。今日不起,固胥愿也。”甚至说:“吾心甚安,请牧师至祈祷。”1917年4月7日离世,享年37岁。
以福音在家族内部的传布路径而论,首先,得益于曾广钟多次向曾纪芬、聂云台、曾约农、曾宝菡、曾宝荷等人传布福音、宣讲基督教教理。其次,曾宝荪、曾约农等人创办之长沙艺芳女校,作为一所基督教学校,对于家族的女性基督徒成员影响甚大。最后,聂云台、聂潞生等人的受洗入教也与传教士对他们的影响密切相关。以入教缘由而论,主要是个人的际遇(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对基督教救国论的认同。以受洗时间而论,多集中于1911—1915年,且视基督教为救国救人的一种手段。其次,以入教时的年龄而论,当属曾纪芬最大,入教时已年届60岁,最小者聂光坡不过6个月大。以性别而论,在曾国藩家族基督徒成员中,男女人数大抵相等。以所属差会而论,曾宝荪属圣公会,曾纪芬、聂云台、萧敏春属监理会,聂潞生、黄蕴仁及其五个子女则属于循道会,曾昭义属路德会,不少基督徒成员甚至自创教会,以寻求中国基督教的自立。以受洗入教的方式而论,除曾宝荪等几人之外,多数基督徒(儿童或女性)都是在男性基督徒(父亲或丈夫)的主导之下一同受洗,而这也是近代中国基督徒家族式受洗的通例。以人员分布而论,除曾宝苏是曾纪泽后裔,曾昭义是曾纪官(曾国荃子)之后,悉数为曾纪鸿、曾纪芬两人后裔,主要缘由在于这两脉人丁兴旺、子嗣繁多。
三、曾国藩家族基督徒的儒、耶合流观
曾国藩、曾国荃,乃至曾纪泽等曾国藩家族的早期成员,尽管已经开始接触西教,甚至与传教士交往频繁,但他们对于儒教士绅的身份认同从未发生过动摇,始终站在基督教的对立面,并视基督教为儒教的一大劲敌。虽然作为曾国藩长孙,且为翰林,曾广钧依然阅读中国传统基督宗教典籍,兼习《圣经》。故而,其所作之诗文展现了其诗文才情与西教知识的有效融合,象征着曾国藩家族儒、耶合流的萌芽。虽然曾广钧在1880年代即已开始尝试将《圣经》故事入典,但真正意义上开始儒、耶合流的是民初纷纷受洗入教的这批基督徒成员。
曾广钧(1866-1929),曾国藩长孙,字重伯,光绪己丑科进士,诗文俱佳,善用典故。他对于基督教涉猎颇深,并认为基督教“以因信得义为教纲,亦似有其妙用与优点”B36。曾广钧引《圣经》经文作典入诗,不仅丰富了典故的出处与源流,更是对中西文化融汇的一种有效尝试。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谈及曾广钧时,也认为他“生有异禀,博览群书,于世界各宗教学派莫不精研贯彻,故有时托之吟咏,微言妙谛,迥人出表”B37。关于曾广钧善用西教典故一事,吴宓更是直接地指出:“环天室诗学六朝及晚唐,以典丽华赡、温柔旖旎胜。用典甚丰,典多出魏晋书南北史,或出耶教《圣经》。”B38
曾广钧曾作《奥斯马家国和吉长公主来沪游历二首》诗歌内容如下:“是法无深浅,窥原见性真。长年礼神女,今日谒天人。自领玄言妙,方知蓝石身。海州潮退早,七鸽证前因。”“飞鸟巢何处,群羊念已差。玉颜终土壤,宝血染尘沙。休毁葡萄树,长吟百合花。定随书拉女,歌舞上天家。”B39曾广钧在序言中坦言,诗文所用之典故,稍显偏僻,且多出自景教经典。在曾氏后裔受洗入教之前,曾广钧就已经开始大量涉猎基督教,并将圣经故事化作典故引入诗歌,象征着曾国藩家族儒、耶合流的萌芽。但真正意义上开始儒、耶合流的是民初纷纷受洗入教的这批基督徒成员。
作为基督徒的曾纪芬不仅没有背弃儒家思想,她曾经辩解道:“先大人曾文正公为有清大儒,先夫子聂仲芳中丞亦服习儒书,道义自守之士。余涵濡听受吾国古先圣哲教义者数十年,信佩至深。今之投身耶稣,非见异思迁。惟理求真实,庶几朝闻夕死之义,与先大人先夫子之所学,固不相背也。”曾纪芬还曾对儒、释、耶三教进行比较,认为耶稣言爱与孔子言仁、佛家言慈悲,本为同物。不过,耶稣阐发天人相与之宗旨,尤其让人感到亲切,而且范围广大(无国别种族),功夫简单(不识字之人只要信主便可立刻得救),不尚空言只求实际(以舍己救人为范),因此,此法足够救儒家矫伪与佛家空虚的弊端B40。由此可见,曾纪芬是一位混合型的基督徒。
曾广钟的基督信仰背后也夹杂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他认为:“永生之说,非佛教之觉性,非道家之丹诀,即儒家之三不朽。夫人之立德立功立言,有光于社会,有光于国家,有光于世界者,是之谓永生。”甚至进一步主张:“铸儒、耶于一炉,以开辟我国民之知识,以鼓舞我国民之精神,以增进我国民之幸福。”B41此外,曾广钟也懂得如何使用中国话语为基督教辩护。有人认为“景教乃墨子教之化身,亦谓耶稣无父”。曾广钟反驳道:“我读《圣经》十诫,言虔诚上帝后,即首先注重于孝事双亲。观耶稣钉十字架时,谆谆以吾母即如母之词,嘱托其母于所爱之门徒约翰。孝养之思,临难无间。诵《约翰福音》至此,未有不为之潸然涕下者也。”曾氏还认为耶稣的兼爱宗旨与墨子爱无差等之说也有区别。即令是兼爱之间,亦有主客之别:“兼者专之对也,专为主位,兼为客位。如讌饮然,同是筵席,同是酒菜,同是杯箸,同是朵頤。而主位自主,必须照拂夫客;客位自客,不能攘夺夫主也……爱有主位,而兼为客位。天经地义,颠扑不破。耶稣其至矣。”B42
与表叔聂云台明显不同,曾宝荪一生持守自身的基督信仰。不过,她一生也在试图使中、西(儒、耶)两种文化相调和,并认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相接触,可比两条河流相汇合。当其汇合之际,当然有波涛奔湍,互相冲突的情形。然而毕竟合而为一,产出一个更新的文化。两边所含的杂质和糟粕,因这种奔腾冲突而淘汰了。这不是文化的损失,乃正是文化的淘冶。B43因此,曾宝荪特别强调中西文化之间交流,试图通过中国事例来印证基督教所揭示的道理。例如,她认为天人合一即为道。至于何为天人合一?她以尧、舜、文王、孔、孟等为例,指出他们的诗文、言行合乎天道,与天合德。然后又引用程明道之语:“尽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则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万物。其次则欲存心养性以事天。”此外,曾宝荪对于佛家学说也甚是了解,她就认为:“佛教唯识的说法更为博大精深,超过我国周秦汉宋诸哲之上,不独我们都是道的化身,而万有也都由一心所造。所以说万象唯心,万法唯识。天人合德尤其当然的了。”不过,她仍然认为:“耶稣的话,最为平易切实。”并引《圣经》之语:“你们因我讲给你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15∶2)约翰也说过:“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即是上帝。”(约1∶1)以证明基督教里面天人合一的意思。
曾宝荪还特意从中西文明与宗教比较的角度出发,阐述儒教、基督教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她指出:世界各国诸多宗教,除了基督教之外,“大都视女子为不洁不利,不能胜识之人。”凡在典礼与祭祀之时,女子都饱受歧视与摒弃。甚至在中国,还以“阴人鸡犬”并称。女子也自惭形秽,甘受压迫,与一般男子相比,其自信力和进取心有天壤之别。B441928年,曾宝荪撰文指出,孔子曾经只有两次提及女性,因此,她怀疑到,可能正是因为孔子几乎从来没有讲论过女子的地位问题,致使后世儒家学者在其传道授业的过程之中存在一种反女性的源流(anti-feminine strain),此种风气延续到宋朝时臻于鼎盛。至此,儒家学说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不仅毫无积极作用可言,还在诸多方面抑制了她们的发展。因此,她认为,中国形成贫困积弱局面的一大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忽视了中国女性。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是不受其女性的影响的。当我们的一半人口处于落后状况时,我们不可能造就一个富强的国家。
曾宝荪还认为中国形成贫困积弱局面的一大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忽视了中国女性。没有任何国家是不受其女性的影响的。当我们的一半人口处于落后状况时,我们不可能造就一个富强的国家。为此,曾宝荪指出,对于中国而言,仅有儒家学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儒家学说只能使一半人口受益。中国女性只能从基督的启示之中发掘自身完满的生命。基督乃女子所生,向女性显现他救主的身份,并在其复活之后向女性展现他荣耀的身体。在基督看来,男女之间本无差别,并将双方的性都置于同等的道德标准之上。基督赐予女性生命、灵魂和进入天堂的道路B45。此外,曾宝荪还曾撰文论述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对于中国女性和妇女解放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B46。因此,时人曾撰文批评道:“曾氏一族已入耶教,受洗礼。而宝荪女士留学英伦,得力于西学,其作事之成绩与毅力乃由于西洋德教之熏陶。譬犹栽花艺谷者,接慕借种乃见繁荣,未尽出于世泽。”B47
四、结语
以孔门弟子、曾子后裔自居的曾国藩家族,一直以捍卫儒学正道为己任,因而在太平运动时期,曾国藩撰发檄文号召儒学士绅卫道护教(儒教)。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基督教却逐渐嵌入以儒学为治家之本的曾国藩家族。曾国藩、曾纪泽、曾广钧三代人无不受其影响。民国初年,社会风气大变,曾国藩家族出现了第一批“叛教者”,即他们背离儒教,并纷纷受洗加入基督教,曾国藩家族最终实现了由独宗孔、孟的单一信仰型家族向儒、耶并峙的双重信仰型家族的转变。此种现象也暗示了曾国藩家族的“泛基督化”趋势。这批基督徒成员主要由两部分所组成,即以长沙为中心的曾氏直系后裔和以上海为中心的聂氏子嗣。他们利用自身扎实的儒学背景,践行儒、耶互补,并有部分成员将佛教信仰亦带入自己的生活之中,因而使得曾国藩家族内部出现儒、耶二教合流与互补的现象。此举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性尝试。
在中西文化对视的时代背景下,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的关系,恰好反应了传统儒家家族在西潮的冲击下,出现了由孔门弟子到耶稣门徒的跨时代转变,而此种转型也正是以曾国藩家族为代表的传统士绅家族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所做出的一种自我调适与文化抉择。因此,在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的近百年(1850—1940年)的关系中,所反映出的是基督教与儒教关系的百年旅程,即由儒耶冲突向儒耶对话的转变。
【 注 释 】
①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版,第8页。
②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③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詩文》(第1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0页。
④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37页。
⑤曾国藩:《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8页。
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第9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82页。
⑦紫山川崎三郎:《曾国藩传:日本人眼中的曾国藩》,王纪卿译,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6—137页。
⑧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94页。
⑨杨国强:《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第94页。
⑩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B11B12B13B14B17B18曾纪泽:《曾纪泽日记》,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248、898—899、1234、1295、1462、856页。
B15B16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95、158页。
B19高伯雨:《听雨楼随笔》(三),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B20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版,第32页。
B21Tseng Pao Swen, “My Religious Experience” ,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66, No.8 (Aug.1935), pp. 458—459.
B22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版,第13页。
B23《最近二年内教会出版之新书》,《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册),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版,第143页。
B24B28聂其焜:《余何以为基督徒(续)》,《上海青年》1916年第19卷第8期,第288、285页。
B25《曾广钟之证道谭》,《金陵神学志》1915年第2卷第2期,第2—3页。
B26B27聂其焜;《余何以为基督徒》,《上海青年》1916年第19卷第7期,第243、245—247页。
B29张心漪:《我的外婆——崇德老人聂曾纪芬》,《曾氏会讯》1985年第30期,第16页。
B30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第二部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9页。
B31《名人皈道》,《上海青年》1915年第18卷第4期,第146页。
B32Mary N. Gamewell:《聂云台夫人之殡仪》,凌华富译:《清心钟》第2卷第1期,第16页。
B33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2册),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版,第18页。
B34《聂萧夫人贤范》,《青年进步》1917年第5期,第6页。
B35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B36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83册),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343页。
B37平等阁主人编著:《平等阁诗话》,时报馆1908年版,第11页。
B38吴宓:《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2页。
B39曾广钧:《环天室诗集》,宣统元年刻本,卷三,第6页。
B40聂曾纪芬:《述余奉教之原由以劝同胞》,《上海青年》1917年第19卷第10期,第348—349页。
B41曾季融:《释耶稣上帝永生说》,《上海青年》1911年第14卷第9期,第193—194页。
B42曾季融:《兼爱说》,《上海青年》1911年第14卷第10期,第230页。
B43曾宝荪:《基督教与国性》,《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0年第6卷第3期,第8—9页。
B44曾葆荪:《女子问题》,《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专著(二)》,1925,第2—3页。
B45Tseng Pao Swen, “Christianity and Women as Seen at the Jerusalem Meet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59, No.7 (Jul.1928), p. 443.
B46Miss P. S. Tseng, “What Christianity Means to Chinese Women”,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June 1939, p. 83-86.
B47《环天诗人逝世》,《大公报》(天津)1929-12-30(13)。
(编校:龙 凯)